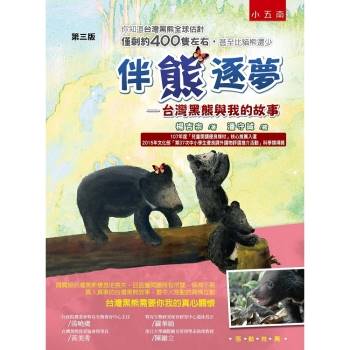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沙漏之家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沙漏之家 作者:楊瀅靜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11-03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77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308 |
中文書 |
$ 308 |
小說 |
$ 315 |
現代小說 |
$ 315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50 |
網路\原創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圖書名稱:沙漏之家
看盡人間光怪陸離的警員,何以對素未謀面的新鄰居產生性幻想?
父親過世後,成了一家之主的她,又要如何處理自己對繼母的慾望?
男子困在空無一人,猶如平行世界的捷運站,他該如何脫身?
由人工智慧掌控的保險業,將對人類家庭造成什麼影響?
在實境節目裡假扮情侶的二人,會有劇終的一天嗎?
十三則短篇小說,十三種關係的透視與重構,以不斷脫軌,失速歪斜的角度,闖動一幢幢貌似穩固的家。
在本書中,人與家庭都是用來探測新關係的,角色們對家的組建方式產生了不一致的想像,更有不少角色就是駭異想法的自身,它們的存在改變了現有家庭的僵固想像,也被讀者從無數希望粉末裡遽然凝視。作者回應著不停滾動的時代,指出其模樣與理解的路徑早已需要更新。更新,就是寫小說的人,面對龐然多語世界的一道必然姿態。
「詩集雖然是我的第一本書,但於我而言,以文類區分,小說的確走在詩之前,卻晚了許久許久才面世,如今即將變成我的第四本書。小說集結成冊很晚,私心盼望它能走得穩健,走得長遠。」──楊瀅靜
作者簡介
楊瀅靜
東華大學中文所博士,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宗教文學獎、林語堂文學獎、葉紅女性詩獎等,出版過詩集《對號入座》(2011)、《很愛但不能》(2017)、《擲地有傷》(2019)。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