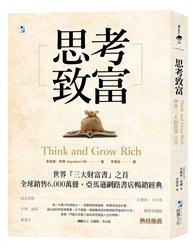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台灣小事的圖書 |
 |
台灣小事 作者:吳鈞堯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8-2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9 |
二手中文書 |
$ 284 |
中文書 |
$ 306 |
小說/文學 |
$ 317 |
現代散文 |
$ 324 |
現代散文 |
$ 324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324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60 |
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台灣小事
在吳鈞堯的散文軸線中,《一百擊》作為跌宕碰撞,其後則在敘事抒情與詼諧語境中,調冶他的散文風格,入圍台灣文學金典獎的《重慶潮汐》編織個人記憶,描繪書街的歷史風華。《台灣小事》顧名思義書寫台灣,從庶民觀點切入大街小巷,許多平凡題材如半票、大盤帽、郵政寶寶等,都如九彎十八拐,卻把彎路寫成國道,且俗雅兼治,趣味煥發,隨興遊走隱然以日常風景、家族顧看、藝文體會為核心,觀看、審思或神遊,都在生命伊始有了際遇,作者跟隨生命軌跡,小我與大我、私情與緬懷,說是激盪,不如說是以一條文字河握手。
作者簡介
吳鈞堯
出生金門,曾任《幼獅文藝》主編,獲九歌出版社「年度小說獎」、五四文藝獎章、中山大學傑出校友等。著作有《火殤世紀》獲文化部文學創作金鼎獎、《重慶潮汐》入圍台灣文學金典獎,以及《100擊》、《遺神》、《孿生》等。多次入選年度小說選、散文選、新詩選,二〇二一年秋出版第一本詩集《靜靜如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