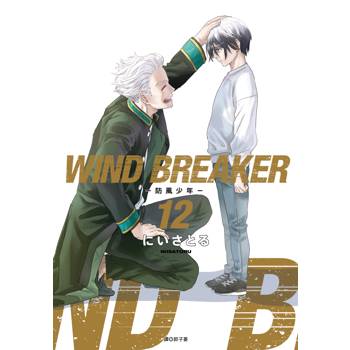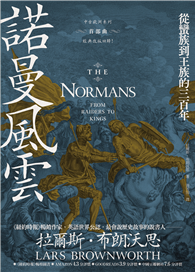雨中跳舞的斑馬
連綿的雨炸開小島,冷淡透明的水珠不斷墜地,落空輪迴輪迴落空。
「這雨,不停嗎?」我目光漲滿心碎。
「你得打破冬天的慣性思維。」躺在地上那隻灰濛濛的斑馬回答。
近一點,我們的距離再近一點,玻璃上雨珠靜靜趴著,傘花掠過斑馬,水滴形黑白相間的馬跳動,一隻,兩隻,許多隻。
「來吧,靠近我!」牠說。
「我可以更靠近冷冽絕望,與你共舞?」
脫掉冬的斗篷,踏水而去,黑白線上雨花四濺,現在,我也是一隻跳舞的斑馬。
沒有名字的鳥
失去的青春小鳥,他們多半有名字,只是,長久桎梏鳥籠內的聲音枯死,活生生的鳥囀飛走,他們從不肯為誰停留。
呼朋引伴的露台,有幾隻鳥兒的足跟輕巧跳躍,每個清晨我用各種水果發酵他們的歌聲,所有的鳥慕甜,櫻桃蜜汁閃動邪惡利誘,一有風吹草動以為是肅殺利器,一群翅膀倏忽躍進天空。
只有他一直在那兒,跟我一樣喜嚐微酸,奇異果、寶貝、小愛,默默,我賦予他很多名字,隔著一層玻璃,以相望時到位的眼神辨識,甚至能真實透視彼此孤零零的旅程,名字會是基本價值嗎?許久沒有人叫喚過我,這麼說來,從未發聲不太鳥我的鳥,我們本是被遺忘的沒有名字的孤鳥。
春天過後,那隻鳥沒有再來,我依舊在露台切放綠中有黃的奇異果片,任由芝麻斑點的小種子,裸露孤寂的寸土,我一直相信,我們不是永別,而是永在。
一個人
我往前跑,有個人緊追著我。我跑過明處跑過暗處跑過天涯跑過海角,他追過明處追過暗處追過天涯追過海角。於是,我一直跑一直跑,他一直追一直追。
你是誰?我停下腳步,望著他。
我是誰?他停下腳步,也望著我。
我只是一個人。坐在潮境,我看著洪水猛獸的生活不斷膨脹縮小縮小膨脹。
你不是一個人。轉過身,他孤獨、寂寞、茫然的背影竄出一張臉孔。
所幸啊,還有一點老派的堅持的愛,活著。說完,我從他的背脊走出來。
阿爾卑斯之眸
翻越愛與別離兩境,舌尖預測的流浪該有多長?聽說阿爾卑斯的欲望深邃而明藍。
張開眼睛,世界義無反顧壓縮於法式,俯視一塊經典音階,蓬鬆的白紗裙舞踏,軟綿雲朵唇齒間歌唱,淺淺一口無邊接疊,甚至不帶半點裝飾音意識流,傳唱七的幸運工序:泡芙酥皮摺疊七次→蛋奶凍煮制七分鐘→切成七公分方塊。
若被靜置被冷卻切割的廓形,愛情是有條不紊的Cream Cake,毫不醒目宣敘著忠貞,深夜詠嘆的Tiramisu一朵煙花情色的罌粟擦亮火花,風霜肆掠相異曲式的七年,滾開吧!膚淺男人。
阿爾卑斯群山顛倒冰湖眼睛裡,懸崖上千年古堡公主和王子抽離童話敘事出走,花式咖啡的味蕾分道揚鑣,一尾日光灼傷的鱒魚戳裂水底山盟,牠的眼眸因此鈷藍,湖岸,一個離人等一杯Espresso,焦苦深焙的靈魂。
迷霧
火迷路水迷路鑰匙迷路記憶迷路,鼻子迷路耳朵迷路眼睛迷路,味覺迷路嗅覺迷路,餘生的唇齒吐出狼煙,嘆息,盡是愁霧。
霧中,伸手不見五指。海馬迴角質全貌老化,不請自來亂石堵塞某些出口,現實翻滾超現實模糊地帶,細碎的耳語對迷境成癮,儘管騎著游霧的白駒,掀開空洞質地,穿越引喻失義的濕地。
呼叫Brain Fog,呼叫Brain Fog,敬請撤退。濃霧獨白:我在這裡,等妳。該死的病毒株,請勿重複申論,總有一個領地屬於私我的泊岸,等霧靄消散,世界栩栩復醒,非你所見混沌。
失去
今天失去了昨天,月光時日陽失去,秋天的樹梢失去葉子,坐在山那方的石頭失去滾動意念,小河喑啞失聲,背井的人失鄉,狂亂的風失章,上岸的魚失去水,沙漏失去沙,瘟疫的小鎮失語,他失去一隻貓,你失去黑髮,我在人間蒸發好多年失去自我。
我們或哀傷或沮喪或疼痛,順應自然法則減去,亦孤單亦緬懷亦安慰的高談與闊論,也許失去的,會以不同面貌重新來過。
沉默的小男孩低頭不停的畫,不久前他失去媽媽,畫冊裡因此更多母親。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雨中跳舞的斑馬的圖書 |
 |
雨中跳舞的斑馬 作者:簡玲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11-1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9 |
二手中文書 |
$ 255 |
中文書 |
$ 269 |
詩 |
$ 289 |
小說/文學 |
$ 299 |
現代詩 |
$ 306 |
華文現代詩 |
$ 306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40 |
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雨中跳舞的斑馬
《雨中跳舞的斑馬》分成六輯:
輯一「水與火」:以火和水為主題,流淌感性或哲理的生命思索。
輯二「對話」:以日常事物的微觀,折射心靈深處思辯。
輯三「一個人」:書寫現代新的人際關係和孤獨感。
輯四「他方」:遠方城鎮所鋪陳空間與時間的層次與想像。
輯五「疫疾時」:有關疫情、疾病和老年的書寫。
輯六「之間」:物與物、人與人,對比、依存、糾結與矛盾。
詩集以抒情的體裁敘事,內容自日常所見所聞或靈光乍現的一瞬,用極短文字貫穿,一百字到三百五十字間起伏的情節,或宏觀或微觀,或象徵或隱喻或借喻,有時現實與超現實交錯,在物象、意象與心象間虛虛實實實實虛虛盤桓,雖不若長詩龐大,乃用精巧簡約,伴隨詩意的節奏,切入生命幽微的角度,有時莞爾有時沉默,直驅心底,留有思索的餘地。
作者簡介:
簡玲
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
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葉紅女性詩獎、基隆海洋文學獎、台中文學獎、台灣詩學詩創作獎、台灣文學館好詩大家寫、文化部台灣詩人流浪計畫。
曾出版:散文詩集《我殺了一隻長頸鹿》。小說集《歸來》、《黑店》。
散文詩選入《躍場──台灣當代散文詩詩人選》,兒童文學作品曾輯入年度《台灣兒童文學精華集》。
章節試閱
雨中跳舞的斑馬
連綿的雨炸開小島,冷淡透明的水珠不斷墜地,落空輪迴輪迴落空。
「這雨,不停嗎?」我目光漲滿心碎。
「你得打破冬天的慣性思維。」躺在地上那隻灰濛濛的斑馬回答。
近一點,我們的距離再近一點,玻璃上雨珠靜靜趴著,傘花掠過斑馬,水滴形黑白相間的馬跳動,一隻,兩隻,許多隻。
「來吧,靠近我!」牠說。
「我可以更靠近冷冽絕望,與你共舞?」
脫掉冬的斗篷,踏水而去,黑白線上雨花四濺,現在,我也是一隻跳舞的斑馬。
沒有名字的鳥
失去的青春小鳥,他們多半有名字,只是,長久桎梏鳥籠內的聲...
連綿的雨炸開小島,冷淡透明的水珠不斷墜地,落空輪迴輪迴落空。
「這雨,不停嗎?」我目光漲滿心碎。
「你得打破冬天的慣性思維。」躺在地上那隻灰濛濛的斑馬回答。
近一點,我們的距離再近一點,玻璃上雨珠靜靜趴著,傘花掠過斑馬,水滴形黑白相間的馬跳動,一隻,兩隻,許多隻。
「來吧,靠近我!」牠說。
「我可以更靠近冷冽絕望,與你共舞?」
脫掉冬的斗篷,踏水而去,黑白線上雨花四濺,現在,我也是一隻跳舞的斑馬。
沒有名字的鳥
失去的青春小鳥,他們多半有名字,只是,長久桎梏鳥籠內的聲...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
散文詩裡的異境世界/蘇紹連
──序簡玲散文詩集《雨中跳舞的斑馬》
輯一/水與火
火舞
烈火
薪火
狂蠅
蠟燭
靜物
枯井
秘密
謬誤
逝水
策馬
蟻島
雨中跳舞的斑馬
雨中的愛麗絲
枯藤
葉子
茶碗
水牢
斷流
輯二/對話
照相機
鉛筆
洞見
風車
死角
寄居
伏案
街頭
樹敵
日記簿
手錶
冰箱
高牆
剪影
續夢
寸斷
頑石
風問
鼻子
沒有名字的鳥
輯三/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的房間
一個人的廚房
一個人的旅程
一個人的陽台
一個人的海
一個人的書
一個人的山
一個人...
散文詩裡的異境世界/蘇紹連
──序簡玲散文詩集《雨中跳舞的斑馬》
輯一/水與火
火舞
烈火
薪火
狂蠅
蠟燭
靜物
枯井
秘密
謬誤
逝水
策馬
蟻島
雨中跳舞的斑馬
雨中的愛麗絲
枯藤
葉子
茶碗
水牢
斷流
輯二/對話
照相機
鉛筆
洞見
風車
死角
寄居
伏案
街頭
樹敵
日記簿
手錶
冰箱
高牆
剪影
續夢
寸斷
頑石
風問
鼻子
沒有名字的鳥
輯三/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的房間
一個人的廚房
一個人的旅程
一個人的陽台
一個人的海
一個人的書
一個人的山
一個人...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