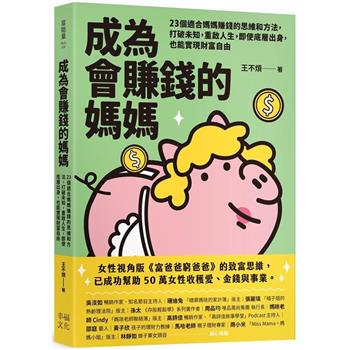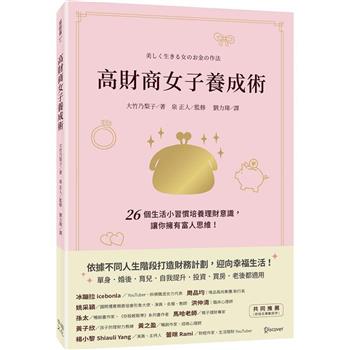睽違二十年,廖偉棠再次出版小說集
「這是時代的失眠症把我魘著了,可是我喜歡這種驚醒,不斷驚醒。」
在《末日練習》中,地球被巨大到如同墨西哥的外星人籠罩天際,人類在它面前沒有祕密;一位詩人與其他乘客一同經歷了飛機故障,而這趟航班是飛行史上最大的謎團;西藏轉世靈童與魔鬼數百回合的傳奇鬥法,每一次都是末日的預演;民國初年,久旱逢雨,神祕的人魚公子變幻莫測;舊愛的鬼魂現身,只為再死一次……
廖偉棠在科幻與玄幻、夢境與清醒之間穿梭,將創傷、暴亂和不義串聯,彷彿一場又一場的噩夢,不斷驚醒。「末日」或許不在未來,而是無所不在,不該發生的已經發生,即將發生的已成為過去;「練習」不是未雨綢繆,而是重複悼亡,預言幽靈的歸返。
廖偉棠:我的小說寫得比詩放鬆很多,雖然我在小說中時刻不忘自己詩人的身分、詩在這個屬於我的文字宇宙中強烈的存在感。在這種放鬆中,我漸漸重獲了結構的快感、虛構與想像的快感,這是我寫那些越來越沉重艱澀的詩時不可能有的。我希望詩與小說之間的界限更模糊,讓作者與讀者的靈魂、離散者和留守者的靈魂,在這些文字的迷宮裡漫遊穿梭、秉燭夜遊。
專文推薦
王德威(中央研究院院士):廖偉棠寫的不是香港的過去與未來。他寫的是香港的「原來」與「後來」。該發生的不該發生的都已經發生,因緣俱分進化。在更廣袤的劫毀裡,香港後來怎麼了? 當大敘事頭頭是道的描寫香港未來時,廖偉棠暗示香港的後來說不清,也不必說得清。
高翊峰(作家):「以詩戲仿了小說、以小說戲仿了詩。」這些戲仿,形式上穿引歷史、古典、科幻、奇幻、寫實、魔幻。作者逐篇如俄羅斯娃娃套用,多重的後設,在不同的時輪所在地,以詞彙向這個時代吹拂文字風暴,試圖洗滌一切似罪與無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