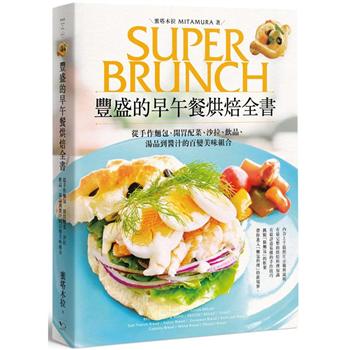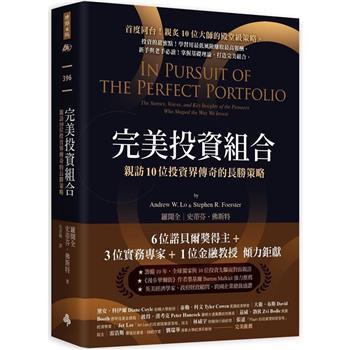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曾說過:「人生不如一行波特萊爾」,吳鈞堯以小品文《一行波特萊爾》,向東、西方兩位導師致敬。
延續《一百擊》鏗鏘詩意、《台灣小事》土地回饋,以百來篇六百字小品,出入鄉情、親情以及更寬更闊的人情。徐國能指出,「語音表情,無一不充滿了他獨有的懷舊風霜」,林佳樺說,「愛他人已不簡單,作者心中,萬物也值得被愛」。
生活中容易錯失的光影、永不下檔的童年內心戲,以及遠近之間、個人與他者的依存,彼此環扣。精簡意在濃縮、言賅釋放遼闊,猶如「每一個人誕生,肌膚都柔軟,正是一朵朵剛剛飄落的雪」,「看古蹟時,最常撿起時間,讓它成為我的另一根骨頭,再用它,刺探一些綠意」、「不近黃昏,不知道夕陽的好,當時有鳥啞啞飛過我與炊煙,把牠看到的都說給了夕陽。」
小品於是成為鍛鍊,用來解釋一條河流,離開了山谷。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一行波特萊爾的圖書 |
 |
一行波特萊爾 作者:吳鈞堯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8-1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0 |
中文書 |
$ 300 |
現代散文 |
$ 300 |
散文 |
$ 300 |
現代散文 |
$ 342 |
中文現代文學 |
$ 34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一行波特萊爾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吳鈞堯
出生金門,曾任《幼獅文藝》主編,獲九歌出版社「年度小說獎」、五四文藝獎章、中山大學傑出校友等。《火殤世紀》獲文化部文學創作金鼎獎(小說)、《重慶潮汐》入圍台灣文學散文金典獎,以及《一百擊》、《遺神》、《孿生》等。多次入選年度小說選、散文選、新詩選,近年回歸詩隊伍,出版《靜靜如霜》、《水裡的鐘》等詩集。
吳鈞堯
出生金門,曾任《幼獅文藝》主編,獲九歌出版社「年度小說獎」、五四文藝獎章、中山大學傑出校友等。《火殤世紀》獲文化部文學創作金鼎獎(小說)、《重慶潮汐》入圍台灣文學散文金典獎,以及《一百擊》、《遺神》、《孿生》等。多次入選年度小說選、散文選、新詩選,近年回歸詩隊伍,出版《靜靜如霜》、《水裡的鐘》等詩集。
目錄
【推薦序】徐國能/餘韻
【推薦序】林佳樺/波特萊爾的三圍
【自序】不只是偏安
說門神
阿河上岸
氣候少女
爺爺小事
奶奶小事
晨泳時分
畫的裡外
木麻黃樹下
嫁牛
年畫娃娃
爺爺的鍋貼
迷蝶南北
反對天空
兩岸空飄
爬行動物
發源地不詳
八二三夜行軍
浪與掛鐘
線外的線
野火喜鵲
蟬回首
麻雀啊麻雀
肉身與銅像
看到羅紅
頭髮說話
買單老大
暗空公園
圈牧的星星
會飛的樹
陸地的魚
咖啡戀愛幫
咖啡漩渦
辛格向前衝
嗑花生
壺底乾坤
抽抽樂
女人列車長
芭比爬上樹
潮濕的字典
國小同學會
昔果山七號
臉與臉譜
谷歌大神
當一個蔣總統
金門婚禮在臺灣
為誰停下
黑熊來了
一行波特萊爾
人生五種球
母親的戲法
老街必須老
小丑與王爺雞
善牧有言
兩個熊寶貝
生死一線
古人連續劇
長角的夏天
冰川祭禮
民宿藏寶圖
人與太陽能
太極聯想
狗的故事
塔與神話
生命靈數
最棒的訪談
男子漢島嶼
疫情山頭
為口罩延年益壽
慢下來敲門
兵馬俑與我
坐好歲月
重返廢墟
三個姊姊
求婚裝甲車
羨慕羅智強
阿嬤與王永慶
溪頭這一邊
溪頭有心人
柑仔店與超商
婆婆的選擇
毛髮小事
毛髮編織
捷運上
樹跟我說話
遇到郝思嘉
謫神記
伯仲結
綠色長城
黑手夢
六字迷障
神前的密語
喀拉拉的大灰
五樓愛情
叛逆老少年
聲音平台
聲音的懲罰
為何夢見她
別人家的孩子
懸日與鳥
密訊翻譯
台北奇俠
雨天的貴人
天山雪蓮的微笑
流浪的樹
魔術地址
環島不老
移動的餅
青年嘆世紀
赫曼.赫塞文本
鹽的滋味
訪孫運璿
台灣的海呢
趨光量測
相遇毛小孩
有鼠的下午
回頭記得貓
因為朋友是客家人
空袖的人
住在紙箱中的人
縫牢的鈕扣
羅斯福路安全島
長與短的冒險
文學四季
邀稿長短談
蜥蜴與蛇
調緩秋光
魚粥的滋味
金庸三十六
宜蘭嘟嘴
北竿鵝舞
噗噗延伸
風景阡陌
留言的介質
芳香老虎
石虎與黑貓
角落裡
調書袋
邊角的風標
一劃道理
南橫用心
故事裡的夾竹桃
當過楓葉鼠
【推薦序】林佳樺/波特萊爾的三圍
【自序】不只是偏安
說門神
阿河上岸
氣候少女
爺爺小事
奶奶小事
晨泳時分
畫的裡外
木麻黃樹下
嫁牛
年畫娃娃
爺爺的鍋貼
迷蝶南北
反對天空
兩岸空飄
爬行動物
發源地不詳
八二三夜行軍
浪與掛鐘
線外的線
野火喜鵲
蟬回首
麻雀啊麻雀
肉身與銅像
看到羅紅
頭髮說話
買單老大
暗空公園
圈牧的星星
會飛的樹
陸地的魚
咖啡戀愛幫
咖啡漩渦
辛格向前衝
嗑花生
壺底乾坤
抽抽樂
女人列車長
芭比爬上樹
潮濕的字典
國小同學會
昔果山七號
臉與臉譜
谷歌大神
當一個蔣總統
金門婚禮在臺灣
為誰停下
黑熊來了
一行波特萊爾
人生五種球
母親的戲法
老街必須老
小丑與王爺雞
善牧有言
兩個熊寶貝
生死一線
古人連續劇
長角的夏天
冰川祭禮
民宿藏寶圖
人與太陽能
太極聯想
狗的故事
塔與神話
生命靈數
最棒的訪談
男子漢島嶼
疫情山頭
為口罩延年益壽
慢下來敲門
兵馬俑與我
坐好歲月
重返廢墟
三個姊姊
求婚裝甲車
羨慕羅智強
阿嬤與王永慶
溪頭這一邊
溪頭有心人
柑仔店與超商
婆婆的選擇
毛髮小事
毛髮編織
捷運上
樹跟我說話
遇到郝思嘉
謫神記
伯仲結
綠色長城
黑手夢
六字迷障
神前的密語
喀拉拉的大灰
五樓愛情
叛逆老少年
聲音平台
聲音的懲罰
為何夢見她
別人家的孩子
懸日與鳥
密訊翻譯
台北奇俠
雨天的貴人
天山雪蓮的微笑
流浪的樹
魔術地址
環島不老
移動的餅
青年嘆世紀
赫曼.赫塞文本
鹽的滋味
訪孫運璿
台灣的海呢
趨光量測
相遇毛小孩
有鼠的下午
回頭記得貓
因為朋友是客家人
空袖的人
住在紙箱中的人
縫牢的鈕扣
羅斯福路安全島
長與短的冒險
文學四季
邀稿長短談
蜥蜴與蛇
調緩秋光
魚粥的滋味
金庸三十六
宜蘭嘟嘴
北竿鵝舞
噗噗延伸
風景阡陌
留言的介質
芳香老虎
石虎與黑貓
角落裡
調書袋
邊角的風標
一劃道理
南橫用心
故事裡的夾竹桃
當過楓葉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