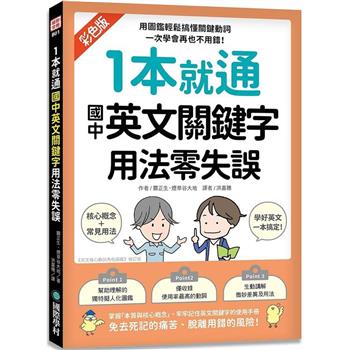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劉禹錫〉
提起詩人劉禹錫(772-842),都會想起他名叫〈烏衣巷〉的短詩來,詩曰: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首詩之所以有名,是把對個人對歷史的興亡感寫出來了,中國人對歷史是敏感的,這樣內容的詩很多,但太多了總會老套,所以真寫得好的並不很多。這首〈烏衣巷〉藉物寫情,有一種很強的傷感在其中,而劉禹錫的傷感不是一般人涕泗縱橫的,他的傷感,有個特殊形容詞,就是「有蘊藉」,蘊是內藏而不外露,藉是有憑藉而不直白。東晉國都在建康(今南京),朱雀橋與烏衣巷是都中勝地,高官名人如王導、謝安都曾住此,但到了中唐,連綿官邸已成為尋常百姓之家,大片天空,只剩下飛舞的燕子了。詩所寫的是一種寥落感,寥落就是滄桑,是有歷史感的人所共有的。
劉禹錫因有才識,對世局常有不滿,而他所處正是唐代由盛而衰的時代,令他不滿就更多,唐代經過盛唐末期的安史之亂,元氣大傷,中唐之後,朝廷大臣結黨營派,劉禹錫跟白居易都遭捲入以王叔文(753-806)為首的黨爭,使已渙散的國政更加四分五裂。白與劉都是王叔文的擁護者,王叔文後被處死,也影響到他們的前途,白居易被貶為永州司馬,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都是黨爭的受害者。
因受害,白居易才有〈長恨歌〉、〈琵琶行〉等名篇行世,劉禹錫因貶謫而大量接觸到底層農人,因而有非常民歌化的「竹枝詞」出現,假如他們官運順遂,就不可能產生這類作品,所以後來有「文必窮而後工」的話。劉禹錫最有名的一首〈竹枝詞〉可能是這首吧: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這首詩的可貴,在只寫民情,不言「大道」,又融入一般鄉下人的口語,毫不裝扮。如「聞郎江上唱歌聲」,寫女的被男的歌聲吸引,詩裡不用較雅的「歌聲」,而用通俗的「唱歌聲」,直白近俚,卻顯得更為自然,可見劉禹錫放下身段,走入民眾,這一點很切合文學社會學者的主張。但民間文學也不見得每件事都直白,有時會暗藏些迷語、暗語在其中的,詩中「晴」與「情」互通,看似文字遊戲,也藏有無限溫柔之思,這跟《詩經》的源流是一樣的。《全唐詩》收錄的〈竹枝詞〉尚有多首,形式內容多類似,詩人走向民眾,歌詠人間最質樸的情感,是杜甫之後的新途,其中劉禹錫跟白居易的貢獻與成就最大。
下面我想談一談劉禹錫一篇很有名的短文,叫《陋室銘》,這篇短文很受清代之後文人的青睞,曾被清初古文家吳楚材選入他有名的《古文觀止》中,又被林雲銘選入《古文析義》,民國之後,也屢被選入學校國文教科書,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全文如下: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可以調素琴,閱金經。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
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
這篇文字可當它韻文看,除了最後一句「孔子云:何陋之有」外,通篇都押韻,多駢句,似也可當成駢文看,但一般駢文都長,這篇卻短,駢文多喜賣弄詞藻,這篇相對樸實,從此看是很有特色的。
雖如此,但嚴格說來它也有缺點。拿來跟前面所引兩首詩相比,〈陋室銘〉比較欠缺真誠,見識也通俗了些,加上觀念有點浮濫,雖拿孔子語結尾,與孔子所達的至高語境相較,還差了一大截。首先「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話沒說錯,但既已隱居陋室,卻以仙、龍自居,看似高崇,其實媚俗。全篇主旨在「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兩句,強調「德馨」的重要,但對何為德馨、德之所以馨、如何馨,並無具體描寫,「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只知居室在鄉,頗有野趣,但後面立接「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兩句,不小心寫出了他實際心態,就有點讓人看低了。陋室中的他所結交的,依然是碩德大儒,對不識字的平頭百姓,總抱著某種程度的厭棄感。他心儀的對象是諸葛亮、揚子雲等名人,而大家也都知道,他在乎的不是諸葛亮、揚子雲曾有過的平居歲月,在乎的是他們後來不論在官場或文壇飛黃騰達的成就。在這種心態之下,使得他在語言上顯得左支右絀又有些扭捏作態了,我們如拿來與田園詩人陶淵明比,是何其的不同?陶詩中也隱逸生活的極多,都平靜而真切,如〈歸園田居‧其二〉,是這樣寫的: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
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
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
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陶淵明曾為官,但後來「不願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決心棄官,當他丟了官職,就真到鄉下安心種田去,對官事便一無懸念了。首句「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表面是鄉居地僻,不利交通,其實是自己有意拒絕「人事」,而他的人事包括鄉村之外的所有「世事」。與他相與之人,都是「披草」(古代農人著簑衣以防雨,簑衣草製,故云披草)的農夫,並無他人。農夫只關心農作的收成,不在乎其他的,甚至道德文章對一般農夫言也都是「雜言」,所以「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而農家生活,有喜也有憂,農家所憂在天氣不好,影響收成,所以最後說「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所說句句真實,毫無虛套。
我不懷疑劉禹錫的文學有真誠的一面,文學史已給他適當位置了,但他的〈陋室銘〉確實還差了點。這篇短文的問題是太被傳統文學的框架框住,臨筆總想攀附點德馨之類的消息於其中,而他「德馨」的範圍又窄了些,他偶爾又會擺出點一般讀書人的架子,認為自己見識廣、才德高,因而瞧不起人。「陋室」如他說的那樣好,居於其中就該有點志氣。志氣是什麼呢?既居陋室,就不再探聽外面的消息,也不再意圖與高官厚爵來往,那些歷史名人,不論諸葛亮也好,揚子雲也好,我一個也不豔羨,我只寧願做自己,不論我選擇陋室或陋室選擇我,我都很有自信,而且來去自由,在這情況下,我便無須裝腔作態的「調素琴」、「閱金經」了。還有,我更不會瞧不起周圍知識不高的人,陸象山曾說:「某雖不識一字,亦不妨我堂堂正正做人」,王陽明也說過:「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我們應該知道,知識界之外也是有漢子在的,所以我絕不輕視白丁。
劉禹錫是個不錯的詩人,可惜的是他不夠徹底,觀念總有點放不開,心中還是想藉自己的清高來博取更高的名聲,言行舉止因而有些錯亂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總在仕、隱之間糾纏爭扎,欲就不能,欲斷又斷不了,很少有人如陶淵明的沉穩痛快的。
〈在他們的時代〉¬
今天(2021/11/23)是臺靜農先生一百二十歲冥誕。
像我們這樣年紀的臺大「中文人」,跟臺靜農先生不可能沒有關係的。我大學不讀臺大,但到臺大上過他的課,後來碩士、博士都是在臺大得的,我的博士學位考試,在臺大的口試是由臺先生主考,在科舉時代臺老師不但是我的「業師」,也是我科場的「座師」了。雖然有多層關係,臺先生跟我們隔了一個世代,老實說,我對他的了解還是不夠的。
有些事不只發生在臺先生的時代,就是發生在我的時代,不刻意解釋,別人也難以了解。譬如我剛才說臺先生是我博士學位的校內主考,難道學位還要在校外再考的嗎?是的,在我那時代,各校還不能授博士,教育部還要辦一場特別的口試,口考委員通常有七人,通過了才由教育部授予博士學位,那時叫做「國家博士」,繁文縟節得很,現在聽起來有點可笑,這制度幾年後就改了,學校就可直接授學位,以致現在沒人懂了。
熟知系裡事務的朋友聽說臺先生當我主考,說臺大有博士生後,臺先生從沒做過主考,光這一點,就很特別,忙問我臺先生問了我哪些問題,我說我全忘了。論文口試時,考生都是名實相符的「苦主」,像法庭被人審問,或像刑場待決的犯人,偶爾問你有沒要說的,自己學烈士就義前陳詞一番,也侃侃了幾句,勇氣其實都是裝出來的,所以過後往往就會「立志」忘他個一乾二淨。倒是口試結束之後某日,指導教授張清徽老師帶我到臺先生府上致謝,才知道臺先生答應做我主考,是張老師「求」來的,張老師在大陸時代曾做過臺先生的學生。在臺府,兩位老師面前我不太敢說話,臺先生看我冷在一邊,客氣說我的論文寫得不錯,他點出了幾處,才知道他是細看過的。他又問我論文提到晚明徐渭的《四聲猿》,還知道徐渭是個書法家嗎?我恭謹回答說知道,記得徐自己說過:「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又問我知道祝允明嗎?我也點頭,但我有自覺,焦點不該集中在我身上,直到告辭,也沒深談。我不喜稠密,相交多清遠,對長輩亦然,後來有幾次陪友人到臺府領取所贈書法,算起來我跟臺老師也有點關係的,但我始終沒一件他的墨寶,原因是我從沒開口跟他要過。
臺先生在大陸時代,是個學者,但當時的學者,比現在的要「有志」多了,他曾從事文學創作,也卓然有成,他的小說曾被魯迅認可,他也熱衷過文化與社會改革運動,讀他小說,知道他曾唱過《馬賽曲》與《國際歌》的,算是個左派的「憤青」吧,有時扮演急先鋒的角色,因此也坐過牢。在當時人的眼中,受罪坐牢都無所謂,故國神州有大片土地好奔馳,又有無數苦難人民待拯救,那是「大我」所在,「小我」是不能懷憂喪志的。我曾看過臺先生用漢隸寫張載〈西銘〉上的話:「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者也」,而這句的前面,就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名言,可見他懷抱所在,而當時有為的青年,大多類此。
但來臺灣後,地變小了,人變少了,剛來時氣氛肅殺的很,要適應這裡生存得靠其他本事,沉默與收歛是其中之一。他在臺大,繼許壽裳、喬大壯兩先生後出任中文系系主任,他的兩位前任,都是離奇死去的。許壽裳一晚在臺大宿舍被人亂刀砍死,警局的說法是闖空門的小偷所為,也有個說法是被當局的特務殺了,但當局為何要殺他呢?也沒人說得清楚,那時是一九四八年,大陸全面變色在即,而臺灣更是亂成一團。喬大壯先生接許壽裳先生的任,不久因故回大陸探親,不料卻自沉於蘇州,喬的死也是一片謎團。喬死後臺大中文系等於沒「大人」了,只有臺先生能接,便由他接了,所以臺先生初接任的那幾年,一直都是活在莫名的陰影之下的。
時局大亂,人心惶惶,為了營生,什麼事都可能做得出來,像當時四伏的險巇,承平時代的人是完全無法想像的。臺先生在臺大連續做了二十年中文系系主任,這記錄好像很難打破,不過在當時,也不算什麼,那還是個政令清簡的時代。沈剛伯先生當臺大文學院院長,一幹就幹了二十一年,算起來比臺先生更久,沈先生除了做文學院院長還兼任歷史學系系主任,還有英千里先生當外文系系主任,也是當了很久,當時好像沒什麼專兼與任期的制度,以今天角度看,都有點亂。
臺先生到臺灣之後,就像變了個樣似的,之前那些有關社會變革與文學開展的豪情壯志,好像不得不收拾了起來,曾經左翼青年的那種孤注一擲性格,也變成步步為營的謹慎小心了。但他馳騁了大半生,一時之間是收攏不住的,所以他刻意尋找可以延續他懸蕩之想,卻不會引起別人的猜測與懷疑的事。他發現中國傳統書法的秘境值得探索,那裡的高山深谷可供攀緣,一方面可以忘身,一方面可供「振衣千仞崗」,萬一失足,傷的是自己,跟別人也一無牽連。
他早年受沈尹默影響,是練過書法的,但他之後的書法旅程,卻有些令人不易猜測。他臨過漢碑中的〈石門頌〉,又因張大千贈他倪元璐書作,對倪書的特殊筆勢也有了興趣與體認,他在習倪書之前,還曾臨過王鐸書法的,倪、王都是晚明的書家,倪元璐在明末做過高官,但並不得志,崇禎死時他也隨之自縊而死,是個忠烈又奇特的人,倪的書風,蒼渾雄放之外又險仄奇絕,應是他人格的寫照吧。據說臺老師也曾學過清代「揚州八怪」金農與羅聘的字畫,也許只是淺嘗吧。他早期寫毛筆字是隨興,但到臺灣後,就不光是隨興,而是全力以之了,因為除寫字之外,沒太多事可做。
非常有趣的是〈石門頌〉與倪體行書,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路數與風格,不要說不能相提並論,幾乎是無任何調合空間的。〈石門頌〉講究的是克制與均衡,每筆都用中鋒,看起來四平八穩,堂堂正正,而倪元璐的書法偏鋒側出,運筆奇險,每字幾乎都朝右傾斜,結體詭譎。倪書的撇筆常輕率些,捺筆往往不到位,或以點代之,單獨一個字擺著,好像隨時要倒,所以有奇險的感覺,但全篇一氣呵成,字字相聯,也是流暢而有神的。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說:「明人無不能行書,倪鴻寶(倪元璐)新理異態尤多,乃至海剛峰(海瑞)之強項,其筆法奇矯亦可觀」,可見也多以「異態」、「奇矯」視二人之書法。我覺得臺先生的倪書寫得比倪元璐的更為奇倔而緊密,但可能有〈石門頌〉在後面撐著,卻是始終沒有要倒的感覺。
這點非常奇怪,為什麼他隸書選擇平穩,而行書選擇奇倔呢。不僅如此,他雖受過沈尹默的影響,但沈行書文靜端凝的書風在他身上一點都看不到。他後來不走王鐸的路而走倪元璐的路,據說也是因為王書「爛熟傷雅」,他後來對金農與羅聘有興趣,原因可能是金農與羅聘在藝術上奇怪的個性,又跟他們處處不與人合的生命態度有關吧。這麼說來,臺先生的人格與他書藝之間的關係,有更值得探索的地方,不可輕易放過。
我記起臺先生問過我徐渭。徐渭也是晚明的詩人與書法家,他的年輩比倪元璐要高,但他的才高與不遇,比起倪的要更嚴重許多。袁中郎在〈徐文長傳〉說他:「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夫,悲夫!」袁文中的「奇」有兩種讀法,也有兩層不同含意,前面幾個「奇」都讀「齊」,就是奇怪、奇特的意思,最後那句「斯無之而不奇也夫」的奇要讀「基」,是「奇偶」的奇,奇是表示命運不好,遭時不順的意思。照袁中郎的說法是,徐渭因為太奇特了,使得他命運壞得透頂。
我一直在想,臺先生是不是奇特呢?當然是,他命運好不好呢?答案可能有好多個,而彼此關聯性不強,有些還很矛盾。有些矛盾,在他書法上可以看出來,但也只能看出一些大概,細微與真實的部分,我們的了解還是不足。他們的時代與我們的之間,似乎隔著一堵不低的牆,想要跨越,還須要花不少工夫的。
我與臺先生相近的機會不多,這是我生性羞怯又慵懶的緣故。但我非常喜歡臺先生的樣子,他個兒高大,皮膚黝黑,是北方貴人的那種長相,不論遠近,都好看得很,他晚年上唇留了一小撮鬍子,臉神肅穆又溫和,完美得有如一尊北魏佛雕。我記得在我博士學位的口試中,那天他穿著一件淺色的港衫,端坐在上座,當時我心亂如麻,但他只消幾句話或使一個眼神,原本衝著我來的許多災難,頃刻之間都消失無蹤了。
佛與菩薩會尋聲救苦,他們總是放心不下別人,因此胸中仍是有波瀾的。臺先生是否也有波瀾呢?有的,這可由他關心徐渭的「不遇」看出來。老年的臺先生在他的歇腳庵,自號靜者,表面是靜靜守著自己一方,什麼都不管。但他的書法平穩坦蕩中透露出不尋常的奇倔之氣,撇捺之間,總微微有點讓人不安,好像他在示人,就算是承平歲月,世上依然隱隱有一種危機在的。
他內心深處,也許並不寧靜。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記事與隨想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記事與隨想
文學的真與善,藝術的美,值得一生追求,當人決定將一生的憂與樂都置於此時,其他都不重要了。
寫作之途孤涼,清末詩人陳衍說過:「詩者,荒寒之路」,不只詩,所有文學都一樣。而同時,智慧也產生於孤獨,這時有人跟你同聲相應,就特別值得珍惜。我的一生經歷過不少困境,還好這世界有文學,讓人在混亂中有一點沉思的空間,也讓人現實之外有點幻想可尋。
───周志文
我讀周志文的散文,總是感應一種珍貴的詩意,金風徐來,秋林之美。愛看時光倒影的人,不免獨登歷史的樓臺,喚醒蟄伏的傷懷,卻偏偏能夠觸及帶著詩意的哲思。雖說此調深奧幽玄,今人多不彈,但知味者自能賞識弦上的風流與韻味。
───唐捐
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落到無人處或落到有人處都沒什麼兩樣,八十歲自帶一種任性超然的氣場。周志文散文心心念念的一點戲謔,萬般深沉,是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也是麥田光影,金黃裡掩映的死亡,是絕望,也是新生。
─── 張瑞芬
作者簡介:
周志文
一九四二年生,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臺灣大學碩士、博士。
曾任中學教師,報社主筆,淡江、臺大教授,現已退休。
文學著作有:《日昇之城》、《三個貝多芬》、《冷熱》、《布拉格黃金》、《時光倒影》、《同學少年》、《記憶之塔》、《家族合照》、《黑暗咖啡廳的故事》、《有的記得,有的忘了》等。
章節試閱
〈劉禹錫〉
提起詩人劉禹錫(772-842),都會想起他名叫〈烏衣巷〉的短詩來,詩曰: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首詩之所以有名,是把對個人對歷史的興亡感寫出來了,中國人對歷史是敏感的,這樣內容的詩很多,但太多了總會老套,所以真寫得好的並不很多。這首〈烏衣巷〉藉物寫情,有一種很強的傷感在其中,而劉禹錫的傷感不是一般人涕泗縱橫的,他的傷感,有個特殊形容詞,就是「有蘊藉」,蘊是內藏而不外露,藉是有憑藉而不直白。東晉國都在建康(今南京),朱雀橋與烏衣巷是都...
提起詩人劉禹錫(772-842),都會想起他名叫〈烏衣巷〉的短詩來,詩曰: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首詩之所以有名,是把對個人對歷史的興亡感寫出來了,中國人對歷史是敏感的,這樣內容的詩很多,但太多了總會老套,所以真寫得好的並不很多。這首〈烏衣巷〉藉物寫情,有一種很強的傷感在其中,而劉禹錫的傷感不是一般人涕泗縱橫的,他的傷感,有個特殊形容詞,就是「有蘊藉」,蘊是內藏而不外露,藉是有憑藉而不直白。東晉國都在建康(今南京),朱雀橋與烏衣巷是都...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
斯文,滋味與痛感/唐捐
拉克勞的收割,烏丟的宇宙──周志文散文之心心念念/張瑞芬
輯一
庭院裡的樹
劉禹錫
東坡在黃州
田水月先生
苦瓜和尚的題畫詩
天下與國家
茶與茶書
明天會更好
士兵的故事
拉克勞的收割
達利與我
輯二
老人與海
殺戒
我的尊嚴
鄉音
故鄉
幾個有關機械的事
八二三的雜憶
人到一老就要小
梅塔與馬勒
我為何寫作?(一)
我為何寫作?(二)
我為何寫作?(三)
輯三
一九五七年
在他們的時代¬
北斗,南斗
思念裴老師
一個有願望的人
流螢飛復息
懷...
斯文,滋味與痛感/唐捐
拉克勞的收割,烏丟的宇宙──周志文散文之心心念念/張瑞芬
輯一
庭院裡的樹
劉禹錫
東坡在黃州
田水月先生
苦瓜和尚的題畫詩
天下與國家
茶與茶書
明天會更好
士兵的故事
拉克勞的收割
達利與我
輯二
老人與海
殺戒
我的尊嚴
鄉音
故鄉
幾個有關機械的事
八二三的雜憶
人到一老就要小
梅塔與馬勒
我為何寫作?(一)
我為何寫作?(二)
我為何寫作?(三)
輯三
一九五七年
在他們的時代¬
北斗,南斗
思念裴老師
一個有願望的人
流螢飛復息
懷...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