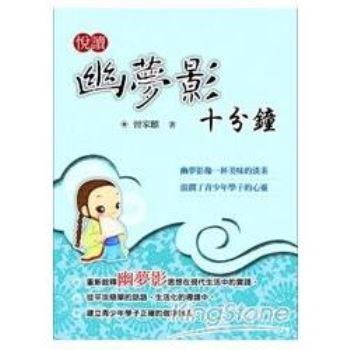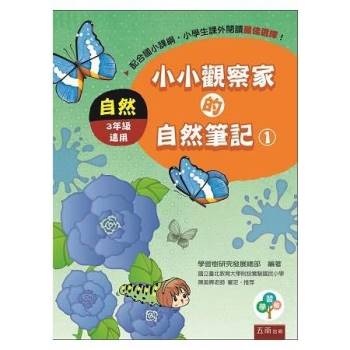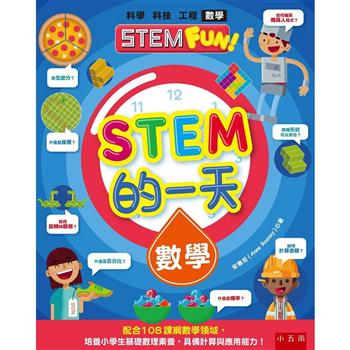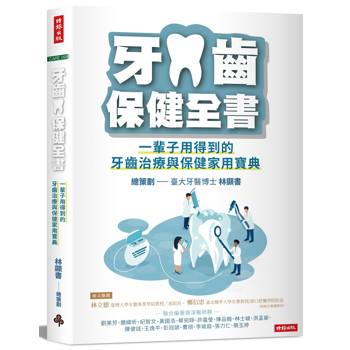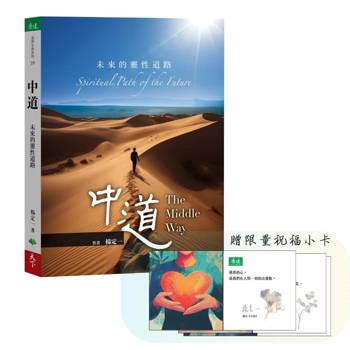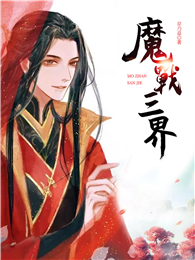蘭陽雨
我鄉環山面海,地形像畚箕,容易捕風捉雨,尤其秋冬,十日九風雨。這幾年,溫室效應,氣候變遷,反聖嬰現象,東北季風來襲,天空更是破了個大洞,雨一落,日連夜,夜連日,沒完沒了。
雨日,常望向窗外,「苦啊~苦啊~」那是來自屋後灌木叢內白腹秧雞的叫聲。豪雨時,都躲起來了,偶也見單獨者,似徘徊又匆匆,大概是出來找食物填肚子,順便啣回去給家人吃。雨勢稍緩時,通常三五出來覓食,曾見二隻起衝突,互不相讓,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煞是好看。
十幾年前開始鄉居生活,翌年,颱風登陸,拉下新鐵門,一窩鳥巢落地,不意絞死三隻麻雀幼雛,難過極了。擔心再發生意外,於是不定期清除,然清除後又築,再清除,再築。麻雀機巧,摸清畚箕地氣候脾性,為了一家人平安,棄枝葉濃密的山欖、老榕,執意落戶鐵捲門內。近幾年颱風都轉向,捲門蓋已長出一綹綹散亂的乾草來,想必內部戶數愈來愈多,居家坪數也愈來愈大。算了。再說吧。
而蟻巢實在無法輕易說算了。
屋外扶桑、野牽牛、木芙蓉,常見一群黑蟻在花蕊間攒動,碗公大的蟻巢就藏在濃密的樹葉裡,彼不犯我,和平共處。但,雨季來臨時,廚房後門旁磁磚隙縫一圓孔,螞蟻如泉水般湧出,長長的隊伍,或整齊或散亂,浩浩蕩蕩大遷徙。我心懷同情憐憫,但全數撲殺,實不得已也。
暴雨猛撲,休耕的稻田成了汪洋大海,屋後水圳如巨蟒翻騰,山下園子裡的菜苗,芥菜、紅鳳菜、高麗菜等等,一株也不留。雨歇,補栽種,不出兩日,雨來了,照樣。本地菜農的心血普遍付諸雨水,自家採摘的菜不夠塞牙縫,只好孵豆芽菜,改吃馬鈴薯、洋蔥等根莖類食物。然餐桌上無綠色菜葉類,幾乎少了悅目的「色」,不出三天,終究提起菜籃,菜攤揀幾把貴死人的南部菜,菠菜、青江菜、空心菜,又肥又綠,一個蟲洞也找不到。
坐困雨林迷宮如我,幾十天了還找不到出口。闖出雨林者,逕往高雄、台南奔去。少不得IG臉書發布即時動態「出雪隧就沒雨了」。然後,秀出波光嶙峋的沙灘照,這樣做還不滿足,LINE加強炫耀「這裡有太陽耶。」「要不要來?」
有時耐不住膩煩,望天叨念:到底要下到什麼時候?我母若聽聞,就勸,下雨不出門就好,如此說話對天公伯無禮。然後說起冬山河截彎取直前,下大雨,屋內很快就淹水,還說有人娶妻那天,雨直直落,家裡進水了,怕豬被淹死,只好把豬趕到新娘房床上。現在,落一二個月也不會淹水,要感謝天公伯,也要感謝老縣長才是。阿母雖如是說,閩南語氣象播報時,仍是定定聆聽明日降雨機率多少,然後,皺眉苦笑。
童年時,家裡淹水記憶猶深,彼時只覺得水漫進屋裡,然後一寸寸升高,我追趕長了腳的椅凳鍋盆,只覺得好玩,直到有一次,水淹進床上,我才懂得害怕。關於「豬仔鬧洞房」,倒教我想起作家簡媜,《月娘照眠床》一書裡提到童年大水時,豬寮裡的豬仔,尖銳的叫聲像刺刀,雞仔驚飛到更高的地方,連肥重的鴨子,也會拍翅膀,設法保護自己。只有無助的豬仔,掙扎在生死縫隙間,頂撞著木欄,尖鼻立在水面上,水像黑壓壓的一群厲鬼,狠毒地灌牠的鼻,一聲悽慘吶喊之後,豬仔濃濁慘烈的嘆息聲漸漸低沉,……
並不全為了現實生活中出門不便而哼唉,雨日,正好專心在家讀書寫字或發懶睡個長覺,然而,枝枝節節的日子裡,牆壁桌椅窗簾都要擰出水來,在發霉的青苔味中,說不出是什麼樣的心情,悶悶緩緩,莫名惆悵著,有次見一隻麻雀從灰黑雨林中竄出,奮力振翅,愈飛愈低,淒清心緒,更是沉落。雨再不停,我恐要孵出病來了。
望雨興嘆,絮叨又起:不勞田調,估計全台除濕機雨傘銷路宜蘭最好,耳鼻喉科診所密度宜蘭最高。
兒子女兒妹婿女婿外孫內孫全都鼻子過敏,鼻塞噴嚏也就罷了,可憐小孫鼻黏膜薄,過敏發作,癢就摳,摳重了,鼻血滴滴落,也曾一個噴嚏就噴出鼻血,血滴子般。明知就醫治標,不得不還是就醫,醫生也無奈,說搬到南部就好了。最可憐的是毛小孩阿咪,體質也過敏,每到秋冬,異位性皮膚炎來犯,不停地搔抓、舔舐、磨蹭,肚皮舔得光禿禿,耳朵、眉骨蹭出一粒粒小紅疹,打針吃藥後一段時日又犯,醫生說,異味性皮膚炎只能控制,無法斷根,每年秋冬季節會反覆發生,我問了耳鼻喉科醫師說過的話:是否搬到南部,阿咪過敏自然不藥而癒。是的,這樣就不易復發。那日我突然想起一老同事,大學時,台南宜蘭姻緣一線牽,每到秋冬時節,邊擤鼻涕邊立願總有一天要搬回台南,如今都當阿嬤的年紀了還困在畚箕地。
過去任教職,新生入學時,班上一個小男生適應不良,連著十幾天抽抽噎噎,有一回,邊哭邊說自己也想停下來不哭,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停不下來,說完,哭得更厲害了。平原的雨是小男孩的眼淚,但總有擦乾眼淚,露出笑容的時候。一如某天清早,雲開見日,左鄰右舍見面互道「出日了」「出日了」,然後忙曬衣曬被,我與阿母則到公園曬背曬心情。那日迎面而來幾個阿公說說笑笑:「等幾百年,總算看到日頭了。」「南部欠水,這裡的雨下一些到南部去就好。」「是啊,天公伯若把南部的日頭再分一些過來,不知有多好。」
好雨好陽光不但知時節,還要通有無互援引,阿公們多美麗的夢幻啊。我不禁想起前年十月十一月,宜蘭累計雨量全國居冠,還造成落石坍方,臉書打開,處處苦雨作樂,A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宜蘭大概有三百天在下雨。」B說「連下二十九天了,一秒都沒停過,地都下塌了。」「……」我鄉落水,誰雨爭鋒,基隆的「雨都」之稱該拱手讓出。
一日興來取書,發現書房臨近大窗的書櫃木頭受潮,十幾本書書脊水漬深淺不一,書口長滿黑墨墨的菌絲,酒精一一擦拭,奈何污漬擴散滲入毛細孔,書已不成書,心一狠,全丟進回收桶,好吧,也來發文「問世間晴為何物,直叫人發霉長菇」。
衣服晾上三五天恐還是潮膩膩,幸有除濕機幫忙,收下時,暖烘烘的。不由得想起小時候,溼答答的日子裡,白天房間外走道、廚房飯桌上衣褲、尿布到處晾掛,待傍晚,祖母就燒一盆炭,蓋上雞籠子,一件件輪流披晾烘烤。炭火一點一滴吸走纖維裡的濕氣,也緩緩注入一股股的溫熱,天冷時,我最喜歡把凍僵的手摀在上面,和衣服一起烘暖。
一場又一場的雨,雨出家家戶戶的簡易「除濕機」也雨出本鄉特殊的行車文化。學生族騎腳踏車時,揹著書包,一手握龍頭,一手撐傘,自自在在。你若說這樣很危險,問怎不穿雨衣,得到的回覆大概是「又不是小朋友,幹嘛穿雨衣。」「習慣了」。機車族,則加裝擋風鏡,中央方框玻璃前還有變速小雨刷。還有,家家戶戶通常有八字型曬衣架,好把衣物撐開,娘家至今仍使用,那是爸爸年輕時親手摺的。
青楓之歌
書房落地窗外有棵青楓,十幾年前栽種時,約莫我高,現在已達二個樓層了。多年來,我興起就站在書房固定位置,襯以青綠、金黃稻田,或休耕時的汪汪水澤,為他留下統一格式,不同背景的不同容顏。
日子重複,照片也不斷重複,某日拍下照片,比對過往,突然想起有對中國父女,從女兒二三歲起,每年都在同一地點留下合影,四十幾年後,照片中多了二個小孫女。這些照片,彷彿縮時的光陰之旅,令人動容的父愛中不免感傷歲月如逝水。慶幸植物的時間以環狀進行,替換裝扮有時,而青楓無論綠意盎然,紅葉滿天,或顏色褪盡,四時都是姿態。
五六年前春節,我買了一盆石斛蘭,花香淡雅,枯萎後掛在青楓枝幹,此後莖條一年比一年粗大,花朵更是騰騰冒出。同事來,看石斛蘭長得極好,說是她家陽台陽光不進來,蝴蝶蘭瘦小,之後送來黃、白各一盆請青楓收養。爾後,鄰居在選舉後又出送二盆,我都代替青楓點頭,一盆盆牢掛樹杈處。
某日,載母親來家裡吃飯,她一下車,望向青楓樹身花顏繽紛美燦,讚歎蘭花開得漂亮,豈知,話鋒一轉,說青楓禿盡可能是養分全被蘭花吸光,要我把蘭花全拆下來,我聽完大笑,心想,母親太有想像力了,也忘了青楓入冬後的樣態,於是仔細說明蘭花需要遮蔭,只是借住樹身,自己會吸取陽光和水分,很有骨氣的,絕不是啃老族。母親點頭,卻說,這棵樹這麼美,不能讓他死,死了可惜。
年後不久,光禿的樹梢終於冒出尖尖的芽苞,裡頭裹藏的嫩葉和小花一夜之間雙雙開裂抽長,新葉由紅轉嫩青,儀式般昭告世人「春天來了。」我不忘請母親快來看看枯枝上的新葉。她一臉驚喜:「啊,真正發穎了,這欉樹真媠。」
又沒幾天,淡黃的小花就結出像一對翅膀的果實,當果實成熟時,竹蜻蜓般隨風旋轉而下,落地,不久又長出新苗。枯葉曾是他母體的一部份,他們一起迎接陽光和雨水,一方慢慢化作春泥滋養一方的生命,一方則以茁壯優雅回報,我深深感受到自然律消長中的和諧與美好,於是,把幼苗一棵棵挖出,重新種在小盆子裡,一盆一盆一排一排,排成一個棋盤大小的「百子圖」,又幻想,如果我有一甲地,或許可以學吳晟老師種樹,讓青楓子孫滿堂成一片森林。
四、五月時,青楓的樹冠一如往常,繁茂如蓋可遮簷,恰恰阻擋了面北窗外的強光。我最喜歡這季節佇立在綠盈盈的窗前,聽啾啾鳥鳴,看風移影動。孫女猶是襁褓時期,有幾回哭個不停,媳婦就抱她坐在書房窗外台階。樹下吹風,說話,唱歌。孩子不哭了,靜靜看著樹,一看看好久。媳婦 拿出手機,拍下胖嘟嘟的萌樣,笑說她在思考人生的方向。
樹木有情,氣候暖化後,青楓是否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
祖母生前常說「九月秋,曝死鰗鰡」,聽起來秋陽和夏日同等潑辣,自古迄今顯然是常態,然而深秋冷氣團來襲,氣溫驟降,楓葉依時序轉紅,蕭孋珠唱在七五年那高亢的〈楓紅層層〉,七九年劉家昌的成名曲〈秋詩篇篇〉,愛情之外,都分別以楓紅描摹了秋的浪漫。直到我遷居鄉下,秋冬時節,青楓依然醉了酒般,回我以一樹殷紅。然而,這幾年入冬後,青楓枝頭的陽橙色來不及轉紅就萎落,落葉厚積亂飛,孫女幼兒園放學回家時,踩在軟墊上沙沙沙,找尋她覺得顏色最漂亮的一片送我,說愛我。而我,則找了一片經鳥啄蟲咬的葉片,依序指著五個洞洞說,這片代表「阿嬤好愛你」。她說:我愛你比較多,又說,愛到一○一大樓那麼高。愛是可以比較可以丈量的,我笑回,我愛你愛到外太空……
季節更迭,無論窗前枝葉青綠或疏落光禿,又或天空陰灰大雨滂沱,我在電腦前疲累渾沌時,便走到窗前,望著青楓,什麼也不想,有時走出門,仰望樹頂,摸摸樹身,看眾蘭花的氣根往上往下延展,有的已然嵌進樹幹,靜脈般與樹合為一體。石斛蘭花朵年年如煙火綻放,又似飛流直下,美得教我忍不住按下快門,到處示人。有次,去將就居時,秀給盛師看,不意他也擔心起青楓養分被蘭花吸取。想起曾笑話母親的疑慮,也想起石斛蘭掛的那截樹杈,當年枝幹披垂,鋸掉時,皮肉看似健康,但已枯腐,莫非蘭花啃老?
「可是,很多大樹不都有蘭花附生?」「那要看這棵樹是否夠強壯。」
竹圍人家
年前外出快走,過鄰家,農路右後方唯一的竹圍叢竟然不見了,一條龍五開間老房舍後壁與我隔田對望,後腦勺剃光頭髮似的,寒風中尤顯颼涼。蘭陽平原環山面海,地形如畚箕,入秋後長達半年的東北季風或颱風來襲時,「長枝仔」葉大,枝幹高聳,抗彎性佳,加上竹子都是叢生,密密實實,可抵狂風擋暴雨,護衛房舍兼消暑,為什麼要砍除呢?
連著幾個冷氣團來襲,再度出門已是一個多月後了。走著走著,猛然發覺那一條龍也不見了,深深惋惜中,快步前行,來到這戶人家。遼闊的視野中,徒增幾分荒涼,也想起十幾年前,剛搬來時,住戶少,自來水公司礙於成本考量,未埋管線,我們不考慮抽取地下水,只好向這戶人家商量接水管,水費另付,沒想到農婦很阿莎力就答應了,只說,都是鄰居,互相幫忙應該的,幾年後,雖自來水公司來埋水管,我們各自分支,但這分情,我永遠銘感於內。
農路小徑可以快走慢跑,經過這戶人家時,若遇矮牆牆面、柏油路面,有粉筆畫人、房子和飛機汽車等圖樣,我常駐足欣賞其樸拙可愛的筆觸、構圖、比例、想像等等。也喜歡往人家埕仔裡瞧,屋簷下晾曬的衣物,開放式鞋櫃那幾款鞋,普通日常,卻模擬出一個家庭成員結構。第二層鞋櫃總是塞了三顆球,有籃球有躲避球,也常見小孩和爸爸傍晚在稻埕上打球,好一幅美麗可愛的農家圖。
矮牆內有幾畦菜圃,夏天,牆外一側棚架下垂著一條條綠盈盈的絲瓜,地面爬著大小南瓜,四時各有作物。牆下太陽花紅豔豔白淨淨的,蔓延在柏油路上,剛搬來時,有一回忍不住停下來欣賞拍照,農婦發現,走過來說,不嫌棄就摘回家種,於是我道謝,採了一大把,她還強調隨時可以來摘。
過去農村處處散落著ㄇ或口字形的「竹圍仔」,由於高聳蓊鬱,包覆屋厝,遠遠望去彷彿一座座綠色「護城牆」,此牆,防風擋雨護衛房舍之外,據老一輩的說,早年更具防盜禦敵之功能。畫家藍蔭鼎筆下的〈竹隙晨光〉〈竹報平安〉〈竹林春色〉等等都呈現了家鄉獨特的竹圍仔景致,他生前遺作〈竹林人家〉,畫的正是他一生最懷念的兒時出生地——羅東阿束社。對照今昔平原地景變遷,昔日畫家筆下的景,可以說是今日的「史」了。
我童年時,常在竹叢下玩泥巴,以竹葉摺公雞和螳螂,學校防空演習時,老師帶我們躲在竹叢下,夏日午後,亦常見農夫蹲坐其下打盹,牛隻在一旁納涼。凡此種種,曾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然隨著經濟發展,居住習慣改變,加上雪隧通車,颳起房地產買賣熱潮,「竹圍仔」一處處消失,稻田長出一戶戶新農舍,這幾年開車行經鄉間,一旦瞧見命運不定的珍稀竹圍仔,總要放慢車速多望幾眼。
他們也要蓋農舍嗎?見面再來恭喜吧。每回經過便如此揣想,不意下午農婦從竹圍夷平處斜前方菜園迎面而來。互道好久不見。要蓋新房嗎?「唉,不是啦,地主把地賣給建商,補貼我們一些,現在在外租屋,實在很不習慣。」又搖頭長嘆,說沒辦法,然後手一指,說建商會在這間厝旁邊的稻田闢出一條路供住戶出入……
「這間厝」就在消失的「竹圍仔」旁,約一千坪,穿越大片稻田,屋前屋後是農路,我沒見過屋主,聽說住台北,假日才過來。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摩天輪時光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摩天輪時光
她說:或許還有一棵樹一朵花,從我記憶的枯井中活過來。
★阿盛、宇文正好評推薦
★林黛嫚專文推薦
黃春美的作品,明確顯現對家鄉宜蘭的熱愛、對親人友朋的真情,樸實的文字透露出誠摯的心意……──阿盛
每一次讀到春美的散文,都像與老朋友促膝聊天,聽她說幽微的心事,日常的風景,恬淡而溫暖,雋永而令人低迴。──宇文正
新世紀的鄉居風貌、逝去的時光在春美筆下重現,栩栩如往日,生氣勃勃。春美擅寫微物,生活細物原只是眼皮子底下經過,由她撿拾起爬梳一番,竟爾如一則寓言,為生活增添色彩……
她對婚姻也有許多心思,那個母親,由於丈夫在發薪日總是喝得醉醺醺,薪水袋內只剩薄薄幾張鈔票,還完米店、菜販、雜貨店的賒賬,沒幾天又開始重新賒欠;那個小妹,遇到渣男,不斷致祭比死亡還沒有希望的婚姻……都是女人在傳統和當代之間的為難。
書中多的是對時間的懇求以及對房間的想望:即便是有夫有子有孫、有經濟能力的女人,心心念念的卻仍然是在自己的房間享受自己的時間。
你想要什麼樣的時間與房間?也許《摩天輪時光》能告訴你。──林黛嫚/專文推薦
作者簡介:
黃春美
宜蘭人。花蓮師院初教系畢業。現已教職退休。文學創作曾獲文建會兒歌徵選、懷恩文學獎、基隆海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獎、蘭陽文學獎、磺溪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著有散文集《一張美麗的拼圖》、《心豆》,童詩集《雲兒翻觔斗》,傳記《藏在時光裡的顏色:陳忠藏藝術之路》,與人合著《來宜蘭旅行》、《宜蘭味》、《時光那端遇見你》、《踢銅罐仔的人》等。作品散見各大報副刊,收錄於《九歌101年散文選》、清華大學中文教學寫作資料庫,轉載於美國宜蘭同鄉會年刊、《中華民國筆會季刊》、《明道文藝》等。
章節試閱
蘭陽雨
我鄉環山面海,地形像畚箕,容易捕風捉雨,尤其秋冬,十日九風雨。這幾年,溫室效應,氣候變遷,反聖嬰現象,東北季風來襲,天空更是破了個大洞,雨一落,日連夜,夜連日,沒完沒了。
雨日,常望向窗外,「苦啊~苦啊~」那是來自屋後灌木叢內白腹秧雞的叫聲。豪雨時,都躲起來了,偶也見單獨者,似徘徊又匆匆,大概是出來找食物填肚子,順便啣回去給家人吃。雨勢稍緩時,通常三五出來覓食,曾見二隻起衝突,互不相讓,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煞是好看。
十幾年前開始鄉居生活,翌年,颱風登陸,拉下新鐵門,一窩鳥巢落地,不意...
我鄉環山面海,地形像畚箕,容易捕風捉雨,尤其秋冬,十日九風雨。這幾年,溫室效應,氣候變遷,反聖嬰現象,東北季風來襲,天空更是破了個大洞,雨一落,日連夜,夜連日,沒完沒了。
雨日,常望向窗外,「苦啊~苦啊~」那是來自屋後灌木叢內白腹秧雞的叫聲。豪雨時,都躲起來了,偶也見單獨者,似徘徊又匆匆,大概是出來找食物填肚子,順便啣回去給家人吃。雨勢稍緩時,通常三五出來覓食,曾見二隻起衝突,互不相讓,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煞是好看。
十幾年前開始鄉居生活,翌年,颱風登陸,拉下新鐵門,一窩鳥巢落地,不意...
顯示全部內容
推薦序
你想要什麼樣的時間與房間?──讀《摩天輪時光》/林黛嫚
都說詩是跳舞,散文是散步;或說詩如電光石火,散文如江流月照;又有鄭愁予說「菜單如詩歌」,余光中應答「帳目如散文」。散文正是文學之母,內容包羅廣闊,有其他文學類別的基本形式,研究散文理論的學者鄭明娳說:「在文學的發展史上,散文是一種極為特殊的文類,居於『文類之母』的地位,原始的詩歌、戲劇、小說,無不是以散行文字敘寫下來的。」也就是說,把小說、詩、戲劇等各具備完整要件的文類剔除之後,剩餘下來的文學作品的總稱,便是散文。這是指散文的文類由來,不是...
都說詩是跳舞,散文是散步;或說詩如電光石火,散文如江流月照;又有鄭愁予說「菜單如詩歌」,余光中應答「帳目如散文」。散文正是文學之母,內容包羅廣闊,有其他文學類別的基本形式,研究散文理論的學者鄭明娳說:「在文學的發展史上,散文是一種極為特殊的文類,居於『文類之母』的地位,原始的詩歌、戲劇、小說,無不是以散行文字敘寫下來的。」也就是說,把小說、詩、戲劇等各具備完整要件的文類剔除之後,剩餘下來的文學作品的總稱,便是散文。這是指散文的文類由來,不是...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林黛嫚──你想要什麼樣的時間與房間?
【推薦語】阿盛、宇文正
輯一:平原事
蘭陽雨
青楓之歌
竹圍人家
餵貓的女人
女生宿舍
一朵蓮花
阿舅的菜園
菜園裡的早餐
爬山
八哥
阿娥
正記
輯二:摩天輪
紙娃娃
摩天輪時光
小妹
行過東螺圳
過年
掃QR CODE
阿莫
煩惱絲
同學會
畫像
二手書
輯三:時間河
幫母親洗澡
等待母親的容
母親的時間,我的時間
重返一九四八
于哥哥
母親與她的兄姐
亨壽
白首話當年
兩個老嫗
本是冤家
輯四:臭皮囊
大疫時期
一家團圓
隔簾裡的病床
柑仔店...
【推薦語】阿盛、宇文正
輯一:平原事
蘭陽雨
青楓之歌
竹圍人家
餵貓的女人
女生宿舍
一朵蓮花
阿舅的菜園
菜園裡的早餐
爬山
八哥
阿娥
正記
輯二:摩天輪
紙娃娃
摩天輪時光
小妹
行過東螺圳
過年
掃QR CODE
阿莫
煩惱絲
同學會
畫像
二手書
輯三:時間河
幫母親洗澡
等待母親的容
母親的時間,我的時間
重返一九四八
于哥哥
母親與她的兄姐
亨壽
白首話當年
兩個老嫗
本是冤家
輯四:臭皮囊
大疫時期
一家團圓
隔簾裡的病床
柑仔店...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