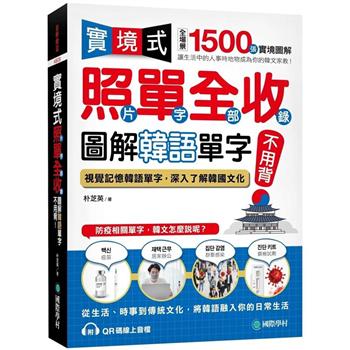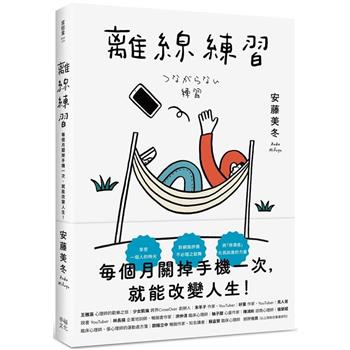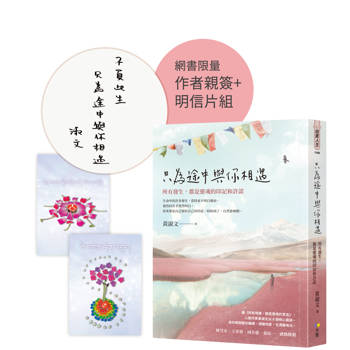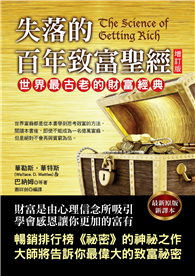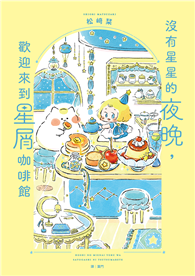風箏升空,只為逃離自己的影子
韓麗珠令人震顫的存在寓言《風箏家族》
絕版多年,再次歸來
在《風箏家族》裡,韓麗珠構築了一個怪異卻熟悉的都市寓言:身體是監牢,也是容器;家庭既是依靠,也是囚禁。本書收錄六篇作品,遊走於現實與寓言、冷酷與詩意之間,共同構築一個被置換、被填補、被窺視的荒謬世界。
〈風箏家族〉於2006年獲得聯合文學中篇小說首獎。文中的母親、姨母、祖母與「我」,一代又一代的女性,在肥瘦變形、空間被侵占、角色被替補的輪迴中尋找自身的位置。肥胖像遺傳病一樣悄然擴散,女性的身體在時光中膨脹成無法容納的形體,直到像氫氣球般接近破裂,或解脫。
〈壞腦袋〉中,一名偷渡客成為被觀看與展示的「家具」;〈林木椅子〉講述一名男子蛻變成椅子的奇幻過程;〈門牙〉裡,女子不斷暴增的牙齒,落入牙醫的收藏中;〈悲傷旅館〉描繪失去家園的女性,購入一位「陪伴者」充填情感空洞;〈感冒誌〉敘述康復者被迫模擬家庭生活,進行角色扮演。在這些故事裡,人物可以被購買、身分可以替代,空缺總有對應物遞補,挑戰我們對家庭、身分與自由的理解。
韓麗珠:「當一本書重新出版,代表著它經歷過自己的死亡,而重新出現在書店裡。它再也不年輕青澀,然而,有到過一些地方,有經過一點難堪的或新奇的事,在它身上又長出了新的故事。」
作者簡介:
韓麗珠
香港當代小說家。2018年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家年獎」得主。
已出版作品:中短篇小說集《人皮刺繡》、《失去洞穴》、《雙城辭典》(與謝曉虹合著)、《風箏家族》、《寧靜的獸》、《輸水管森林》;長篇小說《空臉》、《離心帶》、《縫身》、《灰花》;散文集《半蝕》、《黑日》、《回家》。英譯本:《Mending Bodies》(Jacqueline Leung譯)。
其中,《灰花》獲第三屆紅樓夢獎專家推薦獎。《風箏家族》獲台灣2008年開卷好書獎中文創作獎。《寧靜的獸》獲第八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黑日》獲2021年台北國際書展非小說類首獎。《半蝕》獲2022年梁實秋散文大師獎優選。
章節試閱
風箏家族
電鑽把牆壁鑽破後,鑽動的聲音無處不在。
我總是耗上過長的時間凝視一堵牆,卻無法確知事情起始的年月,只知道大型維修工程開始,尖銳的聲音便鑽進每個生活的細節裡。沒有人宣布工程何時完結,地盤的牌子上寫著竣工日期,但那是久遠以前的日子。最初我們只聽見鑽子空白的聲音,後來聽見牆壁四散的粉末、有垃圾房氣味的樓梯、人手鋪砌的磚塊、商店的天花板,頭部週期性的劇痛。不久後,我聽見一所被清拆的學校、還沒有長大的樹木、獨居老人流血的雙腿、昏迷者爆裂的頭部、流浪貓破損的肚腹和工人的斷手,淹沒了爭吵、電話和呼救的聲音。然而耳朵和鑽子的聲音已融合成一體,眼淚和憤怒像乾涸的水泥,成了一堵堅硬的牆,缺乏運動的人們無法攀越。
我忘記了是什麼時候開始適應這種轉變,要是我能記起,或能改變現狀,而我能適應這種改變,是因為長得太大,而沒有適時地死去。母還沒有對說話產生極端的厭倦前,經常重複地告訴我,那個素未謀面的外祖母臨終時,安慰那些為了履行悲傷的責任,而把身體各部分的肌肉長時間地緊繃的子女,她用快將消失的聲音說︰「轉變是希望的開始。」
我始終無法肯定外祖母說話裡的真確性,即使我從童年開始思索她的說話。正如我無法肯定童年是不是確實在我的生命歷程裡存在過,如果童年就是像大部分人所描述的那樣子。
在殘缺不全的回憶裡,我,和許多跟我同齡的人,年紀幼小,在一個不屬於我們的世界裡,拙劣地掙扎、模仿,互相較量,企圖盡快學會這世界的生存法則,避免成為被排拒在外的人。所謂的童年,就是這樣子。
關於那段幼小的時期,我只能想到氫氣球。看著即將爆破的氫氣球從人們手中脫開,慢慢向上空飄升,遠離這世界,逐漸消失在大廈的背面,是少數能跟快樂靠近的時刻,雖然內裡也藏著更大的、轉瞬即逝的哀傷。
當母站在充滿打樁聲音的街道上,告訴我外祖母躺在地上的情況,我不知道該如何跟她要一枚氫氣球。
那是清晨至中午前的一段怠倦時刻,大部分的人都躲在封閉的大廈裡學習或工作。在臨時搭建的酒樓、不斷翻新的建築物和興建中的小型遊樂場之間,手裡纏滿氫氣球的老男人在冷清的街道上如幽靈般重複地徘徊。在身軀暴脹的外祖母和繽紛的氫氣球之間,為了使要求來得合理,我看著母說︰「她肥胖的身軀,像七彩的氣球,飄到空中爆破。」我以為那是合理的說法,但事情比我能想到的更快。在我的呼吸轉換前發生,像世界突然崩壞,或電源被關掉。那天,我學會了「掌摑」的意思。我一直走在我母身後,看著她的高跟鞋踏在凹凸不平的地面。後來,外祖母和氫氣球在我的腦袋內變得不可分割,即使那時候,我已到了無法對氫氣球產生興趣的年紀。
但母從不以氫氣球比擬外祖母,他們寧願說她像一堆過期果醬,不斷向外傾瀉,核心來源不明。他們合力把她從醫院的床上抬起來,放進召來的貨車上,運送回家,然後把她關在其中一個空房間裡。當家族遺傳的脂肪,在令人猝不及防的情況下,在外祖母的身體內迅速積聚,生機勃勃地不斷壯大,外祖母只能癱軟在某個空房間的地板上,即使她的嘴角始終帶著某種深諳奧祕的笑意。
沒有任何專家能對過量脂肪的形成提出合理解釋(或許他們其實並不感到興趣)。母曾經告訴我,在那個狹小的房間裡,外祖母體內的脂肪惡作劇般不斷膨脹,醫生、護士和外祖母的親人也無法擠進那房間,只能遠遠地探視她。外祖母一直以不由自主的眼神看著自己的身體,但神態卻從不曾那樣的自若過。
母總是以各種理由禁止我跟他們一同探望外祖母,她最常做的事情是伸展她瘦弱的肢體,從中找出脂肪較多的部分,例如枯枝般的大腿,她會按著腿部的肌肉說︰「不行。我們不能碰到她的身體。無論任何部分,一旦觸碰了,她會痛苦得馬上掉淚。」外祖母去世前的一段日子,身軀龐大得無法容納在一個房間內,他們不得不找來裝修工人,拆掉兩個房間中央的牆壁,外祖母才能順利地躺下來。或許我渴望看見外祖母的原因,只是她的體態使我想念家具店中無法找到的巨型沙發。
母能阻止我去看外祖母的臉,但無法禁制我聽她的聲音。那個星期三的下午,母外出後,外祖母打電話來找她,我說,她離開了。外祖母便喚我的名字,問我,是不是她的女兒。我說是的,她便告訴我,她是她的母親。我們透過那落了空的電話聽到對方的聲音,她說,她快要死了,卻沒有任何難過的感覺。「像我這樣的一個人,到了這把年紀,還有,這樣的胖,末了,就會像氫氣球向上飄升。他們沒有一個人相信這種事,但你,最好要相信。」
母並不像外祖母。外祖母成長於糧食不足的時代。母常常說起外祖母,似乎在她的國度裡,每件物件都帶著外祖母的影子或氣味。雖然這並不表示,她善待外祖母。
母看見細長的筷子、對面大廈單位的晾衣竹,或瀕死的野狗,都會說起外祖母。「在那個時代,飢餓使他們無法發現或感受自己的重量,一年之中的任何一個季節,他們都瘦削輕盈得像一根線。下午的風刮起時,他們不得不慌忙地抓著一根燈柱或陌生者的手臂,以免被颶風吹到半空中。當然有許多人死於營養不良或嚴寒的天氣,但因身子太輕而被颶風吹到半空中摔死的人也為數不少。」
只是外祖母在世上活了太久,她的孫兒出生時,人們喜歡把吃剩的食物扔到堆填區去,而外祖母像她的外祖母,或她外祖母的外祖母,脂肪暴發的因子,像嫩芽在她體內日漸茁壯,直至淹沒了她。以致她的親人每次把視線投向她,都在談論著要取出定期存款的多少部分給她訂製一副更大的棺木。
但我母都不像她們。從小,我便看見她的身軀和四肢有時纖幼脆弱得像冬天枯乾的禿樹,有時卻原因不明地膨脹,渾圓結實得像皮球。她為了使身體符合想像中的形態,胡亂地吃下過多藥物,但不見得有多大幫助。
我仍然常常想起那段日子,母的體重久久不降,她的眼神便變得陰晴不定,晚餐的白飯裡經常摻雜著黑黝黝而粗硬的頭髮,她呼出的空氣都帶著酸味,似乎只有我知道母的體味並非來自冰箱內腐壞的食物,而是體內遺傳自祖先們的脂肪。幸好我們都能心照不宣地裝作沒知沒覺,不然把我們緊緊地維繫在一起的家庭活動─不同的軀體圍攏在過小的圓桌吃飯、對脫離現實的新聞報導交換意見、輪流使用洗手間─必然無法順利進行。
我忘了在什麼時候,她的體重突然急速下降,而重新獲得枯樹一般的身子,我們的生活才回到日常軌道。
我不知道自己像外祖母還是我母,如果根據某種宿命的定理,我必會像她們之中的任何一人的話。曾經我認為她們對我來說不過是窗外慣見而陌生的風景,我會隨著年齡漸長而逐步遠離她們,正如我以為軀體不過是某種活動時使用的工具─我曾經耗了一段長長的時間學習素描,有許多年反反覆覆地描繪不同姿態的人像,他們或穿上衣服,或不,而我只著意繪畫他們的頭部,不得不繪畫他們的身體時,我以合乎比例的火柴或竹枝代表。(心理學家說,這是人格發展不完全的象徵。)
即使手和腳曾經筆直而脆弱像一根火柴,始終有一天,還是會以令人無法察覺的速度膨脹,像飽滿的氫氣球,無論如何堅執地肯定那不過是一陣子的事情,遺傳性的脂肪再也不會離開它習慣寄居的身體。
只有醫生對於突發性的肥胖不以為然。「每個人都有脂肪暴發的可能。」他把身子向後靠在真皮椅子上,懶洋洋地說。他戴著白色的口罩,我無法看清他的臉。診療室外等待應診的人,有的雙眼通紅、有的斷了一條腿、有的額上捆著紗布、有的躺在沙發上、有的手上拿著一個連接著身體的水袋……在那個蒼白而充滿刺鼻氣味的空間裡,不合常理的肥胖才是理所當然。寄望醫生的幫助,是不切實際的想法。醫務所門外是一條繁忙的馬路,工人用推土機修築道路。車子不斷往來,我想起醫生的話︰「要是你生於病態肥胖的家族,即使你曾經消瘦得像厭食症患者,你早晚還是會變得跟你家族中的人一模一樣。」
那天開始,我無法在鏡子中辨認自己。
類似的事情,是曾經發生過的,還是將要發生,我漸漸不能確定。
或許我應該在更早以前適應轉變的速度。當我的年紀仍然幼小時,我,和許多跟我年齡相若的人,都在扮演孩童的角色,縱使我們並非全然無知。後來我才發現,每個人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都在做著類似的事情。我不能說,這些角色使我們的日子過得更困難,因為某些情況下,它在賦予著某種方便,例如抵抗周遭惡劣的環境。
維修和擴建的工程似乎從我出生開始一直在進行。我曾經問我母,那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事情,她總是茫然地搖著頭說不知道,這裡的人要不是吸入過多灰塵使記憶力衰退,就是對周遭環境失去知覺,才能在某些情況下顯得逆來順受。例如不分晝夜的鑽牆聲、洗澡時浴室天花板被鑽破、清晨時分,維修工人從窗子爬進來,表示要把水管重新接駁,甚至在晚飯後正在聚精會神地看電視的時刻,突然被告知正在居住的樓房是一幢僭建物。
我們在早上離家出門,晚上回到家裡,那已是不一樣的房子,我們總會發現牆壁破損,油漆剝落、或電線鋪設的位置改變、或煤氣喉管的位置改變、或地上有別人的鞋印,然而日子久了,我們漸漸不以為然。那空間只是睡覺和作息的地方,並不屬於我們。而我的煩惱卻是找不到隱藏的地點,只有角色可以讓我躲起來。
我在繪畫一個才認識了不久的人。
老師走過來看著畫中的人很久,他問我︰「他的身體在哪裡?」
我搖了搖頭說︰「他的身體剛剛消失了。」
那個扮演老師的人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
我只好告訴他,眼睛、頭殼、鼻子和頭髮都比身體更重要。
一群年紀相仿的人,被編派到某一個地方,需要共同學習的,不僅是在這世界生存的各種知識,更祕而不宣的,是關於失去身體這一回事。
那時候,我認為我母的身體、姨母的身體、外祖母的身體,都是與生俱來的,而且自出生以後從沒有改變。可是對於自己將會不斷長高、四肢變得更長的事,也抱著毫不懷疑的態度,似乎每個人都擁有完整的軀體,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從不知道身體和房子的某種共通之處。
直至坐在我右方的高個子浮土失去了一條腿,艱難地推著輪椅上龐大的車輪進入課室。
沒有太多人對於他失去了一條腿感到驚訝,或許他們刻意在浮土面前裝作若無其事,但更大的可能,是他們對於意外早已習以為常,只要那並不是降臨在自己身上。以往浮土總是弓著背部走路以掩飾他的身高,但坐在輪椅上時他像是變了另一個人,臉上總是掛著同一副神情,就像野雞被豺狼銜在嘴巴內的那樣。為了洞悉他如何失去那條瘦長而流麗的腿,我常常跟他在一起。或我只是被那還沒有癒合的創口引誘著而靠近他。似乎只要跟他在一起,腥濕的氣味便持久不散,而那滋養了我的鼻子。我喜歡在午飯時間給他購買食物,而在休息時間,推著他的輪椅在走道上觀看球賽。即使他常常把我們的關係比喻為那對合力逃出火場的跛子和瞎子,我也默默地忍受著。
直至他缺乏血色的臉部重現笑容,終於告訴我︰「那是遊戲的結果。」
他和白白的遊戲地點在堆滿雜物的儲物室。為了體驗人們所說的變幻的人生,他們的協議是,輪流閉上眼睛,由一數到十,各自運用想像力,使對方把眼睛睜開時,世界變得再也不一樣。
浮土先把眼睛閉上。
他從不知白白在什麼時候,手上拿了一把發亮的鋸子。或許他也不會想到,身體還沒有隨著鋸子抖動,腿部已經離開了他的身體。當他張開眼睛,找了很久,也找不到那條被白白鋸下的腿,他始終不知道他把他的腿藏在哪裡。有一段很長的時間,他仍然能感到那條失去了的腿異常痕癢,使他晚上無法真正入睡。
我想對他說,遊戲已結束。但什麼也沒有說出來。白白的父親看過浮土的截肢後,就像看見一件不合意的家庭用品,木著臉說︰「這只是孩子們之間的遊戲。他們只是孩子。」
當我願意回想浮土以及他的腿時,我已在扮演成人的角色,也忘記了自己是否曾經參與那些林林總總的遊戲,興起要把別人的耳朵、手腳或乳房砍下來的念頭,或許我的四肢和頭部也差點被人砍下來,然而我已完全忘記。
我扮演著成人的角色時,才願意相信白白父親的說法。那只是孩子的遊戲。
我母深信,在發育尚未完成的孩童面前提及親人的死亡,會增加孩童夭折的機會,但她始終無法按捺把事情傾吐的慾望。我知道外祖母被埋在深深的泥土下,但從不肯定確切的日期。我母說,外祖母的外祖母,還有她外祖母的外祖母,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身體都迅速地脹大和變胖,因此外祖母該不會感到過分訝異,只是她的身體慢慢地蛻變成那些曾令她懼怕的軀體而已。母說,那是死亡來臨前的徵兆,而那也將會是我們的必經階段。我只是想,所有不曾親眼目睹自己出生過程的人,對於自己曾經是母體內的胚胎,只能相信,或不,而不能完全隔絕於這個系統以外。
但肥胖不是直接致死的原因。
風箏家族
電鑽把牆壁鑽破後,鑽動的聲音無處不在。
我總是耗上過長的時間凝視一堵牆,卻無法確知事情起始的年月,只知道大型維修工程開始,尖銳的聲音便鑽進每個生活的細節裡。沒有人宣布工程何時完結,地盤的牌子上寫著竣工日期,但那是久遠以前的日子。最初我們只聽見鑽子空白的聲音,後來聽見牆壁四散的粉末、有垃圾房氣味的樓梯、人手鋪砌的磚塊、商店的天花板,頭部週期性的劇痛。不久後,我聽見一所被清拆的學校、還沒有長大的樹木、獨居老人流血的雙腿、昏迷者爆裂的頭部、流浪貓破損的肚腹和工人的斷手,淹沒了爭吵、電話和呼...
目錄
壞腦袋
風箏家族
林木椅子
門牙
悲傷旅館
感冒誌
【後記】書的命途
壞腦袋
風箏家族
林木椅子
門牙
悲傷旅館
感冒誌
【後記】書的命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