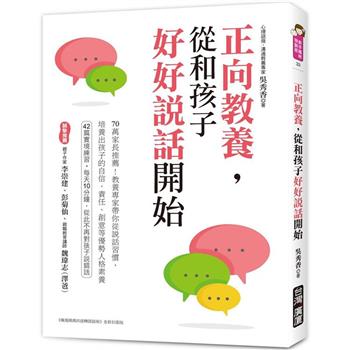氣個什麼勁兒?--阿岩不悅地瞪著佛壇。
--死人還能有什麼搞頭?
活著都無法為所欲為、心想事成了。
你們這些死人又哪能--
阿岩原本就是個死人的名字。大約在幾代以前,民谷家曾有一位叫阿岩的姑娘。
聽說她被譽為貞女之鑑。據聞,她曾挽救民谷家於頹勢,有再興之功。
也不曉得那是多久前的往事了。當時米價暴跌,武士俸祿因而銳減,民谷家也不例外,簡直到了貧困潦倒,被迫考慮賣掉同心的官職換取銀兩的境地。但阿岩挺身而出,救了民谷家。
為了減輕家計負擔,阿岩放棄民谷之姓,住進某旗本武士家中幫傭,廢寢忘食地辛勤工作,攢錢拿回去支持家用,終於幫助父親渡過難關,之後被迎接回家,終其一生--這就是阿岩的故事。
阿岩的感人事蹟被喻為「內助之功,莫過於此」。而她所虔誠信奉的,就是庭院裡的稻荷明神。
阿岩小時候,母親與祖母都曾驕傲地訴說此事,但阿岩聽了卻滿腹狐疑。「犧牲自己、成就他人」真有那麼可貴嗎?若是實在無計可施、無路可退,才將英雄逼上梁山倒也罷了--但在阿岩看來,可行之計所在多有。當時陷入困境的,總不可能只有民谷家,何況民谷老爺並非沒有主公的浪人,領有官邸的同心,不可能唯有一家沒落。既然如此,為何只有民谷家窮迫至此?
答案很簡單,就是民谷家完全不兼差。江戶幕府實行所謂的「三日值班制」。由於人員浮濫,一人便可完成的工作,編制上卻用了二、三人。兩人還嫌多的事卻聘用三人,勢必每三天會多出一天假。但原本每年四十五俵的薪餉,也減少到三十俵。依此情況,若是休假那一天不兼職,勢必要餓肚子。若是町奉行或普請奉行(註11)手下,好歹還有許多受賄機會,但民谷家不過是城門守衛,沒啥肥水可撈。除非不顧顏面、想盡法子鑽營,否則民谷這類下級武士便只有兩袖清風的分了。
只不過,表面上幕府也的確要求武士--儘管一窮二白,決不可從事兼差此種卑下行為。不當差的日子,就應磨練武藝與學問--但即使如此,傻傻地恪遵此一原則的蠢蛋,阿岩認為在江戶打著燈籠也找不著一個。凡武士,必兼差以糊口。
然而,只有民谷家與眾不同。阿岩的父親依然堅守此等原則,不管再如何窮苦,決不兼差,愚魯正直地過活。
這麼做,對是對了,卻不切實際。同時,成了阿岩名字由來的那位祖先,在讚揚她的偉大之前,更應了解她其實是家族的犧牲品。至少阿岩如此認為。的確,那位阿岩是個罕見的女傑,但這並不能改變--她是個傻子的事實。
突然感覺,佛壇的門像是打開了。
是我多心嗎?
有可能。即便是靜止的東西,只要盯著它直看,便會產生蠢動的感覺。
那是疑心生暗鬼。是錯覺。
--真是莫名其妙。
一出生就被冠上阿岩這個名字,這點讓她很不服氣。不管從前那個阿岩有多偉大,但人生在世,為何必須借用故人之名?難道父親希望自己向死人看齊?若是如此--阿岩的人格何存?
阿岩將視線由佛壇上移開,搖了搖頭。
真想敲毀那座佛壇。她不想跟死人有任何牽扯。因此,她偏是不招婿。
--這算什麼。算什麼算什麼--
阿岩再度伸手戳破紙門。她很懊惱,為何世間無人了解她的念頭?甚至連唯一的親人,都不了解她?倘若阿岩真的錯了,何不把理由說個明白,講到她心服口服--
阿岩站起來,粗魯地將紙門悉盡開放。
千萬別把紙門全部敞開哪--父親如此要求阿岩,言外之意,似是在說:畢竟大病初癒,別沾染了外頭的穢氣。因此這整整兩年來她乖乖地聽從。但如今回想起來,阿岩只覺這是父親害怕旁人恥笑的權宜之詞。怕是有人從牆外窺見了民谷家裡。
他鐵定是不願聽到左鄰右舍指指點點,說民谷家有個怪物,有個長相奇醜的女兒吧。
--不要欺人太甚了!
阿岩直想大吼,但忍了下來。
阿岩大口大口地吸氣。不過由於彎腰駝背,深呼吸並不容易。
中途,她突然嗆著了。風吹在臉上,潰爛的額頭隱隱作痛。阿岩雙眼含淚。當然,這不是悲傷之淚。阿岩的左眼一直混濁不清,遇上一點刺激便會掉淚。說不出的煩悶。
阿岩伸手用力拔下額頭上粗糙而蜷曲的髮絲,握在手掌內擲向庭院。
手一放,才發覺--方才的動作想必十分滑稽。
儘管並非刻意,自虐的行徑對阿岩反倒輕鬆。
瞬間,阿岩察覺到人的目光。她突然抬頭。
--有人。有人正在偷看。
神社陰影處,有人從樹籬縫隙凝神注視著。
「誰--是誰?」
是個男人。頭上包著行者頭巾,好像是個僧人。
「真…真無禮!這兒可是民谷又左衛門公館--」
鈴。
男子搖動手中之鈴。
「請問您是民谷家千金--阿岩姑娘嗎?」
男子聲音沉著穩重。聞言,阿岩端正姿勢坐好。
「是,阿岩就是我。你又是誰?」
「看我這身打扮就知道了,我是個御行乞丐。至於姓名,無名小卒不值得一提。」
男子不僅沒有笑容,臉頰更無一絲波動。
「既是無名小卒,找我何事?我看你也是聽到一些無聊之輩的傳言,想來見識一下民谷家的妖怪吧?喏,我就是傳說中的妖怪,要看就看、要笑就笑吧!」
阿岩挺直彎曲的腰桿,正面朝向男子。按照過去的經驗,只要阿岩這樣做,對方都會--
男子正面回望阿岩。
「沒--沒禮貌的傢伙!」
阿岩怒目瞪視。
男子不為所動,只說--今天確實冒昧。
「不過,我既未登堂入室,料想不須拘禮。」
「你這--無賴!」
阿岩擺起架勢。護身之術,她好歹略懂一二。
「欸,先別動手。」
男子揮手阻止阿岩,然後迅速往後一躍,躲進稻荷神社後的陰暗處,不見了蹤影。
阿岩知道,男子想必委身於陰影後。
--然後在那裡嘲笑我吧?
氣息尚在。卻沒有聽到笑聲。
「何必藏頭藏尾?想笑--就笑啊!」
對著稻荷明神的方向--阿岩詛咒似地說道。
「喂,你笑吧!大聲恥笑我吧!」
「我沒有要--」
聞聲不見人。
「嘲笑姑娘的意思。」
「那你是--瞧不起我?」
阿岩怒罵。你就儘管嘲弄我吧,鄙視我吧--
「我只是個卑賤的乞丐,怎敢看不起高貴的武士之女?」
「什麼--」
神社牆角露出男子半張臉。阿岩感受到些微的壓力。男子左眼的視線滴溜溜地在阿岩身上繞,由臉蛋到身形,打量著全身上下每一寸--
--你夠了。
「那,你為何用那種眼神看我?你是不是覺得--我這樣很難看、很可憐?」
「可憐--這個詞兒最不適用。」
男子現出全身。阿岩轉過頭去。
「若是姑娘希望我可憐妳,我倒也可以照辦--」
「我不懂你的胡言亂語。」
「在我看來,妳堅強有骨氣,不需要他人憐憫同情--」
「知道就好--那還不快滾出去!同情對我而言,跟愚弄沒有兩樣。」
阿岩說道,但男子紋風不動。阿岩全身繃緊。
男子上上下下打量著阿岩,接著像是看穿底細似地點點頭。
「不簡單,真是無懈可擊。」
--這是什麼話?你到底想說什麼?
「不僅如此--正如傳言所說,是個美姑娘。」
這句話,讓阿岩怒得扯斷了原本綑縛自己的視線之繩,她以惡鬼般的神情瞪著男子。
在她發聲之前--
鈴。
男子再度搖動手中的鈴鐺。
意外的,男子竟露出微笑。
「你--」
「我剛剛所說,決非虛言。」
男子以令人不寒而慄的低沉嗓音說道--姑娘人美,故稱美人,我是據實以告。
阿岩聞言火冒三丈,跺腳大罵。
「你--你作弄人也有個限度!我這張臉都爛成這模樣了,何美之有?你再給我胡言亂語,我當場就用這雙手把你--」
「姑娘所言差矣。即便顏面幾乎潰爛,仍難掩天生的美麗。不僅如此,姑娘更有一顆純潔的心靈,無垢至此,令人疼惜。說姑娘人美,其因在此。」
--他為何毫不動搖?
阿岩亂了方寸。
--這傢伙--到底是何等人物?
阿岩背脊一陣寒意。
夕陽餘暉照耀著稻荷神社,紅色鳥居更為醒目。
阿岩感覺那紅色光芒朦朧閃爍。是她落淚的緣故。
過了一會兒,阿岩好不容易才開口。
「你別開玩笑--」
言盡於此。
「並非玩笑。」
--男子立刻接著回答。
「那你是在--安慰我?」
「三兩句安慰的話豈能打動姑娘?」
「夠了!我說一言你便頂一句,真是油嘴滑舌!若真如你所言,為何人人對我另眼相看?為何人人嘲笑我不知羞恥?因為我醜,故引人側目;世人是在嘲笑我這張猙獰面孔。我家好歹也有鏡子,我也能分辨美醜!」
男子露出悲憫神色,凝視阿岩。至於這時的阿岩怒意已極,果真如惡鬼般猙獰。男子說道--容我失禮。
「若是府上有鏡子--好歹請個髮髻師為妳梳理吧。」
「這--這頭髮蜷曲至此,梳髻又能如何?」
「妳這話就不老實了,阿岩姑娘。在頭髮蜷曲之前,妳便疏於打理了……不,妳原本對外貌根本就毫不關心,不是嗎?」
阿岩啞口無言。他說得對,確實是如此。
阿岩固然討厭骯髒,對打扮卻毫不感興趣。
結髮一事也是如此。她向來認為自己結髮乃是基本教養,因此阿岩既不願買昂貴髮油,也不曾請人挽髻。但即使如此,也沒有不便之處。阿岩認為自己無須媚俗,此乃理所當然。就連好面子的父親又左衛門也不曾因此責怪阿岩。男人話聲又起,彷彿已看穿阿岩內心--
「那是因為,姑娘從前即使不打扮也美若天仙。」
阿岩倏地抬起頭來,用視線探尋男子所在。
「阿岩姑娘--我看妳,是不打算招婿吧。」
--這傢伙為何哪壺不開提哪壺?
還是看不到男子蹤影,阿岩慌了手腳。
「何--何出此言?」
我一看就明瞭了--聲音從稻荷神社後方傳來。
「姑娘的心地純真透明,旁人看得一清二楚。容我直言,若妳現今人人稱醜,原因無他,乃是妳不曾精心打扮。妳臉上的傷痕雖然嚴重,但坦白講,任何疤痕都可遮掩。經過一番抹白塗紅,自然得以粉飾。姑娘生來是美人胚子,眼裡有白點更顯可愛,瘡疤更賽酒窩。那彎曲的腰部,只要找來按摩師細細推拿,只需半個月便可拉直。然後再梳頂油亮的頭,戴上頭巾就成了。如此易事姑娘卻不願做,還不是因為不喜歡矯飾外貌,我說的沒錯吧?」
男子再度現身,手搭掛在樹籬上。
阿岩沒有回答,側頭留意佛堂。
感覺佛堂裡頭不平靜。佛壇紙門反射夕陽,泛起些許朦朧紅光。
阿岩心想,這種念頭不僅自己,凡是武士之女應皆作此想。與其花枝招展,不如琢磨品性,更顯高貴--阿岩受的是這樣的教育,也始終認為--此乃合情合理。
回眸看,男子臉部陰影更濃了。太陽即將西沉。男子說道:
「妳從前即使不打扮也很美,倒是不打緊。不過現在可不同,非打扮不可。」
阿岩心生不悅--打扮!那是愚婦所為。
又不是總把脖子塗得白森森的妓女,身為武士女兒,搽脂抹粉的成何體統?更何況也沒錢買胭脂水粉。貧窮同心的女兒,講究行頭不過是種浪費。阿岩長這麼大不曾訂製和服,連梳子與髮簪都不曾用過。男子--繼續說道:
「阿岩姑娘,聽我一言。街頭巷尾的無恥之徒笑妳,並非因為妳面上的疤痕醜惡,而是因為妳原可遮蔽卻不遮,脂粉不施卻不覺羞恥,這份強韌讓大家心生畏懼。因為他們怕妳,於是嘲笑妳。」
--因為害怕,
--所以嘲笑。
--阿岩以指尖碰觸額頭。用力一按,膿水滲流出來。
「因為害怕--所以嘲笑是什麼意思?」
「不是嗎?除了嘲笑之外,他們還能如何?妳遭受此等變故,都能不當作一回事兒。那些嘲笑妳的傢伙,若是易地而處,只怕無法在世間茍活。他們淨是些膽小如鼠、沒志氣的猥瑣小人。」
「我--才不想討好那些傢伙。」
鈴,男子搖響手中鈴鐺。
「阿岩姑娘,妳真的很了不起。夠堅強。妳沒有做錯什麼。不過雖沒犯錯,卻也沒做對。妳生性強悍,因此不了解別人的痛苦。妳不覺得痛苦,別人卻為妳喊疼。誠如妳所說,同情形同蔑視,憐憫與看好戲無異。可是啊,這世上總有些人渣就是需要旁人一點關心。正因為是人渣,總是汲汲營營,受輕蔑也無所謂,總強過視若無睹--有這種想法的人可多了。」
「你--到底--」
「不管同情抑或怨恨,全憑受領的一方如何體會。願意受人同情者,即便別人實際上是看不起,也不會認為有失顏面。世事人情便是如此,人人莫不順應此道而活。阿岩姑娘,心意這種玩意兒,是不能強求對方心領神會的。端看接受者存的是什麼念頭。所以,今兒個聽了我這番話,妳是喜是怒--那就悉聽尊便了。」
「悉聽--尊便。」
匡啷匡啷,佛壇的木魚槌滾動著。
胡說八道!莫名其妙!故意作弄我!簡直欺人太甚!下賤的死老百姓,別跟我耍小聰明。夠了,住嘴住嘴!難道--難道錯在本姑娘?
「即便妳能打破這些個禮俗常規,結果也只是讓自己孤立無援。妳再怎麼堅強,一輩子孤軍奮戰也終有敗亡的一天--也罷,是我多事了。」
匡鐺。木魚槌掉落榻榻米上。
吵死了。你們這些死人別涉足塵世--
「阿岩姑娘,聽我一句忠告,令尊或許是迂闊了點,但妳好歹也是他心上一塊肉。希望妳能了解令尊一番用心良苦。」
「什麼--用心良苦?」
男子以欠缺抑揚頓挫的嗓音,做了結論道:
「只要妳有心體恤令尊,我就幫妳找個夫婿吧。」
日暮昏暗,男子的臉孔漸漸融入黑夜。
「試著打扮看看。打扮過後--若真是無法忍受--再回絕親事便是。」
當她回過神來,男子早已不見蹤影。
庭院與佛堂已完全漆黑。
阿岩靜靜地關上紙門。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嗤笑伊右衛門(新版)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嗤笑伊右衛門(新版) 作者:京極夏彥 出版社: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6-0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6 |
二手中文書 |
$ 253 |
科幻/奇幻小說 |
$ 272 |
小說/文學 |
$ 288 |
日本文學 |
$ 288 |
日本推理/犯罪小說 |
$ 288 |
中文書 |
$ 288 |
推理小說 |
$ 28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嗤笑伊右衛門(新版)
★第25屆泉鏡花文學賞受賞作、第118回直木賞候補作。
★日本怪談推理大師.京極夏彥巧手改編,化日本著名怪談『四谷怪談』為悽惻動人的愛情篇章。
★《巷說百物語》御行又市再度登場,此次將帶來何種令人動容的故事?
阿岩-一位因生瘡而慘遭毀容,但仍堅毅過活的女子。在同情女兒遭遇的同時,又為家門斷後憂慮不已的父親民谷右左衛門。入贅民谷家,從沒露過笑臉的嚴肅浪人伊右衛門──
吞噬這三個人物的怨念與接踵而來的陰慘事件,在活躍於《巷說百物語》的御行又市串場處逐一真相大白。
黑暗從愛與恨、美與醜、現實與瘋狂、現世與彼岸的夾縫間不斷滲出的江戶時代,阿岩與伊右衛門的『四谷怪談』在作者筆下借屍還魂,幻化成又一個詭異淒美的故事。
作者簡介:
京極夏彥
小說家.創意家,一九六三年生於北海道。一九九四年以琢磨多年的妖怪小說《姑獲鳥之夏》晉身文壇,備受各界矚目。之後以《魍魎之匣》獲第四十九屆日本推理作家協會賞、《嗤笑伊右衛門》獲第二十五屆泉鏡花文學賞、《偷窺狂小平次》獲第十六屆山本周五郎賞,更以《後巷說百物語》奪得了第130回直木賞。除了獨樹一格的文學創作之外,還以與其他作家對談、聯合創作、民俗研究等其他形式活躍於文壇。
京極夏彥官方網站
★「大極宮」:www.osawa-office.co.jp/
★「お化け大學校」:www.obakedai.jp/blog/
譯者簡介:
蕭志強
東吳日研所、法光佛研所畢。曾任報社記者、主編、電台節目主持人。日文譯著九十餘冊。
校潤:林哲逸
現為專職譯者,愛好閱讀與妖怪,譯有《姑獲鳥之夏》、《魍魎之匣》、漫畫版《狂骨之夢》等,以及多部輕小說。
章節試閱
氣個什麼勁兒?--阿岩不悅地瞪著佛壇。
--死人還能有什麼搞頭?
活著都無法為所欲為、心想事成了。
你們這些死人又哪能--
阿岩原本就是個死人的名字。大約在幾代以前,民谷家曾有一位叫阿岩的姑娘。
聽說她被譽為貞女之鑑。據聞,她曾挽救民谷家於頹勢,有再興之功。
也不曉得那是多久前的往事了。當時米價暴跌,武士俸祿因而銳減,民谷家也不例外,簡直到了貧困潦倒,被迫考慮賣掉同心的官職換取銀兩的境地。但阿岩挺身而出,救了民谷家。
為了減輕家計負擔,阿岩放棄民谷之姓,住進某旗本武士家中幫傭,廢寢忘食地辛勤工作...
--死人還能有什麼搞頭?
活著都無法為所欲為、心想事成了。
你們這些死人又哪能--
阿岩原本就是個死人的名字。大約在幾代以前,民谷家曾有一位叫阿岩的姑娘。
聽說她被譽為貞女之鑑。據聞,她曾挽救民谷家於頹勢,有再興之功。
也不曉得那是多久前的往事了。當時米價暴跌,武士俸祿因而銳減,民谷家也不例外,簡直到了貧困潦倒,被迫考慮賣掉同心的官職換取銀兩的境地。但阿岩挺身而出,救了民谷家。
為了減輕家計負擔,阿岩放棄民谷之姓,住進某旗本武士家中幫傭,廢寢忘食地辛勤工作...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京極夏彥
- 出版社: 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6-05 ISBN/ISSN:978986325353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推理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