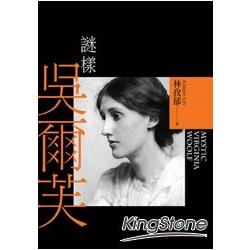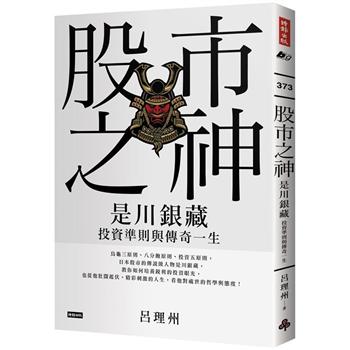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謎樣吳爾芙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140 |
作家傳記 |
$ 158 |
中文書 |
$ 176 |
世界文學人物傳記 |
$ 180 |
作家傳記 |
$ 180 |
社會人文 |
$ 180 |
世界文學論集 |
電子書 |
$ 200 |
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謎樣吳爾芙
維吉妮亞‧吳爾芙,她的人生與她的作品,為什麼是謎樣的?
生長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末期的倫敦,吳爾芙有著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壇巨星父親。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她的一生當中,吳爾芙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一天正規的學校教育。她父親萊斯利‧史帝芬在家中的圖書室,便是吳爾芙智識的最佳來源。熱愛閱讀,又極富想像力的她,在孩提時代便擅長於觀察週遭的環境。整座倫敦城,不單只是吳爾芙寫作靈感的來源,更進一步的,在文學以及繪畫、電影和攝影創作之中,重生了新的風貌,也將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過渡到了現代主義的浪潮之中。
作者在本書之中,除探討吳爾芙的人生,與她的寫作,以及與視覺藝術的關係外,更進一步以吳爾芙式的思考方式來探討東方哲人孔子的學說,將東西方對於人文思考的概念作一整合,藉著差異之中來觀照人文的省思。
作者簡介
林孜郁
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英文暨比較文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有:文學及藝術評論。現為助理教授,任教於土耳其加濟安泰普大學西方語言學系(the Department of Wester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Gaziantep)。同時也是倫敦文學協會的國際代表(www.literarylondon.org),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ISSN:1303-0094)的編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