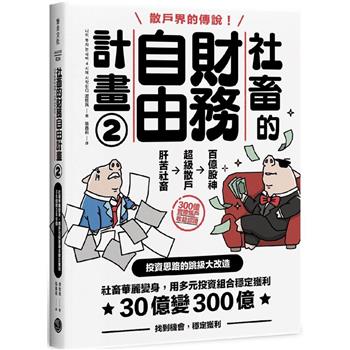【那個死於勞動教養的上訪老農——祭河南宜陽縣農民趙文才】
1
「廣受爭議的勞教所死訊頻傳,名目多樣,有「洗臉死」、「睡覺死」、「沖涼水死」、「激動死」……
勞教制度在法理上缺乏基礎,在實體和程序上都存在重大瑕疵,在接二連三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衝擊下顯得搖搖欲墜。」
上述這兩段文字,出自《世界博覽‧半月刊》雜誌(二○一○年第十一期)的一篇報導,標題為:〈屢屢死亡與勞教所異化:「勞教制度」困局求解〉。從標題可以看得出來,該文是在近年來勞教所頻頻傳出非正常死亡事件的社會背景之下,探討如何革除勞教制度的弊端的。
作為一名曾經的法律人,我曾對「良法與惡法」問題有著相當的學術興趣,對現實中的一些「惡法」深惡痛絕,譬如收容遣送制度、城管制度、戶籍制度等等,我還記得自己在多篇學術論文中引述過「惡法非法」的學術觀點。也因此,勞動教養制度(簡稱勞教),作為當代中國「惡法」領域持續時間最長、侵犯人權程度最為嚴重的一項制度,更準確地說,一大弊政,自然是我所極為關注的。
這些年來,我陸續了解到許許多多的無辜公民被關進勞教所裏受盡折磨的案例,其荒謬、野蠻、醜惡和無良,曾令我憎惡,也令我驚顫莫名。
二○一○年的夏天,我在「中國新聞媒體觀察網」的「法治中國」欄目上,又讀到了一則有關勞教所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報導,這是一位河南的殘疾農民在勞教所冤死的案例。這篇報導的標題是:「八年前,宜陽縣農民趙文才耕牛被盜搶/七年後,上訪無果被勞教,離奇死在嚴管室」。
當我將這篇新聞報導稿打印出來一遍遍細讀的時候,窗外充沛的陽光斜斜地灑進室內,在我的周圍,編織成一種溫煦而又躍動的氛圍,可我的內心,卻被一股強烈的悲痛之情所充溢。
後來,當我看到這位河南宜陽縣的年邁殘疾冤死者臨死前幾張慘不忍睹的死狀照片時,頓感心如刀絞,繼而無法抑制地流淚。於是我低下頭來默禱,既為含冤受難的逝者,也為平息自己心頭湧出的悲憤情緒。心中滿盈的酸楚,仍是一如奔騰的海潮。
如今,對於我曾搜集過的眾多勞教案例,其中相當一部分勞教案例的具體細節,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但我仍清晰地記得這宗發生在河南宜陽的勞教冤死案例。我又想起了那天心頭的疼痛,和那無法控制奪眶而出的淚水。在這個日新月異紛紛攘攘的時代,我相信,所有的感觸都有它的意義。
此刻再回想起這宗案例,一句詩句倏地閃入我的腦海,那是十九世紀德國詩人海涅的那首膾炙人口的詩〈羅蕾萊〉。詩中的第一句是這麼說的:
「我不知道為了什麼,我會這般悲傷。有一個舊日故事,在心中念念不忘。」
2
這個舊日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趙文才。
你是河南省洛陽市宜陽縣豐李鎮小李屯村的一名普通農民。如今,這個小小的村子已脫離了宜陽縣管轄,在行政上劃歸給了洛陽市洛龍區豐李鎮。小李屯村,是你們家族世代紮根生活的地方,祖祖輩輩就在這片屬於洛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上以務農為生,耕作、開荒、種植、收成、生兒育女、養老送終。
這裏是你們家族賴以生存的土地,這裏見證著你們家族一代代人的生老病死、人生況味。這裏地處河南西部的淺山丘陵地帶,北部與屬於黃河支流之一的洛河相望――這是一個至今依舊偏僻窮困的地方。
你是一個地道的農民,一輩子與泥土相伴,也一輩子與黃土、鋤頭、鐮刀、農藥和化肥打交道,長年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家生活。
因為少時就失去了父親,為了體諒體弱多病的母親,照顧家中的三個妹妹,你在很小的年紀就下地幹活、擔負起養家的責任了。成年後隨著母親過世、妹妹嫁人、自己結婚生子,你又一肩挑起了這個家,開始為自己的家庭操勞忙碌了。
你特別地能吃苦耐勞,在田間地頭經營起莊稼來,有的是一身的力氣,無論是耕種,還是收割,你都是一把好手。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凍的,你也要去田裏忙活一陣子,常常凍得滿臉通紅的。
等到到了農閑季節,你又開始了自己的另一種忙碌:去鎮上做苦力,打零工,比如幹些搬運貨物、挖煤之類的活,掙點工錢以補貼家用。
你是一個勤勞的農人,也是一個幹活的能手,可儘管你平生盡力勞動,難得有閑下來的時候,在村裡幹活比誰都勤快,可你的一生卻仍然飽嚐了貧窮和拮据的滋味。五十多年的辛苦操勞,換來的是一輩子的窮苦生活。數十載辛勤的農家生活,幾十年窘迫的日子,你經歷了歲月的風吹雨打,一點點地變得佝僂、瘦小。在還不到六十歲的年紀,你就已經儼然像是一個滿頭白髮、滿臉皺紋、滿手溝壑的老人了。
儘管貧窮,可你和你的祖輩們一樣,仍是以土地為生,窮得安樂,窮得坦然,彷彿生來如此,從來都不怨天尤人的。儘管也常聽說村裏有人進城務工,但你從來就沒有動心過,你總覺得自己習慣了鄉間生活,你的生命,已經和這塊土地融合成一片了,你這輩子就在這裏生活,死了也要融化成泥土的一部分。
你的身上,有著農村人與生俱來的憨厚、善良、安樂,還有儉樸的品性。你平時從不捨得自己買新衣服,衣服穿破了總是補了又補,再繼續穿。你的身上常常穿著破了褲腳的褲子,和一件老舊的風衣——這件風衣是你的最愛。
你們家是小李屯村一戶普通的農家。你和妻子任妞共育有兩個孩子:長子趙現鋒,小學畢業後就放棄了學業,去了市郊小店區的一家工廠做雜工,工作崗位是在流水線上用丙酮擦拭汽車的散熱片;次女趙利霞,也是念完小學就輟學了,之後陸續在外打工,二○一○年年底又跟著二舅前往河南,當了一名焊工學徒。
3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後期,你從鎮上的耕牛市場購回了兩頭耕牛,為了買這兩頭牛,花掉了你們家的一大筆積蓄。從此後你就常常扛著犁和耙,趕著牛,到田地裏去耕田。
耕田的時候,你的雙腳浸泡在水田裏,頭上戴著斗笠,弓著身子,左手牽著牛繩和椏枝,右手扶著犁,口中吆喝著,微微低著頭,一步一步地向前耕田。
若是在夏日,犁地耙田幹了不一會兒,你的全身就會被汗水浸透,濕了的衣服貼在身上,映出微微駝起的脊背。
這兩頭牛成了你犁地耙田的好幫手,又聽話又好使。你對這兩頭牛十分鍾愛,將它們當成自己的命根子,一年兩次的耕作就全指望它們了。為了讓牛圈保持清潔,你幾乎每天都要打掃牛圈,替牛更換墊草、清理牛糞什麼的。
一天數次,你會為兩頭牛準備好充足的飼料,給它們鍘細細的草料,餵它們水,有時你還會將一堆蘿蔔刨成絲,然後剁碎,再拌上米糠,讓它倆細嚼慢嚥。
有時,你會牽著這兩頭耕牛,到村外去尋找嫩綠茂密的草地,讓它倆在草地上慢悠悠地踱步,吃草,咀嚼。在天氣晴朗的日子,你會將它倆牽出牛圈來到太陽底下曬太陽,還用篦子對它倆從牛頭到尾巴、從腹部到四肢,進行全身的梳理――因為你生怕牛身上長出虱子。再不你就會在太陽底下為兩頭牛洗刷、撓癢。
每到這個時候,它倆就會時不時地伸出舌頭來,舔舔你的手心、手背。它倆大而黑的眼睛裏便盛滿了溫順和感激,這時你就會像對待朋友一樣跟它倆說話、聊家常。
在你的悉心照料之下,一直以來這兩頭耕牛都養得膘肥腿直,看起來十分的健壯,村裏人看在眼裏都非常地羨慕。
村裏熟悉你的人都說,你就像家裏養的兩頭耕牛一樣的忠厚、勤勞、老實巴交、讓人信得過。因此每當你到鎮上打零工,總會有村民託你順便辦點事,在農忙的時候,也會有人請你幫忙幹點農活。
還有一點與牛相像的,是你的脾氣。從小你的身上就有一股牛脾氣,性格特別地倔強,家人、親友都覺得你有點擰,不順服,有點較真,凡事都要講出個理來。這樣的脾氣讓你什麼事都講究規則,在村裏你從不亂扔垃圾,犁地時你總是避免踩踏到別人家的水田,看到村民亂丟狗屎或牛糞,你也會跑過去清理幹淨,連和家人朋友打牌時你也從不許別人耍賴、作弊。
你雖然一生貧窮,對錢財看得格外得重,但更看重的是「講理」,凡事就認一個「理」字,有一股「認死理」的精神。——你是一個像牛一樣倔強的人。
4
你沒有想到的是,倔強的性格會給你帶來厄運;你也沒有想到的是,有人盯住了你犁地耙田的好幫手、生活中忠實的夥伴——你最心愛的兩頭耕牛。
那一天,是二○○二年的四月二十六日深夜、二十七日凌晨。初春的村莊寧靜中帶著一絲寒意,在夜深人靜的時分,一幕越貨行劫的勾當在夜幕的掩蓋下正悄然進行。
凌晨一點半左右,同村和鄰村的農民趙宜有、牛長斌、趙留義、趙慶偉、趙新偉等五人躡手躡腳地來到你們家。這五個人先將你們家門口躺在角落昏睡的狗毒死,然後由三個人手持兇器把住幾個屋門,再由趙宜友、牛長斌二人翻牆而入,將兩頭耕牛盜走,牽出門外,同時有人將你們家的磚砌院牆搗了兩個大窟窿,隨後悄悄地逃走。
在這夥竊賊行竊的過程中,你睡夢迷糊中感覺到屋外有動靜,依稀聽出這幾個人是鄉裏遠近聞名、遊手好閑的獷悍無賴,平日裏盡幹些打架鬥毆、偷雞盜狗的事,也因此多次進出公安局派出所的大門。因怕家人遭殃,在那一刻你顯得膽怯而懦弱,嚇得大氣也不敢出一聲。
等到早上天一亮,你就帶上女兒趙利霞,匆匆趕到豐李鎮派出所去報案。當時派出所的警員還沒有上班,值班人員便讓你們回村等待,同時你的妻子任妞也撥打了洛陽市「一一○」的報警電話。
回到家中過了一段時間,豐李鎮派出所來了兩名警員,他們的到來引起周邊群眾的圍觀。兩位警員到現場看了看又走了,臨走時說回去會通知縣刑警隊來現場勘察、拍照。可是在這之後,警方卻再也沒有人前來。
圍觀群眾散去後,盜牛團夥的家人留在原地,將你們家屋門外、圍牆上可能留下指紋的磚塊撣了一遍,以圖銷毀指紋證據。
在派出所警員和圍觀群眾離開之後,你和家人順著牛蹄印尋找,一路跟蹤到鄰村的油坊頭村,來到一戶開宰牛作坊的張雲發家門口,赫然發現兩頭牛就在張家,但張某拒絕歸還。
你找到該村的村幹部,村幹部陳某去張家看了看,對你說:「一頭牛應值八千,給你四千,……,別把事情鬧大了。」他的這一說法讓你楞住了,你當場不置可否。
當天夜裏,張家將牛宰殺掉,用一輛人力三輪車、一輛機動三輪車,拉到位於洛陽市南昌路的肉牛養殖基地,賣掉了。
四月二十九日,你再次來到派出所,告知發現兩頭被盜的耕牛在鄰村油坊頭村張雲發家、及該村村幹部陳某提議折價賠償的事。派出所的接待人員露出一副不耐煩的樣子,打斷你的話,然後說道:「五一我們放假五天,等我們上班後再說這件事情。」
之後,豐李鎮派出所在你們家再三的要求之下,不得已傳訊了盜牛團夥趙留義、趙新偉等人,問完話後卻又將他們給放走了,自此警方對盜牛一事再無下文。
五月二日晚上,你的妹夫劉小民來到你家,此行他是受盜劫團夥委託,讓你去小李屯村村幹部、盜牛團夥之一的趙宜友親戚趙青三家進行私下「和解」,也就是「私了」的。劉小民的勸說遭到你的拒絕,你十分篤定地對他說:「我只要法律給我解決」。
因為你不斷前往派出所要求處理、以及你拒絕「私了」的態度,惹得這夥盜牛團夥惱羞成怒,此後他們便經常地糾集在一起,到你家門口滋擾,並且還時不時地辱罵你和你的家人,甚至有時還拳腳相加。
五月三日上午,盜劫團夥趙宜友、趙新偉、牛長斌、李念堂等人公然竄到你家毆打你,邊打還邊叫囂著:「我們打的就是你,怎麼著,反正公安局上下都被我們買通了。」然後,又將你拖到街上毒打了一頓。可是當你的家人前去報警時,派出所對此卻置若罔聞,不去追究兇徒毆打傷人的法律責任。
5
為了討還耕牛、尋求公道、追究盜牛一夥的盜竊、毆打傷人的法律責任,從此你和家人開始不斷地上訪。從縣城、市區到省城,從河南到北京,從一家單位到下一家單位,你們一家奔波於艱難困苦的漫漫上訪路。
二○○三年的一月六日,你和家人到河南省公安廳上訪,之後將省公安廳開具的一份督辦信函,送到了洛陽市公安局。
然而,省公安廳的這份督辦信函,並沒有使得這起案件引起重視,進而加以解決,反而使你再次受到盜劫團夥的傷害。
一月八日上午,趙宜友、牛長斌、趙留義、趙慶偉、趙新偉等五人埋伏在你家門口附近,當你從地裏幹活回村,剛走到自家門口時,他們趁你不防突然竄出來圍了上來,將你打倒後按壓在地上,撿起地上的磚塊,朝你的身上亂砸一通。
當日,你被打得渾身是傷,滿身是血,傷口處鮮血不停流淌,眼睛、鼻子也血流不止,右腿腿骨被砸成粉碎性骨折。後經法醫鑒定,傷情級別為「輕傷」。(依法規定傷害等級達到「輕傷」,加害者已涉嫌故意傷害罪)
這次,你被盜牛團夥毆打得落下了右腿殘疾,需要拄著枴杖才能行走。此後,你艱難地拄著雙拐,到各有關機關單位繼續上訪。
一次,你拄著雙拐到縣委大院上訪,想向縣委書記反映情況,結果被宜陽縣公安局以「擾亂辦公秩序」為由,先後分別於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八月十一日、二○○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加以拘留,拘留時間分別為五日、十日和十五日。
拘押期間,拘留所幹警對你多次毆打、餓飯,還專挑剩的和壞的饅頭給你吃,並且指使其他被拘留人員毆打你。此外,拘留所幹警多次提出要你別再上訪,把此事「私了」,反覆勸說「賠你點錢算了」。對此,你的態度一如既往,依然不同意「私了」,堅決要求依法處理。
你和家人將宜陽縣的各大機關幾乎都跑遍了,市裏和省城也去了很多遍,但事情卻一直都沒能得到解決。無奈之下,到了二○○五年,你們夫妻倆便一起到北京上訪——這是你們最後的一點指望了。
但你們可曾聽說過,在北京,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截訪工作人員,他們來到京城的任務,就是專門攔截、跟蹤、圍堵地方上訪者,甚至會動用暴力、採取關押等措施,以阻止上訪者的上訪。
果不其然,宜陽縣公安局早就盯住了你們一家,該局派來的截訪幹警在北京將你倆抓住,毒打了一頓,然後遣送回原籍。返回之後,將你倆關押進了宜陽縣陳寨溝一處專門容留上訪者的拘押場所。
後來你倆費了一番氣力,從這家拘押場所逃了出來,再次來到了北京上訪。但這次,你們再度被宜陽縣公安局的截訪幹警抓住、毒打,並再度送回原籍,再又關進了陳寨溝的這家拘押場所,然後嚴加看管。這次,你倆總共被關押了二十天。
二○○五年六月十五日,正是農村收麥子的時節,宜陽縣公安局來人將你的妻子任妞逮捕,以所謂的「毆打了趙宜友的女兒趙新朋」的罪名。後經法院審理,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任妞一年管制,她在看守所裏被關押了幾個月,最後看守所讓她簽署一份所謂「不上訴、不上訪」的保證書之後,予以釋放。
在你和妻子雙雙被釋放回家後,你倆又開始了不屈不撓的上訪,去省城,赴北京。期間,你們夫妻倆多次被地方截訪幹部接回,予以關押,也多次遭到毆打,你的牙槽骨讓人打壞,門牙也被打掉,你的傷殘程度更加嚴重了,幾乎已完全喪失了勞動能力,在村裏甚至就連拄著雙拐也不能種地了。
為了生活,也為了繼續上訪討個說法,到了二○○七年,你又來到北京。這次來北京你打算長住,每天以撿拾瓶子、撿垃圾為生,然後有空就時不時地到各大機關去上訪,反映案情經過,遞交上訪材料。
這一年九月初的一個晚上,你借住在老鄉的一間破屋子裏,被來京截訪的你們村長趙見聚、以及他帶隊的一群截訪幹部抓住,劈頭劈臉便是一頓好打,然後用車直接拉回洛陽。到了洛陽,你先被關進拘留所。過了一段日子,你又被轉移到另一個地方,一處新的羈押場所。那段日子任妞到處找不到丈夫,整日面容愁苦,以淚洗面。
任妞沒有想到的是,這次她丈夫在一個新的羈押場所,遭遇了這幾年上訪以來最嚴重的凌虐和折磨。她更沒有想到的是,在這個羈押場所,她那無辜的、殘疾的丈夫會被摧殘致死,再也沒能從監所裏走出來。
置她丈夫於死地的,是一個不是監獄的「監獄」,不是牢房的「牢房」,一個唯獨中國才有、世界各國絕無僅有的羈押場所——勞動教養所。其具體的名稱,叫做河南省洛陽市黃河橋勞動教養所。
6
現在,請允許我在講述趙文才的故事時,暫時在這裏停頓一下,讓我們先來看一看勞教制度在現代中國的前身今世。
六十多年前,一個「敢叫日月換新天」的新生國度誕生在古老的神州大地。連年戰爭的創傷還未及撫平,一連串疾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就接踵而來,源源不絕。在百廢待興的頭十年,就陸續有土改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對武訓傳、胡風反革命集團、俞平伯紅學研究和胡適思想的政治批判、三大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運動、反右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等等無休無止的政治風暴,左一個運動,右一個批判,攪得神州大地雞犬不寧,血流漂杵。
在一九五○年代政治運動的暴風雨中,一種師法前蘇聯的「古拉格」、而後形成了世界上僅中國獨有的社會管制制度,在這片土地應時而生。它將存在數十年,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它已與當今的時代氛圍格格不入,卻依然屹立不倒。
它,就是勞教制度。它的全稱,是所謂的「勞動、教育和培養」制度。
這項制度,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土改、鎮反、肅反、反右等政治運動中逐步建立起來的,迄今已足足超過半個世紀了。五十多年的風雨與滄桑,當時出臺的許多政策都已消散在歷史的煙塵裏,但勞教制度卻還頑強地存在著。
翻開一九五○年代的歷史,當時出臺勞教制度針對的,主要是這三種人:其一,在運動中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其他壞分子」指政治騙子,叛變投敵分子等);其二,某些直系親屬在土改、鎮反和社會主義改造中,被殺、被關、被鬥者的家屬;其三,遊手好閑、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力的人、政治上不適合繼續留用的人(主要指右派分子)。從收治的對象可以看出,勞教制度分明是那個年代「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的產物,是所謂「塑造社會主義新人」的一項「創舉」。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一制度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權的,堪稱現代社會中荒謬絕倫、殘民害理、逞兇肆虐的一項弊政,一件「惡法」。它不是監獄,只是所謂「把這些人集中起來,送到一定地方,讓他們替國家做工」的工作和勞動場所,卻與羈押、拘禁囚犯的監獄並無二致,其勞動強度相較監獄有過之而無不及;它不是學校,卻大言不慚地聲稱要對收治人員進行所謂的「政治、思想的改造工作」、「思想教育」云云,辦成所謂「教育人、挽救人的特殊學校」。
它的收治對象,並不是觸犯刑律的犯罪分子,而是所謂「不夠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此係合法公民)、「運動中被鎮壓者的家屬」(此係「連坐」)等等被貼上特定政治標籤的公民,卻完全以對待囚犯的方式囚禁、管束他們。甚至於,收監的囚犯還有一定的刑期,被勞教的人員卻沒有明確的期限,被勞教者中,長達幾年、十幾年、甚至長達二十多年的比比皆是。
它的產生,並沒有經過周密的調研、論證和全民討論,只是有關機關揣摩、迎合偉大領袖浮想聯翩的階級鬥爭實踐的結果;它是一項剝奪人身自由的嚴厲處罰,卻並無拘捕、起訴、審判、上訴等法律程序,僅由公安機關內部進行封閉式的匯報審批、自行裁判、獨家決定,而毋須經過法庭審訊定罪,即可將公民收治關押,其程序上的獨斷性、隨意性和主觀性令人咋舌;它的產生和存在,沒有法理的基礎,也缺乏立法機關出臺的任何法律,僅憑執政黨高層一紙所謂關於「徹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最高行政機關一紙所謂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就可以長期地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
在這樣一種「無法無天」的虐政之下,盈千累萬的共和國公民被剝奪了自由及各項公民權利,被貶為政治賤民,淪為現代版的奴隸,在惡劣的環境中從事繁重超負荷的體力勞動,流離失所,受盡折磨,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麥子不死-寫給底層受難者的八封信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5 |
中文書 |
$ 299 |
社會 |
$ 306 |
弱勢族群 |
$ 306 |
文學作品 |
$ 306 |
其他類型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麥子不死-寫給底層受難者的八封信
書籍介紹
為底層人立傳,與受難者同哭!
在北京,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截訪工作人員,他們來到京城的任務,就是專門攔截、跟蹤、圍堵地方上訪者,甚至會動用暴力、採取關押等措施,以阻止上訪者的上訪。河南宜陽縣農民趙文才,就這樣為上訪而死。
曹大和,這個貴州省仁懷市高大坪鄉銀水村高路組的貧地農民,在被遣送回鄉的火車上,遭到捆綁一夜後死去。
一個三歲小女孩李思怡,因民警拒絕她強制戒毒的母親回家安頓孩子,整整十七天無人聞問,竟活活餓死家中。
……
本書深入剖析八則當代中國真實發生的社會新聞,
揭露「中國崛起」的華麗外衣下,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生活真相!
作者簡介:
楚寒,
1975年出生於江蘇建湖縣,在本地讀完中小學,後離家求學、工作,獲四級技工證書、律師資格證書及法學碩士學位。做過工人,當過律師,從事過教師等多份職業。熱愛人文社會科學,關注國族前途命運、底層社會和困境冤屈群體。曾獲臺灣五四文學獎等獎項,著有未刊評論集《政治,你有多少的罪惡?》(自印本)、隨筆評論集《羽毛筆的自由》、思想性隨筆集《火焰不死》、雜文評論集《提刀獨立》、人文隨筆集《星空下的憂思》。
章節試閱
【那個死於勞動教養的上訪老農——祭河南宜陽縣農民趙文才】
1
「廣受爭議的勞教所死訊頻傳,名目多樣,有「洗臉死」、「睡覺死」、「沖涼水死」、「激動死」……
勞教制度在法理上缺乏基礎,在實體和程序上都存在重大瑕疵,在接二連三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衝擊下顯得搖搖欲墜。」
上述這兩段文字,出自《世界博覽‧半月刊》雜誌(二○一○年第十一期)的一篇報導,標題為:〈屢屢死亡與勞教所異化:「勞教制度」困局求解〉。從標題可以看得出來,該文是在近年來勞教所頻頻傳出非正常死亡事件的社會背景之下,探討如何革除勞...
1
「廣受爭議的勞教所死訊頻傳,名目多樣,有「洗臉死」、「睡覺死」、「沖涼水死」、「激動死」……
勞教制度在法理上缺乏基礎,在實體和程序上都存在重大瑕疵,在接二連三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衝擊下顯得搖搖欲墜。」
上述這兩段文字,出自《世界博覽‧半月刊》雜誌(二○一○年第十一期)的一篇報導,標題為:〈屢屢死亡與勞教所異化:「勞教制度」困局求解〉。從標題可以看得出來,該文是在近年來勞教所頻頻傳出非正常死亡事件的社會背景之下,探討如何革除勞...
»看全部
作者序
序
我是在二○一一年的春天開始這本書的寫作的。想要系統地寫底層受難者的故事已有好些年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夙願,一份命定的責任。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像潮水一樣退去了,各種媒體紛紛回顧、聚焦於新世紀頭十年的宏大敘事。但此時,我將目光投向那些「小人物」,他(她)們是弱者,居底層,遭苦難,時時繫念於我的心間,因為他(她)們在那裏,宛若我往昔刻骨銘心的私人記憶。
關注底層受難者,緣起我少年時代矢志執念的理想:服務困境冤屈人群。十多年前,我投身於法律服務的工作,與底層受難者們一道四處奔波也起始於此。...
我是在二○一一年的春天開始這本書的寫作的。想要系統地寫底層受難者的故事已有好些年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夙願,一份命定的責任。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像潮水一樣退去了,各種媒體紛紛回顧、聚焦於新世紀頭十年的宏大敘事。但此時,我將目光投向那些「小人物」,他(她)們是弱者,居底層,遭苦難,時時繫念於我的心間,因為他(她)們在那裏,宛若我往昔刻骨銘心的私人記憶。
關注底層受難者,緣起我少年時代矢志執念的理想:服務困境冤屈人群。十多年前,我投身於法律服務的工作,與底層受難者們一道四處奔波也起始於此。...
»看全部
目錄
自序
那個在眾人面前被捆綁的人——祭貴州仁懷市農民、廣東佛山農民工曹大和
那個殞命黑磚窯的智障奴工——祭甘肅宕昌縣農民、山西洪洞縣黑磚窯奴工劉寶
那個死於飢餓的三歲女孩——祭四川成都女童李思怡
那個含冤屈死的少年人——祭內蒙古呼和浩特青年工人呼格吉勒圖
那個深夜死於血拆的長者——祭山西太原農民孟福貴
那個被城管圍毆致死的涼粉小販——祭四川嶽池縣農民、重慶小販劉建平
那個﹁被精神病﹂致死的小學教師——祭陜西西安小學教師王恒雷
那個死於勞動教養的上訪老農——祭河南宜陽縣農民趙文才
那個在眾人面前被捆綁的人——祭貴州仁懷市農民、廣東佛山農民工曹大和
那個殞命黑磚窯的智障奴工——祭甘肅宕昌縣農民、山西洪洞縣黑磚窯奴工劉寶
那個死於飢餓的三歲女孩——祭四川成都女童李思怡
那個含冤屈死的少年人——祭內蒙古呼和浩特青年工人呼格吉勒圖
那個深夜死於血拆的長者——祭山西太原農民孟福貴
那個被城管圍毆致死的涼粉小販——祭四川嶽池縣農民、重慶小販劉建平
那個﹁被精神病﹂致死的小學教師——祭陜西西安小學教師王恒雷
那個死於勞動教養的上訪老農——祭河南宜陽縣農民趙文才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楚寒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2-11-01 ISBN/ISSN:978986326004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0頁
- 類別: 中文書> 社會科學> 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