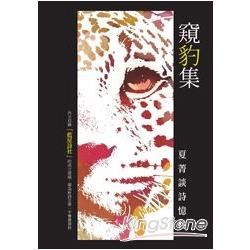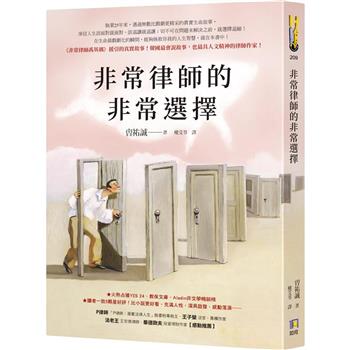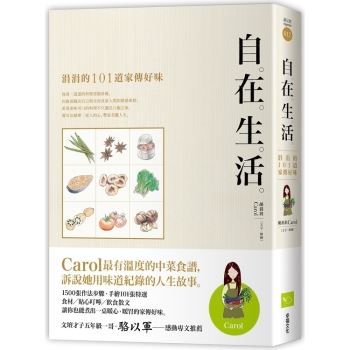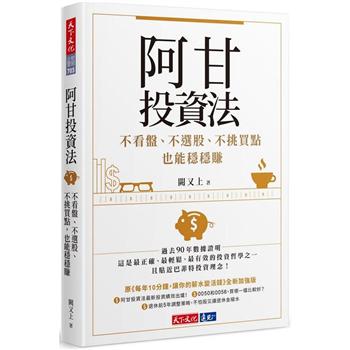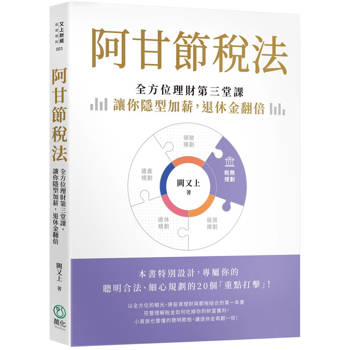第一輯 短論
談詩中的哲理
詩與詩人
再談〈詩與詩人〉
《藍星詩頁》發刊詞
當前新詩的危機
論詩的晦澀
詩壇一年――一九五九年詩人節感言
說瓜苦――籲請新詩人反省及檢討
隱憂
反傳統及中國化
三年有成
灌溉這株仙人掌
佛勞斯特的啟示
從牛角尖裡走出來!――論現代詩的方向
詩與啄木鳥
第二輯 評介
仙人掌――介紹余光中譯《中國新詩選》
和而不同五十年――余光中和我
詩的悲哀――周夢蝶《孤獨國》及向明《雨天書》讀後感
君子之交四十年――我與夢蝶
詩的經驗與表達――簡介瘂弦〈馬戲的小丑〉
好詩選介――瘂弦:〈三色棒下〉
〈芭蕾舞會〉簡介――兼論「暗示」與「象徵」
為覃子豪立像
《藍色小夜曲》評賞
愁雲滿天――悼鄧禹平
遊俠詩人吳望堯
追夢得夢――序麥穗詩集《追夢》
第三輯 談論現代詩
現代詩的面面觀與前途――詩集《少年遊》代序
以詩論詩――從實例比較五四與現代的新詩
詩與想像力――兼釋言曦、陳紹鵬、吳怡諸先生列舉的新詩
詩辯――一幕短劇
從一首詩出發――並呼籲詩人應獨來獨往
老當益壯的佛勞斯特
不斷開闢新境界的美國詩哲:佛勞斯特
詩,拯救得了嗎?
第四輯 訪談及對話
終身追她不悔改――向明:夏菁答八問
自然、簡約與親和――王偉明:與夏菁談新詩和散文
詩是終身的追求――綠音:詩人夏菁專訪
詩心、詩意、詩天空――綠音、夏菁漫談當代詩歌創作
附錄 早年的藍星――重刊《藍星談往》
後記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窺豹集:夏菁談詩憶往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窺豹集:夏菁談詩憶往
這是詩人夏菁半世紀以來唯一談論現代詩的文集。收集了早年在《公論報》、《聯合報》、《藍星詩頁》、《文星雜誌》、《自由青年》等刊出的作品;台灣新詩論戰時的文章,以及近年來在台、港和美國發表的對話及訪談錄等,共計四十篇。
集中包括推介名家余光中的譯詩、鄧禹平的抒情詩、周夢蝶及向明的第一本詩集、瘂弦的早年作品,以及當時乏人注意的美國大詩人佛勞斯特(Robert Frost)等的專文。
夏菁對六、七十年代詩風的晦澀,提出了警告;並主張「詩的可讀性」。對現代詩的前途,懷抱信心;這些均可在本集中見及。作者對詩的眾多意見,可在名詩人及編輯向明、王偉明及綠音的訪問錄及對話中讀到。
後附〈早年的藍星〉長文一篇,是作者的第一手資料。對台灣早年三大詩社之一的「藍星詩社」成立經過及其成員,做了生動的描述,堪為新詩發展史上的寶貴資料。
作者簡介:
夏菁
盛志澄的筆名。浙江嘉興人。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碩士。曾任聯合國專家及科州大學教授。早年在台,曾發起「藍星詩社」,主編《藍星詩頁》、《文學雜誌》及《自由青年》的新詩。已出版詩集《噴水池》、《雪嶺》、《獨行集》、《折扇》等十二種,以及散文《落磯山下》、《船過無痕》等五本。現居美國。
目錄
第一輯 短論
談詩中的哲理
詩與詩人
再談〈詩與詩人〉
《藍星詩頁》發刊詞
當前新詩的危機
論詩的晦澀
詩壇一年――一九五九年詩人節感言
說瓜苦――籲請新詩人反省及檢討
隱憂
反傳統及中國化
三年有成
灌溉這株仙人掌
佛勞斯特的啟示
從牛角尖裡走出來!――論現代詩的方向
詩與啄木鳥
第二輯 評介
仙人掌――介紹余光中譯《中國新詩選》
和而不同五十年――余光中和我
詩的悲哀――周夢蝶《孤獨國》及向明《雨天書》讀後感
君子之交四十年――我與夢蝶
詩的經驗與表達――簡介瘂弦〈馬戲的小丑〉
好詩選介――瘂弦:〈三色棒...
談詩中的哲理
詩與詩人
再談〈詩與詩人〉
《藍星詩頁》發刊詞
當前新詩的危機
論詩的晦澀
詩壇一年――一九五九年詩人節感言
說瓜苦――籲請新詩人反省及檢討
隱憂
反傳統及中國化
三年有成
灌溉這株仙人掌
佛勞斯特的啟示
從牛角尖裡走出來!――論現代詩的方向
詩與啄木鳥
第二輯 評介
仙人掌――介紹余光中譯《中國新詩選》
和而不同五十年――余光中和我
詩的悲哀――周夢蝶《孤獨國》及向明《雨天書》讀後感
君子之交四十年――我與夢蝶
詩的經驗與表達――簡介瘂弦〈馬戲的小丑〉
好詩選介――瘂弦:〈三色棒...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夏菁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3-02-05 ISBN/ISSN:978986326062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76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