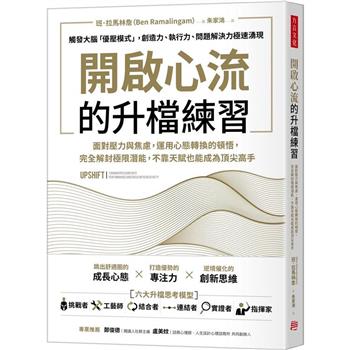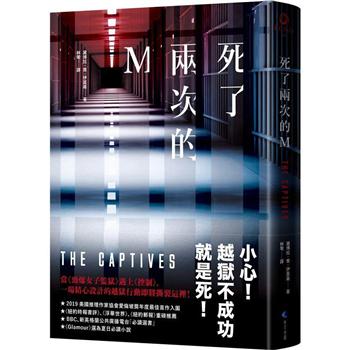推薦序
超越差異,跨界求同──張隆溪學術思想述評∕韓晗
(前文略)
長期以來,我們編寫「世界文學史」、「世界科技史」鮮有將「中國文學」或「中國科技」置入這一範疇中。尤其是「中國現代文學史」長期以來被當做是對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否定與超越,卻少有學者認為這應是世界現代文學運動的重要一環。如施蟄存與卡夫卡(Franz Kafka)、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與李金發等等,彼此相差不過二十年左右,但之間許多共性卻被忽略掉了(或者說單純從微觀的某個共同點出發,忽視了他們在早期全球化語境下的共性),但實際上基於「求同」的視角完全可以看到中國文學參與世界文學現代化進程的功績與努力。張隆溪曾如是論述這一問題:
文、史、哲不僅要包括中國文化的內容,而且必須包括中國之外其他文化的內容。我們脫離世界範圍來孤立瞭解中國文化,就不能對中國文化的性質和特點有真正的瞭解,也不能對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和時代有比較全面的認識。
因此,張隆溪「求同」的學術思想另一個重要前提是「跨界」。除了前文所述跨文化、跨民族、跨學科、跨領域之外,還存在著「跨國界」眼光。當然,他這種「跨國界」並非是將多個「他國」進行總結性述評,而是基於中國的本土經驗這一空間屬性,力圖在人類大文明的文、史、哲範疇內使得中國文化化歸為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
但值得一提的是,與錢鍾書相似,張隆溪雖然主張超越差異與各種邊界的「求同」,但他仍然不曾放棄立足於文本與細節的具體研究,學術思想主要從宏觀的角度出發,但在宏觀之下必須要有微觀的具體實踐,這樣才能構成一個完整、可操作的學術體系。在這個問題上,張隆溪與錢鍾書有著明顯的師承關係。張隆溪自己也認為,「(錢鍾書)總是超越中西語言和文化界限,絕不發抽象空疏的議論,卻總在具體作品和文本的互相關聯中,見出同中之異,異中之同。」 並且,他還引用了錢鍾書的名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 來表明自己基於歷史與時空的學術觀。
綜上所述,張隆溪的學術思想可以用「超越差異,跨界求同」來概括。這裡所謂差異,便是一種追求對立的相異性;而跨界,則是打破科技、文化與政治造成的各種人為邊界──如學科、民族、政治制度、國家與文化等等。宏觀地看,就是立足中華文化的本土經驗,以國際視角來尋求不同知識體系中的相同之處,以便總結出人類文明的普世規律與價值,並努力促進中華文化與傳統中國學術融入全球化的語境,使其在未來的時日裡煥發出新的光彩,而這一切又寄予於對於具體文本、史料與材料等研究對象的微觀研究。
毋庸置疑,張隆溪的學術思想不只是針對中國(或漢語)學界有著指導性的意義,對於當下一切傳統文化、學術如何面向並融入世界,實際上都有著可資參考的價值。
當下時代所謂「全球化」,主要是西方中心主義,經濟發達的國家與地區因在世界上享有主導地位,在政治對話、經濟競爭乃至軍事制裁中都擁有主動權。進而使得一些歷史悠久尤其是地屬東方的傳統國家(或民族)因為經濟發展的落後,導致其文化、學術、藝術與哲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邊緣化。如埃及、印度以及中東、東亞等國家或地區。其當地學者、藝術家或作家要麼選擇積極融入西方語境,放棄本民族(或本國)文化、哲學甚至語言,從而為自己在「他者」的世界裡獲得一席之地;要麼固守自己的傳統文化精神,雖然在短期內可以吸引西方的視線,但卻總與世界大環境發生一定的距離,時至日久,其被邊緣化乃是早晚之事。
在近年來的著述中,張隆溪用到最多的一個詞就是「東方」而不是「中華」或是「中國」。從詞彙本身的概念來講,「東方」明顯要包括比「中國」更為豐富的內涵,不只是中國,當然也包括印度、伊朗、埃及甚至南美等國家,這些國家實際上和中國一樣,正在面臨著自己的文化、學術與藝術如何融入世界這一歷史性課題。
因此,張隆溪在一定程度上為世界上這些傳統的學術、文化與藝術指明了一條發展路徑:如何在「跨界求同」的層面上,使得自身能為以保全個性為前提並融入到世界語境當中。儘管張隆溪並未明確地分析這一問題,但他對於「求同」這一思想的闡述,事實上完全可以為其他東方國家的傳統文化、藝術與學術的發展指明方向。
而且,張隆溪反映了一代中國學人的治學精神。他的學術思想既反映時代特徵,又蘊含民族精神。因此,今後對張隆溪的研究還應該深入,有利於瞭解一個正在變化的中國。
我們看到,張隆溪從比較文學、闡釋學出發,發軔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邏各斯主義」之上,主張「跨界求同」的學術思想,其精神根源還是源自於講究「和合」、「大同」的傳統中國文化與現代中國學術──張隆溪在著述中曾多次對西方經典學者如黑格爾、福柯與于連等人進行過不同程度的批評,認為他們對中國文化明顯瞭解不夠。正因缺乏瞭解,所以才會人云亦云地塑造出一個「對立」的異文化他者形象。
但是,若論及張隆溪學術思想與現代中國學術的淵源,除卻前文所論的錢鍾書之外,還有兩位學者不得不提。一位是曾執教於北京大學的陳源(西瀅,一八九六─一九七○),另一位是清華大學的陳寅恪(一八九○─一九六九)。前者曾提出「跨中西文化」之壁壘,力圖以「雅俗之辨」來區分世界文學的高下,而後者則認為「跨語際」研究基礎太薄弱,關鍵要比較歷史觀念的源流。
張隆溪學術思想萌芽、成熟的年代,既與陳源、陳寅恪不同時,也與錢鍾書著《談藝錄》、《管錐編》有著幾十年的時間差距。因此,張隆溪對於世界問題的看法,既是對前人的繼承,也是對他們的超越。張隆溪繼承了陳源「跨中西文化」的研究思想,但卻超越了作為新壁壘的「雅俗」之辨;他賡續了陳寅恪對「歷史觀念」的源流的比較,並從中「求同」,但對於「跨語際」的研究又從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的闡釋學的層面提出了自己新的見解。
事實上,張隆溪的學術思想正是站在中西方當代文哲巨人的肩上而構建完成的,但同時也為時代所決定。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今,東西方文化對立不斷、政治經濟衝突不絕。從中國到美國再走向世界的張隆溪,對於這種對立、衝突的感觸勢必要勝於他的前輩。在他學術思想三個階段中,我們還可以對比地發現:第一段與第二段的歷史分期,恰是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節點,而第二段與第三段的歷史分期,又基本與「九一一」恐怖事件相吻合。
所以張隆溪的學術思想雖看似是人文理論的智慧結晶,但卻是與現實問題緊密相連的精神成果,當然更是一位中國學人在全球化下的實踐與思考,它從深層次反映了當代中國學術融入世界語境的過程。就目前而言,學界對張隆溪的研究還並不太夠。據此筆者認為,今後學界應該更加重視張隆溪的學術思想,並在廣度、深度上應對其有所挖掘、研究與總結。這不但可以豐富世界比較文學界、文化學界乃至整個人文社科界的研究成果,而且可以將其作為一個重要的個案,進行更加細緻的研究解讀。
我們充分地認識到,經歷了三個階段的張隆溪學術思想,已發展成熟,不但具備研究意義,亦對於學術、文化與藝術研究實踐有著重要的指導價值。這一問題前文已經有相當多的筆墨來闡釋,這裡不再贅述。但我們必須要考慮一個新問題是:今後張隆溪的學術思想,還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誰也不是預言家,但在人文社科領域裡,對於一位思想家的預測又變得如此重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無論是晚年牛頓,還是晚年馬克思或是晚年黑格爾,其思想都曾發生過「告別青春」甚至「否定自我」的嬗變。中國古人也有名言「吾年七十方知六十九歲之非」。因此,誰也無法否定今後張隆溪的學術思想是否會因為各種因素而發生轉向。
但基本上值得確定的是,張隆溪以「跨界」而「求同」的學術理念應不會有本質性改變。「跨界」,實際上是對於全球化語境的認同與響應,打消壁壘、填實溝壑、廢除對立、拆解保守,在多元中消解矛盾並以開放性的姿態尋求共性,乃是人類文明今後發展的大趨勢。雖然現在這一趨勢在發展的過程中存在著一定的波折與反復,我們必須承認,作為一個總的趨勢,任何人或事既不能也無法改變。
因此筆者認為,張隆溪學術思想在今後抑或還會被繼續充實、修正,但不會被顛覆。整體地看,他用前瞻性的眼光描摹了世界潮流,並力圖給中華文化以一個新的定位的方式,這是其學術思想的核心組成。從這個角度來講,在今後的研究中,張隆溪或許還會對一些新的現象提出新的觀點、新的問題並作出新的闡釋,但這種闡釋勢必還會基於「跨界求同」的基本核心。
「超越差異」是「跨界求同」的前提,「跨界求同」是「超越差異」的結果,兩者共同構成了思考、分析與解決問題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張隆溪的學術思想正在潛移默化或者直接地影響著更多的後學者,並為其思考新的問題、解決新的課題打開了新的視野並提供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