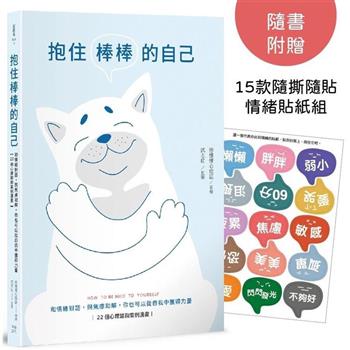從賽金花的生平和眾名家筆下的賽金花,兩面探討切入的「賽學」,帶領讀者深入淺出的重現清末第一名妓──賽金花的面貌:她的情仇、她的功、她的名。本書並配有關於賽金花的珍貴歷史影像。
本書特色
從賽金花的生平探究,和賽金花對後世的影響兩層面來看賽金花。不只看到歷史真相,還能在電影、文學、畫作中蒐集到此清代名妓的身影。
作者簡介
舒蘭
本名戴書訓,1931年生;江蘇邳縣人。中國文化大學文學士,美國東北密大藝術碩士。曾任軍、公、教職。著有詩集、詩話、詩史、詩論和兒童詩及譯著等十餘種。編有《中國地方歌謠集成》一套七十冊、《中國新詩史話》四巨冊等。與詩友薛林、林煥彰創辦《布穀鳥兒童詩學》季刊,推動兒童詩教及兒童文學,不遺餘力。曾獲優秀青年詩人獎、詩教獎、詩運獎、金筆獎、文藝獎章、傑出服務獎及出席世界詩人大會,列名中、英、美名人錄。現旅居美國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