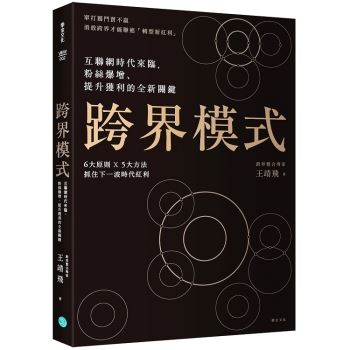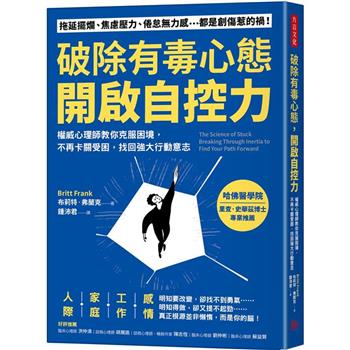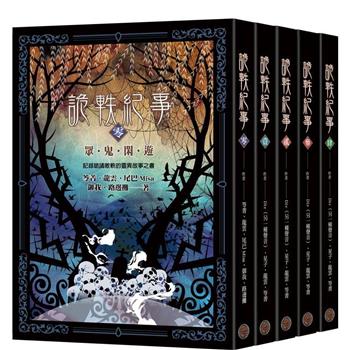推薦序
真相‧細節‧菩提心 姜弘
文熹老弟的散文隨筆將要結集出版,向我索序,我雖視力不佳,但我們的交往,於情於理是不能推辭的,就在這裡寫下我讀這些文章時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書名《拈花一笑野茫茫》,這「拈花一笑」出自禪宗典故,說的是佛祖拈花,迦葉一笑,由會心而衣缽相傳的故事。後面的「野茫茫」三字,我卻不知道出處和所指。問文熹,他笑而不答,好像是在考我,看我能否悟出這三個字的深意。翻看目錄,發現那篇談聶紺弩刑事檔案的文章題為「悲涼之霧,遍披華林」,這不是魯迅評《紅樓夢》的話嗎?於是,我立刻想到了《紅樓夢》結尾的最後一句話:「祇見白茫茫一片曠野,並無一人」,對照開頭的那四句詩:「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於是,我明白了,文熹的這個書名,該不是隱含著「悲憫」二字吧?是與不是無須追問,這是我讀他這些文章所獲得的總的印象。
這些文章在今天都叫「隨筆」,寫的都是自己的見聞感受,也有讀書筆記。這類文字在古代屬於「稗官野史」,後又稱「筆記小說」。既「稗」且「野」,當然是非正統非主流的,與《資治通鑑》、二十四史之類有助於專制統治的官書正史不同甚至相反,所以在專制時代是被輕視甚至遭禁絕的。然而唯其如此,其中保留了更多歷史真相,可信度遠超過那些以「瞞」和「騙」為職責的官書正史,所以受到有新思想的改革者的重視。魯迅就特別重視這種野史,他對中國歷史的深刻認識就與此相關。
在文體風格方面,也因其「稗」和「野」,非正統非主流,自然也就不受拘束,不端架子,隨意漫談,信筆所之,因而也稱「隨筆」。這類文章有兩大顯著特點:篇幅短小;文字精粹。《世說新語》可說是最早的這類文章的典範,體現了魏晉文風的顯著特點:「清峻通脫」--清峻,簡潔有力;通脫,瀟灑自由。前者主要指對所寫事物的觀察和描寫的真切生動,後者是說作者的感情態度。這也就是說,既要寫真實,又要出於誠心,要在不欺瞞、不虛飾,就見聞所及寫下自己的真實觀感。篇幅短小,文字精粹,均由此而來。說不上什麼典型人物典型環境,有的祇是片斷、細節,卻讓人從斷片、局部、一鱗半爪中窺見到社會歷史的真相。--從《世說》裡我們看到了魏晉之際的世態人情,戰亂使得王綱解紐,文化多元,才能那樣自由,那樣珍視人--人的價值、人的才智、人的風采;難怪魯迅說那是個「為藝術而藝術」的時代。那以後一千多年間,筆記小說代有佳作,《聊齋》是離我們最近的朝代最膾炙人口的文學珍寶,那些鬼狐的善良美麗,以及他們讓人憐憫的命運,折射出那個大一統專制王朝的黑暗,也讓我們品味出蒲松齡這個窮書生的品格襟懷。
文熹的這些文章,涉及到百年中國的三次歷史大變動,即1911年的革命、1949年的「解放」、1966年的「造反」。這三次大變動也都通稱「革命」,而實際上卻大不相同。不僅目的、性質不同,進行的方式和造成的後果更有天壤之別。有關正史和野史裡口述歷史和各種回憶錄,對此有著很不相同的記述和評價。或歌頌、或暴露,有的寫上層人物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的功勳;有的寫普通民眾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的慘狀。對同一歷史事件,見聞褒貶大相徑庭,這就是所謂的「立場」決定的。這也難怪,如佛洛伊德所說:「人不會觀察他不想觀察的東西」。愛倫堡在他的長篇回憶錄《人.歲月.生活》的開頭,以汽車前燈為喻,說他之所憶所記,祇是人生長途行進中眼前閃過的瞬間片斷,遠不是歷史現實的全貌。由此可見,從不同人寫出的不同歷史及其評價中,又可以反觀不同人的眼界、目光和襟懷的不同。--文熹的這些文章當然都是有感而發,有為而作,卻說不上是「歌頌」還是「暴露」,所寫的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他祇是以平常人的平常心,在追憶、重溫、思索那些難以忘懷的人和事。
魯迅早說過:「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知識者的任務。」事實的確如此。辛亥先驅者,國共兩黨的締造者,都是最先覺悟的知識分子。同理,歷史也已經昭示,凡改革受挫或走上邪路的時候,也必定是知識分子受壓抑和摧殘的時候。這本書裡寫的也多半是這種知識分子,既有辛亥時期的先驅者,更有後來歷史大轉折中的受難者。這中間,王元化的情況比較特殊,他雖然是個受難的知識分子,但後來卻又當過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是個不小的官員。然而也正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從清末到民國時期,中國社會的人才流動渠道是暢通的,有才能的人不難脫穎而出--王元化的祖父母雖然是貧窮的殘障人,但王元化的父親在基督教聖公會的資助下,苦讀成才,留學美國,回國後被清華大學聘為教授。王元化成長於清華園並成為兼通中西文化的大師級人物,究其原因,不能不承認當時的社會制度和社會風氣的優良一面--尊重知識,重視文化,愛護人才,有道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雖有上下尊卑之別,卻沒有後來的階級成份、出身血統的鐵柵欄。上世紀前半期湧現出那麼多大師級人物,後來卻出現了「人才斷層」,就與此緊密相關。
從王元化的家世不僅可以看到那個時代對文化和人才的重視,而且可以看出當時的多元文化格局,即中西古今各種文化同時並存的局面。同樣,文熹自己家和他們的四代世交殷海光家也是如此。毫不奇怪,那是個新舊交替的時代,東西文化既衝突又融合的時代。我們這些八九十歲的在「舊社會」受過中等教育的人都可以證明,傳統文化的基本知識和基本訓練是在中學階段完成的,進入大學還有「大一國文」,進一步拓寬、深化傳統學養。舊大學的理工科學生也能熟練地用文言寫作,會吟詩填詞,因為他們接受的是通才教育,而不是工匠訓練。可見,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全盤反傳統」,造成了以後的「文化斷裂」,完全是不顧事實的妄說。當然,「斷裂」確實存在而且還在加深加寬,不過這是後來的事,不能歸咎於新文化運動。
說到文化、新文化,就不應該忽略宗教問題,因為新文化就是從這裡來的:沒有西方宗教的傳入,就沒有什麼「西學東漸」,也不會有「文化衝突」,那以後的維新、革命、新文化運動等等也都無從發生,有的祇能依然是「揭竿而起」引起的連年戰亂和改朝換代。所以,回顧百年歷史不能忘記「文化衝突」這個開端,談文化衝突又不能忽略宗教的作用。這本書裡有幾篇文章觸及宗教問題,如基督教聖公會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宗教在「文革」中受到的摧殘。這裡祇說前者--文熹在文章裡具體談到武昌首義之源泉、反清革命團體武昌日知會與基督教聖公會的關係,就是說,日知會中的大多數都是基督徒,許多教友是投筆從戎的革命志士,有的還是國外歸來的留學生,也就是魯迅所說的「覺悟的知識者」。這裡提供的歷史細節告訴我們,辛亥先驅者的「覺悟」,絕不是為了「翻身」、「坐天下」,而是在民族民主革命要求中包含帶有西方人文主義普世價值的宗教精神和犧牲精神。孫中山1912年元月1日正式公佈的《中華民國國歌》的首兩句:「東亞開化中華早,揖美追歐,舊邦新造」,就充分說明那場革命的性質和精神資源的由來。孫中山本人就是基督徒,武昌首義之前的許多反清革命活動也與教會有關,特別是武昌首義革命黨人與清軍的激戰中,以聖公會為主的基督教在武漢的部份教會都給予了全力協助與支持。
我原來沒有注意過宗教問題,因為不信也不懂;「子不語」和「無神論」影響了我的大半生。是文熹的言談和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我的看法和態度。他不是教徒,也未必精通哪一教的教義,但他能以同情和理解的態度對待不同教派,饒有興味地參與他們的活動並給予幫助。在聽他向我講述這一切的過程中,我逐漸明白:他是把這當做一種文化而融融其間的。確實,宗教問題可以說也就是文化問題,問題的核心都是「人」--仁愛、慈悲、博愛,以及逍遙、兼愛等等,無不是對人的關愛。孟子所說的「四端」之首就是「仁」,即「人皆有之」的「憐憫之心」。裡面對祇剩下「飲食男女」而文化宗教皆成為其工具和奴僕的花花世界,心懷悲憫、勾畫出不同的世態人情,不也是如魯迅所說,是為了「揭出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嗎?
二○一二年農曆重陽節於武昌東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