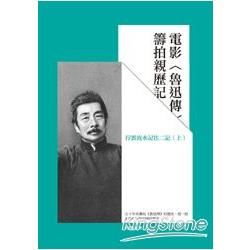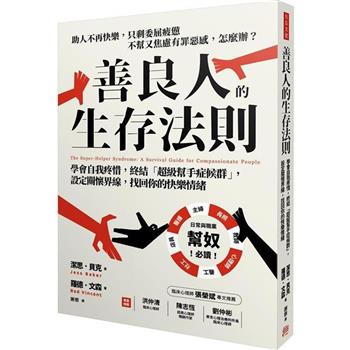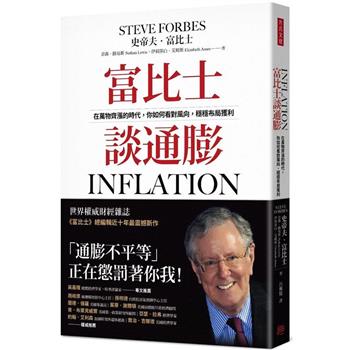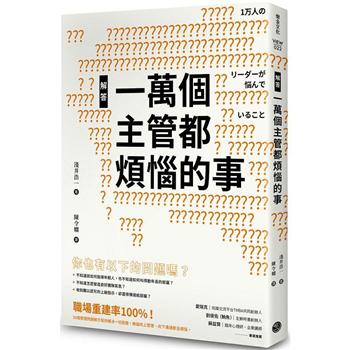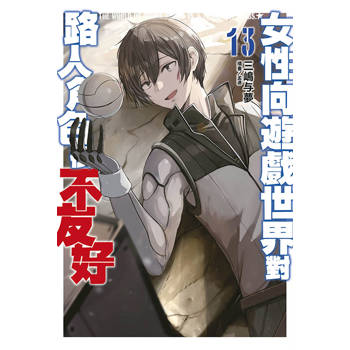前言
沈鵬年
北京守愚齋章詒和大姊關於人生的精闢概括,引起我深深的共鳴。她說:「人的一生,童年有遊戲,中年有經歷,晚年有回憶。其間自有許多變化,但人對自己的理解沒有變,對生活的基本態度和情感傾向沒有改變。這是什麼?這就是文化。它也正是我們寫作的惟一緣由。」——我如今已屆85歲高齡,回眸平生,所具有的也無非是童年遊戲、中年經歷和令人難忘的回憶而已。電影《魯迅傳》則是我畢生最為重要的親身經歷。
(一)
我童年遊戲中印象最深的,在祖居三學書屋中找到了有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腳的鳥和生著翅膀的人的繪圖《山海經》,我把書中所見告訴了積玉、懷大、慶生等小同學,他們不信,用香煙畫片打賭,有書為證,我贏得了許多「水滸」、「三國」的香煙畫片。從此萌發了我鑽古書看繡像的興趣;稍後,在嗣母攜領下去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看書購書,嗣母說這是「人生的心路旅行」,是「知識的汪洋大海中學習游泳……」。她讓我熟讀新詩、散文和小說,教我從書本上認識了魯迅。書香門第的薰陶,我童年遊戲的良伴便是開始玩弄新文學版本書。嗣母的溺愛和慷慨,她帶我去內山書店購到了魯迅、西諦親筆簽名的第二十六號《北平箋譜》和皮脊燙金的《海上述林》;她給我金條從一個記者手中交換了新文學版本中最珍貴的1909年印自日本東京的《域外小說集》;她為我向宋慶齡、蔡元培領銜的魯迅紀念會用大洋百元訂購了柚木箱紀念本《魯迅全集》(我的限定版編號是第四十五號);她給我鉅款從陳世芳(解放後曾任上海舊書店門市部主任)的舊書鋪購了阿英所藏流散的部分新文學珍本書。平心而論,這一些都是新文學書中「頂級」「極品」。於是,年方十六就在拉都路小洋樓佈置了兩周(魯迅和知堂)初版書的「皕週一廛」藏書室,儼然以小小藏書家自居。就這樣,從童年到青年,淘舊書舊期刊、玩新文學版本,成了我惟一的癖好、最大的樂趣和一生的最愛。這種童年遊戲養成的癖好和樂趣伴隨著我的生命,經歷了種種風險,度過了近八十個春秋。作為一個新文學版本書的老玩家,我是「藏以致用」。早在1946年已向郭沫若出版《文集》提供了他早年譯文歌德的《赫曼與竇綠苔》;「文革」浩劫中向俞平伯、豐子愷出示「五四」時代的珍本《憶》和《燕知草》,使他們得到了慰藉;後來又用珍藏五十多年的歷史資料寫了8萬字的《文以載道•秀出天南》,為文史大家金性堯討回公道;阿英之子錢厚祥籌編《阿英全集》,向我借去了珍本書27種(借條至今還在);最近媒體盛稱的許廣平《魯迅回憶錄手稿本》,許多原始祖本來自我的珍藏……。1956年上影廠攝製由佐臨導演的《魯迅生平》紀錄片,其中有《域外小說集》的特寫鏡頭,這兩冊原書是我提供的;1964年天馬廠攝製由謝晉導演的彩色故事片《舞臺姐妹》,影片中有主角竺春花(謝芳主演)由地下黨員(女記者)江波陪同參觀「魯迅作品展覽會」的場景,作為道具的全部魯迅著作是從我家借去的。我童年遊戲的良伴珍本通過銀幕面向廣大觀眾,也是十分有趣的。凡此種種,足以為章大姊所說「童年的遊戲」也「是文化」一部分的佐證。
更加可以告慰嗣母的,由於「童年遊戲」的積累,在我26歲時結集出版了新中國建國以後第一部容量40萬字的《魯迅研究資料編目》,從而使我具備了在夏衍、葉以群等前輩領導下參加電影《魯迅傳》創作和籌備的資格。市委宣傳部因而調我為電影《魯迅傳》負責資料工作。
(二)
我一生刻骨銘心、最難忘懷的,是從32歲開始參加創作和籌備拍攝電影《魯迅傳》。它使我獲得了畢生最大的幸福和歡樂;也從而經受了長期的磨難和痛苦。我原來是中共長寧區委的國家幹部、上海作家協會會員,32歲借調、35歲(組織決定用另一黨員幹部對調)而正式調入電影廠的。
在此期間,有幸親承周恩來、柯慶施、李立三、石西民、周揚、夏衍、林默涵、邵荃麟、陽翰笙等前輩謦欬,當場記錄了他們的意見和指示;去魯迅生前生活和工作的紹興、杭州、北京、廣州和上海等地遍訪了數百位知情者,獲悉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使我擴展了眼界、增長了見聞、豐富了學識、提高了水平,感到難以言宣的歡欣和振奮。古人雲:「朝聞道夕死可也。」我人生的殊勝因緣,任何福祉,實無逾於此者。幸福滋生力量,我以業餘時間整理編印多冊《訪談記錄集》;用新的材料編著《魯迅生平及有關史事年表》供內部參考;寫了近百篇調查報告為電影張目。我在電影廠為創作《魯迅傳》文學劇本沒日沒夜地忘我工作,甚至連慈母在家鄉病危臨終也未能去見上最後一面;不幸的是,儘管籌備費化了50多萬,電影未能拍攝,我又為沒有攝成的《魯迅傳》電影經歷了一連串的政治運動。我為它在「四清」時挨過「整」;我為它在「文革」中受盡迫害。好不容易「四人幫」被粉碎了,我為它在「清查」和「整黨」時又幾乎過不了「關」……。苟活到61歲,組織要我離休,一事無成,兩鬢已斑。沒有拍攝的電影《魯迅傳》猶如永恆的夢中情人,使我魂牽夢縈,懷念無窮;又好似冥冥中的索命「無常」,對我勾魂攝魄、心憾終身。我收穫了無限的幸福,又背負了無端的讒言和誣陷。行無愧怍心常坦,心底無私天地寬,相信歷史是歪曲和抹煞不了的。
沒有拍攝成的電影《魯迅傳》構成了我中年時代的全部經歷。我經歷了幸福、經歷了歡樂、經歷了磨難、經歷了痛苦……。我感到影片未能拍攝的永遠的遺憾,但沒有虛度年華而後悔。因為我保存了歷史——最寶貴的文證等原始資料。——正如章大姊所說:「這就是文化」。
(三)
離休前夕,奉命為電影《魯迅傳》做的掃尾工作,就是1985年12月25日夏衍前輩授意我根據《魯迅傳》藝術檔案,寫出四萬多字的《巨片〈魯迅傳〉的誕生與夭折》。根據我的筆記,夏衍前輩說:
電影《魯迅傳》誕生與夭折這件事,被歪曲和湮沒二十多年了。這本來是一項嚴肅的創作任務,涉及我們黨當時按照文藝特性和藝術規律領導文藝的一
次實驗。大躍進和國民經濟嚴重困難,黨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和科技、文藝界的廣州會議,創作民主和政治寬鬆的空氣比較濃厚。編劇和導演對數易其稿的電影文學劇本定稿後繼續堅持不同意見,有點過份。劇本上集的四章結構是編劇導演共同擬訂、並經創作顧問團專門開會審議通過的。這是影片的底線。讓趙丹、藍馬、於是之、謝添、于藍、石羽等影劇界的精英在銀幕上各顯神通,來一場電影「群英會」總是藝壇盛事吧!遺憾的是,在市委下達拍攝命令、西民同志指出「劇本不宜再作變動」後,導演認為分鏡頭的自由不能發揮,住進了醫院,我們沒有及時提出強有力的措施,也失職了。
夏衍前輩囑咐:文章從事實出發,寫清楚歷史真相,不追究個人的責任。涉及編劇、導演和黨委負責人,一律「淡化」處理。還說:柯慶施提倡寫「十三年」是執行毛主席的意見,他並沒有反對拍《魯迅傳》。
——因此,拙文在《下篇•功虧一簣》第六、第七節中把電影夭折涉及的人和事全部「淡化」處理,語焉不詳了。
拙文寄給夏衍前輩後,1986年4月28日得到復信:
「來信及大作已拜讀,並已轉請喬木、周揚同志審閱,他們如有意見,當再奉告。」
接著他來上海治療眼疾,約我在醫院見面,轉告了「喬木、周揚同志」同意發表的「意見」,於是拙文便在學林出版社同年11月出版的《生活叢刊》作為「特稿」全文發表。
發表拙文的《生活叢刊》由新華書店發行,外銷港臺和美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讀了拙文給我來信,肯定拙文前半部分,對後半部分提出質疑。他說魯迅被毛澤東主席奉為「新中國的聖人」,拍《魯迅傳》電影得到周恩來總理大力支持,為何區區一個張春橋竟敢致《魯迅傳》胎死腹中?!他希望把事實真相公諸于眾。我當時謹記夏公的囑咐,保持了沈默。事過境遷,汲取教訓,何必糾纏於個人的是非……
夏公德高望重,人稱「電影祖師爺」。對《魯迅傳》電影投產拍攝,殫精竭慮、煞費苦心。花盡心血惹來無謂口舌,無奈中瀟灑地道「濕手捏了燥乾粉」,希望「儘快定稿,不要錯失良機。」《魯迅傳》流產二十年後,為進一步回答海外論客質疑,囑咐「只寫事實,淡化個人,不糾纏是非」。前輩風儀,不可企及。
事隔半個世紀,竟然有人繪影繪聲、無中生有,說什麼1963年3月導演、演員正在拍攝現場,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下令「《魯迅傳》停拍!」於是主演「痛哭流涕,剃去鬍子」;導演「氣得一病不起,長住醫院」。——果真如此嗎?
請看前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上海電影局黨委書記、電影局長兼上影廠長吳貽弓主編的「上海市專志系列叢刊」《上海電影志》的記載:
「1961年3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在杭州召開座談會,座談天馬(廠)準備投產的故事片《魯迅傳》文學劇本問題。夏衍在滬期間多次與《魯迅傳》主創人員交換意見,並參加劇本修改。但由於對劇本的意見無法統一,外借人員合同到期,後報請中共中央宣傳部同意,決定暫停投產。」(見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上海電影志》第68頁。)
這條權威性的記載,揭示了歷史的事實真相。
《魯迅傳》電影最後「暫停投產」的關鍵,在於「對劇本的意見無法統一」。此事與兩年後提出「大寫十三年」的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風馬牛不相及」。
我是籌攝《魯迅傳》全程參與的親歷者,現場記錄「對劇本的意見無法統一」的當事人。為保存歷史而轉輾藏匿這些原始文證,忍辱負重逾半個世紀。應該將事實公諸於眾了。夏衍在《舊夢錄自序》寫道:「記事離不開論人。明知其有,而加以隱諱,就是失真。」《魯迅傳》創作組長葉以群含冤而死四十五年了,「交遊零落,只今餘幾!」實錄其事,還他公道、是後死者的責任。
(四)
流光如駛,夏衍前輩仙逝一十五載,令人不勝懷念。根據檔案,夏衍前輩對我的資料工作有過評價。
1961年7月,夏衍前輩在翠明莊修改《魯迅傳》劇本時要我做他的助手。同年8月11日他在一份文化部印發的文件中寫道:
「重大歷史事件的真實性,這是原則問題。我在修改(《魯迅傳》劇本)中幾次叫沈鵬年同志查核材料,也大都是歷史事件方面的材料。……我是核對了魯迅在這個時期的所有雜文、書簡,又查了陰陽曆對照表,力求做到一時一事、季節、氣候、服裝、花木的開謝等等,即使不能做到『無懈可擊』,也要盡可能做到『少』懈可擊。對此,我曾和你們講過笑話,我說即使有一事不符,可能大多數觀眾不會有意見,但如沈鵬年同志等特殊觀眾,卻是連一點點小漏洞也一定會看出來的。」(見文化部1961年8月16日列印第116號檔)
1963年12月他在《電影論文集》第273頁(1985年1月重版本第261頁)公開寫道:
「《魯迅傳》的創作,資料工作搞得很好,改編時就有了依據。」
這是夏衍前輩對我的愛護和鞭策,衷心銘感無已。夏衍前輩所說「歷史事件的真實性,這是原則問題」,成為我資料工作的座右銘,永志不忘。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行雲流水記往二記(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37 |
中文書 |
$ 356 |
電影 |
$ 396 |
電影 |
$ 405 |
電影實務 |
$ 405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行雲流水記往二記(上)
這部《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內有大量的史料詳盡地告訴我們,尊重歷史是攝製組的重要特色,對劇本中涉及到的重要歷史事件,都取嚴肅認真的態度,不搞「戲說」,都在遵循不違背「歷史真實」的原則下進行創作。內容彙集了各位大師以及普通創作人員,對社會主義電影理論,電影創作等方方面面的探討,其中不泛精闢見解,珍貴異常,這是電影《魯迅傳》創作過程中,留下的一筆寶貴財富。
本書特色:
本書內容彙集了各位大師以及普通創作人員,對社會主義電影理論,電影創作等方方面面的探討,其中不泛精闢見解,珍貴異常,這是電影《魯迅傳》創作過程中,留下的一筆寶貴財富。
作者簡介:
沈鵬年
中國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曾任上海電影集團幹部,研究電影及現代文學史料達二十餘年。
章節試閱
前言
沈鵬年
北京守愚齋章詒和大姊關於人生的精闢概括,引起我深深的共鳴。她說:「人的一生,童年有遊戲,中年有經歷,晚年有回憶。其間自有許多變化,但人對自己的理解沒有變,對生活的基本態度和情感傾向沒有改變。這是什麼?這就是文化。它也正是我們寫作的惟一緣由。」——我如今已屆85歲高齡,回眸平生,所具有的也無非是童年遊戲、中年經歷和令人難忘的回憶而已。電影《魯迅傳》則是我畢生最為重要的親身經歷。
(一)
我童年遊戲中印象最深的,在祖居三學書屋中找到了有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腳的鳥和生著翅膀的人的繪圖《山...
沈鵬年
北京守愚齋章詒和大姊關於人生的精闢概括,引起我深深的共鳴。她說:「人的一生,童年有遊戲,中年有經歷,晚年有回憶。其間自有許多變化,但人對自己的理解沒有變,對生活的基本態度和情感傾向沒有改變。這是什麼?這就是文化。它也正是我們寫作的惟一緣由。」——我如今已屆85歲高齡,回眸平生,所具有的也無非是童年遊戲、中年經歷和令人難忘的回憶而已。電影《魯迅傳》則是我畢生最為重要的親身經歷。
(一)
我童年遊戲中印象最深的,在祖居三學書屋中找到了有人面的獸、九頭的蛇、三腳的鳥和生著翅膀的人的繪圖《山...
»看全部
作者序
序
成恒健
「老人莫『懷舊』,『懷舊』勞神傷身。」然而對有些老年人來說,某些「舊事」十分重要,不懷念,不說清楚,就是對歷史不負「責任」。
共產黨人最講認真,最看重自己的「責任」。沈鵬年就是這樣一位老先生,85歲的高齡,身子骨又不算硬朗,打針吃藥自不必說,還時不時地住院,請醫生療理病症。就是這樣一付身板,不管是暑夏,還是寒冬,拄著一根竹節手杖,起早貪黑,東奔西走,跑圖書館,鑽資料室,為整理自己走訪積累的數十萬字資料作補充訂正,前後逾三十年,辛勤編撰,終於成冊。「健康誠可貴,理念價更高」,為了盡到一個共...
成恒健
「老人莫『懷舊』,『懷舊』勞神傷身。」然而對有些老年人來說,某些「舊事」十分重要,不懷念,不說清楚,就是對歷史不負「責任」。
共產黨人最講認真,最看重自己的「責任」。沈鵬年就是這樣一位老先生,85歲的高齡,身子骨又不算硬朗,打針吃藥自不必說,還時不時地住院,請醫生療理病症。就是這樣一付身板,不管是暑夏,還是寒冬,拄著一根竹節手杖,起早貪黑,東奔西走,跑圖書館,鑽資料室,為整理自己走訪積累的數十萬字資料作補充訂正,前後逾三十年,辛勤編撰,終於成冊。「健康誠可貴,理念價更高」,為了盡到一個共...
»看全部
目錄
序
前言
第一章 中國電影史上的盛舉──籌拍《魯迅傳》
一、田一野文章是回答海外媒體的質疑
二、拍攝電影《魯迅傳》是時代的需要
三、為葉以群搞資料、借調作協三個月
四、訂出《攝製準備工作計畫》、成立攝製組
五、新華社對《魯迅傳》的追蹤報導、媒體大力宣傳
第二章 許廣平對《魯迅傳》攝製組極大支持
一、擔任創作顧問團顧問,為劇本提供豐富素材
二、認真審閱劇本,提出書面意見
三、應葉以群之請,出面約李立三談話
四、幫助演員于藍,塑造影片中許廣平形象
五、對資料工作的具體支持和鼓勵
第三章...
前言
第一章 中國電影史上的盛舉──籌拍《魯迅傳》
一、田一野文章是回答海外媒體的質疑
二、拍攝電影《魯迅傳》是時代的需要
三、為葉以群搞資料、借調作協三個月
四、訂出《攝製準備工作計畫》、成立攝製組
五、新華社對《魯迅傳》的追蹤報導、媒體大力宣傳
第二章 許廣平對《魯迅傳》攝製組極大支持
一、擔任創作顧問團顧問,為劇本提供豐富素材
二、認真審閱劇本,提出書面意見
三、應葉以群之請,出面約李立三談話
四、幫助演員于藍,塑造影片中許廣平形象
五、對資料工作的具體支持和鼓勵
第三章...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沈鵬年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3-09-10 ISBN/ISSN:978986326116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86頁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