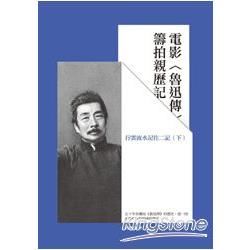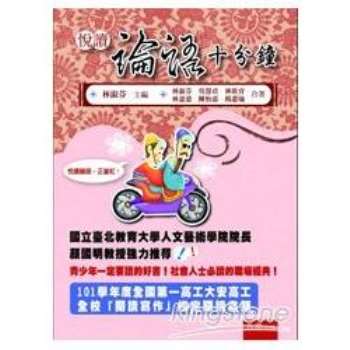五十年前籌拍《魯迅傳》的歷史,是一段值得珍惜和回味的歷史。
這部《電影〈魯迅傳〉籌拍親歷記》內有大量的史料詳盡地告訴我們,尊重歷史是攝製組的重要特色,對劇本中涉及到的重要歷史事件,都取嚴肅認真的態度,不搞「戲說」,都在遵循不違背「歷史真實」的原則下進行創作。內容彙集了各位大師以及普通創作人員,對社會主義電影理論,電影創作等方方面面的探討,其中不泛精闢見解,珍貴異常,這是電影《魯迅傳》創作過程中,留下的一筆寶貴財富。
本書特色:
本書內容彙集了各位大師以及普通創作人員,對社會主義電影理論,電影創作等方方面面的探討,其中不泛精闢見解,珍貴異常,這是電影《魯迅傳》創作過程中,留下的一筆寶貴財富。
作者簡介:
沈鵬年
中國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曾任上海電影集團幹部,研究電影及現代文學史料達二十餘年。
章節試閱
陳荒煤同志對《魯迅傳》第五稿意見
1962年1月20日在錦江518室
昨天又將五稿看了一遍,存在的幾個問題,應該說是老問題……
默涵同志說的「事件太多」。我體會這「多」是指:與魯迅無關的、交代時代的東西太多了;同時又沒有選擇好每個時期中最能代表和突出魯迅的東西予以精煉的容納和吸收。因此現在的篇幅就顯得過長了,將超過15本,可以拍兩集——當然,像魯迅這樣的人物,拍三部也不為多,問題在於能深刻的通過藝術形象來反映他最動人的東西,而不是平鋪直敍的介紹他的生平。四間房(即四章)不能平分秋色,要以人物的中心事件為主,可能一章就小,二章稍長一些……。總之要大刪,刪的原則是堅決保留與人物思想發展直接有關、而刪去不必要的無關的枝節部份。現在的寫法有點像編年史,而不是藝術概括:有點像歷史,而不像史詩,史料甚多,詩意不夠。
表現手法上一定要注意電影特性,旁白可以減少,開頭介紹魯迅的一大段沒有必要。假使觀眾通過電影引起了進一步研究魯迅的興趣,那就請他去看王士菁的《魯迅傳》好了。有許多問題不必全靠電影解決。第12頁的旁誦,介紹魯迅抄古碑「麻醉自己的靈魂……」用了許多報紙和標題,這是純粹交代性的手法,又占篇幅又費事,觀眾又不易懂。而范愛農的戲最少,但完整,有感情,很動人。因此表現手法一定要注意電影特性。
這部片子,還要考慮出國的問題,而外國有些傳記片是拍得很好的:如《居里夫人》、《左拉傳》、《筆伐強權》、《巴士特傳》、《蕭邦傳》等等。因此,我們的《魯迅傳》決不能使人家看了感到失望,甚至說:「這是藝術記錄片,而不是藝術傳記片。」
寫時代應該有虛有實、有明有暗,這樣可以省出篇幅,充裕的刻劃人物。現在卻全用實寫了,如五四運動寫它從火燒趙家樓到車站南下送行,但寫魯迅則不足,結果很可能有錯覺;魯迅只是冷眼旁觀,冷言嘲諷……,那麼轟轟烈烈的運動在開展,他卻無所適從……。
某些史料雖然重要,但不合電影化的要求就不用。第三章開頭部份:胡適高升,李大釗搞工運,農民逃荒,魯迅教書……以及魯迅許多作品的篇名等等,既難處理好,觀眾又看不懂。
寫魯迅與正人君子的戰鬥,用現在這樣的對比方法好不好,值得考慮,一面魯迅是面帶病容、咳嗽服藥、勉力作文;一面陳源則西裝畢挺,僅僅擦擦眼睛,稍感煩燥而已,(特別在第24場中)相形之下,顯得魯迅的鬥爭是如此吃力,且有滑稽之感。
默涵同志還談到「語言問題」,這個意見提得很好。如果把魯迅在文章中反映的思想性很高又非常尖銳的文句,硬要改為他日常生活中的對話,就顯得不自然。我曾經見過他二次,談話非常樸實,並不出口成章,每句話都是對時代下結論似的。魯迅是偉大的,但卻寓偉大于平凡之中。如果銀幕上的形象,只是通過講一些警句式的話,並不能表現出他的偉大來。有許多後來講的話,也沒有必要提前。
其他一些問題:
(1)伏筆痕跡太露:如小孤孀、瘋子為《狂人日記》伏筆;阿有為《阿Q正傳》伏筆,形象可以出現,但痕跡太露不好。想在第一章內把魯迅作品中所有人物都集中表現,這是不合適的。似乎魯迅之所以寫《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僅僅由於一、二個印象的促使,反而把整個作品的社會意義縮小了。
(2)對作品的影響和評價,不一定也不是銀幕上所能解決的:如《阿Q正傳》出來後,寫有些人的猜測,這不合適。寫了魯迅為什麼要寫這部作品這就夠了,至於作品的影響如何?這就不是電影所要交代的了,也不必再去交代。
(3)其他人物中:王金發的問題還沒有全部解決,如范愛農摩頭、與章介眉同座等,均待改。段祺瑞和日本顧問下棋,有重起之感,似無此必要。錢玄同太高了。
(4)寫魯迅,既不能寫成是受苦受難的傳教士;也不要表現為「赤膊上陣」的戰士。現在這兩者都有一些,有些像傳教士和赤膊上陣的混合體。有幾場好一點,有幾場不如從前,如點名一場……。點名和辭職等是好戲,的確表現了魯迅的性格。
具體工作如何做?
希望導演寫一個報告:對劇本的進展和不足,已解決的問題和尚存在的問題提出意見;文學本基本上告一段落,導演在分鏡頭前先搞一個分場提綱,使之更接近於電影化。分場提綱上可以吸收五稿發表以後的意見,徵得作者同意,為分鏡頭作準備。這樣有個交代,白塵同志也不致等待。這個意見待市委宣傳部批准後,抄報中宣部、文化部。修改提綱出來後,要白塵來或者你們去北京,到中宣部約了白塵當面再談。這不是一般作品,這件事急不得,欲速則不達,但一定要搞好。
陳荒煤同志對《魯迅傳》第五稿意見
1962年1月20日在錦江518室
昨天又將五稿看了一遍,存在的幾個問題,應該說是老問題……
默涵同志說的「事件太多」。我體會這「多」是指:與魯迅無關的、交代時代的東西太多了;同時又沒有選擇好每個時期中最能代表和突出魯迅的東西予以精煉的容納和吸收。因此現在的篇幅就顯得過長了,將超過15本,可以拍兩集——當然,像魯迅這樣的人物,拍三部也不為多,問題在於能深刻的通過藝術形象來反映他最動人的東西,而不是平鋪直敍的介紹他的生平。四間房(即四章)不能平分秋色,要以人物的...
作者序
後 記
以半個世紀前的原始文證為依據,把現場親身經歷的《電影〈魯迅傳〉籌攝實錄》告一段落,想起魯迅先生第一部文集《墳》後記引錄的古詩:……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淒傷!——不免感慨繫之。
——「大戀」何所存?緣何而「淒傷」?
(一)
何謂「大戀之所存」?
這裏保存著新中國建國初期文壇——影壇關於籌攝電影《魯迅傳》的最真實的歷史。若干年來,坊間出現了不少有關電影《魯迅傳》杜撰的離奇故事,使人眼花繚亂,難識「廬山真面目」。本書提供的第一手資料,請廣大讀者、學者、研究者鑒賞和鑒別。
這裏保留著「魯迅研究史」上一段珍貴的秘笈。周揚、夏衍、邵荃麟、陽翰笙、馮乃超諸前輩的「魯迅觀」,過去鮮為人知。通過籌攝電影《魯迅傳》,他們的「魯迅觀」暢談無遺。由於本書的出版,當年的咳吐珠玉、不會隨風而逝、化為煙埃而消失。——這對今後的「魯迅研究史」也算提供了一份新的研究資料,可供專家、學者們咀嚼、體味、思考後作出各自的判斷。
這裏還有我過去的生命的一部份——逝去青春的餘痕。從「而立」之年到耄耋高齡,我在「上影」廠消磨了半個多世紀的歲月。也是我在「上影」集團曾經工作過的證據。人生多苦辛,磨難何所懼,憑這一點得到了一些安慰。這是非常值得留戀、值得紀念的。
這裏顯示了夏衍同志所說「這是一項嚴肅的創作任務,涉及我們黨當時按照文藝特性和藝術規律領導文藝的一次實驗。」電影《魯迅傳》如果攝製成功,就是貫徹「文藝八條」的一個範例。可惜功敗垂成。建國十七年間,中央和上海市委有關領導如此具體而直接抓一個「劇目」,是前所未有的。當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對魯迅是很尊重的,他一到上海,便批准在虹口公園建設新的魯迅紀念館;1956年10月14日魯迅靈柩從萬國公墓遷葬虹口公園,柯慶施親扶魯迅靈柩送葬;接著創議拍攝電影《魯迅傳》。
據《魯迅傳》創作組組長葉以群同志親口告訴我:拍攝電影《魯迅傳》要起用一個「非黨導演來執導」的決定,也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同志「拍板」的。柯慶施認為「電影《魯迅傳》攝成後要面向外國,用一個國民黨熟悉的『非黨導演』執導,至少胡適那幫人看了就沒有話說了」。陳鯉庭在創作組中之所以敢於抵制葉以群寫的劇本、陳白塵寫的劇本、夏衍寫的劇本……,「有恃無恐」,其源蓋出於此。
——《電影〈魯迅傳〉籌攝實錄》也是順應魯迅研究工作者所需要的。2008年葛濤先生兩次賜函云:「聽說您已經80多歲了,倘若您再不把您所知的歷史真相披露出來,後人將會受到一些魯學家的誤導,無法真實地瞭解到您所做訪談工作的真正的價值!」葛濤先生還說:「很希望通過史料瞭解當年《魯迅傳》創作過程的真實面貌,……瞭解當時情況的當事人已經很少了,如不趕快把這些歷史資料收集、保存下來,將來的歷史會無法準確地記錄這件事的。」這些誠摯的期望給我以信心和力量,在上影有關老同志的支持下,基本上把「當年《魯迅傳》創作過程的真實面貌」公諸於眾。至於葛濤先生「關心的」關於「《魯迅傳》創作組和攝製組的一些細節故事」,雖然涉及了一部份,尚未能全部托出,比如記載在石羽筆記中的《導演報告》,本是攝製組中一件大事,書中一字未提,此中隱情尚待進一步披露。
(二)
那麼,我究竟緣何而「淒傷」?
「狂臚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後起緣。」我學習、研究魯迅的「緣」始於1936年10月20日萬國殯儀館瞻仰魯迅先生遺容。在恩師張瓊的教導下,我立下了「情系魯迅獻終身、不求依附但求真」的誓願。——八十五度春秋證明我沒有違背早年的心願。
我出身名門、是具有一定資歷的魯迅研究工作者,為人一貫低調、與世無爭。
可是,近三十年來,尤其是在近幾年,魯迅研究領域個別新秀,(如陳某、王某)在權威刊物發文,指名污蔑我。我不願和後輩爭短長,置之不理。不少好心朋友為我著急,說他們用納粹法西斯戈培爾「謠言千遍會變『真理』的故伎」,欲去我而後快。嚴肅勸我:即使自己不以為意,身背黑鍋,世人不察,也是對歷史和子孫後代不負責!
朋友的話,言之有理。但我知道:我與這幾位新秀素不相識、從未謀面,毫無個人恩怨。他們只是誤聽偏信了他們某師長對我的誣陷不實之詞,跟著起哄……。謠言固然止于智者,必要的說明也是應該的。——為此,針對某新秀瞎編我的身世,茲將家世簡略交代:
我出身洞庭東山沈氏家族,是一個具有「革命」傳統的家庭。
先曾祖錫章公是追隨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光復上海有所貢獻。中華民國元勳張人傑(即張靜江)親題「源遠流長」匾以表彰。抗戰爆發,先祖裕春公為「愛國、擁共、抗日」向中共領導的「江抗」(新四軍前身)捐獻軍糧大米二百石(每石156斤)。為此,日寇侵佔東山,我家三學書屋遭日寇焚毀。(見《東山歷史文化叢書》記載)
早年,我從內山完造先生手中購得的《海上述林》和《北平箋譜》;經地下黨職工委書記彭柏山先生介紹向魯迅紀念會購得的木箱紀念本《魯迅全集》(編號第45號)保存至今均已超過七十五年。我以黃金向《文匯報》一記者換來的1909年日本東京版《域外小說集》,珍藏至今亦逾六十年。我千辛萬苦覓得的新文學珍本書如:新潮社初版本《呐喊》;魯迅親筆簽名本《兩地書》;豪華版《蘇聯版畫集》;胡適親筆簽名的《四十自述》;郁達夫親筆簽名的《達夫全集》;徐志摩、陸小曼親筆簽名的《愛眉小札》;茅盾布面精裝本初版《子夜》;以及周作人、郭沫若、蔣光赤、柔石、胡也頻、李偉森等舊社會的以及胡風和胡風集團等新社會的「禁書」、「珍本」(還有如郭沫若《一隻手》、《瓶》、《前茅》、「反蔣檄文」以及當年共青團員施蟄存《追》等)歷經日本侵略者的黑色恐怖、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文革」浩劫的紅色恐怖,由於老伴陳雪萼和長女育群等的多次轉移、苦心保護,依舊完好無損。不妨借「剝」魯迅先生贈許廣平詩以自勉:
「七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藏書」怡倦眼,此中甘苦兩心知。
值得自豪的,我保存了胡風在魯迅先生支持下編的《木屑文叢》,在雪峰支持下編的《工作與學習叢刊》,以及胡風的第一本文集《文藝筆談》、《密雲期風習小記》等初版本,經我在上影的「文革」難友朱微明同志(彭柏山夫人)介紹,提供給剛出獄的胡風先生。為此胡風先生要梅志先生給我回信,表達「胡風(對我)的感謝」。在舉世傾國的「反胡風」高潮中保存胡風的「手澤」(有胡風親筆簽名)珍籍,首先要感謝我老伴陳雪萼的密切配合。
——再套用一句《水滸》的話「天可憐見」!我是一個「不愛名利只愛書」的共產黨人。我出身富裕的書香門第,在張瓊等恩師教育下,半工半讀,走上革命道路,歷經艱難,榮獲了建國六十周年的紀念章。
上海解放前,我在中共地下黨直接領導下工作的片斷,被載入《中共上海黨史資料選輯•洞庭東山旅滬職業青年革命活動史料》第二輯第43頁(附下)上海總工會編、勞動出版社出版《上海工運史料》對我也有記述。
由於我力所能及,盡了一個共產黨員應盡的義務,2002年至2004年曾三次受到上海市一級組織的表彰和獎勵。(見於上海市委的和上海總工會的有關報刊)
我整理的禪宗典籍《古尊宿語錄》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後,正好旅居美國紐約,辭謝了美國宗教研究院沈家楨院長邀我為該院「研究員」的聘請;我們幫助撫育了兩個美國外孫,美國女婿贈與萬元美金鉅款,我們全部捐給了美國國際兒童救濟中心和上海兒童福利院(均有證書);不願離開祖國,多次拒絕當美國「移民」。——由此可見,富貴榮華於我如過眼雲煙,不屑一顧。
但是,由於在研究魯迅領域和籌攝《魯迅傳》過程中,「得罪」了兩個「權力」者,他們通過《魯迅研究月刊》等媒體,把我誣陷為「偽造」歷史的「騙子」?!在國內刊物「封殺」、不給我發表文章……。對此我從不計較,但事實真相不容混淆、應該辯明。
——我一生清白,無端遭誣,申訴無門,能不「淒傷」!
(三)
這兩個權力者,其實是我的熟人和同事:
第一位是前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顧問唐弢。
結怨起因:1947年美帝國主義正在以飛機槍炮大力支援蔣介石破壞國共和談、公開鎮壓共產黨、進攻解放區時,身為《文匯報》編委的唐弢在同年的《文匯日記》題詞:「在政治上學習歐美,在經濟上學習蘇聯,這是今天中國民主運動的正確方向。」這在當年是被認為「不正確」的態度。是共產黨公開批評的「第三條道路」的主張。
——1957年唐弢在上海作協爭取入黨,作協副主席兼書記葉以群徵求我對唐弢的意見,我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把唐弢手跡的照片交給以群,希望幫助唐弢提高覺悟、端正入黨的認識。——唐弢為此對我恨之入骨。
第二位是前天馬電影製片廠廠長、《魯迅傳》導演陳鯉庭。
結怨起因:我奉命在徐家匯藏書樓查閱三十年代舊報刊時,在1933年12月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機關報《民報》上,看見陳鯉庭連續三天發表「痛恨共產黨」的「緊要啟事」。我頓時大吃一驚,自己是黨員,卻在為「痛恨共產黨」的導演工作,感到不安。便要藏書樓代攝了這三天報紙的照片,報告廠黨委。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本來這些陳年爛瘡疤不揭也罷。不料,時至2008年,這位百歲老人並不諱言自己在1933年被國民黨反動派「一批鬼鬼崇崇的特務」抓捕的「歷史」。「知恥近乎勇」是傳統美德,可惜他未能循著歷史的本來面目,讓讀者感知當年真實的狀況,卻以時代相隔久遠而「粉飾歷史」,為國民黨特務大唱讚歌。例如在他授意下寫道:
「陳鯉庭走上電影道路……,得以在報紙上寫電影評論文章,又該拜謝逮捕他的特務。……陳鯉庭被捕,送進了員警總局。唯一的一次傳訊是談話式的,……審訊者將信將疑,又把陳鯉庭轉移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主管這裏軍法處的處長叫陶百川,此人居然在上海《民報》副刊當主編,屬於半個文人,……向陶百川交涉說情,據理力爭,陳鯉庭終於走出牢門,見到了明媚的陽光。」(見《遙遠的愛———陳鯉庭傳》2008年10月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第36——37頁)
陳鯉庭口中「通情達理」的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反映在魯迅先生筆下是「忍看朋輩成新鬼」的柔石、殷夫等左聯五烈士英勇犧牲之地;也是「龍華千古仰高風,烈士身亡志未窮,牆外桃花牆裏血,一般鮮豔一般紅」的血淚遺址。魯迅先生在1936年4月15日還沉痛地寫道:
「……看桃花的名所,是龍華,也有屠場,我有好幾個青年朋友就死在那裏面,所以我是不去的。」
———這血淚斑斑的屠場居然使「陳鯉庭見到了明媚的陽光」。誤導青年,怎麼對得起柔石、殷夫等在龍華犧牲的無數革命先烈?!
夏衍同志說:
「1933年前後,國民黨反動派進一步加緊扼殺進步的國產電影運動,當時的『電檢會』,竟連『九一八』三字也不許在銀幕上出現,據說誠恐有傷『中日親善』;……到1933年底,藝華影片公司被『影界鏟共同志會』搗毀,電影院被『影界鏟共同志會』警告,要拒演田漢等的影片,魯迅先生以愛護和捍衛中國民族電影之熱誠,把這些反動的罪行都記錄了下來,寫在《准風月談》後記中,作為國民黨反動派迫害中國進步電影的歷史鐵證。」
事實是:陳鯉庭「走出牢門」是有條件的。「明」的條件,在國民黨的黨報《民報》上公開發表「痛恨共產黨」的《緊要啟事》,而且要連續刊登三天。至於「暗室操作」,則非外人所知了。因為陶百川和潘公展一樣,當年雖以「文人」面目現身於世,卻都是國民黨的文化特務頭子。從「電檢會」到「影界鏟共同志會」的所作所為都是出自他們「傑作」。
為了對歷史負責,有必要把真實情況披露如上。
(四)
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的普通黨員,從上海解放開始,我先後在黨的滬西區委、江寧區委和長寧區委工作近十年。在吳亮平書記和張祺書記的直接領導和關懷下,鼓勵我利用業餘和假日編著出版了《魯迅研究資料編目》和《革命先驅者論文化藝術》兩部百萬字的資料、工具、史料集。經過組織推薦,成為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會員。
中央和市委決定拍攝電影《魯迅傳》,市委宣傳部調我至上影《魯迅傳》創作組負責資料工作……,從此在上影耽了半個多世紀。
我真正為《魯迅傳》創作組工作,是1958年至1962年整整五年。五年中在夏衍和葉以群的直接領導、關注下,完成了中央和市委有關領導對《魯迅傳》創作的建議、意見的記錄整理;編著二十余萬字、全方位、多角度的《魯迅生平及有關史實年表》;訪問與魯迅有關的數百位元知情人的記錄、整理和編印;為主要演員趙丹、藍馬、石羽、于是之等塑造劇中人魯迅、李大釗、胡適和范愛農、王金發等角色寫了《創作手記》和《人物瑣談》;奉命整理發表了有關魯迅生平新史料的《採訪札記》近百篇;周揚寫信給我,要我為魯迅研究作出新的成績,夏衍、葉以群、陳白塵都鼓勵我編寫《魯迅歷史調查記》,為此收集了魯迅抄古碑、研究佛經和探索馬克思主義的大量材料……。
由於奉命查閱三十年代報刊時,發現1933年12月陳鯉庭在《民報》連續三天發表「痛恨共產黨」的「鄭重啟事」,我拍攝了照片,無意中得罪了陳鯉庭。於是,被「整」的厄運籠罩我二十多年。
早在1963年原《魯迅傳》顧問團負責人、文化部夏衍副部長在《電影論文集》公開稱我對「《魯迅傳》創作,資料工作搞得很好」;但陳鯉庭以廠長的權力「整」我所謂「貪污資料」。「文革」中「上海電影系統大批判組」批判他「把持《魯迅傳》創作組導演和行政大權」,「在《導演闡述》中叫嚷要把魯迅的愛表現為厚重寬大。」他說這是沈鵬年「製造假材料陷害他」……。
「文革」十年,我沒有政曆問題、也沒有「現行」問題。被「審查」十年的主要「罪名」就是所謂「製造假材料陷害陳鯉庭」……;
究竟是什麼「假材料」?——就是《魯迅傳》導演陳鯉庭在攝製組作過一次《導演報告》,電影術語《導演闡述》。——陳鯉庭否認作過《導演報告》反誣是「沈鵬年偽造」。
事實上,《魯迅傳》的主要演員石羽親筆寫的《魯迅組學習筆記——1961.2.28》中,明確記錄「第二階段理解魯迅——『導演報告』……」,這也是攝製組確實有過《導演報告》的旁證。
後 記
以半個世紀前的原始文證為依據,把現場親身經歷的《電影〈魯迅傳〉籌攝實錄》告一段落,想起魯迅先生第一部文集《墳》後記引錄的古詩:……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淒傷!——不免感慨繫之。
——「大戀」何所存?緣何而「淒傷」?
(一)
何謂「大戀之所存」?
這裏保存著新中國建國初期文壇——影壇關於籌攝電影《魯迅傳》的最真實的歷史。若干年來,坊間出現了不少有關電影《魯迅傳》杜撰的離奇故事,使人眼花繚亂,難識「廬山真面目」。本書提供的第一手資料,請廣大讀者、學者、研究者鑒...
目錄
第六章 天馬廠《魯迅傳》攝製計畫──1962年開拍
一、陳荒煤代表文化部同意《魯迅傳》定稿
二、楊仁聲代表市委宣傳部、電影局同意《魯迅傳》定稿
三、天馬廠接受《魯迅傳》定稿向市委、中央的報告
四、市委、中央批覆同意、天馬廠審議通過《魯迅傳》攝製計畫
第七章 陳鯉庭的《魯迅傳》攝製計畫及流產
一、《分鏡頭劇本》是「拍攝的依據」、《計畫》的核心
二、陳鯉庭的計畫之一:紹興、杭州再度收集資料
三、陳鯉庭的計畫之二:徐家匯藏書樓抄錄各種資料
四、陳鯉庭的計畫之三:要沈鵬年搞幾份專題調查
五、關於人物分類:按藝術形象、還是劃分階級成份
六、關於場景情節:以劇本為基礎,還是用資料來豐富?
七、丁一補救方案失敗、《魯迅傳》攝製組解散
八、周總理不勝惋惜、「書齋劇」言外之意
第八章 黨委書記要我整理發表有關《魯迅傳》材料
第一類:為趙丹、藍馬、石羽、于藍整理有關材料
第二類:在《光明日報》發表電影《魯迅傳》人物瑣談
第三類:奉命發表電影《魯迅傳》史實調查
第四類:關於擬寫而流產的《魯迅歷史調查記》
第九章 攝製組無奈解散、《魯迅傳》餘波仍湧
一、 魯耕說:「陳鯉庭不賣我的賬,所以我不敢碰」。
二、趙丹遺憾「《魯迅傳》幾起幾落,不了了之,再也沒有開拍。」
三、始終關懷我的是長者葉以群
四、我和導演陳鯉庭沒有個人恩怨
五、對導演陳鯉庭從尊敬到反感
六、翻拍《民報》照片「觸雷」,陳鯉庭狠心「整」我
七、開了三次「翻案」會、「退賠八十五元」了事
八、 陳鯉庭否定《魯迅傳場景表》、自搞《結構分析表》
九、張春橋「蹲點」上影揪「夏(衍)陳(荒煤)路線」
十、四十年來圍繞《魯迅傳》湧起三次「餘波」
第十章 尊重歷史事實、澄清三重迷霧
第一重迷霧:《魯迅傳》「停拍」與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無關。
第二重迷霧:《魯迅及有關史實年表》絕非「別有用心的捏造」
第三重迷霧:《魯迅傳創作組訪談記錄》絕非「文壇謠言」
附 錄 我為何寫《籌拍歷史巨片〈魯迅傳〉始末》──孫雄飛給夏衍、陳荒煤等同志的報告/孫雄飛
後 記
第六章 天馬廠《魯迅傳》攝製計畫──1962年開拍
一、陳荒煤代表文化部同意《魯迅傳》定稿
二、楊仁聲代表市委宣傳部、電影局同意《魯迅傳》定稿
三、天馬廠接受《魯迅傳》定稿向市委、中央的報告
四、市委、中央批覆同意、天馬廠審議通過《魯迅傳》攝製計畫
第七章 陳鯉庭的《魯迅傳》攝製計畫及流產
一、《分鏡頭劇本》是「拍攝的依據」、《計畫》的核心
二、陳鯉庭的計畫之一:紹興、杭州再度收集資料
三、陳鯉庭的計畫之二:徐家匯藏書樓抄錄各種資料
四、陳鯉庭的計畫之三: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