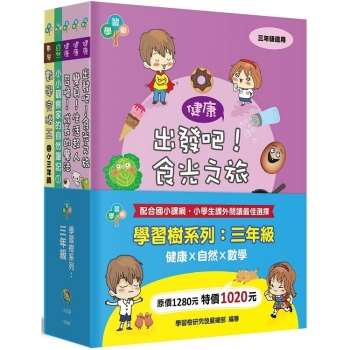板橋上次進京是在雍正三年。當時他三十二歲,不過是一名在村塾混嚼谷的藍衫秀才。他在京城逗留了大半年。大部分時間住在甕山無方上人的寺院裡。白天跟上人一起引山泉灌菜園。到夜晚,便品茗,談詩,論畫。外出遊覽的地方也多是道觀禪院,結交的多是禪宗尊宿及羽林子弟。窮秀才不願低聲下氣與達官貴人攀附,出家人中,能詩懂畫的畢竟不多,像無方上人那樣的飽學之士,更是罕見。板橋只與他唱和較多,也曾多次將詩詞題贈,並認真為他畫過幾幅畫。無奈,他的「六分半」書,連同他最拿手的墨竹,除了少數幾位摯友,真正能賞識的的人並不多。
而此次卻大不相同了。剛赴罷瓊林宴,求畫求字的人便絡繹登門。特別感到意外的是,他這名噪揚州的畫竹大家,剛來到京城時,他的墨竹竟沒有引起多大的轟動。他的書法反倒獲得不少讚譽之詞。諸如:「獨闢蹊徑」,「自樹旗幟」,「脫盡前人窠臼」,「一字一筆,兼眾妙之長」等等。唉!二十餘年辛勤追求、磨穿鐵硯般的苦練,總算得到了明眼人的肯定與賞識。他的心血與努力終於得到了報償。
是的,今晨的美夢,很可能就來自這種得意舒暢的心境。倘若說,這是因為他成了皇榜進士,「字因人貴」,所以人們競相求字。事實絕非如此。平心而論,他今天的字,確已非十多年前可比了。因此,對那些讚譽之詞,他覺得當之無愧。
尤其使他感動的是一位名叫圖清格,字牧山的滿族工部郎中。此公進士出身,晚年隱居蘆溝橋附近的沙窩村。該村離京城四十餘里,他竟然幾次來甕山訪板橋。圖清格善繪畫,學石濤和尚技法,花卉極精。他與板橋一見如故,盛情邀板橋至沙窩村做客。板橋前去拜訪時,盤桓十幾天方歸。每次相聚,圖清格差不多總有畫幅相贈。而他索要的「回贈」,必是板橋的書法作品。板橋在《又贈牧山》詩中,曾寫下這樣深情的詩句:
訪君古樹荒墳邊,
葉凋草硬霜凜栗。
一醉十日亦不辭,
蘆溝歸馬催人疾。
三天前,圖清格到了香山,下榻臥佛寺,派車接板橋去香山看紅葉。板橋慨然相允。雖然圖清格所邀的朋友中,有幾位頗多綺羅之氣,使人不堪忍受。但有了飽學主人美酒佳饌的款待,加之,秋高氣爽,巧雲片片,楓葉流丹,瓷塔滴翠。兩天中,一直處於陶醉狀態的揚州才子,不但詩興勃發,而且筆底煥彩,佳作連篇。他並不吝惜,有索即贈。
以詩會友,以字會友。看到相識和不相識的人,一致對自己的「六分半」傾倒,板橋感到無比的幸福與驕傲。
他覺得,自己的字所以會有今天的境界,固然由於幾十年的執著追求;但也與他元配夫人徐氏的開導,絕對分不開。
中秀才之後,板橋久久陷入痛苦之中。他覺得聖賢書中,確有著很多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那不但有益於國家,也有益於自身,即使不為功名,人生在世讀聖賢書也是多多益善。但要走舉業的路,光書讀得多,會寫八股文,試帖詩,遠遠不夠,還得寫出一筆規範的小楷字。多年中,他就將宋四家之一、黃山谷的碑帖作為範本,刻意摹寫。可是,仍然學得不到家。他深感苦惱。
有一天晚上,他思考如何將字寫好,久久睡不著。妻子已經呼呼入睡了,他還在苦苦思索。一面伸開右手食指。運筆似地不住地在被窩中劃來劃去。不知什麼時候,他的手指在妻子的背上劃寫起來。妻子被劃醒了,朦朧中問道:「你不好好睡覺,劃拉什麼?」「我在摹體。」「你自己有體嘛。」「你說什麼?」「你自己有體,為何摸別人的呢?」「噢,不錯,不錯!」他興奮地大聲喊了起來。
妻子說的「體」是身體,他領會成了字體。不料,一句睡夢之中的巧合話,卻給了他極大的啟迪。從那一天開始,他苦苦思索走自己的路,創自己的體。是的,不論黃山谷也罷,顏真卿也罷,就是學得跟他們酷似逼真,也還是黃字,顏體。學了人家,失掉自己!倘使自古以來,人人都只學他人,恐怕至今仍然只有甲骨文一種書體。莫說真、草、隸,連大篆、小篆也不會有,更不要說崔蔡鍾繇,歐柳顏趙,書苑百家了。
經過許多天的琢磨,板橋決定在隸書的基礎上,將真、草、篆幾種書體融合在一起,創造一種新書體。即:以楷隸為主,草篆為副,再融入畫蘭、畫竹筆法。經過數年的摸索,反覆的試驗,終於漸漸形成自家風格:撇筆長而瘦,宛如蘭葉,用內壓法;捺筆短而肥,酷似竹葉,用外拓法;其蹲衄之處,撇筆在接近收尾的中部,捺筆則在收筆之處,宛如隸書的隼尾波。運筆倏而多變,中鋒、側鋒、方筆、圓筆、衄筆、渴筆、蹲筆、挫筆,兼收並蓄。尤其是側鋒,更是被他運用的得心應手:飽含飛動之勢,而無嶙峋之弊。在字體上,他更是不拘繩墨,大、小、方、圓、正、斜、長、短,什麼奇形都有;甚至加以增筆、減筆、移位、換筆。這樣寫,看似雜亂無章,實則亂而有致,趣味盎然。在章法布局上,更是刻意追求峭拔,或如風起雲湧,時得舒卷變幻之氣;或似飛花霰雪,極盡自然灑脫之趣。這樣數年苦練,異峰突起,許多人為他的書法所傾倒。當人們詢問他的字體名號時,板橋隨口答道:「似『八分』而短,就叫『六分半』吧。」
「哈哈!二十年的心血沒白費!『六分半』不但征服了揚州,也開始征服京師咯!」他高興地自語起來。
他忽然記起,昨天與圖清格約定,今日同游宣武門內的法源寺。法源寺建於唐代貞觀年間,原名憫忠寺、順天寺、崇福寺。雍正十二年始改法源寺。該寺不但歷史悠久,而且憫忠台內藏有歷代石刻、經幢,是吊古和研討書法藝術難得的場所。更使板橋感興趣的是,據說北宋徽宗皇帝趙佶,就曾在法源寺做過階下囚。這位迷信道教的皇帝,善畫翎毛花卉,「知百藝、通學問」,寫得一手婦人氣十足的「瘦金書」。但他秉性昏庸,毫無治世之才。在位二十六年,最大的「建樹」,除了宴樂冶遊,就是重用奸臣蔡京、童貫,以及貶斥飽學而卓有識見的政治家司馬光等廉吏。以致奸佞滿朝,賢士絕跡;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結果,金兵乘虛而入。這位只會向拿筆的忠臣施淫威的宴樂皇帝,在拿大刀、騎快馬的異族侵略者面前卻嚇掉了三魂七魄,慌忙將皇位讓給兒子。但為時已晚,已經救不了垂危的國勢。兒子欽宗坐了不到兩年皇帝,就跟老子一起做了金人的俘虜。父子二人被押解北上,就囚在法源寺內。趙佶滿以為得到了苟全性命之所,作畫賦詩以表感戴,高興了好一陣子。不料,不久之後,又乖乖地被押送到關外遙遠的五國城,直到病死在那裡。與之形成對照的是,他的一位名叫謝枋得的臣下,生前曾寫過一篇《祭辛稼軒先生墓記》為「精忠大義」的辛棄疾蒙天地間大冤而吶喊。當他擔任信州知州時,金兵來犯,他率部英勇抵抗。城破後,隱遁建甯唐石山。元代建國以後,終於將他找到,強制他歸順。但他「一身不事二主」,像文天祥一樣,堅決拒絕做元人的臣僕。當他被拘在法源寺內「自擇生路」時,毅然絕食而死!
唉,在同一座古寺內,宋室一君一臣,竟演出如此天差地異的歷史活劇!如此勝跡,豈可不遊?!其實,這個願望,並非始自今日。板橋三十三歲那年,北游京師時即曾造訪過,因該寺正在大修,向隅而歸。
「篤,篤,篤!」有人在敲門。「日上三竿,大進士該起駕啦!」
是老友無方上人在門外催促。
……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難得糊塗:鄭板橋傳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99 |
文學小說 |
二手書 |
$ 280 |
二手中文書 |
$ 502 |
中文書 |
$ 502 |
文學家 |
$ 513 |
作家傳記 |
$ 513 |
社會人文 |
$ 513 |
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難得糊塗:鄭板橋傳
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鄭板橋
「揚州八怪」之一,詩書畫三絕的才子,置身清初滿人入關的新時代。
他,幾經榮辱,選擇以書畫為一生所寄。
浮沉世事,難得糊塗!
「我平生寫字作畫,用以慰天下之勞人,不供天下安享人也!癖也如此,性也如此。其奈我何?哈、哈、哈!」──鄭板橋
鄭板橋(1693-1765),名燮,字克柔。三歲喪母,青年發憤,中年以七品小吏造福鄉里;是中國文壇的奇才、書畫界的怪傑,獨創「六分半書」的書法新境,以蘭竹畫藝彪炳千秋。本書以生動的故事筆法完整重現鄭板橋的一生。
作者簡介:
房文齋(1932-),筆名魯鈍,中國山東青島市人。1946年6月參加工作。先任小學教師,後在各級行政部門任職。1960年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1979年3月到濰坊學院任教。離休前,任濰坊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已出版長篇小說:《鄭板橋》,《空谷蘭》,《辛棄疾》,《鄭板橋外傳》,《紅雪》,《夢斷秦樓》,《朱元璋》,《仰止坊》,《金瓶梅傳奇》等九部。其中,《辛棄疾》榮獲山東省1996年度精神文明建設精品工程獎。
主編與參編之中國大專教材和輔助教材十餘種。專著包括:《小說藝術技巧》、《揭祕金瓶梅》,散文集《莽原霜花》,詩集《燼餘詩存》,回憶錄《昨夜西風凋碧樹》等作。
章節試閱
板橋上次進京是在雍正三年。當時他三十二歲,不過是一名在村塾混嚼谷的藍衫秀才。他在京城逗留了大半年。大部分時間住在甕山無方上人的寺院裡。白天跟上人一起引山泉灌菜園。到夜晚,便品茗,談詩,論畫。外出遊覽的地方也多是道觀禪院,結交的多是禪宗尊宿及羽林子弟。窮秀才不願低聲下氣與達官貴人攀附,出家人中,能詩懂畫的畢竟不多,像無方上人那樣的飽學之士,更是罕見。板橋只與他唱和較多,也曾多次將詩詞題贈,並認真為他畫過幾幅畫。無奈,他的「六分半」書,連同他最拿手的墨竹,除了少數幾位摯友,真正能賞識的的人並不多...
»看全部
作者序
許多朋友大概都有著這樣的體會:傾心敬慕著某一個人,不論他是今人還是早已作古的前賢,總是抑止不住要將一腔崇敬之情形諸語言或筆墨。筆者對於鄭板橋先生,正是懷著這種激情。
筆者對板橋先生的崇仰,始於少年時代。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讀大學期間,即開始搜集有關板橋先生的資料。無奈,接踵而至的是政治風雲變幻,命運多舛!直到陰霾蕩盡,尊嚴復歸的八十年代,才先後發表過幾篇有關板橋先生的論文。一九八八年,又出版了長篇小說《鄭板橋》。不料,這些鄙陋的文字,竟得到不少行家和讀者的肯定和歡迎。
現在,筆者又把《鄭板橋...
筆者對板橋先生的崇仰,始於少年時代。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就讀大學期間,即開始搜集有關板橋先生的資料。無奈,接踵而至的是政治風雲變幻,命運多舛!直到陰霾蕩盡,尊嚴復歸的八十年代,才先後發表過幾篇有關板橋先生的論文。一九八八年,又出版了長篇小說《鄭板橋》。不料,這些鄙陋的文字,竟得到不少行家和讀者的肯定和歡迎。
現在,筆者又把《鄭板橋...
»看全部
目錄
自序
一往情深古板橋
平生負恩獨乳母
堅毅穎悟麻丫頭
四十年來畫竹枝
無枷無鎖自在囚
石鍾山下秋水寒
梅花老去杏花勻
焦山苦讀嘗冷曖
千人罵香「六分半」
畢竟惜玉還憐香
瘦西湖上巧撞船
亭亭孤竹動人憐
三頭毛驢下濰縣
蕭蕭竹聲似民怨
「神仙」「善人」難售奸
苦嚼蓮子守歲寒
鬧市測字困「半仙」
傷卑嗟老不盡情
癡魂何日出愁城
今天准你賣鹹鹽
貪杯誤中狗肉計
禮尚往來懲狡奸
魯班門下魚幻龍
破裘能補不畏寒
月老妙手牽紅線
文網彌張徒喚天
因禍得福枉捉姦
「連升三級」看色變
可憐天下父母心
秋風蕭瑟巧賣扇
只...
一往情深古板橋
平生負恩獨乳母
堅毅穎悟麻丫頭
四十年來畫竹枝
無枷無鎖自在囚
石鍾山下秋水寒
梅花老去杏花勻
焦山苦讀嘗冷曖
千人罵香「六分半」
畢竟惜玉還憐香
瘦西湖上巧撞船
亭亭孤竹動人憐
三頭毛驢下濰縣
蕭蕭竹聲似民怨
「神仙」「善人」難售奸
苦嚼蓮子守歲寒
鬧市測字困「半仙」
傷卑嗟老不盡情
癡魂何日出愁城
今天准你賣鹹鹽
貪杯誤中狗肉計
禮尚往來懲狡奸
魯班門下魚幻龍
破裘能補不畏寒
月老妙手牽紅線
文網彌張徒喚天
因禍得福枉捉姦
「連升三級」看色變
可憐天下父母心
秋風蕭瑟巧賣扇
只...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房文齋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3-07-10 ISBN/ISSN:978986326119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70頁
- 類別: 中文書> 傳記> 文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