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樊駿先生說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已不再年輕。近20多年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思想解放、歷史還原、美學重建、文化想像等社會學術思潮的背景下,展開了對現代文學思潮、文學社團流派、作家作品等的深入討論,取得了創新而紮實的學術成果,呼喚並追求「持重」的學術之境。相對說來,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性在不斷增強,它的現實性和當代性卻有所減弱。
現代文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注重學術性與現實性的並舉,能夠不斷提出和發現既來自複雜的現代文學本體,又擁有獨特的現實關懷和個人體驗的學術問題和方法。在我看來,「文學制度」就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產生了重要作用(正面的和負面的),並延續到了當代文學的一個有待深入討論的學術問題。
「制度」本身也是發生在當下社會現實和思想界的一個重要問題,「人與制度」、「思想與制度」可以說是當代知識份子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話題。當然,本文主要討論現代文學制度問題,擁有進入問題的現實體驗,但並不直接回答現實問題。近年來,學術界如王曉明、李歐梵、錢理群、孟繁華、楊洪承、韓毓海、羅崗、欒梅健和何言宏等學者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制度的相關問題都曾有過相當深入的研究。
代表性著作有洪子誠的《問題與方法》(三聯書店,2002年)、曠新年的《1928年的文學生產》(《讀書》1997年9期)和《1928年:革命文學》(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王曉明的《批評空間的開創: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倪偉的《「民族」想像與國家統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及文學活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藤井省三著,董炳月翻譯的《魯迅〈故鄉〉閱讀史──近代中國的文學空間》(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楊洪承的《文學社群文化形態論》(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以及欒梅健的《前工業文明與中國文學》(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等等。
文學制度作為文學生產的制約力量,關涉到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權力、想像與規則等問題,因此,應該引起學術界的足夠重視和深入探討。以前對文學的社會背景、文學出版與傳播、文學社團與流派、文學教育與文學創作之間的複雜關係都曾有過深入研究,已經涉及到文學的制度問題,但卻沒有建立起文學制度研究的整體性和理論性視野,忽略了對文學活動各要素之間的整體的動態把握,在理論上也把文學制度完全看成是文學的社會外部力量,忽略了文學體制的內生性機制。文學的制度問題,無論是對中國文論建設還是中國文學史研究而言,都應該成為一個有待深入討論的學術話題。
本論文把現代文學制度建構理解為一個整體的運作系統,總的說來,它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是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的獨特性和豐富性的證明。在現代社會與文學互動與衝突過程中,文學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在闡釋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過程中的文學制度力量,既要注意它的制約性和規定性,又不能忽略它的有限性。在理論上適當借鑒有關西方文學體制理論,如福柯的知識與權力,哈貝馬斯的「公共空間」和布迪厄的「文學場」理論等等。
在研究方法上擬在既有的「社會歷史分析」、「審美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基礎上,實現方法論的綜合,打通審美研究與文化研究的方法隔膜,以文學制度中的「個案」分析,爭取回到歷史現場。圍繞現代文學與制度的互動與衝突關係,討論在現代文學發展演變過程中出現的「作家」、「文本」、「社團」、「論爭」、「批評」和「讀者」等文學現象所呈現的制度力量,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在文學制度中「創造、生長和超越」,文學制度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傳統和文學資源。
進而,從一個側面和角度回答和解釋何謂「中國」,何謂「現代」,何謂「現代文學」等問題,力圖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提供一種新思路。顯然,它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在某種程度上,還具有一定的學術史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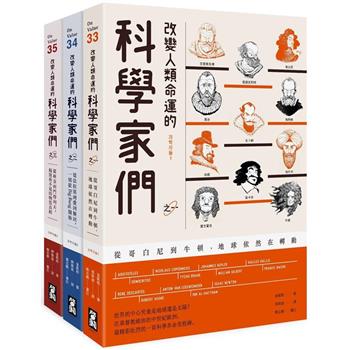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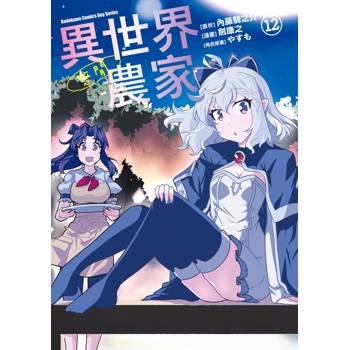
 公職考試2025試題大補帖【電路學(含電子學與電路學)】(106~113年試題)(申論題型)[適用三等/高考、關務、地方特考、技師考試](CK4204)](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18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