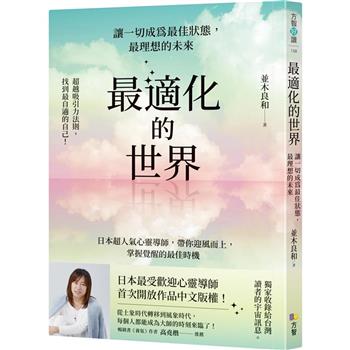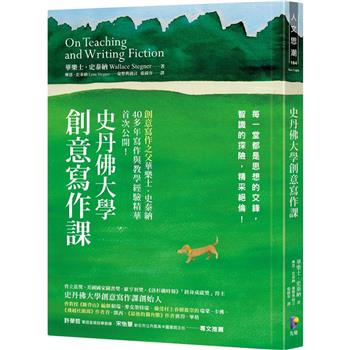詩必然是意識的真實,現象學提供了我們發現詩之美好的一個真實管道,當現象學轉向對文學進行發現時,必然成為一種對意識與真實的批判,對作者意識的再發現,使表述從繁蕪中純粹出來,讓文學作品純粹是人類意識的一種表述方式,一種形式。
我們可以運用現象學方法剖析、梳理葉覓覓、隱地、向陽、蕭蕭、林婉瑜、白靈、黃河浪、張默等當代詩人的詩作,期望能夠在現象學的規範下,使那些隱藏在文學作品中的意識描述性地、純粹性地現形,進而發現意識的真實。
本書特色
本書利用哲學中的現象學作為進路,剖析梳理隱地、向陽、蕭蕭等知名台灣當代詩人的詩作
現象學方法轉向對詩語言進行發現的初探之作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意識的現形:新詩中的現象學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30 |
二手中文書 |
$ 285 |
中文書 |
$ 300 |
詩 |
$ 334 |
華文文學研究 |
$ 342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80 |
文學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劉益州
筆名楊寒,創世紀詩社同仁,現任台中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曾獲青年優秀詩人、安高詩集整理獎、中縣文學獎、創世紀五十週年詩創作獎等,出版詩集《我的心事不容許你參與》、《與詩對望》、《巫師的樂章》、《楊寒短詩選》(中英對照)以及小說集《大刀歌》、《巫師的樂章》。
目錄
序 許又方
自序 意識在表述中的現形 劉益州
意識的表述形式:葉覓覓詩集《越車越遠》中的「自我」表述
自我與他者的呈現:隱地《詩歌舖》中主體際性敘述之研究
他者的綿延:向陽《歲月》中自我與生命時間意識的表述
空間與行動:蕭蕭《毫末天地》中空間意識的呈現
愛與主體的澄明:林婉瑜《索愛練習》中的意識呈現
身體與表述:白靈《愛與死的間隙》中的存有見證
空間與他者:黃河浪《香江潮汐》中「香港」的空間表述
空間的想像與詮釋:論黃河浪《披黑紗的地球》旅遊詩中的時空想像
表述的視角:張默旅遊詩中「物我」視角的開展──以《獨釣空濛》為討論中心
序
推薦序
若依美國學者M.H. Abrams 在其名著《鏡與燈:浪漫理論與文學批評傳統》(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中所勾勒的文學批評四要素:作品、作者、讀者與世界,則文學思辯的領域,不外乎作品之所以構成的美學成分,諸如體式、修辭、音響等表現層面的問題,此其一;再者,由作品的文字爬梳中,試圖領略作者的「意圖」(intention);或是,仔細檢閱作家的生平與經歷,以期增進對其作品意指的理解。第三,由讀者觀點出發,強調個人閱讀的反應,留意作品文字擴展、動人的能量。最後,望向一切存有,勾抉作品中寄寓的世界觀,視其如何迎向宇宙人生紛至遝來的衝擊與挑戰,提出什麼樣的回應或啟示。
無論是文學的創作或研究,浮淺地來看,都不能脫離上述四個層面。或者說,這四個層面,究其實只是一體。擅於描繪人生百態的法國現實主義文學家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曾說:「作家必須熟悉一切現象,一切感情。他的心中應有一面難以言喻、足以聚焦任何事物的鏡子,將變幻無常的宇宙,從這面鏡子上反映出來。」帶著如此接近博物學的理念,巴氏大手筆展開他道盡人世滄桑的寫作計畫,《人間喜劇》(Comédie Humaine)共九十一部的動人鉅著,於焉問世。我認真檢閱巴氏的作品,當然未能一一遍讀,但文學中可以發現的問題,如前述者,大抵都可找到足以給人豐盛啟示的線索。
而據說,《人間喜劇》在巴氏最初的寫作計畫中,是被命名為「社會研究」。顧名思義,巴爾札克無疑欲藉寫作反映他所知世界的點點滴滴,秉持研究的嚴謹態度,帶著些許批判,傳達某種理想。如此看來,容我重申,又足證純文學的寫作與學術性研究在某個層面上是相通的,他們都屬創造性活動,也都立足於作品的核心,輻射、連結至作者、讀者,以及宇宙世界的領域。
益州是一位早慧的詩人,偶爾也寫些小說,文字能量極為豐沛。近日他寄來近幾年潛心思考所得的數篇文學研究論述,跨度涵括古典與現當代詩歌、小說,當然,還有他最用心領會的詩。我細細瀏覽,發現他研究的進路多元並呈,敘事學、符號學、現象學、空間理論及各式文化研究概念等,看得出來用功至勤。早些年他跟我討論一些古典文學的問題,在我不甚成熟的指導下完成《詩經「山」意象研究》,並獲碩士學位。當時我清楚記得,古代文獻的艱澀,頗令益州感到挫折與茫然,對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就不覺滿意。雖說如此,我卻從他努力想從《詩經》文句中勾銜出某種美學條律的嘗試中,看到他對學術研究的潛能,因此鼓勵他繼續深造。
多年過去,益州在學術上的表現已經與他的現代詩創作幾乎並駕齊驅了,寫作與研究再一次由他介筆融合,值得留意。他希望我為其即將出版的論文集寫篇序,我既欣喜於他甫獲博士學位,更為其學術造詣突飛猛進感到高興。忝為人師,最快樂的莫過於看到學生的成就高過自己,益州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是為序。
許又方
謹誌於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
二○一一年十一月廿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