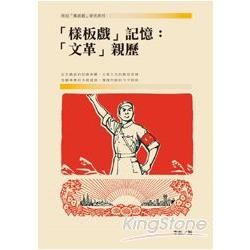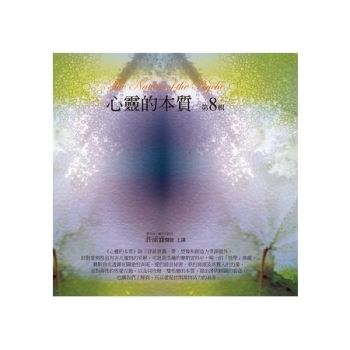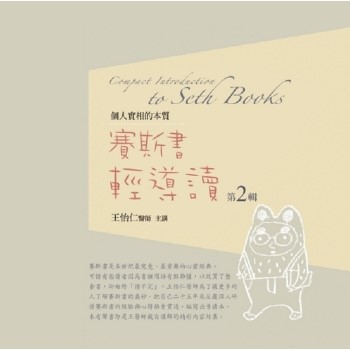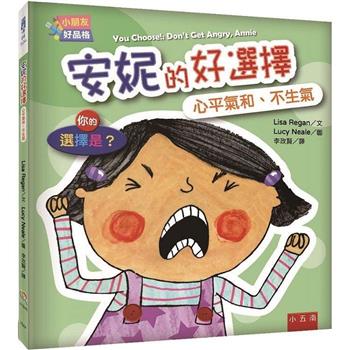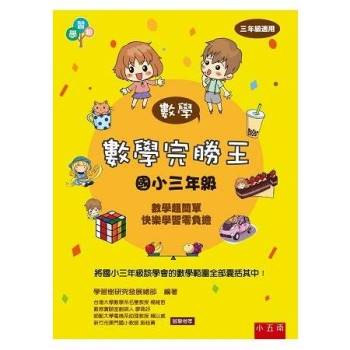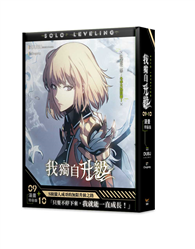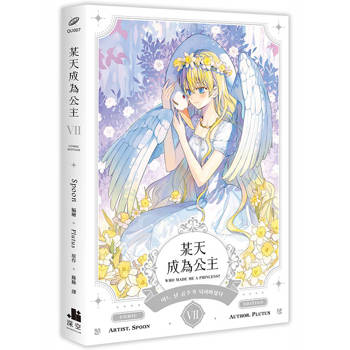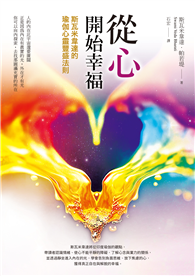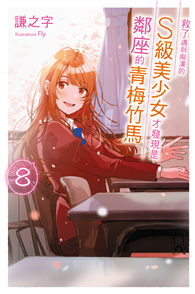一、為什麼需要記憶
著名的「文革」史學者徐友漁曾經在〈記憶即生命〉一文中動情地呼喚人們珍視歷史記憶:
舊的世紀和千年即將過去,新的世紀和千年就要來臨。在這欲望急劇膨 脹,不論現實的還是虛擬的財富都備受關注的世界,有多少人想過,我們每一個人乃至我們整個人類,其實有一筆與生俱來的誰也拿不走的財富,它是我們最大的希望,這財富就是我們的──記憶。珍視它和呵護它,就是維護我們的尊嚴和生命;忽視它或者躲避它,不僅是拋棄和糟蹋世間最寶貴的財富,而且是背叛我們自己。
記憶是一種關於歷史存在的精神形式,它意味著對歷史的重新敘述。個體的記憶意味著一個人的生命史與社會史,集體的記憶意味著一個民族的精神家園。一個沒有記憶的個體和民族是沒有未來的,因為歷史包含著未來變遷的方向性因子,歷史的血脈與未來的繁衍,賡續不絕,源遠流長;無視歷史也不會有幸福的當下,因為沒有歷史意識的當下生活是虛無的、盲目的、淺薄的。
歷史的基本涵義包括作為過去史實的歷史,以及作為對過去思考、理解和解釋的歷史。前者是作為思考對象的本原的歷史;後者是研究意義上的史學的涵義,歷史記憶即屬於後者,對歷史的記憶的梳理過程,也是一個精神清理與反思的過程。記憶應該是什麼?應該如何記憶?人們需要的是何種記憶?也就是說,應該通過記憶得以喚醒歷史,還是通過遺忘淘汰歷史?這是一個選擇問題。而選擇的權力是一個需要追問合法性的存在。誰有權力去敘述記憶?何種記憶才是被許可的?徐友漁警示道:「記憶在本真的意義上是人的精神資源、精神財富,但它往往被某些政治和社會力量當成權力合法性資源,因此,記憶必然有可能被利用、歪曲或壟斷。」 但是,無論記憶最後呈現的是什麽面目,無論何種記憶,它都是社會所需要的。
具體就「文革」記憶來說,徐賁認為當下的當務之急是:「迫切需要形成一種有助於汲取『文革』教訓的集體記憶。」
無論是把「文革」看成是一個教訓,還是當作一個經驗,其中都包含著某種對「文革」的記憶。「文革」的隱患在哪裏?是哪些隱患?對這類問題的回答同樣取決於人們對「文革」的記憶。這種記憶應該不僅是經歷過「文革」的人們的個人記憶,而且更應該是整個民族,或至少是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所共有的集體記憶。「文革」結束已經過去了三十六年,今天的「文革」記憶遠比「文革」剛結束後不久要更多樣,也更充滿分歧和衝突。這不僅是由於當事人在「文革」中的不同經歷形成了不同的記憶,而且還由於「文革」後出生的年輕人與前一兩代人之間有代溝,因此產生了「後記憶」與「記憶」的差別。有鑑於此,現在更迫切需要形成一種有助於汲取「文革」教訓的集體記憶。在過去的一二十年裏,這樣一種集體記憶並未能充分形成。
歷史記憶是一種經驗性的智慧庫存,也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它的內容分為集體的與個人的,宏大的與微觀的,積極的與消極的。在「形成一種有助於汲取『文革』教訓的集體記憶」之前,應該建立一個各種記憶對話、溝通的平臺,營造一種不同記憶碰撞的理性氛圍。
畢星星則進一步提出了「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革』記憶」的問題,他說:
問題在於,即使對於「文革」這樣的全民大災難,每個人的感受也是不盡相同。即使在最混亂的十年,也有弄權得逞的,也有安富尊榮的,也有僥倖得益的。昔陽大寨這樣大力複製半個世紀前的舊景,也無非是留戀當年穩坐全國政治激流中心位置的懷舊情思。這裏就有一個要求,一個人的人生敘述,某一個團體的集合記憶,必須和國家民族的集體記憶的價值取向相一致。我們要大力重建的,是整個國家民族,至少是這個國家民族大多數人擁有的集體記憶。我們必須警惕一些在「文革」中受益的人群,將自己的幸福記憶強加在全體國民頭上,變成集體書寫集體記憶。
畢星星警惕的是「文革」受益者對於記憶內容的壟斷,不無道理。我認為,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爲什麽「這個國家民族大多數人擁有的集體記憶」就一定是正當的?有沒有「大多數人擁有的集體記憶」會形成一種集體暴力的可能?如何界定「受益的人群」?這個群體正形成一種利益集團,還是已經被分化?這些問題需要論證,而不是情感上認為理所當然。
就「樣板戲」的歷史記憶而言,其史料分析有三個關鍵的問題:首先,應該記憶者是誰;其次,他與「樣板戲」是何種關係;再次,他的歷史記憶反映的關鍵問題是什麼。
二、記憶與主觀情感
經歷不同的過來人,對「樣板戲」的記憶可能有迥然不同的感受與印象,即便同樣是「文革」的被迫害者,他們對「樣板戲」的態度也不盡相同,而影響不同的判斷的主要原因是言說者的主觀情感。下面試圖以微音與金敬邁、章明的分歧來說明這一問題。
二○○二年,廣東資深媒體人微音曾對「樣板戲」重登廣州的藝術舞臺,發表了一段頗具歷史感的辯證分析。
首先,他認為,「樣板戲」作為一種政治藝術的霸權性文本,造成了中國文壇百花肅殺的殘局。「這是『四人幫』的『曠世之作』,也屬『四人幫』罪惡滔天的醜行之一。」 他對「樣板戲」所履行的思想專制的職能進行了全盤否定。然而,政治上的否定並不意味著藝術上絕無可取之處。在懸隔一段歷史距離的今天看來,不可否認「樣板戲」在藝術創造方面的價值。「孤立地就這些戲來說,無論唱腔、表演、情節,均千錘百鍊,堪稱精品。尤其是《紅燈記》、《智取威虎山》、《沙家濱》等劇,看後至今仍歷久難忘。」同時,微音又指出,由於觀眾生活經歷與情感體驗的差異,因而關於「樣板戲」的價值判斷會不可避免地受到情感偏見的影響。「在打倒『四人幫』後,『樣板戲』停演,因其時『文革』的傷痛尤深,情有難堪,這是理所當然。」 儘管情感印記會影響立場觀點,微音還是堅持應該實事求是看待「樣板戲」的創作過程和思想主題。「這些作品大多產生於『文革』之前,是從文藝基層中產生,經眾多大藝術家加工錘鍊而成的。這些作品,有力地宣揚了我國人民的偉大革命精神,宣揚了革命鬥爭的艱苦性,宣揚了為革命無私無畏所做的傑出貢獻,宣揚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崇高品質與革命理想。」 上面的看法,體現了微音作為一個中共老報人的黨性,也是尊重事實的中允之論。
其次,微音深入辨析了「樣板戲」產生的政治原因。即,「四人幫」既是個反革命集團,為何又要大肆吹捧「樣板戲」呢?他的理解是:「『四人幫』既要搞反革命,就必然要用革命的面孔來裝潢自己、粉飾自己。他們之所以大肆宣揚『樣板戲』,利用這些文藝作品,樹『八個』,打一大片,扼殺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創造性,以文藝專制始,以思想專制終。」 所謂「革命」與「反革命」,其內涵並非不言自明,也並非一定的標準所能決定。在專制社會,命名的權力往往把握在權力的最高統治者手裏。例如某位領袖嘴裏經常提到的「形左實右」就是一個隨意使用的政治標籤,何謂「左」、何謂「右」?完全視領袖自己的需要而決定。微音在上述文字中揭示了所謂「四人幫」(有人或曰「五人幫」)「革命」是假、「反革命」是真,並指出「樣板戲」是一種「反革命」工具。這種解釋雖然未能完全脫離僵化的二元對立思維,但是畢竟道明了基本事實。
最後,微音還對「樣板戲」創作功勞的歸屬進行了辯證解釋:
有人說:「樣板戲」是江青的傑作,演出「樣板戲」等於宣傳江青。錯了!就總體來說,「樣板戲」是當年傑出的藝術創作家與出色的表演藝術家共同創造的碩果,絕不能因江青個人插手而以偏概全,以個人一得之見而否定集體創作之功。如果是這樣,江青在九泉之下,也會拱手為之致謝的。總之,還這幾個戲以本來面目,是應該的。
微音關於「樣板戲」的上述觀點,思路清晰,見解鮮明,思考周密,分析辯證,是難得的中允之論。
微音的文章一石激起千重浪,「文革」受難者金敬邁與章明則對他的上述看法進行了火藥味頗濃的商榷。
第一,他們認為「樣板戲」從來就是不僅僅只是戲而已,而是野蠻專政的法西斯工具。
「樣板戲」是御用的屠刀,是飛機大炮,是無堅不摧的原子彈,林彪、江青一夥用它來剷除異己、清洗政壇,以樹立他們在黨內的絕對權威,順便也把千千萬萬無辜的人們打得血肉橫飛,家破人亡。多少民族的精英:吳晗、鄧拓、老舍、傅雷、羅瑞卿、張志新、遇羅克……以及劉少奇、彭德懷等黨和國家的元勳們也是在「樣板戲」高亢的唱腔伴奏中或含冤死去,或上吊、服毒、投水、跳樓乃至於被槍決的!上下五千年只剩下八齣所謂的「戲」,國家命運、民族存亡全都不在話下了!「樣板戲」是棍子,把我國幾千年來的文化藝術成果(包括「五四」以來新文藝成果)掃成「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樣板戲」是刀,是架在文藝工作者和人民群眾脖子上的鋥光閃亮的鋼刀。誰反對「樣板戲」誰就不得好死!「樣板戲」又是神,它幾乎和「紅寶書」享有同等的輝煌,不得議論,不得懷疑,不得唸錯,它比聖經還聖經,比憲法還憲法,神聖不可侵犯。世上有這樣魔法無邊的「戲」嗎?
就這一點而言,其實論爭雙方都有交集,並無分歧,充分認識到藝術已經蛻化為一種政治鬥爭的武器,尤其揭示政治藝術造成了一種史無前例的民族災難。
第二,金敬邁與章明認為,「樣板戲」與江青有著無法割捨的關係。
歷史文獻鐵案如山:「『樣板戲』是江青同志嘔心瀝血的結晶。」江青自己也說:「誰反對樣板戲就是反對老娘!」而她的一大幫孝子賢孫甚至說江青單憑這項「功勞」就完全可以當黨的主席,紛紛然大上其「勸進表」。怎麼能說「樣板戲」是什麼「集體創作的碩果」呢?難道不怕「老娘」的陰魂來要您的小命?一九六六年中央正式發下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中,已經把江青在所謂「京劇改革」的「偉大作用」說得清清楚楚,何曾提到什麼「藝術家的集體創作」?
其實,微音並沒有否認「樣板戲」帶有鮮明的江青印記這一事實,他實事求是地指出,「樣板戲」同時也凝聚中共一代高層領導以及幾代戲曲藝人的心血。而金敬邁與章明對此似乎並未慮及。他將江青的〈座談會紀要〉這一反面文獻作為論證江青與「樣板戲」的緊密關係,而無視「樣板戲」誕生、形成的複雜過程,這一論證本身就是有問題的。畢竟江青在〈紀要〉中沒有提到「藝術家的集體創作」,並不意味著這是一種的客觀的事實。金敬邁說:「我已通告全家,凡我兒孫,若遇『樣板戲』,立即換臺,稍有怠慢,我就砸爛電視機。」 這樣的情緒性反應,可見其態度之決絕,作為個人好惡固然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因此全盤否定「樣板戲」的藝術價值則無疑失於片面化、絕對化。
微音的文章之所以造成商榷者如此激烈的反彈,究其原因,與金敬邁、章明所遭受的痛入骨髓的靈肉創傷是有關係的,他們以對「文革」的極度憎恨取代了對「樣板戲」的具體分析 。
巴金等遭遇過「文革」迫害的人對「樣板戲」同樣留下的是恐懼、驚悸的創傷記憶。巴金回顧說:
聽了幾段,上床後我就做了一個「文革」的夢,我和熟人們都給關在「牛棚」裏交代自己的罪行。一覺醒來,心還在咚咚地跳,我連忙背誦「最高指示」,但只背出一句,我就完全清醒了。我鬆了一口氣,知道大唱「樣板戲」的時代已經過去,「牛棚」也早給拆掉了,我才高高興興地下床穿衣服。
我接連做了幾天的噩夢,這種夢在某一個時期我非常熟習,它同「樣板戲」似乎有密切的關係。對我來說這兩者是連在一起的。我怕噩夢,因此我也怕「樣板戲」。現在我才知道「樣板戲」在我心上烙下的烙印是抹不掉的,從烙印上產生了一個一個的噩夢。
近來幾次夢見自己回到大唱「樣板戲」的日子,醒來我總覺得心情很不舒暢……所以聽見唱「樣板戲」有人連連鼓掌,有人卻渾身戰慄。
作家鄧友梅講過一些他在「文革」中的可怖經歷:與被迫害致死的人的靈牌一起挨鬥,一邊挨鬥一邊放革命樣板戲,鬥後放入一個冷屋,屋子冷,引起了腸胃痙攣和嘔吐。所以他一直反對再唱「樣板戲」 。
與上述「樣板戲」痛苦記憶相比,有些並未經受牢獄之災的人,往往將它作為青春激情歲月的亮麗彩虹,與恐懼記憶相比,他們的懷舊心態反映的是某種美感和喜悅。因而一聽到「樣板戲」,立刻會情不自禁地加入合唱。
對於那些因「文革」運動以及「樣板戲」而受到過衝擊的人來說,「樣板戲」意味著一種刻骨銘心的痛苦。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疤痕猶在,談何懷舊?然而,不可否認,對於大多數處於中立地位的普通群眾,尤其是那些京劇的愛好者來說,美好的回憶也是完全正常的。「樣板戲」深入人心,憑藉的是幾代人精益求精的藝術創造。「樣板戲」在當年的轟動,也並非完全是官方強制灌輸的結果,觀眾的主動接受(烏托邦狂想)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13 |
各類戲劇 |
$ 442 |
中文書 |
$ 519 |
戲劇 |
$ 531 |
藝術設計 |
$ 531 |
表演藝術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樣板戲」記憶:「文革」親歷
封面文案
紅色戲曲的記憶典藏,文革人生的酸甜苦辣
客觀事實的多維透視,價值判斷的今夕對照
內容簡介
本書根據「文革」記憶主體的身份與職業,分為編劇、演員、導演、音樂、電影、錄音、攝影、演出、知情者見證、觀眾十大類別,每一類別即為一個完整的章節。通過大量的可靠史實重構歷史;通過「樣板戲」親歷者的往事回眸保存珍貴的戲曲史料;通過敘述者對今昔歷史的對比,更為清晰地展示「樣板戲」的發展過程,並從各個角度展現它的多重面目。
本書特色
訪談經歷文革時期,對樣板戲記憶的各色人物,因親歷者的角色而更凸顯出歷史的真切。
作者簡介:
李松,文學博士,目前任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自2007—2010年在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2010—2011在哈佛大學東亞系從事訪問研究。曾經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主要著作有《「樣板戲」編年史》(秀威,2011,2012)、《文學理論新視野》(秀威,2012)、《文學研究的知識論依據》(秀威,2012)、《「樣板戲」的政治美學》(秀威,2013)等。
章節試閱
一、為什麼需要記憶
著名的「文革」史學者徐友漁曾經在〈記憶即生命〉一文中動情地呼喚人們珍視歷史記憶:
舊的世紀和千年即將過去,新的世紀和千年就要來臨。在這欲望急劇膨 脹,不論現實的還是虛擬的財富都備受關注的世界,有多少人想過,我們每一個人乃至我們整個人類,其實有一筆與生俱來的誰也拿不走的財富,它是我們最大的希望,這財富就是我們的──記憶。珍視它和呵護它,就是維護我們的尊嚴和生命;忽視它或者躲避它,不僅是拋棄和糟蹋世間最寶貴的財富,而且是背叛我們自己。
記憶是一種關於歷史存在的精神形式,它意味著對...
著名的「文革」史學者徐友漁曾經在〈記憶即生命〉一文中動情地呼喚人們珍視歷史記憶:
舊的世紀和千年即將過去,新的世紀和千年就要來臨。在這欲望急劇膨 脹,不論現實的還是虛擬的財富都備受關注的世界,有多少人想過,我們每一個人乃至我們整個人類,其實有一筆與生俱來的誰也拿不走的財富,它是我們最大的希望,這財富就是我們的──記憶。珍視它和呵護它,就是維護我們的尊嚴和生命;忽視它或者躲避它,不僅是拋棄和糟蹋世間最寶貴的財富,而且是背叛我們自己。
記憶是一種關於歷史存在的精神形式,它意味著對...
»看全部
作者序
雖然「文革」學研究在中國大陸至今仍然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政治禁區,「文革」文學與藝術的研究成果卻借助不直接涉及政治敏感問題而披有一層「保護色」,也就是不直接談政治問題而不顯得那麼「扎眼」,因而勉強獲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間。「樣板戲」是「文革」文藝的主體組成部分,近四十年來,海內外關於這一文學文本、劇場演出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近十年來,我對「樣板戲」的研究歷史與現狀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整理與消化 ,同時就我個人感興趣的、而又認為值得開掘的問題進行了一系列思考。我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如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
一、「樣...
一、「樣...
»看全部
目錄
李松「樣板戲」研究系列‧總序
導言
第一篇 編劇
翁偶虹:千秋功過記《紅燈》
阿甲:
阿甲出庭指出江青人格卑鄙、手段殘忍
阿甲談《紅燈記》
給XXXX記者的信
汪曾祺:
關於「樣板戲」
關於《沙家濱》
「樣板戲」談往
江青與我的「解放」
說裘盛戎
名優之死──紀念裘盛戎
關於于會泳
汪曾祺:我的檢查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楊毓瑉憶汪曾祺
梁清濂憶汪曾祺
蕭甲:蕭甲憶「樣板戲」
趙起揚:「文革」中焦菊隱
張士敏:我參與樣板戲《海港》始末
邢野:《平原游擊隊》修改記
楊益言:江青的「江姐夢」
第二篇 演...
導言
第一篇 編劇
翁偶虹:千秋功過記《紅燈》
阿甲:
阿甲出庭指出江青人格卑鄙、手段殘忍
阿甲談《紅燈記》
給XXXX記者的信
汪曾祺:
關於「樣板戲」
關於《沙家濱》
「樣板戲」談往
江青與我的「解放」
說裘盛戎
名優之死──紀念裘盛戎
關於于會泳
汪曾祺:我的檢查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楊毓瑉憶汪曾祺
梁清濂憶汪曾祺
蕭甲:蕭甲憶「樣板戲」
趙起揚:「文革」中焦菊隱
張士敏:我參與樣板戲《海港》始末
邢野:《平原游擊隊》修改記
楊益言:江青的「江姐夢」
第二篇 演...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李松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3-12-11 ISBN/ISSN:978986326199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92頁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