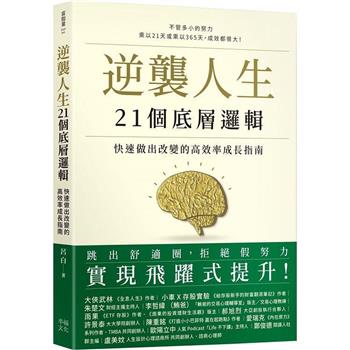戴鎦齡:讓「烏托邦」進入中文的人
提起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你也許並不陌生。但你一定不知道,20世紀三十年代,剛從愛丁堡大學學成歸來的他,將莎翁的十四行詩,一首一首地譯成中文,當作情書,寄給了後來成為他夫人的女友。這一「無心之譯」,後來成就了一段被學界爭相傳誦的佳作,至今仍然被公認為是最好的莎翁十四行詩譯作之一。
在他的譯作中,最為大眾所知的,則是他翻譯了湯瑪斯‧莫爾《烏托邦》一書。其中堪稱譯名經典的「烏托邦」一詞,便是由他首創。
八十年代培養出我國第一位英語語言文學博士,他的名字已被英國劍橋世界傳記中心載入名人辭典。
他就是抗戰時期在國立武漢大學外文系任教的翻譯家戴鎦齡。
戴鎦齡(1913―1998),江蘇鎮江人。關於他家世,在戴克中博文中有這樣的介紹:
曾祖父戴恒是同治二年進士,當過翰林,辦過上海機器織佈局,歷史上有他一筆。再往上追溯,戴恒的父親戴善之(永慶)是咸豐年間潤州首富,蕪湖有戴公堤,修甘露寺他一拋就是十萬白銀,也算一個人物。二百年來,真正載入官家正史的京江戴氏後人除了戴恒就只有戴鎦齡了。……
戴鎦齡是我的叔祖父,他是我曾祖父戴恒的弟弟戴怡(靜夫、敬夫)最小的兒子。他本人可能完全沒有他父親的印象,因為他僅三歲時父親就去世了。他也幾乎不可能有多少關於他母親的記憶,他父親去世後(也可能在去世前),他母親就被趕出了家門。據曾祖父留下的書信記載,戴怡是戴家最有才氣的人,「戴家的良駒」。他十幾歲中舉,當時的前科狀元李承霖親筆向戴恒報告喜訊。可惜的是從此戴怡就再未進學,背靠殷實的家庭過起了名士的日子。從他留下的詩詞信劄看來,他是一個性情中人,除了丫鬟以外他娶了四房太太,有十餘個兒女。他的大公子也如法炮製,前後也有五房夫人。據說是戴怡64歲時與如皋丫頭春風播種,生出了戴鎦齡。當時大家庭一片責備,但他堅持納妾,老太爺火也真旺,後來還生了一個鉑齡。老太爺駕鶴以後,長子鐵齡立馬將鎦齡的媽媽趕出了家門。家人傳說「鎦齡」有「留下」的含義。可憐的戴鎦齡四歲就沒了爹娘。
父親走後,長兄為父,鐵齡掌管了全家的大權,同邑同宗的海齡(我祖父)家裡的孩子請了國文、英文、算學先生發蒙,他卻只能旁聽,稍大一點就被送去黃橋當學徒,過寄人籬下的日子。戴鎦齡真是好勝好強、能吃苦、要上進、要出人頭地!他先去上海讀之江大學,後又來武昌文華圖專讀書。他苦讀,一本英文字典從A背到Z。爸爸常說戴鎦齡真是下死功夫啊!我父親1931年從愛丁堡大學回國在武漢大學任教,他們經常走動。爸爸常說,新時代了,他哥哥已不敢過度的欺負他了,
我爺爺也幫他向他哥哥掙得了一些房產。他立刻賣了部分產業,自籌路費負笈英倫。他也去了爸爸就讀的愛丁堡大學……
在去英國留學之前,戴鎦齡於1933年9月考入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攻讀圖書館學本科,1935年6月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在此期間,他先後在《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上發表了〈西洋分類法沿革略說〉(1934年6卷1期)、〈紐西蘭民眾圖書館概論〉(1934年6卷2期)、〈尼加拉瓜民眾圖書館概況〉(1934年6卷2期)、〈挪威民眾圖書館概況〉(1934年6卷2期)、〈巴勒斯坦民眾圖書館概況〉(1934年6卷2期)、〈目前美國圖書館界財政問題之面面觀〉(1934年6卷4期)、〈字典簡論〉(1935年7卷1期、7卷2期)、〈Wanted: A Chinese Encyclopedia(我們需要一部中文百科全書)〉(1936年8卷1期)等9篇論文與譯文,1934年還出版了譯著《圖書館的財政問題》(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出版,1934年)。令人驚歎的是,戴鎦齡只是利用1934年近兩個月的暑假就完成了約十萬言的《圖書館的財政問題》的翻譯工作。他在〈譯者序言〉中說:「余於今年夏日譯成此書。回憶暑假兩個月中,玩時愒日,殖學荒怠,僅在迻譯方面,稍稍著力;又以暑威逼人,時有鬱蒸之思,下筆殊難自滿。初意來校後,可從容將其斟酌損益,期於十分信達;但近因校課繁重,卒卒曾無須臾之間,一理宿債。」儘管「疵漏難免」,但是,校長沈祖榮卻對戴鎦齡的譯著評價甚高,曰:「譯者,係本校本年度第二年級同學戴鎦齡君,他是在暑假之間譯成此書,思得有所貢獻於國內圖書館界。余閱畢此書,見其文筆流暢,內容切當,故甚嘉許戴君之發憤,而又想到我國圖書館之困難問題,財政亦其重要之一端,故樂為介紹,並付學校刊行之」。
那時,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採用的是美式圖書館學教育制度,即從修完大學二年級課程的學生中招收圖書館學專業學生,學制僅兩年。因此,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長程煥文教授贊嘆說:「一個大學本科生,在攻讀圖書館學專業的兩年間竟然發表了7篇中文圖書館學專業論文與譯文和1篇英文圖書館學專業論文(另1篇英文論文發表於畢業後參加圖書館工作之時),並且還出版了一部譯著,這的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即便是在今天,很多博士生都做不到,碩士生和本科生就更不用說了,真是令人佩服和不可思議。」
卻說戴鎦齡在愛丁堡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後,於1939年回國。從是年起直至1953年夏,歷任武漢大學外文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及校務委員等職,中間曾兼任武漢地區及四川、安徽兩省兄弟院校教授。1940年考入武大經濟系的黃鎡曾經回憶當年:「在學習中有幾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年級英語是戴鎦齡老師教授的。他對學生要求很嚴,每次上講臺,總要指名一兩位同學站起來背誦已經教過的課文中的某一段,或講解某一段課文,率以為常。」1944年,戴鎦齡與方重等人合編《近代英美散文選》,朱光潛以英文為該書作序,當年8月開明書店印行。葉聖陶為該書所寫廣告詞道:「作者根據多年的教學經驗,精選散文二十五篇,從哈代起到當代英美作家止:內容不限於文藝,政論、自然科學文字、社會科學文字都有。適合於大學和高中高年級英語教學之用。每篇之後附有作者小傳和注釋,對於教學自修,都極有幫助。」
抗戰時期,戴鎦齡曾與武大教授陳源、羅念生、方重、朱光潛、費鑒照等志同道合好友多次聚會,商議翻譯各種西洋名著。四十年代初,有人將他翻譯的散文彙編成集,取名《英國人論》,收入「青年文庫」在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除翻譯外,他還在四川的樂山、成都、重慶等地的報紙雜誌上發表了大量的散文和文學評論,成為頗有知名度的學院派後起之秀。在成都主持開明書店的葉聖陶曾專門在「明湖春」設盛筵兩席,歡迎兩位學者蒞臨成都。一位是從昆明來的朱自清,另一位便是假期來成都訪友的戴鎦齡。葉聖陶後來創辦文藝講習會,邀戴鎦齡主講過西洋文學。朱自清也看好這位剛從英倫返國的青年才子,並通過文人酒會將他介紹給馮玉祥、豐子愷等人。由此可見,戴鎦齡在四十年代初的學界文壇已非等閒之輩58。其侄孫戴克中說,「他在武大時相當活躍,那時他才三十餘歲,詩酒乘年華。在家鄉他也讓人刮目相看,我大伯伯在淪陷的泰興辦楊陋學塾用了他的房子,讓他當掛名的校長,也免了日本人的盤查。」
抗戰勝利,武大復員回到珞珈山,戴鎦齡「也相當進步,反蔣十分積極。吳宓在武大當系主任時他幾乎隔三岔五就去拜訪,和他討論問題。學生不滿意講授《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課程的老師,他主動承擔了該課程的講授任務。他也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撰寫了不少文章載於報刊。解放後他更是積極思想改造,一直是共產黨依靠的力量,1952年就當了外文系主任。1948年他家住在特三區新修的教授住宅,吳宓因為沒有家小而住不上牢騷滿腹。……戴鎦齡對孩子相當嚴厲,我真真的記得一天的傍晚我和李國平教授家的孩子爬在他家的窗臺上看戴老大、戴老二被罰跪在地板上的模樣。」
五十年代受教過戴鎦齡的薛芳馨回憶:「我在武大外語系英語專業學習時,戴鎦齡老師是我們外語系系主任。他教我們大四的英語翻譯課。1952年我們外語系部分同學借調到武漢市外賓招待委員會擔任臨時翻譯時,戴老師與吳紀先教授又曾擔任過我們的顧問。平時他與同學們關係非常好。我們畢業時,他給我們班的同學每人贈送了一本英語文學書籍作為紀念。我獲贈的是一本《蘇聯短篇故事選集》英譯本。……當年在武大外語系英語專業學過的老同學可能還記得,那時有一種傳說:戴老師能背得出英文簡明牛津辭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這本英語詞典是當代英語詞典中最具權威性的詞典之一,詞條豐富。我曾就此事詢問過他老人家,他說:『全部背出一部詞典那是誇大其詞,但查閱的次數多了,許多詞和詞條能熟練掌握這是完全可能的。』我隨即告訴他,我校的一位英語教師最近到杭州旅遊,回來後他抱怨杭州的旅館多收了他的錢。他用了『Overcharge』這個詞,戴老師即用英語解釋『Overcharge』的意思,即『Charge too much for thing to person』(對人或物要價太多或太高)。我回去一查,果然與簡明牛津詞典上的解釋一模一樣。這說明戴老師對該詞典應用之熟練,記憶力之強。」
1953年全國院系調整,中南五省外語院系合併入廣州中山大學後,戴鎦齡便長期在中大任教(「文革」期間曾在廣州外國語學院任教四年),先後任外語系教授、系主任、校務委員、校黨委委員等職。在他到中大之前,廣東的英語教育幾乎為空白。中大外語學院教授王賓回憶,「是戴老壯大了中大外語學院。文革前,中大的英語系一直佔據著全國前三的位置,這全賴於戴老帶領著一批教師潛心治學與悉心育人。」
熬過了文化革命之後,戴鎦齡趕上了中國難得的好時代。1981年11月,他被國務院批准為英語語言文學專業首批博士生導師,接著便培養出中國第一位英語語言文學博士。他先後為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開設過十多門課程,如英語詩歌、歐洲古典名著、莎士比亞、西歐文藝批評史、英語寫作、翻譯等。
戴鎦齡專於英國語言文學,尤擅古典文藝批評,還旁涉圖書館學、語言和文藝、詞典學和翻譯學。他的翻譯以不失原文語言風格、精神實質見長,譯詩尤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在中國有很多譯本,他的譯本在音節和韻式的處理方面獨闢蹊徑,成為其中翹楚。據其夫人徐開蜀介紹,他最初的動機不是發表,而是作為戀愛時兩地之間的書信。譯一首,便給徐寄去一首。全部譯完,徐保管,他又不斷地修改,最後卻毀於紅衛兵之手。好在儲安平主持《觀察》雜誌時,得悉戴鎦齡藏有妙筆之作,討去四首刊登出來,遂得以流傳。眾所周知,詩歌一經翻譯淪為散文的分行羅列,由音步或者平仄體現出來的形式美竟告闕如。戴鎦齡的詩歌修養跨越英漢兩種語言系統,翻譯莎詩時自然要追求形式美的對稱,其譯文堪稱現代中國翻譯史上一絕。
在其譯作中,最為大眾所知的,則是他翻譯了湯瑪斯‧莫爾《烏托邦》一書。其中堪稱譯名經典的「烏托邦」一詞,便是由他首創。該書的原著是英國政治家和作家湯瑪斯‧莫爾;Utopia是他根據希臘文生造出來的一個詞,ou在希臘文裡主要是「無」的意思,topos在希臘文裡有「位置、地方、空間」的意思。譯名「烏托邦」可以理解為「烏」是沒有,「托」是寄託,「邦」是國家,這三個字合起來的意思即為「空想的國家」。
除了《烏托邦》,戴鎦齡還譯有《浮士德博士的悲劇》(英/馬婁著)、《英國文學史綱》(蘇/阿尼克斯特著),撰有論文〈論科學實驗對近代英國散文風格形成的影響〉、〈近代英國傳記的簡潔風格〉、〈英國文藝批評史中的唯物論觀點傳統〉、〈談中西文論中的以水為喻〉等,著作有《戴鎦齡文集:智者的歷程》、《外國圖書館學術研究:戴鎦齡文集續篇》等。正是因為他的博學多識、為中國英語教育作出的傑出貢獻,他的名字已被英國劍橋世界傳記中心載入「名人辭典」,成為一名真正受到世界認同的學者。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才情與風範:抗戰時期的武大教授續編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40 |
中文書 |
$ 282 |
社會人物 |
$ 288 |
學者/科學家 |
$ 288 |
社會人文 |
$ 288 |
歷史 |
電子書 |
$ 320 |
中國史地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才情與風範:抗戰時期的武大教授續編
抗戰時期,國立武漢大學西遷樂山後弦歌不輟,創造了教育史上的輝煌奇跡,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本書搜羅了當年數十位文法理工四大學院教授們的事蹟與逸聞,展現他們才情四射的人格魅力與為人師表的泱泱風範。書中絕大多數教授均有留洋經歷,在國難時期都不約而同選擇回到祖國,投身抗戰;他們為國家、為教育付出的心力,委實難能可貴,令人感佩。
本書特色
這是一部以列傳形式書寫的中國知識份子命運史,作者蒐集豐富而珍貴之史料,佐以詳實之筆調,呈現出那個年代難能可貴的學人風貌。
作者簡介:
張在軍
筆名張弩弓。中國鄂中京山人。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著有《文化苦語》、《滿天星》、《花香筆不香》、《苦難與輝煌──抗戰時期的武漢大學》、《堅守與薪傳──抗戰時期的武大教授》、《西遷與東還──抗戰時期武漢大學編年史稿》等文集十餘種。
章節試閱
戴鎦齡:讓「烏托邦」進入中文的人
提起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你也許並不陌生。但你一定不知道,20世紀三十年代,剛從愛丁堡大學學成歸來的他,將莎翁的十四行詩,一首一首地譯成中文,當作情書,寄給了後來成為他夫人的女友。這一「無心之譯」,後來成就了一段被學界爭相傳誦的佳作,至今仍然被公認為是最好的莎翁十四行詩譯作之一。
在他的譯作中,最為大眾所知的,則是他翻譯了湯瑪斯‧莫爾《烏托邦》一書。其中堪稱譯名經典的「烏托邦」一詞,便是由他首創。
八十年代培養出我國第一位英語語言文學博士,他的名字已被英國...
提起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你也許並不陌生。但你一定不知道,20世紀三十年代,剛從愛丁堡大學學成歸來的他,將莎翁的十四行詩,一首一首地譯成中文,當作情書,寄給了後來成為他夫人的女友。這一「無心之譯」,後來成就了一段被學界爭相傳誦的佳作,至今仍然被公認為是最好的莎翁十四行詩譯作之一。
在他的譯作中,最為大眾所知的,則是他翻譯了湯瑪斯‧莫爾《烏托邦》一書。其中堪稱譯名經典的「烏托邦」一詞,便是由他首創。
八十年代培養出我國第一位英語語言文學博士,他的名字已被英國...
»看全部
作者序
這是我寫武大的第四本書。我所以甘願下幾年功夫、費萬貫錢財來為當年民國五大高校1之一的國立武漢大學留下某種歷史軌跡,是為了從特定角度來回顧中國教育最輝煌的時代。同時也因為秀威願意出版這種連武大自己也不願意出的「賠錢貨」。否則,我興許只寫一兩本就不會繼續了。
當初在出版第一部書《苦難與輝煌:抗戰時期的武漢大學》的過程中,編輯善意提醒我書稿篇幅過長的問題,所以出第二部書《堅守與薪傳:抗戰時期的武大教授》(以下簡稱《堅守》)時,我就痛下狠心刪削篇幅,控制字數。
好比吳冠中當年毀畫一樣,開始屠殺...
當初在出版第一部書《苦難與輝煌:抗戰時期的武漢大學》的過程中,編輯善意提醒我書稿篇幅過長的問題,所以出第二部書《堅守與薪傳:抗戰時期的武大教授》(以下簡稱《堅守》)時,我就痛下狠心刪削篇幅,控制字數。
好比吳冠中當年毀畫一樣,開始屠殺...
»看全部
目錄
自序
第一章:文學院的教授
中文系
馮沅君:驚鴻一瞥的詞史女教授
黃 焯:不言學派的章黃繼承者
外文系
費鑒照:肺病中早逝的浪漫詩人
陳登恪:中文外文兩系「共有財產」
陳堯成:一輩子的武大日語教授
李儒勉:三進三出的語音學教授
顧 如:從「南開皇后」到「白宮女皇」
李 納:「不學無術」的英國籍教授
戴鎦齡:讓「烏托邦」進入中文的人
楊安妮:熱心抗日的瑞典女教授
羅念生:獻身古希臘文化的學者
朱君允:管理女生的外文系教授
史學系
楊人楩:信仰自由主義的史學家
徐中舒:先秦史研究的領軍人物
梁園...
第一章:文學院的教授
中文系
馮沅君:驚鴻一瞥的詞史女教授
黃 焯:不言學派的章黃繼承者
外文系
費鑒照:肺病中早逝的浪漫詩人
陳登恪:中文外文兩系「共有財產」
陳堯成:一輩子的武大日語教授
李儒勉:三進三出的語音學教授
顧 如:從「南開皇后」到「白宮女皇」
李 納:「不學無術」的英國籍教授
戴鎦齡:讓「烏托邦」進入中文的人
楊安妮:熱心抗日的瑞典女教授
羅念生:獻身古希臘文化的學者
朱君允:管理女生的外文系教授
史學系
楊人楩:信仰自由主義的史學家
徐中舒:先秦史研究的領軍人物
梁園...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張在軍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3-12-03 ISBN/ISSN:978986326206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50頁
- 類別: 中文書> 傳記> 社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