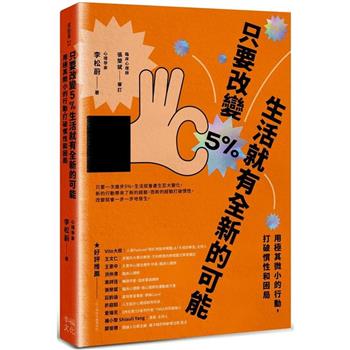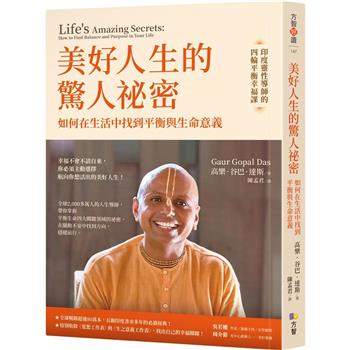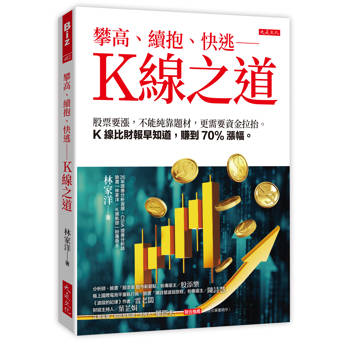明代詩人寫作了大量歌詠崑曲的詩篇,對於崑曲歷史研究具有三點重要價值:
一、對於崑曲演唱,包括職業戲班、家班演出和虎丘、西湖等地的唱曲活動,作了翔實生動的記錄。
二、為崑曲批評提供了詩化的形式,曲家和劇作,一得詩人歌詠,常常提高了知名度,擴大了影響。
三、對於崑曲理論中的問題,作了富有詩意的表述,如著名的「沈湯之爭」,雙方都曾以詩歌作為表述自己見解的方式。
詠崑曲詩歌,包括祝允明、李攀龍、王世貞、湯顯祖、沈璟、袁宏道、袁中道等名家之作,也包括不以詩名的作者的成功之作。本書首次對這方面詩歌發掘整理,從中精選280餘首,加以注釋與簡析,使其價值得以彰顯,亦使讀者於欣賞詩篇中得到審美愉悅。
本書特色
本書首次對這方面詩歌發掘整理,從中精選280餘首,加以注釋與簡析,使其價值得以彰顯,亦使讀者於欣賞詩篇中得到審美愉悅。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明代詠崑曲詩歌選注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05 |
中文書 |
$ 427 |
表演藝術 |
$ 475 |
戲劇 |
$ 486 |
各類戲劇 |
$ 486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明代詠崑曲詩歌選注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趙山林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曾任華東師範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副院長。在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洛杉磯大學、密西根大學、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校參加學術會議、訪問或發表演講。專著有《中國戲曲觀眾學》、《中國戲劇學通論》、《中國戲曲傳播接受史》等。
趙婷婷
史丹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博士候選人。研究中國戲劇、戲劇理論、小說和詩歌。2014年獲美國亞洲戲劇研究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Performance)「新興學者獎」(Emerging Scholar Award)。
趙山林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曾任華東師範大學文學與藝術學院副院長。在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洛杉磯大學、密西根大學、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高校參加學術會議、訪問或發表演講。專著有《中國戲曲觀眾學》、《中國戲劇學通論》、《中國戲曲傳播接受史》等。
趙婷婷
史丹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博士候選人。研究中國戲劇、戲劇理論、小說和詩歌。2014年獲美國亞洲戲劇研究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Performance)「新興學者獎」(Emerging Scholar Award)。
目錄
崑曲叢書第三輯總序
前言
體例
謝肅(不詳)
閶門望虎丘
祝允明(一四六○至一五二六)
觀《蘇卿持節》劇
觀戲有感二首
王濟(一四七四至一五四○)
壬午秋宴諸公羅春亭
顧璘(一四七六至一五四五)
武皇南巡舊京歌
韓邦靖(一四八八至一五二三)
席上贈歌者
黃省曾(一四九○至一五四○)
江南曲(五首選一)
謝榛(一四九五至一五七五)
重九前一日謝黃門仲川同酌溫中丞純甫宅,賦得風字
岳岱(一四九七至一五七四後)
悼樂工劉淮
聽歌
吳錦(不詳)
贈查叟
吳承恩(約一五○○至一五八二)
金陵何太史宅聽小伶彈箏次韻
高應冕(一五○三至一五六九)
張澤山池亭觀伎
何良俊(一五○六至一五七三)
夏日同邢雉山太史、張王屋太學、舍弟叔皮祠部集姚秋澗市隱園,雜詠四首(選一)
許石城宅賞牡丹
謝讜(一五一二至一五六九)
送徐天池入京
送王伯良至京看其郎君
李攀龍(一五一四至一五七○)
寄贈梁伯龍
歐大任(一五一六至一五九六)
伏日同文壽丞、徐子與、顧汝和飲袁魯望齋中,聽謳者楊清歌
梁辰魚(一五一九至一五九一)
冬夜莫雲卿攜妓宴故相國顧文康公南堂,同李文仲、張完甫、陳仲甫、張仲立、顧茂仁、茂儉,分得梁字
春夜高瑞南宅賞牡丹聽歌姬,次韻三首
孫樓(生卒年不詳)
宴梁少白宅,聽吳中新樂,群至半山橋
陳完(不詳)
教戲
徐學謨(一五二一至一五九三)
子柔嗔曼重習弋陽舊曲,醉中誤出穢語,醒複悔之,更裁五絕句相解,予如其數代曼作答(五首)
葉權(一五二二至一五七八)
聽查八十琵琶
王寅(不詳)
過休陽訪查八十不遇二首
汪道昆(一五二五至一五九三)
席上觀《吳越春秋》有作,凡四首
王世貞(一五二六至一五九○)
嘲梁伯龍
張鳳翼(一五二七至一六一三)
楊校書過池上看鴛鴦,因為顧曲之集,兼懷梅子馬
白堤舟次觀朱鴻臚在明女樂
傳《灌園》畢,懷子繩
顧學憲攜聲伎入城,縱觀連日作
毛肇明、方叔覲、禇藎甫、楊濟卿、蔣公鼎、文夢珠六君挈過承天寺張女戲作
始春閱顧道行詩志感
懷顧道行三首
盛時泰(一五二九至一五七八)
酬梁伯龍
張獻翼(?至一六○四)
劉會卿病中典衣買歌者因持絮酒就其喪所試之
劉鳳(不詳)
觀作劇
贈主謳殷玉琴(四首)
程公遠(不詳)
西江月‧戒婦女觀戲
田藝蘅(不詳)
席中逢故顧閣老家侍兒
王昆侖(不詳)
宮詞(五十二首選一)
王叔承(不詳)
金陵豔曲
夏緇(不詳)
南中曲
顧養謙(一五三七至一六○四)
蘇州歌
焦竑(一五四○至一六二○)
邢供奉(二首選一)
顧大典(一五四一至一五九六)
贈沈伯英
屠隆(一五四二至一六○五)
仙人好樓居為梅禹金
長安元夕聽武生吳歌
王驥德(一五四二至一六二三)
【榴花泣】散套‧哭呂勤之
汪道會(一五四四至一六一三)
煙條館聞歌(五首選三)
吳夢暘(一五四六至一六二○)
暑夜孝若攜妓飲長橋上,同諸從踏月歌
汪景淳室聽伎,同晉叔、諸德祖賦四首
梅鼎祚(一五四九至一六一五)
酬屠長卿序《章台》傳奇,因過新都寄汪司馬
頓姬坐追談正德南巡事
鄒迪光(一五五○至一六二六)
正月十六夜集友人于一指堂,觀演昆侖奴、紅線故事,分得十四寒
冬夜與顧仲默諸君小集,看演《神鏡》傳奇,次仲默韻
酒未闌而范長白忽乘夜過唁,複爾開尊,演霍小玉《紫釵》,不覺達曙,和覺父韻
八月十五夜虎丘坐月(三首選一)
餘閱搬演《曇花》傳奇而有悟,立散兩部梨園,將於空門置力焉,示曲師朱輪六首(選三)
鴻寶堂秋蘭花下留錢征榮小集,看演《藍橋》傳奇。錢有作,和韻
友人攜所歡詣餘草堂看劇,有賦
元成丈載酒樓船於闔閭城西濠沿泛衍劇二首
再集元成先生清晝堂二首
一指堂同承明兄看演《長命縷》傳奇,此是梅禹金所作,禹金物故,即事生感二首,仍用詠玉蘭之韻
余有童兒,皆黃口也,而能衍劇,覺父以詩賞之,即韻為答
周承明有端午前一日蔚藍堂觀演,《裴航》傳奇之作,余於午日集客觀劇,就其韻和之
立秋後二日集客鴻寶堂演《蕉帕》傳奇,和錢征榮韻
湯顯祖(一五五○至一六一六)
戲答宣城梅禹金四絕
見改竄《牡丹》詞者失笑
哭婁江女子二首有序
七夕醉答君東二首
醉答君東怡園書六絕(選一)
寄生腳張羅二,恨吳迎旦,口號二首
正唱《南柯》,忽聞從龍悼內楊,傷之二首
寄劉天虞
唱《二夢》
作紫襴戲衣二首
聽於采唱《牡丹》
口號付小葛送山子廣陵三首
滕王閣看王有信演《牡丹亭》二首
越舸以吳伶來,期之元夕,漫成二首
傷歌者
九日遣宜伶赴甘參知永新
楚江秋四首
臧懋循(一五五○至一六二一)
夜集流波館聽楊姬歌,分得「真」字
九月十六夜集汪景純宅,同吳允兆、諸德祖諸君子聽妓,因拈庭來顰時韻,賦得四絕
俞安期(一五五○至一六二七後)
次韻和范長倩觀家歌僮作劇二十首,因調長倩(其二)
胡應麟(一五五一至一六○二)
寄張伯起
歐水部招同張太學、劉大理、顧司勳夜集徐園,遲李臨淮不至,同用心字二首
贈高深甫二首
狄參戎邀集園亭觀女劇,即席賦
羅生館中閱伎作
徐明府仁卿招集墅中有序
七月望抵武林,陸履素使君招集湖上,樂人周生瑾者年少善歌,酒酣持扇索題,即席塗抹四韻
狄明叔後房姬侍甚都,而新畜小鬟十餘,合奏南劇,尤為賓客豔慕,先是餘未及睹,特此訊之
伶人奏劇,適歌陸浚《明珠記》,戲成此章呈水部
狄明叔邀集新居,命女伎奏劇,凡《玉簮》、《浣紗》、《紅拂》三本,即席成七言律四章
為沈生題扇。沈生善歌,余使習司馬《大雅堂》四劇,詩以勖之
歌者屢召不至,汪生狂發,據高座劇談《水滸傳》,奚童彈箏佐之,四席並傾,餘賦一絕賞之
同房仲過雲間,舟中聽趙五叔遠夜歌作
再贈小范歌《玉簪》
湖上酒樓聽歌王檢討敬夫、汪司馬伯玉二樂府及張伯起傳奇,戲作三首
贈梨園邵生
安二席上重聽輕紅歌作
李應徵(不詳)
舟過松陵沈子勺邀同顧別駕王半刺諸公宴集作兼呈長公伯英
徐熥(不詳)
七夕曹能始宅上觀妓
歌者陳郎戲作姬妝即席調贈
吳兆(不詳)
潯陽張侍禦宅詠伎
冬至夜集曹能始園亭觀伎
錢希言(約一六一二前後在世)
今夕篇
沈璟(一五五三至一六一○)
【二郎神】套曲
張大復(一五五四至一六三○)
夏士琰投贈《草堂聽歸、雷兩翁談曲》之作,賦答四韻
懷人詩(十一首選二)
江盈科(一五五五至一六○五)
湯理問邀集陳園,楊太史、鍾內翰、袁國學同集,看演《荊釵》
董其昌(一五五五至一六三六)
清源狄將軍席上觀女樂
潘之恒(一五五六至一六二二)
昆山聽楊生曲有贈
白下逢梁伯龍感舊二首
觀劇贈王文冰(五首)
觀演杜麗娘,贈阿蘅江孺
觀演柳夢梅,贈阿荃昌孺
病中觀劇有懷吳越石
贈吳亦史(四首)
范允臨(一五五八至一六四一)
贈清之歌姬彩鸞
祁承火業(一五六三至一六二八)
單子老而耽於傳奇,手著行世者已數種,偕予同遊苕溪舟中戲贈
黃知和(不詳)
讀《四聲猿》,調寄沁園春
王伯稠(不詳)
贈梁伯龍
聽沈二彈北曲
贈歌者
柳應芳(不詳)
金陵竹枝詞二首
湯三俊(不詳)
吳江竹枝詞
陸弼(不詳)
晩泊毗陵諸君攜酒過集舟中
顧起元(一五六五至一六二八)
樂府
復憶得十二事,亦齋中所不廢也,因漫賦之。一入宦途,雅好都盡,言此但似憶昨夢耳,為之慨然(十二首選三)
陶奭齡(一五六五至一六三九)
乳周侄治具曹山,邀謝大將軍寤雲,出家伎奏樂,賓主各沾醉。丈方對弈,即鼾睡局中。夜歸風雨甚,偶讀堯丈詩,有「醉和風雨夜深歸」之句,遂足成博笑。兼訂後期,時二月晦日也
程嘉燧(一五六五至一六四三)
聽曲贈趙五老(五首選四)
曲中聽黃問琴歌,分韻八首
贈徐君圖按曲圖歌
聞歌引題畫新柳贈叟徐四
湯賓尹(一五六七至一六二八後)
南中春詞(二十三首選三)
虎丘
婁堅(一五六七至一六三一)
起龍枉招,偶以觀劇不赴
袁宏道(一五六八至一六一○)
張伯起
江南子(五首選一)
迎春歌和江進之
答君禦諸作(四首選一)
馮小青(不詳)
讀《牡丹亭》
袁中道(一五七○至一六二三)
流波館宴集,時楊舜華病起同長孺諸公賦
同顧司馬沖庵虎丘看月,兼懷梅開府克生
茅元儀(一五七○至一六三七)
觀大將軍謝簡之家伎,演所自述《蝴蝶夢》樂府
陳泰始京兆開社,觀演《李白彩毫記》,同馬季聲、徐興公、鄭汝交、倪柯古、陳叔度、高景倩、林懋禮、陳昌基賦,探得四支
卜世臣(一五七二至一六四五)
【上馬踢】《中秋夜集虎丘四望閣》套曲
鍾惺(一五七四至一六二四)
舟中看《邯鄲夢》傳奇偶題左方
彥吉先生席上觀劇贈周郎七絕二首
王思任(一五七四至一六四六)
題湯若士小像
李流芳(一五七五至一六二九)
三月十三夜同陸大無界待月虎丘得殿字
海上和孟陽觀伎詩次韻
范鳳翼(一五七五至一六五五)
李徹侯玄素同文文學啟美迭奏家樂,招予同觀,分韻得「豪」字,時玄素于席上成詩
蔡復一(一五七六至一六二五)
送韓孟郁
茅維(一五七六至一六四四後)
病裡思聽音樂,戲呈諸公
汪然明(一五七七至一六五五)
春日湖上觀曹氏女樂
秋日過汝開侄山居聽周元仲彈琴,余出歌兒佐酒
次兒去粵西三年不通音信,入夏焦勞成疾,伏枕浹旬,得詩八章,自嘲並示兒輩(八首其七)
徐石麒(一五七八至一六四五)
雙舟伎酌
沈德符(一五七八至一六四二)
秦淮冶兒曲十六首(選一)
慧山逢徐君話舊五首(選一)
毛以燧(不詳)
哭王伯良先生詩十三首(選二)
沈自晉(一五八三至一六六五)
臨江仙
范景文(一五八七至一六四四)
題米家童有序
秋夜鄧未孩、馮上仙、曹愚公招飲淮河樓上,看演《黃粱》傳奇
辰叟、聖符招同介孺看演《牡丹亭》傳奇,得三字
招戲設席于吳門舟上,晚泊虎丘
病起聽歌坐中,約以茶賞,適仁常寄詩相訊,即用其韻成詠
臘日郭伏生來自敬仲所,留飲味元堂,同王貞伯
立秋日錢與立諸君送之廣陵影園,月下聽歌,次鄭超宗韻
阮大鋮(一五八七至一六四六)
同虞來初、馮夢龍、潘國美、彭天錫登北固甘露寺
劉同升(一五八七至一六四六)
同年宴集演《牡丹亭記》有序
王彥泓(一五九○?至一六四二)
櫟園姨翁坐上預聽名歌,並觀二劍,即事呈詠
白山茶插髻,甚可觀,因書二絕
逋客叔菊筵
雲客堂中夜集(二首)
凌義渠(一五九一至一六四四)
汶陽懷范香令
吳應箕(一五九四至一六四五)
旅夜看《犀軸》傳奇,是沈青霞煉事,末句深有感于聞氏
朱隗(不詳)
鴛湖主人出家姬演《牡丹亭記》歌
屠茝佩(不詳)
觀沈氏諸姬演劇
許經(生卒年不詳)
四印堂夜集觀姬人紫雲歌舞即席賦贈二首(之二)
張岱(一五九七至一六七九)
祁奕遠鮮雲小伶歌
曲中妓王月生
胡夏客(一五九九至一六七二)
江南曲
祁彪佳(一六○二至一六四五)
贈袁鳧公
坐千人石聞童子清歌,有客倚洞簫和之
徐士俊(一六○二至一六八一)
哭卓珂月(六首)
王翃(一六○三至一六五三)
鷓鴣天․同馬巽倩水部、張深之金吾、陸嗣端職方、吳余常文學飲月斷橋,戲為陳章侯茂才贈蔣、王二較書
賀聖朝
碧牡丹․同朱近修、吳於庭觀女劇
前言
體例
謝肅(不詳)
閶門望虎丘
祝允明(一四六○至一五二六)
觀《蘇卿持節》劇
觀戲有感二首
王濟(一四七四至一五四○)
壬午秋宴諸公羅春亭
顧璘(一四七六至一五四五)
武皇南巡舊京歌
韓邦靖(一四八八至一五二三)
席上贈歌者
黃省曾(一四九○至一五四○)
江南曲(五首選一)
謝榛(一四九五至一五七五)
重九前一日謝黃門仲川同酌溫中丞純甫宅,賦得風字
岳岱(一四九七至一五七四後)
悼樂工劉淮
聽歌
吳錦(不詳)
贈查叟
吳承恩(約一五○○至一五八二)
金陵何太史宅聽小伶彈箏次韻
高應冕(一五○三至一五六九)
張澤山池亭觀伎
何良俊(一五○六至一五七三)
夏日同邢雉山太史、張王屋太學、舍弟叔皮祠部集姚秋澗市隱園,雜詠四首(選一)
許石城宅賞牡丹
謝讜(一五一二至一五六九)
送徐天池入京
送王伯良至京看其郎君
李攀龍(一五一四至一五七○)
寄贈梁伯龍
歐大任(一五一六至一五九六)
伏日同文壽丞、徐子與、顧汝和飲袁魯望齋中,聽謳者楊清歌
梁辰魚(一五一九至一五九一)
冬夜莫雲卿攜妓宴故相國顧文康公南堂,同李文仲、張完甫、陳仲甫、張仲立、顧茂仁、茂儉,分得梁字
春夜高瑞南宅賞牡丹聽歌姬,次韻三首
孫樓(生卒年不詳)
宴梁少白宅,聽吳中新樂,群至半山橋
陳完(不詳)
教戲
徐學謨(一五二一至一五九三)
子柔嗔曼重習弋陽舊曲,醉中誤出穢語,醒複悔之,更裁五絕句相解,予如其數代曼作答(五首)
葉權(一五二二至一五七八)
聽查八十琵琶
王寅(不詳)
過休陽訪查八十不遇二首
汪道昆(一五二五至一五九三)
席上觀《吳越春秋》有作,凡四首
王世貞(一五二六至一五九○)
嘲梁伯龍
張鳳翼(一五二七至一六一三)
楊校書過池上看鴛鴦,因為顧曲之集,兼懷梅子馬
白堤舟次觀朱鴻臚在明女樂
傳《灌園》畢,懷子繩
顧學憲攜聲伎入城,縱觀連日作
毛肇明、方叔覲、禇藎甫、楊濟卿、蔣公鼎、文夢珠六君挈過承天寺張女戲作
始春閱顧道行詩志感
懷顧道行三首
盛時泰(一五二九至一五七八)
酬梁伯龍
張獻翼(?至一六○四)
劉會卿病中典衣買歌者因持絮酒就其喪所試之
劉鳳(不詳)
觀作劇
贈主謳殷玉琴(四首)
程公遠(不詳)
西江月‧戒婦女觀戲
田藝蘅(不詳)
席中逢故顧閣老家侍兒
王昆侖(不詳)
宮詞(五十二首選一)
王叔承(不詳)
金陵豔曲
夏緇(不詳)
南中曲
顧養謙(一五三七至一六○四)
蘇州歌
焦竑(一五四○至一六二○)
邢供奉(二首選一)
顧大典(一五四一至一五九六)
贈沈伯英
屠隆(一五四二至一六○五)
仙人好樓居為梅禹金
長安元夕聽武生吳歌
王驥德(一五四二至一六二三)
【榴花泣】散套‧哭呂勤之
汪道會(一五四四至一六一三)
煙條館聞歌(五首選三)
吳夢暘(一五四六至一六二○)
暑夜孝若攜妓飲長橋上,同諸從踏月歌
汪景淳室聽伎,同晉叔、諸德祖賦四首
梅鼎祚(一五四九至一六一五)
酬屠長卿序《章台》傳奇,因過新都寄汪司馬
頓姬坐追談正德南巡事
鄒迪光(一五五○至一六二六)
正月十六夜集友人于一指堂,觀演昆侖奴、紅線故事,分得十四寒
冬夜與顧仲默諸君小集,看演《神鏡》傳奇,次仲默韻
酒未闌而范長白忽乘夜過唁,複爾開尊,演霍小玉《紫釵》,不覺達曙,和覺父韻
八月十五夜虎丘坐月(三首選一)
餘閱搬演《曇花》傳奇而有悟,立散兩部梨園,將於空門置力焉,示曲師朱輪六首(選三)
鴻寶堂秋蘭花下留錢征榮小集,看演《藍橋》傳奇。錢有作,和韻
友人攜所歡詣餘草堂看劇,有賦
元成丈載酒樓船於闔閭城西濠沿泛衍劇二首
再集元成先生清晝堂二首
一指堂同承明兄看演《長命縷》傳奇,此是梅禹金所作,禹金物故,即事生感二首,仍用詠玉蘭之韻
余有童兒,皆黃口也,而能衍劇,覺父以詩賞之,即韻為答
周承明有端午前一日蔚藍堂觀演,《裴航》傳奇之作,余於午日集客觀劇,就其韻和之
立秋後二日集客鴻寶堂演《蕉帕》傳奇,和錢征榮韻
湯顯祖(一五五○至一六一六)
戲答宣城梅禹金四絕
見改竄《牡丹》詞者失笑
哭婁江女子二首有序
七夕醉答君東二首
醉答君東怡園書六絕(選一)
寄生腳張羅二,恨吳迎旦,口號二首
正唱《南柯》,忽聞從龍悼內楊,傷之二首
寄劉天虞
唱《二夢》
作紫襴戲衣二首
聽於采唱《牡丹》
口號付小葛送山子廣陵三首
滕王閣看王有信演《牡丹亭》二首
越舸以吳伶來,期之元夕,漫成二首
傷歌者
九日遣宜伶赴甘參知永新
楚江秋四首
臧懋循(一五五○至一六二一)
夜集流波館聽楊姬歌,分得「真」字
九月十六夜集汪景純宅,同吳允兆、諸德祖諸君子聽妓,因拈庭來顰時韻,賦得四絕
俞安期(一五五○至一六二七後)
次韻和范長倩觀家歌僮作劇二十首,因調長倩(其二)
胡應麟(一五五一至一六○二)
寄張伯起
歐水部招同張太學、劉大理、顧司勳夜集徐園,遲李臨淮不至,同用心字二首
贈高深甫二首
狄參戎邀集園亭觀女劇,即席賦
羅生館中閱伎作
徐明府仁卿招集墅中有序
七月望抵武林,陸履素使君招集湖上,樂人周生瑾者年少善歌,酒酣持扇索題,即席塗抹四韻
狄明叔後房姬侍甚都,而新畜小鬟十餘,合奏南劇,尤為賓客豔慕,先是餘未及睹,特此訊之
伶人奏劇,適歌陸浚《明珠記》,戲成此章呈水部
狄明叔邀集新居,命女伎奏劇,凡《玉簮》、《浣紗》、《紅拂》三本,即席成七言律四章
為沈生題扇。沈生善歌,余使習司馬《大雅堂》四劇,詩以勖之
歌者屢召不至,汪生狂發,據高座劇談《水滸傳》,奚童彈箏佐之,四席並傾,餘賦一絕賞之
同房仲過雲間,舟中聽趙五叔遠夜歌作
再贈小范歌《玉簪》
湖上酒樓聽歌王檢討敬夫、汪司馬伯玉二樂府及張伯起傳奇,戲作三首
贈梨園邵生
安二席上重聽輕紅歌作
李應徵(不詳)
舟過松陵沈子勺邀同顧別駕王半刺諸公宴集作兼呈長公伯英
徐熥(不詳)
七夕曹能始宅上觀妓
歌者陳郎戲作姬妝即席調贈
吳兆(不詳)
潯陽張侍禦宅詠伎
冬至夜集曹能始園亭觀伎
錢希言(約一六一二前後在世)
今夕篇
沈璟(一五五三至一六一○)
【二郎神】套曲
張大復(一五五四至一六三○)
夏士琰投贈《草堂聽歸、雷兩翁談曲》之作,賦答四韻
懷人詩(十一首選二)
江盈科(一五五五至一六○五)
湯理問邀集陳園,楊太史、鍾內翰、袁國學同集,看演《荊釵》
董其昌(一五五五至一六三六)
清源狄將軍席上觀女樂
潘之恒(一五五六至一六二二)
昆山聽楊生曲有贈
白下逢梁伯龍感舊二首
觀劇贈王文冰(五首)
觀演杜麗娘,贈阿蘅江孺
觀演柳夢梅,贈阿荃昌孺
病中觀劇有懷吳越石
贈吳亦史(四首)
范允臨(一五五八至一六四一)
贈清之歌姬彩鸞
祁承火業(一五六三至一六二八)
單子老而耽於傳奇,手著行世者已數種,偕予同遊苕溪舟中戲贈
黃知和(不詳)
讀《四聲猿》,調寄沁園春
王伯稠(不詳)
贈梁伯龍
聽沈二彈北曲
贈歌者
柳應芳(不詳)
金陵竹枝詞二首
湯三俊(不詳)
吳江竹枝詞
陸弼(不詳)
晩泊毗陵諸君攜酒過集舟中
顧起元(一五六五至一六二八)
樂府
復憶得十二事,亦齋中所不廢也,因漫賦之。一入宦途,雅好都盡,言此但似憶昨夢耳,為之慨然(十二首選三)
陶奭齡(一五六五至一六三九)
乳周侄治具曹山,邀謝大將軍寤雲,出家伎奏樂,賓主各沾醉。丈方對弈,即鼾睡局中。夜歸風雨甚,偶讀堯丈詩,有「醉和風雨夜深歸」之句,遂足成博笑。兼訂後期,時二月晦日也
程嘉燧(一五六五至一六四三)
聽曲贈趙五老(五首選四)
曲中聽黃問琴歌,分韻八首
贈徐君圖按曲圖歌
聞歌引題畫新柳贈叟徐四
湯賓尹(一五六七至一六二八後)
南中春詞(二十三首選三)
虎丘
婁堅(一五六七至一六三一)
起龍枉招,偶以觀劇不赴
袁宏道(一五六八至一六一○)
張伯起
江南子(五首選一)
迎春歌和江進之
答君禦諸作(四首選一)
馮小青(不詳)
讀《牡丹亭》
袁中道(一五七○至一六二三)
流波館宴集,時楊舜華病起同長孺諸公賦
同顧司馬沖庵虎丘看月,兼懷梅開府克生
茅元儀(一五七○至一六三七)
觀大將軍謝簡之家伎,演所自述《蝴蝶夢》樂府
陳泰始京兆開社,觀演《李白彩毫記》,同馬季聲、徐興公、鄭汝交、倪柯古、陳叔度、高景倩、林懋禮、陳昌基賦,探得四支
卜世臣(一五七二至一六四五)
【上馬踢】《中秋夜集虎丘四望閣》套曲
鍾惺(一五七四至一六二四)
舟中看《邯鄲夢》傳奇偶題左方
彥吉先生席上觀劇贈周郎七絕二首
王思任(一五七四至一六四六)
題湯若士小像
李流芳(一五七五至一六二九)
三月十三夜同陸大無界待月虎丘得殿字
海上和孟陽觀伎詩次韻
范鳳翼(一五七五至一六五五)
李徹侯玄素同文文學啟美迭奏家樂,招予同觀,分韻得「豪」字,時玄素于席上成詩
蔡復一(一五七六至一六二五)
送韓孟郁
茅維(一五七六至一六四四後)
病裡思聽音樂,戲呈諸公
汪然明(一五七七至一六五五)
春日湖上觀曹氏女樂
秋日過汝開侄山居聽周元仲彈琴,余出歌兒佐酒
次兒去粵西三年不通音信,入夏焦勞成疾,伏枕浹旬,得詩八章,自嘲並示兒輩(八首其七)
徐石麒(一五七八至一六四五)
雙舟伎酌
沈德符(一五七八至一六四二)
秦淮冶兒曲十六首(選一)
慧山逢徐君話舊五首(選一)
毛以燧(不詳)
哭王伯良先生詩十三首(選二)
沈自晉(一五八三至一六六五)
臨江仙
范景文(一五八七至一六四四)
題米家童有序
秋夜鄧未孩、馮上仙、曹愚公招飲淮河樓上,看演《黃粱》傳奇
辰叟、聖符招同介孺看演《牡丹亭》傳奇,得三字
招戲設席于吳門舟上,晚泊虎丘
病起聽歌坐中,約以茶賞,適仁常寄詩相訊,即用其韻成詠
臘日郭伏生來自敬仲所,留飲味元堂,同王貞伯
立秋日錢與立諸君送之廣陵影園,月下聽歌,次鄭超宗韻
阮大鋮(一五八七至一六四六)
同虞來初、馮夢龍、潘國美、彭天錫登北固甘露寺
劉同升(一五八七至一六四六)
同年宴集演《牡丹亭記》有序
王彥泓(一五九○?至一六四二)
櫟園姨翁坐上預聽名歌,並觀二劍,即事呈詠
白山茶插髻,甚可觀,因書二絕
逋客叔菊筵
雲客堂中夜集(二首)
凌義渠(一五九一至一六四四)
汶陽懷范香令
吳應箕(一五九四至一六四五)
旅夜看《犀軸》傳奇,是沈青霞煉事,末句深有感于聞氏
朱隗(不詳)
鴛湖主人出家姬演《牡丹亭記》歌
屠茝佩(不詳)
觀沈氏諸姬演劇
許經(生卒年不詳)
四印堂夜集觀姬人紫雲歌舞即席賦贈二首(之二)
張岱(一五九七至一六七九)
祁奕遠鮮雲小伶歌
曲中妓王月生
胡夏客(一五九九至一六七二)
江南曲
祁彪佳(一六○二至一六四五)
贈袁鳧公
坐千人石聞童子清歌,有客倚洞簫和之
徐士俊(一六○二至一六八一)
哭卓珂月(六首)
王翃(一六○三至一六五三)
鷓鴣天․同馬巽倩水部、張深之金吾、陸嗣端職方、吳余常文學飲月斷橋,戲為陳章侯茂才贈蔣、王二較書
賀聖朝
碧牡丹․同朱近修、吳於庭觀女劇
序
前言
詠劇詩歌宋元就有,明代以後,作者層出不窮,作品數以萬計,其中大量涉及崑曲,提供了有關崑曲歷史、演出和批評的珍貴資料,因此我們編成《明代詠崑曲詩歌選注》,以供學者研究參考和廣大讀者閱讀欣賞。至於清代、近代詠崑曲詩歌,也將陸續選注。對於明代詠崑曲詩歌的價值,下面略作介紹。
崑曲演出的生動記錄
進入明代,隨著俗文學的發展,觀賞戲曲日益成為文人精神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崑曲興盛之後,尤其如此。
梁辰魚的朋友孫樓有《宴梁少白宅,聽吳中新樂,群至半山橋》:
瑤席開新樂,銀燈剪絳花。
合歡羅上彥,分部鬥名家。
連袂歌相答,飛觥興轉賒。
如何逢永夜,皎月易為斜。
這首詩生動地反映了「吳中新樂」即魏良輔改革之後的昆山腔初興時,梁辰魚等人為推廣崑曲所作出的努力,以及當時文人對這種「新樂」的濃厚興趣。
梁辰魚《浣紗記》問世之後,演出頻繁,汪道昆就有《席上觀〈吳越春秋〉有作,凡四首》,記錄了觀看演出的情況。此外,鄒迪光有《正月十六夜集友人于一指堂,觀演昆侖奴、紅線故事,分得十四寒》、《冬夜與顧仲默諸君小集,看演〈神鏡〉傳奇,次仲默韻》、《酒未闌而范長白忽乘信過唁,復爾開尊,演霍小玉〈紫釵〉,不覺達曙,和覺父韻》等詩,所寫也是文人觀看崑曲演出的活動。
這裡要說一下鄒迪光。他字彥吉,號愚穀,無錫(今屬江蘇)人。他與湯顯祖等曲家有交往,是一位戲劇愛好者。中年罷官後,築室錫山,多與文士觴詠,征歌度曲。他的家班是有名的,潘之恒在談到當時的著名演員時就曾提到「鄒班之小潘」 。鍾惺(一五七四至一六二四)曾在鄒迪光家看過戲,寫有《彥吉先生席上觀劇贈周郎》七絕二首。
以上汪道昆等人觀看的崑曲演出,地點是在廳堂。當時酒樓也有演出,胡應麟(一五五一至一六○二)《湖上酒樓聽歌王檢討敬夫、汪司馬伯玉二樂府及張伯起傳奇戲作》三首:
光陰百歲迅流霞,一曲東籬擅馬家。
何似翰林【新水令】,秋風遷客走天涯。
水雲深處木蘭航,白雪紛飛《大雅堂》。
莫向五湖尋舊跡,於今司馬在鄖陽。
掩徑頻年侶博徒,陽春堂上白雲孤。
才聞北里歌《紅拂》,又見東園演《竊符》。
三首詩分寫王九思、汪道昆、張鳳翼三人的散曲和戲曲的演唱情況。特別是張鳳翼的《紅拂記》和《竊符記》,演出的頻率很高,可見廣受歡迎的程度。
明代不少地區有一些自發的大型的帶節令性的戲曲演出活動,如杭州的西湖「演春」(見田汝成《熙朝樂事》),南京的夏日秦淮曲宴(見潘之恒《鸞嘯小品》),等等,其中最負盛名的當屬蘇州的虎丘中秋唱曲大會。對於這一盛會,袁宏道(一五六八至一六一○)《虎丘》一文作了如下描繪: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與此可以相互印證的,是鄒迪光《八月十五夜虎丘坐月》一詩中所作的描繪:
層巒紫霧散,重阿綠雨歇。
天衢淨無翳,濯濯吐華月。
柔颸遞薄爽,衣袂時一揭。
摩肩客糜集,前後相凌越。
引履何錯蹂,蒸氣亦勃窣。
鵝管東西沸,歌唇南北發。
列隊非有期,尋響如效答。
時時遏雲遊,往往振木末。
此詩寫虎丘中秋唱曲大會的場面,十分真切生動。歌唱的聲音此起彼伏,響遏行雲,聽眾摩肩接踵,反響熱烈,都覺得這是一種難得的藝術享受。
另外,卜世臣亦作有【上馬踢】《中秋夜集虎丘四望閣》套曲:
【上馬踢】金天霽爽開,虛穀馳清籟,林端晚照微,碧空霞散彩。路入三泉,額外添瀟灑。試上古台,縱目雄奇,蟾魄憑欄待。
【月兒高】碎影初篩,霎侵鬥牛界。萬里長煙淨,鴻悲蘋瀨。宋玉愁深,秋光卻難買。把一塊生公石,做了風流寨。
【蠻江令】足擁行多礙,聲喧語不解。狡童和豔女,浪謔饒情態。兩兩攜手,拂塵坐青苔。耳畔紅牙伎,對壘通宵賽。
【涼草蛩】舉卮才暢懷,露涼蟲韻改。東方白,曉星在,且收拾琴樽返棹哉。黑甜聊快,等月印山塘,還呼酒伴重來。
用套曲的形式,描繪虎丘中秋曲會的場景,饒有風情,別具韻味。相傳卜世臣的新劇《冬青記》就曾在虎丘演出過,「觀者萬人,多泣下者」 。作者對此也許保留著十分美好的回憶吧。
記錄虎丘中秋曲會的還有張岱《陶庵夢憶》卷五的《虎丘中秋夜》等。從有關虎丘中秋曲會的詩歌的和散文的記錄看來,這一自發的戲劇演出活動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一種群眾性藝術活動如此長盛不衰,不能不說是中國藝術史上的一個奇蹟。
其實,虎丘的唱曲活動不僅中秋舉行,平時也經常舉行。如袁宏道《江南子》所描述的:
蜘蛛生來解織羅,吳兒十五能嬌歌。
舊曲嘹厲商聲緊,新腔嘽緩務頭多。
一拍一簫一寸管,虎丘夜夜石苔暖。
家家宴喜串歌兒,紅女停梭田畯懶。
在各階層人士普遍喜愛崑曲的大氛圍裡,戲曲與文人精神生活已經如此息息相關,以至於有的文人為了觀劇而減少了日常應酬。如婁堅有《起龍枉招,偶以觀劇不赴》一詩:
知君具蔬果,呼我共談言。
卻為聽歌去,真同歸市喧。
兒童心尚在,張弛道堪論。
衰白新添歲,謀歡始上元。
明萬曆年間,龍洞山農為《西廂記》新刻本作序,結尾說:「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李贄對這句話很不贊同,他說:「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正是從這種「童心說」出發,李贄評價院本、雜劇、《西廂曲》、《水滸傳》皆是「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皆是「古今至文」(以上引文均見李贄《焚書》卷三《雜述》)。婁堅看來是贊同李贄的主張的,他公開聲言自己「兒童心尚在」,並且在行動上也是「真人真情,任性而行」,要看戲就看戲,要不赴宴就不赴宴。考察晚明士風,這也是一條有趣的材料。
更有甚者,有的文人真的「以戲代藥」。湯顯祖的友人潘之恒有《病中觀劇有懷吳越石》詩,在《情癡》一文中又說:「不慧抱恙一冬,而觀《牡丹亭記》,覺有起色。信觀濤之不餘欺,而夢鹿之足以覺世也。」(《鸞嘯小品》卷三。)茅坤幼子茅維亦有《病裡思聽音樂,戲呈諸公》一詩:
繞籬黃蝶隱秋花,病裡閒情遣狹斜。
伎作東山懷謝傅,笛吹古墓憶桓家。
那堪殘曲歌金縷,敢向今時鬥麗華。
紅燭最嬌丸髻妓,胡床企腳聽琵琶。
可見,欣賞崑曲對當時許多的文人來說,已經成為一種消遣,一種享受,一種陶醉,一種寄託。因此他們在談論人生、談論藝術的時候,也經常很自然地涉及戲劇,或以戲劇為喻。如吳從先《小窗自紀》說:「絕好看的,戲場姊妹們變臉;最可笑的,世事朋友家結盟。」沈捷《增訂心相百二十善》說:「人生雖是戲場,須妝一腳正生,不貽後人非笑。」這些與詠崑曲詩歌可以參看。
崑曲批評的詩化形式
明代詠崑曲詩歌中有一部分是運用詩歌的形式,對戲曲作家、戲曲作品、戲曲表演發表評論。
當時戲曲界的名家名作,有詩人及時加以歌詠,從而提高了知名度,進一步擴大了影響。如梁辰魚,便引來了不少詩篇。如李攀龍《寄贈梁伯龍》:
彩筆含花賦別離,玉壺春酒調吳姬。
金陵子弟知名姓,樂府爭傳絕妙辭。
王世貞《嘲梁伯龍》:
吳閶白麵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豔詞。
七尺昂藏心未保,異時翻欲傍要離。
潘之恒《白下逢梁伯龍感舊》二首:
梨園處處按新詞,桃葉家家度翠眉。
一自流傳江左調,令人卻憶六朝時。
一別長幹已十年,填詞贏得萬人傳。
歌梁舊燕雙棲處,不是烏衣亦可憐。
這些詩篇合觀,梁辰魚的為人性格、藝術才能以及作品受到廣泛歡迎的情況,便都生動地凸現出來了。
湯顯祖的名作《牡丹亭》問世之後,歌詠者就很多。其友人潘之恒作有《贈吳亦史》四首,評論十三歲的小演員吳亦史飾演的柳夢梅,第二首云:
風流情事盡堪傳,況是才人第一編。
剛及秋宵宵漸永,出門猶恨未明天。
這首詩高度評價了《牡丹亭》,稱其為「才人第一編」。對於這次《牡丹亭》演出的效果,詩中也有形象的表現,可以說是留下了《牡丹亭》演出較早的一份記錄。
湯顯祖本人也寫有《滕王閣看王有信演〈牡丹亭〉二首》:
韻若笙簫氣若絲,《牡丹》魂夢去來時。
河移客散江波起,不解銷魂不遣知。
樺燭煙銷泣絳紗,清微苦調翠殘霞。
愁來一座更衣起,江樹沉沉天漢斜。
這兩首詩表現了湯顯祖對王有信演出的讚賞。魂夢來去,苦調清微,反映了《牡丹亭》深入發掘人物內心世界的藝術力量以及旖旎纏綿、曲折委婉的藝術風格。這是劇作者本人的感受,特別值得重視。
崑曲的音樂美感特別突出,隨著崑曲的流行,人們也在逐步體味、研究它在音樂美感方面的特點,最為人們熟知的說法就是「水磨腔」,正如沈寵綏《度曲須知》談到魏良輔時所說:「憤南曲之訛陋也,盡洗乖聲,別開堂奧。調用水磨,拍捱冷板。聲則平、上、去、入之婉協,字則頭、腹、尾音之畢勻。功深鎔琢,氣無煙火。啟口輕圓,收音純細。」這一音樂美感的批評,在汪道會、許經等人的詩中也有表現。
汪道會《煙條館聞歌》五首之一這樣寫道:
新詞不是古《涼州》,別有江南《白苧》秋。
每到關情聲更咽,圓勻一串出珠喉。
煙條館為文徵明館名。文徵明及其子文彭、文嘉均為江南名士,都愛好崑曲,文徵明手寫的《南詞引正》,是魏良輔《曲律》最早也是最好的版本。從汪道會這首詩看來,煙條館的崑曲清唱水平是很高的,也充分體現了魏良輔改造後的崑曲嘹亮、圓勻的特點。
許經《四印堂夜集觀姬人紫雲歌舞即席賦贈二首》之二云:
隴頭團扇總新聲,水樣磨成珠樣明。
最喜堂堂垂手處,不將平視惱劉楨。
四印堂為董其昌堂名。這次演出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歌姬紫雲演唱的崑曲,「水樣磨成珠樣明」將崑曲委婉細膩、溫潔圓潤的美感描繪得極為形象。
明代末年,隨著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文人士大夫政治熱情的高漲,人們對政治題材的戲曲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所謂政治題材的戲曲,一是抨擊魏忠賢暴政、歌頌東林黨人鬥爭的時事劇,如範世彥《磨忠記》、高汝拭《不丈夫》、陳開泰《冰山記》等;二是描寫前朝的忠奸鬥爭以借古諷今的,如無名氏《犀軸記》等。吳應箕《旅夜看〈犀軸〉傳奇,是沈青霞煉事,末句深有感于聞氏》一詩寫道:
生平愛說沈青霞,孤憤長鳴一劍斜。
旅夜無聊翻雜劇,逢場作戲豈虛誇。
偶然燈火窺雙淚,為與悲歌和一笳。
若使史遷重載筆,肯將女子後朱家。
《犀軸記》寫的是嘉靖時忠臣沈煉(青霞)等人與權奸嚴嵩的鬥爭,與馮夢龍《古今小說》中《沈小霞相會出師表》一篇題材相同,是一部具有鮮明政治傾向的歷史劇。祁彪佳《遠山堂曲品》說:「是記成於逆璫亂政時,借一沈青霞以愧世之不為青霞者。雖不能協律比聲,逞運斤之技,亦可稱鐵中錚錚。」 吳應箕是複社的中堅人物,對於權奸、閹黨亂政誤國,是極為痛恨的。本詩通過抒寫觀看《犀軸記》的感想,借古喻今,寄託內心的憤懣和悲慨。末句把聞氏這樣一位有膽有識的女子與大俠朱家相提並論,表現了一種真知灼見。
戲曲理論的詩意表述
除了記錄崑曲演出、發表崑曲評論以外,還有相當一部分詠崑曲詩歌,探討了戲曲史和戲曲理論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
例如,著名的「沈湯之爭」,雙方都曾以詩歌作為表述自己見解的方式。沈璟的見解見於他作的【二郎神】套曲,其中的【二郎神】曲寫道:
何元朗,一言兒啟詞中寶藏,道欲度新聲休走樣!名為樂府,須教合律依腔。甯使時人不鑒賞,無使人撓喉戾嗓。說不得才長,越才長越當著意斟量。
【黃鶯兒】曲寫道:
曾記少陵狂,道細論文晚節詳。論詞亦豈容疏放?縱使詞出繡腸,歌稱繞梁,倘不諧音律,也難褒獎。耳邊廂,訛音俗調,羞問短和長。
沈璟繼承何良俊(字元朗)的觀點,認為對於戲曲來講,合律依腔是最重要的,因此主張嚴守格律。依據這一標準,沈璟等人對湯顯祖的《牡丹亭》進行了刪改。湯顯祖對這種刪改很不滿意,他認為「意,趣,神,色」比斤斤守律重要得多。他的這種藝術見解也寫進了詩歌。他在《見改竄〈牡丹〉詞者失笑》一詩中寫道:
醉漢瓊筵風味殊,通仙鐵笛海雲孤。
縱饒割就時人景,卻愧王維舊雪圖。
朱權《太和正音譜》評:「關漢卿之詞,如瓊筵醉客。」湯顯祖在這首詩中說自己的作品就像關漢卿的雜劇一樣,具有瓊筵醉客一般的特殊風味,又像吹奏給仙人聽的鐵笛一樣,響遏海雲,不同凡響。因此自己的作品不為一般世俗的人所理解,是很自然的。他譏笑改竄《牡丹亭》的人枉拋心力,正如在王維的冬景圖上割蕉加梅一樣,完全失去了原作的意趣。他在《答凌初成》一文中也說:「不佞《牡丹亭記》,大受呂玉繩改竄,云『便吳歌』。不佞啞然失笑曰:昔有人嫌摩詰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其中駘蕩淫夷,轉在筆墨之外耳。」由此可見,湯顯祖最重視的是「在筆墨之外」的「駘蕩淫夷」的「意趣」,亦即作者的情感、才氣、理想、個性在作品中的自然顯露,而這也就構成了作品的特殊風貌和強烈感染力。
很明顯,研究沈璟、湯顯祖的這些詩歌,有助於加深對明代戲曲理論批評史、乃至美學史的理解。
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究竟如何?這是在整個文藝理論包括戲曲理論中眾說紛紜的問題。不少詠崑曲詩歌對此也發表了見解。袁宏道的同道江盈科《湯理問邀集陳園,楊太史、鍾內翰、袁國學同集,看演〈荊釵〉》詩中寫道:
傳奇演出號《荊釵》,恰少歡會多離哀。
極意描寫逼真境,四座太息仍徘徊。
或云此戲本偽撰,當日龜齡無此變。
便如說夢向癡人,添出一番閑識見。
從來天地是俳場,生旦醜淨由人裝。
假固假兮真亦假,浪生歡喜浪悲傷。
何如對客傾杯酒,且自雄談開笑口。
醒能多事醉能忘,曲裏糟丘真樂土。
五更酩酊金罍竭,歸鞭撻碎長安月。
西窗一覺成未成,曉雞喔喔催明發。
江盈科與袁宏道等人一起觀看的《荊釵記》,是長期活在崑曲舞臺上的名作。但是對於《荊釵記》與其本事的關係,論者有種種猜測。對於這些猜測,江盈科是不同意的。他認為《荊釵記》對人情世態「極意描寫逼真境」,因此便能打動觀眾,使得「四座太息仍徘徊」。如果不懂得戲曲創作需要也允許藝術虛構,允許「假固假兮真亦假」,硬要將劇中人物與歷史人物生硬對號,那就「便如說夢向癡人,添出一番閑識見」,就會鬧笑話。他認為「從來天地是俳場,生旦醜淨由人裝」。這種說法與李贄「戲則戲矣,倒須似真」(《李卓吾批評琵琶記》)之說正可互相參看,是符合文學創作包括戲曲創作的規律的。
同文學藝術的其他門類一樣,戲曲藝術也要不斷創新,才有生命力,才能適應觀眾不斷變化的審美需求。這一頗具理論重要性的問題,在詠崑曲詩中也時有探討。茅坤之孫茅元儀在《觀大將軍謝簡之家伎,演所自述〈蝴蝶夢〉樂府》一詩中寫道:
耳目無久玩,新者入我懷。
奇賞竟何許?忽在天之涯。
豈無歌舞圍?蠻音習濫哇。
塞耳亦已久,負此風日佳。
我公宴笑余,奴隸狼與豺。
開尊出家伎,惠我忘形骸。
煉音變時俗,出態如初芽。
命意何寥廓,托詞非優俳。
由此詩可以看出,茅元儀在評論戲曲時,特別強調一個「新」字。他對謝弘儀《蝴蝶夢》的評價,也是從「煉音」、「出態」、「命意」、「托詞」四個方面強調了它的屏棄陳言,自出新意。與此可以作為參照的是,在《批點牡丹亭記序》中,茅元儀也說過,《牡丹亭》之所以能成為一代戲曲傑作,就是因為「其播詞也,鏗鏘足以應節,詭麗足以應情,幻特足以應態,自可以變詞人抑揚俯仰之常局,而冥符於創源命派之手」。注意到「耳目無久玩,新者入我懷」即觀眾審美心理的變化,強調在藝術上要打破「常局」,「創源命派」,這是茅元儀戲曲見解中高明的地方。這一見解,與李漁《閒情偶寄》強調戲曲要「新」、要「變」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這種注意對觀眾的適應與引導,在革新中求生存、求發展的觀點,正是抓住了戲曲創作的關鍵。
張岱《祁奕遠鮮雲小伶歌》:
世間何事堪搤掔,好月一輪茶一碗。
更有清謳妙入神,三事雖佳難落款。
鮮雲小傒真奇異,日日不同是其戲。
揣摩已到骨節靈,場中解得主人意。
主人賞鑒無一錯,小傒喚來將手摸。
無勞甄別費多詞,小者必佳大者惡。
昔日余曾教小伶,有其工致無其精。
老腔既改白字換,誰能練熟更還生。
出口字字能丟下,不配笙簫配弦索。
曲中穿渡甚輕微,細心靜氣方領略。
伯駢串戲噪江南,技藝精時慣作態。
銅雀妙音今學得,這回真好殺羅三。
這首詩說觀看一出好戲是一種絕妙的享受,就好像品嘗一碗好茶,欣賞一輪好月。同樣的意思,亦見於《陶庵夢憶》卷六《彭天錫串戲》:「餘嘗見一出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傳之不朽,嘗比之天上一夜好月與得火候一杯好茶,只可供一刻受用,其實珍惜之不盡也。」當然,戲要成為好戲,不僅劇本要好,演員的表演要好,家班主人的教習也要好。這裡稱讚祁奕遠家伶的表演精益求精,日日不同,關鍵是處理好了「生」與「熟」的關係。對此,張岱在《與何紫翔》一文中,以彈琴為例,作了深入的闡發:
昨聽松江何鳴台、王本吾二人彈琴,何鳴台不能化板為活,其蔽也實;王本吾不能練熟為生,其蔽也油。二者皆是大病,而本吾為甚。何者?彈琴者,初學入手,患不能熟;及至一熟,患不能生。夫生,非澀勒離歧遺忘斷續之謂也。古人彈琴,吟揉掉注,得手應心。其間勾留之巧,穿度之奇,呼應之靈,頓挫之妙,真有非指非弦,非勾非剔,一種生鮮之氣,人不及知,己不及覺者。非十分純熟,十分淘洗,十分脫化,必不能到此地步。
張岱的結論是:
蓋此練熟還生之法,自彈琴撥阮,蹴踘吹簫,唱曲演戲,描畫寫字,作文做詩,凡百諸項,皆藉此一口生氣。得此生氣者,自致清虛;失此生氣者,終成渣穢。
張岱這裡所談,是藝術中「生」與「熟」的辯證法。從演員來說,「熟」是熟能生巧、駕輕就熟,「生」是精益求精、常演常新;從觀眾來說,「熟」是熟悉感、親切感,「生」是陌生感、新奇感。從「生」 到「熟」是一次飛躍,要付出艱辛的努力;從「熟」到「生」又是一次飛躍,也要付出艱辛的努力。「生」與「熟」兩方面恰當地結合起來,演出就能達到新的水平,看戲就能看出新的感受。對於崑曲表演藝術和觀眾心理學中這一重要問題,張岱結合豐富的藝術實踐,運用詩歌和散文相配合的形式加以表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從上面的簡略論述可以看出,明代詠崑曲詩歌是一座豐富的寶藏,發掘、整理、研究明代的詠崑曲詩歌,對於瞭解明代文人的心理狀態和藝術見解,對於考察明代崑曲創作、演出、評論和研究的狀況,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書由我和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博士生趙婷婷共同選注。限於水平,選注或有不當之處,敬請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詠劇詩歌宋元就有,明代以後,作者層出不窮,作品數以萬計,其中大量涉及崑曲,提供了有關崑曲歷史、演出和批評的珍貴資料,因此我們編成《明代詠崑曲詩歌選注》,以供學者研究參考和廣大讀者閱讀欣賞。至於清代、近代詠崑曲詩歌,也將陸續選注。對於明代詠崑曲詩歌的價值,下面略作介紹。
崑曲演出的生動記錄
進入明代,隨著俗文學的發展,觀賞戲曲日益成為文人精神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崑曲興盛之後,尤其如此。
梁辰魚的朋友孫樓有《宴梁少白宅,聽吳中新樂,群至半山橋》:
瑤席開新樂,銀燈剪絳花。
合歡羅上彥,分部鬥名家。
連袂歌相答,飛觥興轉賒。
如何逢永夜,皎月易為斜。
這首詩生動地反映了「吳中新樂」即魏良輔改革之後的昆山腔初興時,梁辰魚等人為推廣崑曲所作出的努力,以及當時文人對這種「新樂」的濃厚興趣。
梁辰魚《浣紗記》問世之後,演出頻繁,汪道昆就有《席上觀〈吳越春秋〉有作,凡四首》,記錄了觀看演出的情況。此外,鄒迪光有《正月十六夜集友人于一指堂,觀演昆侖奴、紅線故事,分得十四寒》、《冬夜與顧仲默諸君小集,看演〈神鏡〉傳奇,次仲默韻》、《酒未闌而范長白忽乘信過唁,復爾開尊,演霍小玉〈紫釵〉,不覺達曙,和覺父韻》等詩,所寫也是文人觀看崑曲演出的活動。
這裡要說一下鄒迪光。他字彥吉,號愚穀,無錫(今屬江蘇)人。他與湯顯祖等曲家有交往,是一位戲劇愛好者。中年罷官後,築室錫山,多與文士觴詠,征歌度曲。他的家班是有名的,潘之恒在談到當時的著名演員時就曾提到「鄒班之小潘」 。鍾惺(一五七四至一六二四)曾在鄒迪光家看過戲,寫有《彥吉先生席上觀劇贈周郎》七絕二首。
以上汪道昆等人觀看的崑曲演出,地點是在廳堂。當時酒樓也有演出,胡應麟(一五五一至一六○二)《湖上酒樓聽歌王檢討敬夫、汪司馬伯玉二樂府及張伯起傳奇戲作》三首:
光陰百歲迅流霞,一曲東籬擅馬家。
何似翰林【新水令】,秋風遷客走天涯。
水雲深處木蘭航,白雪紛飛《大雅堂》。
莫向五湖尋舊跡,於今司馬在鄖陽。
掩徑頻年侶博徒,陽春堂上白雲孤。
才聞北里歌《紅拂》,又見東園演《竊符》。
三首詩分寫王九思、汪道昆、張鳳翼三人的散曲和戲曲的演唱情況。特別是張鳳翼的《紅拂記》和《竊符記》,演出的頻率很高,可見廣受歡迎的程度。
明代不少地區有一些自發的大型的帶節令性的戲曲演出活動,如杭州的西湖「演春」(見田汝成《熙朝樂事》),南京的夏日秦淮曲宴(見潘之恒《鸞嘯小品》),等等,其中最負盛名的當屬蘇州的虎丘中秋唱曲大會。對於這一盛會,袁宏道(一五六八至一六一○)《虎丘》一文作了如下描繪:
每至是日,傾城闔戶,連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靚妝麗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間。從千人石上至山門,櫛比如鱗,檀板丘積,樽罍雲瀉。遠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雷輥電霍,無得而狀。布席之初,唱者千百,聲若聚蚊,不可辨識。分曹部署,競以歌喉相鬥,雅俗既陳,妍媸自別。未幾而搖頭頓足者,得數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練,一切瓦釜,寂然停聲,屬而和者,才三四輩。一簫一寸管,一人緩板而歌,竹肉相發,清聲亮徹,聽者魂銷。比至夜深,月影橫斜,荇藻凌亂,則簫板亦不復用。一夫登場,四座屏息,音若細發,響徹雲際,每度一字,幾盡一刻,飛鳥為之徘徊,壯士聽而下淚矣。
與此可以相互印證的,是鄒迪光《八月十五夜虎丘坐月》一詩中所作的描繪:
層巒紫霧散,重阿綠雨歇。
天衢淨無翳,濯濯吐華月。
柔颸遞薄爽,衣袂時一揭。
摩肩客糜集,前後相凌越。
引履何錯蹂,蒸氣亦勃窣。
鵝管東西沸,歌唇南北發。
列隊非有期,尋響如效答。
時時遏雲遊,往往振木末。
此詩寫虎丘中秋唱曲大會的場面,十分真切生動。歌唱的聲音此起彼伏,響遏行雲,聽眾摩肩接踵,反響熱烈,都覺得這是一種難得的藝術享受。
另外,卜世臣亦作有【上馬踢】《中秋夜集虎丘四望閣》套曲:
【上馬踢】金天霽爽開,虛穀馳清籟,林端晚照微,碧空霞散彩。路入三泉,額外添瀟灑。試上古台,縱目雄奇,蟾魄憑欄待。
【月兒高】碎影初篩,霎侵鬥牛界。萬里長煙淨,鴻悲蘋瀨。宋玉愁深,秋光卻難買。把一塊生公石,做了風流寨。
【蠻江令】足擁行多礙,聲喧語不解。狡童和豔女,浪謔饒情態。兩兩攜手,拂塵坐青苔。耳畔紅牙伎,對壘通宵賽。
【涼草蛩】舉卮才暢懷,露涼蟲韻改。東方白,曉星在,且收拾琴樽返棹哉。黑甜聊快,等月印山塘,還呼酒伴重來。
用套曲的形式,描繪虎丘中秋曲會的場景,饒有風情,別具韻味。相傳卜世臣的新劇《冬青記》就曾在虎丘演出過,「觀者萬人,多泣下者」 。作者對此也許保留著十分美好的回憶吧。
記錄虎丘中秋曲會的還有張岱《陶庵夢憶》卷五的《虎丘中秋夜》等。從有關虎丘中秋曲會的詩歌的和散文的記錄看來,這一自發的戲劇演出活動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一種群眾性藝術活動如此長盛不衰,不能不說是中國藝術史上的一個奇蹟。
其實,虎丘的唱曲活動不僅中秋舉行,平時也經常舉行。如袁宏道《江南子》所描述的:
蜘蛛生來解織羅,吳兒十五能嬌歌。
舊曲嘹厲商聲緊,新腔嘽緩務頭多。
一拍一簫一寸管,虎丘夜夜石苔暖。
家家宴喜串歌兒,紅女停梭田畯懶。
在各階層人士普遍喜愛崑曲的大氛圍裡,戲曲與文人精神生活已經如此息息相關,以至於有的文人為了觀劇而減少了日常應酬。如婁堅有《起龍枉招,偶以觀劇不赴》一詩:
知君具蔬果,呼我共談言。
卻為聽歌去,真同歸市喧。
兒童心尚在,張弛道堪論。
衰白新添歲,謀歡始上元。
明萬曆年間,龍洞山農為《西廂記》新刻本作序,結尾說:「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李贄對這句話很不贊同,他說:「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正是從這種「童心說」出發,李贄評價院本、雜劇、《西廂曲》、《水滸傳》皆是「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皆是「古今至文」(以上引文均見李贄《焚書》卷三《雜述》)。婁堅看來是贊同李贄的主張的,他公開聲言自己「兒童心尚在」,並且在行動上也是「真人真情,任性而行」,要看戲就看戲,要不赴宴就不赴宴。考察晚明士風,這也是一條有趣的材料。
更有甚者,有的文人真的「以戲代藥」。湯顯祖的友人潘之恒有《病中觀劇有懷吳越石》詩,在《情癡》一文中又說:「不慧抱恙一冬,而觀《牡丹亭記》,覺有起色。信觀濤之不餘欺,而夢鹿之足以覺世也。」(《鸞嘯小品》卷三。)茅坤幼子茅維亦有《病裡思聽音樂,戲呈諸公》一詩:
繞籬黃蝶隱秋花,病裡閒情遣狹斜。
伎作東山懷謝傅,笛吹古墓憶桓家。
那堪殘曲歌金縷,敢向今時鬥麗華。
紅燭最嬌丸髻妓,胡床企腳聽琵琶。
可見,欣賞崑曲對當時許多的文人來說,已經成為一種消遣,一種享受,一種陶醉,一種寄託。因此他們在談論人生、談論藝術的時候,也經常很自然地涉及戲劇,或以戲劇為喻。如吳從先《小窗自紀》說:「絕好看的,戲場姊妹們變臉;最可笑的,世事朋友家結盟。」沈捷《增訂心相百二十善》說:「人生雖是戲場,須妝一腳正生,不貽後人非笑。」這些與詠崑曲詩歌可以參看。
崑曲批評的詩化形式
明代詠崑曲詩歌中有一部分是運用詩歌的形式,對戲曲作家、戲曲作品、戲曲表演發表評論。
當時戲曲界的名家名作,有詩人及時加以歌詠,從而提高了知名度,進一步擴大了影響。如梁辰魚,便引來了不少詩篇。如李攀龍《寄贈梁伯龍》:
彩筆含花賦別離,玉壺春酒調吳姬。
金陵子弟知名姓,樂府爭傳絕妙辭。
王世貞《嘲梁伯龍》:
吳閶白麵冶游兒,爭唱梁郎雪豔詞。
七尺昂藏心未保,異時翻欲傍要離。
潘之恒《白下逢梁伯龍感舊》二首:
梨園處處按新詞,桃葉家家度翠眉。
一自流傳江左調,令人卻憶六朝時。
一別長幹已十年,填詞贏得萬人傳。
歌梁舊燕雙棲處,不是烏衣亦可憐。
這些詩篇合觀,梁辰魚的為人性格、藝術才能以及作品受到廣泛歡迎的情況,便都生動地凸現出來了。
湯顯祖的名作《牡丹亭》問世之後,歌詠者就很多。其友人潘之恒作有《贈吳亦史》四首,評論十三歲的小演員吳亦史飾演的柳夢梅,第二首云:
風流情事盡堪傳,況是才人第一編。
剛及秋宵宵漸永,出門猶恨未明天。
這首詩高度評價了《牡丹亭》,稱其為「才人第一編」。對於這次《牡丹亭》演出的效果,詩中也有形象的表現,可以說是留下了《牡丹亭》演出較早的一份記錄。
湯顯祖本人也寫有《滕王閣看王有信演〈牡丹亭〉二首》:
韻若笙簫氣若絲,《牡丹》魂夢去來時。
河移客散江波起,不解銷魂不遣知。
樺燭煙銷泣絳紗,清微苦調翠殘霞。
愁來一座更衣起,江樹沉沉天漢斜。
這兩首詩表現了湯顯祖對王有信演出的讚賞。魂夢來去,苦調清微,反映了《牡丹亭》深入發掘人物內心世界的藝術力量以及旖旎纏綿、曲折委婉的藝術風格。這是劇作者本人的感受,特別值得重視。
崑曲的音樂美感特別突出,隨著崑曲的流行,人們也在逐步體味、研究它在音樂美感方面的特點,最為人們熟知的說法就是「水磨腔」,正如沈寵綏《度曲須知》談到魏良輔時所說:「憤南曲之訛陋也,盡洗乖聲,別開堂奧。調用水磨,拍捱冷板。聲則平、上、去、入之婉協,字則頭、腹、尾音之畢勻。功深鎔琢,氣無煙火。啟口輕圓,收音純細。」這一音樂美感的批評,在汪道會、許經等人的詩中也有表現。
汪道會《煙條館聞歌》五首之一這樣寫道:
新詞不是古《涼州》,別有江南《白苧》秋。
每到關情聲更咽,圓勻一串出珠喉。
煙條館為文徵明館名。文徵明及其子文彭、文嘉均為江南名士,都愛好崑曲,文徵明手寫的《南詞引正》,是魏良輔《曲律》最早也是最好的版本。從汪道會這首詩看來,煙條館的崑曲清唱水平是很高的,也充分體現了魏良輔改造後的崑曲嘹亮、圓勻的特點。
許經《四印堂夜集觀姬人紫雲歌舞即席賦贈二首》之二云:
隴頭團扇總新聲,水樣磨成珠樣明。
最喜堂堂垂手處,不將平視惱劉楨。
四印堂為董其昌堂名。這次演出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歌姬紫雲演唱的崑曲,「水樣磨成珠樣明」將崑曲委婉細膩、溫潔圓潤的美感描繪得極為形象。
明代末年,隨著社會矛盾的激化和文人士大夫政治熱情的高漲,人們對政治題材的戲曲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所謂政治題材的戲曲,一是抨擊魏忠賢暴政、歌頌東林黨人鬥爭的時事劇,如範世彥《磨忠記》、高汝拭《不丈夫》、陳開泰《冰山記》等;二是描寫前朝的忠奸鬥爭以借古諷今的,如無名氏《犀軸記》等。吳應箕《旅夜看〈犀軸〉傳奇,是沈青霞煉事,末句深有感于聞氏》一詩寫道:
生平愛說沈青霞,孤憤長鳴一劍斜。
旅夜無聊翻雜劇,逢場作戲豈虛誇。
偶然燈火窺雙淚,為與悲歌和一笳。
若使史遷重載筆,肯將女子後朱家。
《犀軸記》寫的是嘉靖時忠臣沈煉(青霞)等人與權奸嚴嵩的鬥爭,與馮夢龍《古今小說》中《沈小霞相會出師表》一篇題材相同,是一部具有鮮明政治傾向的歷史劇。祁彪佳《遠山堂曲品》說:「是記成於逆璫亂政時,借一沈青霞以愧世之不為青霞者。雖不能協律比聲,逞運斤之技,亦可稱鐵中錚錚。」 吳應箕是複社的中堅人物,對於權奸、閹黨亂政誤國,是極為痛恨的。本詩通過抒寫觀看《犀軸記》的感想,借古喻今,寄託內心的憤懣和悲慨。末句把聞氏這樣一位有膽有識的女子與大俠朱家相提並論,表現了一種真知灼見。
戲曲理論的詩意表述
除了記錄崑曲演出、發表崑曲評論以外,還有相當一部分詠崑曲詩歌,探討了戲曲史和戲曲理論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
例如,著名的「沈湯之爭」,雙方都曾以詩歌作為表述自己見解的方式。沈璟的見解見於他作的【二郎神】套曲,其中的【二郎神】曲寫道:
何元朗,一言兒啟詞中寶藏,道欲度新聲休走樣!名為樂府,須教合律依腔。甯使時人不鑒賞,無使人撓喉戾嗓。說不得才長,越才長越當著意斟量。
【黃鶯兒】曲寫道:
曾記少陵狂,道細論文晚節詳。論詞亦豈容疏放?縱使詞出繡腸,歌稱繞梁,倘不諧音律,也難褒獎。耳邊廂,訛音俗調,羞問短和長。
沈璟繼承何良俊(字元朗)的觀點,認為對於戲曲來講,合律依腔是最重要的,因此主張嚴守格律。依據這一標準,沈璟等人對湯顯祖的《牡丹亭》進行了刪改。湯顯祖對這種刪改很不滿意,他認為「意,趣,神,色」比斤斤守律重要得多。他的這種藝術見解也寫進了詩歌。他在《見改竄〈牡丹〉詞者失笑》一詩中寫道:
醉漢瓊筵風味殊,通仙鐵笛海雲孤。
縱饒割就時人景,卻愧王維舊雪圖。
朱權《太和正音譜》評:「關漢卿之詞,如瓊筵醉客。」湯顯祖在這首詩中說自己的作品就像關漢卿的雜劇一樣,具有瓊筵醉客一般的特殊風味,又像吹奏給仙人聽的鐵笛一樣,響遏海雲,不同凡響。因此自己的作品不為一般世俗的人所理解,是很自然的。他譏笑改竄《牡丹亭》的人枉拋心力,正如在王維的冬景圖上割蕉加梅一樣,完全失去了原作的意趣。他在《答凌初成》一文中也說:「不佞《牡丹亭記》,大受呂玉繩改竄,云『便吳歌』。不佞啞然失笑曰:昔有人嫌摩詰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其中駘蕩淫夷,轉在筆墨之外耳。」由此可見,湯顯祖最重視的是「在筆墨之外」的「駘蕩淫夷」的「意趣」,亦即作者的情感、才氣、理想、個性在作品中的自然顯露,而這也就構成了作品的特殊風貌和強烈感染力。
很明顯,研究沈璟、湯顯祖的這些詩歌,有助於加深對明代戲曲理論批評史、乃至美學史的理解。
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究竟如何?這是在整個文藝理論包括戲曲理論中眾說紛紜的問題。不少詠崑曲詩歌對此也發表了見解。袁宏道的同道江盈科《湯理問邀集陳園,楊太史、鍾內翰、袁國學同集,看演〈荊釵〉》詩中寫道:
傳奇演出號《荊釵》,恰少歡會多離哀。
極意描寫逼真境,四座太息仍徘徊。
或云此戲本偽撰,當日龜齡無此變。
便如說夢向癡人,添出一番閑識見。
從來天地是俳場,生旦醜淨由人裝。
假固假兮真亦假,浪生歡喜浪悲傷。
何如對客傾杯酒,且自雄談開笑口。
醒能多事醉能忘,曲裏糟丘真樂土。
五更酩酊金罍竭,歸鞭撻碎長安月。
西窗一覺成未成,曉雞喔喔催明發。
江盈科與袁宏道等人一起觀看的《荊釵記》,是長期活在崑曲舞臺上的名作。但是對於《荊釵記》與其本事的關係,論者有種種猜測。對於這些猜測,江盈科是不同意的。他認為《荊釵記》對人情世態「極意描寫逼真境」,因此便能打動觀眾,使得「四座太息仍徘徊」。如果不懂得戲曲創作需要也允許藝術虛構,允許「假固假兮真亦假」,硬要將劇中人物與歷史人物生硬對號,那就「便如說夢向癡人,添出一番閑識見」,就會鬧笑話。他認為「從來天地是俳場,生旦醜淨由人裝」。這種說法與李贄「戲則戲矣,倒須似真」(《李卓吾批評琵琶記》)之說正可互相參看,是符合文學創作包括戲曲創作的規律的。
同文學藝術的其他門類一樣,戲曲藝術也要不斷創新,才有生命力,才能適應觀眾不斷變化的審美需求。這一頗具理論重要性的問題,在詠崑曲詩中也時有探討。茅坤之孫茅元儀在《觀大將軍謝簡之家伎,演所自述〈蝴蝶夢〉樂府》一詩中寫道:
耳目無久玩,新者入我懷。
奇賞竟何許?忽在天之涯。
豈無歌舞圍?蠻音習濫哇。
塞耳亦已久,負此風日佳。
我公宴笑余,奴隸狼與豺。
開尊出家伎,惠我忘形骸。
煉音變時俗,出態如初芽。
命意何寥廓,托詞非優俳。
由此詩可以看出,茅元儀在評論戲曲時,特別強調一個「新」字。他對謝弘儀《蝴蝶夢》的評價,也是從「煉音」、「出態」、「命意」、「托詞」四個方面強調了它的屏棄陳言,自出新意。與此可以作為參照的是,在《批點牡丹亭記序》中,茅元儀也說過,《牡丹亭》之所以能成為一代戲曲傑作,就是因為「其播詞也,鏗鏘足以應節,詭麗足以應情,幻特足以應態,自可以變詞人抑揚俯仰之常局,而冥符於創源命派之手」。注意到「耳目無久玩,新者入我懷」即觀眾審美心理的變化,強調在藝術上要打破「常局」,「創源命派」,這是茅元儀戲曲見解中高明的地方。這一見解,與李漁《閒情偶寄》強調戲曲要「新」、要「變」的觀點是完全一致的。這種注意對觀眾的適應與引導,在革新中求生存、求發展的觀點,正是抓住了戲曲創作的關鍵。
張岱《祁奕遠鮮雲小伶歌》:
世間何事堪搤掔,好月一輪茶一碗。
更有清謳妙入神,三事雖佳難落款。
鮮雲小傒真奇異,日日不同是其戲。
揣摩已到骨節靈,場中解得主人意。
主人賞鑒無一錯,小傒喚來將手摸。
無勞甄別費多詞,小者必佳大者惡。
昔日余曾教小伶,有其工致無其精。
老腔既改白字換,誰能練熟更還生。
出口字字能丟下,不配笙簫配弦索。
曲中穿渡甚輕微,細心靜氣方領略。
伯駢串戲噪江南,技藝精時慣作態。
銅雀妙音今學得,這回真好殺羅三。
這首詩說觀看一出好戲是一種絕妙的享受,就好像品嘗一碗好茶,欣賞一輪好月。同樣的意思,亦見於《陶庵夢憶》卷六《彭天錫串戲》:「餘嘗見一出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傳之不朽,嘗比之天上一夜好月與得火候一杯好茶,只可供一刻受用,其實珍惜之不盡也。」當然,戲要成為好戲,不僅劇本要好,演員的表演要好,家班主人的教習也要好。這裡稱讚祁奕遠家伶的表演精益求精,日日不同,關鍵是處理好了「生」與「熟」的關係。對此,張岱在《與何紫翔》一文中,以彈琴為例,作了深入的闡發:
昨聽松江何鳴台、王本吾二人彈琴,何鳴台不能化板為活,其蔽也實;王本吾不能練熟為生,其蔽也油。二者皆是大病,而本吾為甚。何者?彈琴者,初學入手,患不能熟;及至一熟,患不能生。夫生,非澀勒離歧遺忘斷續之謂也。古人彈琴,吟揉掉注,得手應心。其間勾留之巧,穿度之奇,呼應之靈,頓挫之妙,真有非指非弦,非勾非剔,一種生鮮之氣,人不及知,己不及覺者。非十分純熟,十分淘洗,十分脫化,必不能到此地步。
張岱的結論是:
蓋此練熟還生之法,自彈琴撥阮,蹴踘吹簫,唱曲演戲,描畫寫字,作文做詩,凡百諸項,皆藉此一口生氣。得此生氣者,自致清虛;失此生氣者,終成渣穢。
張岱這裡所談,是藝術中「生」與「熟」的辯證法。從演員來說,「熟」是熟能生巧、駕輕就熟,「生」是精益求精、常演常新;從觀眾來說,「熟」是熟悉感、親切感,「生」是陌生感、新奇感。從「生」 到「熟」是一次飛躍,要付出艱辛的努力;從「熟」到「生」又是一次飛躍,也要付出艱辛的努力。「生」與「熟」兩方面恰當地結合起來,演出就能達到新的水平,看戲就能看出新的感受。對於崑曲表演藝術和觀眾心理學中這一重要問題,張岱結合豐富的藝術實踐,運用詩歌和散文相配合的形式加以表述,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從上面的簡略論述可以看出,明代詠崑曲詩歌是一座豐富的寶藏,發掘、整理、研究明代的詠崑曲詩歌,對於瞭解明代文人的心理狀態和藝術見解,對於考察明代崑曲創作、演出、評論和研究的狀況,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書由我和斯坦福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博士生趙婷婷共同選注。限於水平,選注或有不當之處,敬請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