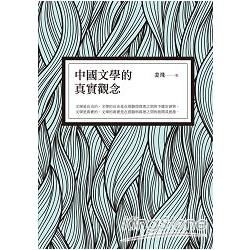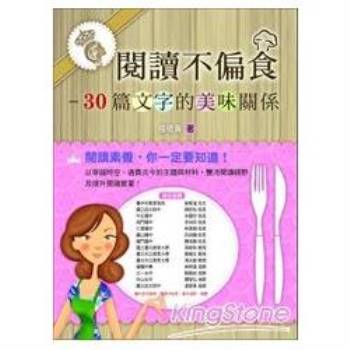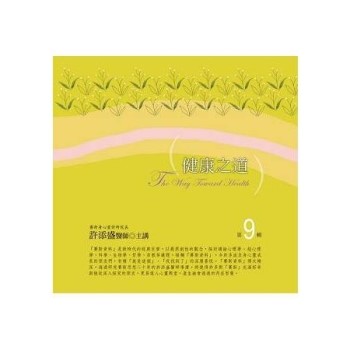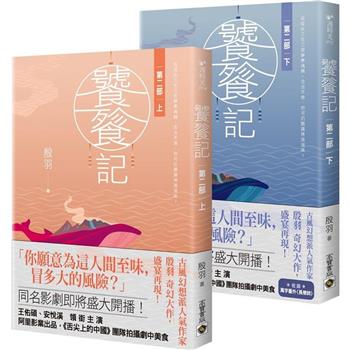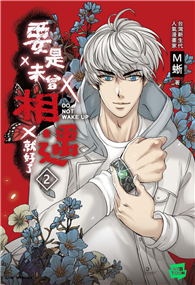文學的真實性即是在文學敘述之中,以文學的形式傳達出來的真理性或者經驗性。
文學真實包括兩個向度:一是經驗性的真實,簡稱「經驗之真」;一是真理性的真實,簡稱「真理之真」。
「經驗之真」與「真理之真」作為文學真實的兩個主要意義,同時也形成了中國文學真實觀念的結構,而中國文學真實觀念的歷史也就在「經驗之真─真理之真」的結構中展開和演變。
文學真實深刻地連繫著文學的本質,是文學的來源、基礎和理由。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中國文學的真實觀念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406 |
華文文學研究 |
$ 435 |
中文書 |
$ 458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510 |
華文文學研究 |
$ 522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580 |
文學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中國文學的真實觀念
內容簡介
目錄
導論
第一章 人倫之真與經驗之真的最初表述──先秦誠論
第一節 先秦儒家誠論
第二節 先秦道家誠論
第三節 誠論之在墨韓詩騷
第二章 經驗之真與儒家之道(一)──兩漢誠論
第一節 西漢前期誠論
第二節 西漢後期誠論
第三節 東漢誠論
第三章 經驗之真(一)──魏晉南北朝誠論
第一節 魏晉誠論
第二節 南北朝誠論
第四章 經驗之真與儒家之道(二)──隋唐宋金元誠論
第一節 隋唐誠論
第二節 宋金元誠論
第五章 經驗之真(二)──明清誠論
第一節 明代前期誠論
第二節 明代後期誠論:心學
第三節 明代後期誠論:情真
第四節 從明末清初到康熙年間的誠論
第五節 從乾嘉到同光年間的誠論
第六章 多歧互滲時代的「真」──清末民初的文學真實論
第一節 梁啟超:從工具與真理之真到審美與經驗之真
第二節 王國維:非工具化的經驗之真
第三節 中國固有的小說真實觀念及其在清民之際的嬗變
第七章 漢語、真理與經驗的轉折──文學革命期間的文學真實論
第一節 白話文學觀念背後的文學真實考慮
第二節 新文化運動中的真理之真與經驗之真
第八章 「政治之真-經驗之真」──革命與救亡背景下的文學真實論
第一節 革命文學論爭時期的「政治之真-經驗之真」
第二節 三十年代左翼與自由主義者的文學真實觀念
第三節 四十年代的文學真實觀念
結語及其他
第一章 人倫之真與經驗之真的最初表述──先秦誠論
第一節 先秦儒家誠論
第二節 先秦道家誠論
第三節 誠論之在墨韓詩騷
第二章 經驗之真與儒家之道(一)──兩漢誠論
第一節 西漢前期誠論
第二節 西漢後期誠論
第三節 東漢誠論
第三章 經驗之真(一)──魏晉南北朝誠論
第一節 魏晉誠論
第二節 南北朝誠論
第四章 經驗之真與儒家之道(二)──隋唐宋金元誠論
第一節 隋唐誠論
第二節 宋金元誠論
第五章 經驗之真(二)──明清誠論
第一節 明代前期誠論
第二節 明代後期誠論:心學
第三節 明代後期誠論:情真
第四節 從明末清初到康熙年間的誠論
第五節 從乾嘉到同光年間的誠論
第六章 多歧互滲時代的「真」──清末民初的文學真實論
第一節 梁啟超:從工具與真理之真到審美與經驗之真
第二節 王國維:非工具化的經驗之真
第三節 中國固有的小說真實觀念及其在清民之際的嬗變
第七章 漢語、真理與經驗的轉折──文學革命期間的文學真實論
第一節 白話文學觀念背後的文學真實考慮
第二節 新文化運動中的真理之真與經驗之真
第八章 「政治之真-經驗之真」──革命與救亡背景下的文學真實論
第一節 革命文學論爭時期的「政治之真-經驗之真」
第二節 三十年代左翼與自由主義者的文學真實觀念
第三節 四十年代的文學真實觀念
結語及其他
序
導論
真實是人類的一種必要的想像。
離開真實,人類的一切表達、從而整個人類文化,都可能意義全消。
文學作為人類對自身精神與境遇的審美表達,同樣應該直面「真」相或者腳踏「實」地。文學當以真實為基座,舍此基座,便可能流於漂浮的游談,喪盡其精神和根據,而所謂的審美追求也將一腳踏空;真實亦當如旗桿,文學之旗在風中自由似夢的捲舒不應離開旗桿的真實挺立,否則,文學這面風中之旗勢將隨風飄逝。在文學敘述中,「真實」可能是經驗之真,質地可以觸摸,也可能是真理之真,給人方向、節制與思索。然而,文學中所謂的「真實」並非一種不言而喻的當然之物,它有時也可能僅僅是一種宣稱,而在所宣稱的「真實」背後還另有真實――於是,真實的也許是崇高的社會理想,或者是堅硬的現實功利,甚至,「真實」可能是鬥爭的口號和工具,是權力的修辭。實際上,在穿過文化規範、權力操縱、功利打算、主觀判斷和語言構造之後,「真實」所呈現的,只能是斑駁的投影,或者說,人類所把握到的「真實」,包括「文學真實」,往往只是一種有根據的想像。
真實、文學真實,乃是一個直逼文學本源的重要論域。這個論域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文化中呈現出不同的景致,各有傳承和新變、增益和減損、發掘和重塑,有進有退,有改道,有折中,遺下豐富的學術資料,以及理論智慧。同時,從古至今的中外文論和批評,有關文學真實的觀念紛然雜陳,不可勝計,有時甚至顯得恍惚不明,讓人困惑未已。
面對這個資源豐富而又令人困惑的重要論域,一般性地建構學者自己的體系誠能揭示一些在學者個人的視點上發現的幽微學理,但更有說服力的探尋應當首先注目於歷史過程,應當首先縱向追索文學真實觀念的歷史,然後方能有根據地橫向建構文學真實的理論體系。實際上,倘若回到具體的語境,在文學真實觀念的演進歷程之中,其暗藏的內在機制和結構將從幽暗的歷史煙雲深處清晰現身。
這裏要做的,就是在歷史清理之中實現學理建構,即對中國從先秦到1949年的文學真實觀念展開一次全面的歷史清理,並在清理過程中勾畫出中國文學真實觀念的內在結構。從二十世紀以前的誠論到二十世紀的文學真實論,在此將做貫通之理解。
1.「真」的意義區劃:經驗與真理
問題出現了:何謂真實?何謂文學真實?
夷考其實,「文學真實」一語並不見諸中國傳統文論表述。作為西方文論概念,「文學真實」在二十世紀全面置換了中國文學真實論域固有的「誠」、「修辭立其誠」、「性情之真」,以及「仁義禮智」所代表的「人倫真理」,並在中國化的同時承擔了近一個世紀以來批評和闡釋中國文學真實的責任。細辨之,「文學真實」顯然不是以「文學」一詞對「真實」一詞作簡單限定,「文學」的「真實」與一般意義上的「真實」相去甚遠。但要回答「文學真實」諸問題,卻應該首先厘清一般所謂「真實」的內蘊。在古代漢語中,「真實」的一個重要的意義指涉是「相符」,即名與實、內與外、言與行、德與位、能與事等的「相符」,唯能「相符」,方可謂之真實。而在現代漢語中,「真實」也以「相符」為意義基礎,所謂「思維內容與客體相符」,亦即觀念、表達符合於客觀事實。顯然,對「文學真實」來說,「相符」的理解模式未可拋卻。不過,僅以所謂「相符」理解「文學真實」似嫌不足,應該進一步探討。
實際上,現代漢語的「真實」一詞乃是源於古代漢語的「真」。而就意義的普遍性觀之,「真」最重要的意義,一是「真實、真誠」,一是所謂「本原、自身」。細考之,可以發現古代漢語的「真」、現代漢語的「真實」確實以此二義為主,即:一是通過感知和表像所直接把握到的人與世界的真切相遇,或者人的誠而不偽的內心狀態――此為經驗意義上的「真實、真誠」,即經驗之真,或曰經驗性真實;一是通過思維的歸納或演繹,或者徑直通過直覺把握到的宇內萬物抽象的運行規律或者隱藏於其後的內在結構、秩序與動因――此為所謂的「真理」,即潛藏於現象背後的「本原、自身」,是為真理之真。直指本質的「真理」乃與「謬誤」、「錯誤」相對,而經驗意義上的「真實、真誠」則與「虛偽」、「虛假」相對。經驗意義上的「真實、真誠」與直指本質的「真理」構成了漢語之中「真實」一詞的兩個主要意義區劃。實際上,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論語境中,「文學真實」一語之中的「真實」也有這兩個意義區劃,即:「文學真實」或者偏於總體性、抽象性的本質真理的揭示,或者趣近個體性、直接性的經驗真實的抒寫。此意義區劃,不僅呈現出了對「文學真實」可能存在的兩種字面解釋,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劃分出了兩種文學真實話語: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學真實」,從具體的寫作技術層面看,所謂真理之真與所謂經驗之真有時呈互補之勢。而在話語層面上,真理話語與經驗話語歧異判然,它們之間實際上一直存在著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的表現即為真理話語與經驗話語在文學真實論域持續展開的話語權競逐。正是這種話語權競逐使得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學真實」忽而偏執於真理話語,忽而傾向於經驗話語,也正是這種話語權競逐引發了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真實論域不休的甚至殘酷的爭訟和無盡的至今無解的問題。而放眼望去,其實中西文學真實觀念的整個歷史也是因為這種話語權競逐而顯得問題叢生、撲朔迷離。當然,話語權的競逐也常在某些歷史時期歸於穩定的和平共處狀態――即兼重經驗之真和真理之真的狀態。於是,「真實」、「文學真實」的意義區劃,以及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的話語權競逐與共處,遂成為此間探討「文學真實」的下手之處。
2.「真理」與文學真實
且說「真理」。漢語中的「真理」一詞初見於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集》之中,其後唐三藏的《大唐西域記》、釋道宣的《廣弘明集》等書屢見「真理」,而白居易、宋之問等人的詩中亦每稱「真理」。然考其所指,悉為佛教的教義、正理,不涉文學。唯《法苑珠林》所謂「浮言翳真理,為此沉惡趣」,旁涉「言」與「真」的關係,或可向文學真實觀念稍作引申。
唐以後言及「真理」並以之指稱佛理者亦夥。當然也有以「真理」指稱他事者,譬如王若虛云:「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於自得」,「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缽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真理也哉」。此處所言的「真理」,大抵是為詩之道。通觀古代中國所謂「真理」一詞,殆與現代漢語之中的「真理」含義頗不相類。
到了二十世紀,「真理」一詞在漢語中主要不再指稱佛理或者詩文之道,這個詞的所指逐漸寬泛,並逐漸與西方的「真理」含義合流。而在西方,所謂的「真理」曾有強烈的超驗色彩,從古希臘的柏拉圖到中世紀,從神秘的「理念」到宗教的「太一」,超驗的真理享有不容違拗的權威。不過,與之同時,另一種真理觀、即所謂「符合說」的真理觀或曰真理的符合論(correspondencetheoryoftruth)亦在古希臘開其端緒,其後,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由於「教會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學的威信逐步上升」,一般意義上的真理遂成為「主觀判斷與客觀對象相符合」的人間「真理」,顯得科學而理性。這種「符合說」的真理觀被後世描述為:「1.真理的『處所』是命題(判斷)。2.真理的本質在於判斷同它的對象相『符合』。3.亞理士多德這位邏輯之父既把判斷認作真理的源始處所,又率先把真理定義為『符合』。」在海德格爾的「去蔽說」之前,「符合說」幾乎是常識性的真理觀。產生於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理觀也屬於「符合說」――這也是二十世紀中國主流的真理觀。在二十世紀,對現代漢語中「真理」一詞的通行理解正是基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符合說」,即,「真理」是「認識主體對存在於意識之外、並且不以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的規律性的正確反映」。顯然,這裏的真理亦屬認識論範疇,在主客二分的哲學框架下,如果客觀事物與主觀判斷相符合,或者認識符合於事物之本然,那麼認識主體就把握了真理。然而,這種「符合」、「真理」可能是基於認識主體的經驗性實踐和理論性總結,也可能是為了社會進步、為了建構人間秩序或者為了某一群體的利益而被指明的「符合」、被宣稱的「真理」,這種被指明、被宣稱的真理具有工具主義性質,或者說其基礎是一種實用的真理觀(pragmatictheoryoftruth),這種真理之所以被指明、宣稱和確定,其出發點不是認識論的,而是效果論的――雖然這種著眼於效果的「真理」總是朝著認識論或者說符合論的方向而獲得論證。真理作為真理,一旦被指明和確定,它就可能獲得某種正當性甚至權威性。事實上,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語境中,真理往往是超越於個體經驗之外的「宏大敘事」。因為這種真理被指明為符合社會歷史的客觀本質、符合偉大的現實需要,又因為這種指明本身所意味著的某種應當接受的必然性、決定性、客觀性以及進步的、革命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意義,於是,被指明、被確定下來的這種真理往往相似於崇高的超驗真理,享有不可質疑的權威,成為「時代共名」和「權力話語」。中國文論在二十世紀的百年風雲顯示,這種真理觀念對中國的文學真實理論確曾起過結構性的作用。
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總體性、全面性的抽象之物,「真理」塑造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真實觀。在有關文學真實的一系列爭論中頻頻出現的「歷史真實」、「社會生活本質」、「整體真實」、「本質真實」甚至「理想真實」,等等,均屬於甚為抽象的「真理」話語,這樣的「真理」話語一度覆蓋了文學的經驗性,成為檢驗文學表達是否真實的普遍標準。自然,「真理」不是由單個的文學寫作主體自行建構的,對於單個的文學寫作主體而言,「真理」是既定的、前定的、權威的,應該接受之、反映之、表現之。「真理」話語使得文學敘述獲得了一個位於表達主體之外的視點,這個視點更崇高、更正確、更正當。執著於表現「真理」的觀念導致對「文學真實」的追求在很長時期一直偏向目的性、工具性、集體性和正確性,而偏離個體性、審美性,偏離直接的經驗、切身的體驗。在此情形之下,「文學真實」所指者何?其所指乃是以文學形式宣示的社會生活和歷史進程的「本質」、「真理」,一種對於文學寫作主體而言被「給予」的「本質」、「真理」。在文學寫作之中,居於本位的便是「本質」、「真理」,於是,文學的一切鋪陳和所有刻劃,都成為圍繞、服務此「本質」、「真理」的修辭行為,成為一種工具性存在,而對其自身的目的性和規律性的考慮則常被無限延遲。
其實,如果將視野擴大到整個中國文學真實觀念的演化歷史,更可以看到:儒家的人倫真理或者「天之道」、「人之道」,或者「社會本質」、「本質真實」等真理性範疇不但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亦對整個中國文學表達、尤其是經驗性的表達都有過建構、支配、節制和遮蔽的作用,而且從古至今,一以貫之。
3.「經驗」與文學真實
在此,與人倫真理、社會本質、本質真實等真理之真相對應的是經驗之真。如果不避表達的簡單化,則可以說,本質、真理賦予文學敘述以理性的意義和現實的功用,而經驗真實則使文學敘述有血有肉,使之盡呈豐盈之態。離開經驗真實,單純的本質、真理斷難獨力撐起任何文學作品。在中國文論表述中,有所謂「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之論――花木自不可無根,而「義」、或曰「真理」之「實」,亦未可離卻「情」之根本(「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此「情」此「根」,乃屬經驗範疇。倘無真「根」,則「花」無所依;倘無經驗性的真「情」,則真理之「義」何以立?鮑姆嘉通以為美就是「被稱為真理的那種屬性在感覺中的表現」,如無「感覺」的真實、經驗的真實,文學之中所謂的「真理」以及所謂的「美」何處可尋?在黑格爾那裏,也有所謂「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美就是理念,所以從一方面看,美與真是一回事」,「這就是說,美本身必須是真的」,「但是這理念也要在外在世界實現自己,得到確定的現前的存在,即自然的或心靈的客觀存在」。在此,理念即真、即真理,而美是理念,故美亦真,此暫不論;且注目於作為真理的理念所由實現的「外在世界」、「自然的或心靈的客觀存在」――倘離卻經驗,則此外物與心靈何由把握與呈現?倘此把握與呈現並無經驗的真實,則作為真理的理念亦何由實現?可知在作為審美形式的文學中,本質、真理對於經驗性的真實未可暫離。不過,鮑姆嘉通、黑格爾都是以「真理」、「理念」為本位而對經驗性真實作必要的垂顧,這僅是文學表達的一條路徑。文學表達的另一條路徑、也是最重要的路徑乃是以傳遞經驗真實為本位,而一切人間真諦與精神品格自然包蘊於經驗真實的傳遞中。然則不管是為宣示真理之真而反求經驗,還是以傳遞經驗真實而令真諦自明,經驗真實都是文學表達的第一要義。王國維也曾說,「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倘無經驗性的真實,無真切的感受與體驗,則所謂「具體」何由實現?
似乎所謂經驗性真實就是指情感之真、感受之真、體驗之真;然而文學表達之中的經驗真實到底應當如何準確地界定?
實際上,問題的實質是:何謂文學表達論域中的「經驗」?由於經驗必然是身歷的、心歷的、實有的、真實的,否則便不可謂之「經驗」,也就談不上所謂「經驗真實」,所以,這裏所謂的「經驗真實」乃是「經驗性的真實」;之所以用「經驗」一詞修飾、限定「真實」一詞,只因要與「真理性的真實」相區別,非謂「經驗」之中有「真實」亦有「虛造」者也。既為「經驗」,當然真實。
然而「經驗」為何物?「經驗」是指人所感覺和知覺的、「生物的或社會的閱歷」。而在文學論域,「經驗」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純經歷性的」,另一種則是「不但有過這個經歷,而且在這經歷中見出深刻的意義和詩意的情感,那麼這經驗就成為一種體驗了」,「體驗是經驗中的一種特殊形態」,「是經驗中見出深義、詩意與個性色彩的那一種形態」。顯然,「體驗」對文學表達有直接的重要性。但是,「純經歷性」的經驗的重要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舍此「經歷」,「體驗」無由萌生。在這裏,所謂「經驗」、所謂「經驗真實」,兼含「經歷」與「體驗」二義。
經過感覺、知覺、表像,尤其是經過所謂「自覺的表像運動」,經驗真實或者說體驗遂在文學寫作之中發生實質性的建構作用,形成文學情感、文學形象以及文學化了的各種人生情境。在文學寫作的心理過程中,表像是從心到文的關鍵步驟,因為對於文學寫作主體而言,「美感」、一定的創造性等都形成於表像階段,並且,表像的一端繫連著感覺、知覺到的一切經驗,另一端繫連著被表達的文學情感、文學形象及各種人生情境。表像是經驗性的,從而文學表像的真實即是文學寫作主體的經驗真實。而表像的真實又直接決定文學表達的真實――不但決定文學敘事主幹的真實性、深刻性,尤其決定文學敘事質地的真實感、真切感,因為表像是「最具體的、最主觀的和最豐富的」,而這種具體、主觀和豐富的「表像」只能來自真實、真切的感覺和知覺(感覺、知覺具有顯而易見的生動性、豐富性和直接性),來自經驗真實。文學寫作主體也許可以基於已有的經驗而推論未知的「經驗」,但是卻斷難憑空虛造。魯迅有云:「藝術的真實……只要逼真,不必實有其事也」――「不必實有其事」乃謂不必有某一表達所嚴格對應的具體的確鑿的經驗真實,可以虛設表達之物,只要「逼真」即可;然而,倘無真切的相關經驗以供推論、揣度和移用,何能「逼真」?因此,對於文學寫作、文學真實而言,表像的真實、從而經驗的真實,乃是決定性的。
應該承認,文學寫作對主體的經驗資源有選擇性,文學敘述並不必然是真實存在和發生的具體事物,而常常表現為凌空蹈虛的虛構和想像,文學的審美性質將這種選擇、虛構和想像判定為合法。同時,作為文學敘述媒介、作為文學表達的全部現實的語言,其與外在世界、與人的體受在物理上是異質的,文學表達不可能、也不必要特別地製造出與外在世界、與人的體受同質同構的另一個物理性「真實」。文學寫作主體所建構的必然是一個「虛構的世界、想像的世界」。然而,文學的這種虛構性、想像性卻並不是拒絕文學真實、尤其是拒絕經驗真實的依據。文學史上有許多文學表達具有觸目驚心、出人意表的想像性、虛構性甚至荒誕感,而所謂經驗、所謂真實,似乎將要在這想像、虛構和荒誕之中流失殆盡,但是,閱讀的經驗表明,「當故事變得越來越不可思議的時候,故事本身的真實性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增強」,整體形式雖然荒誕,但是「所有的事物被展示時都有著現實的觸摸感和親切感」,寫作主體「認真地和現實地刻劃每一個細節」,精細捕捉「具體事物的真實」。整體表達的虛構、荒誕無礙其局部、細節、敘述質地的可觸可摸的經驗感、真切感,是為此類文學表達能夠長驅直入文學閱讀主體的內心並引出廣闊思索的關鍵。而閱讀主體所獲得的經驗感、真切感,當然源於寫作主體不可須臾失手的經驗真實。
4.真理話語與經驗話語
在真理、經驗以及它們與文學真實的關係被勾畫出來之後,文學真實似乎便獲得了大致的規定――所謂文學真實,即是在文學敘述之中以文學的形式傳達出來的真理性或者經驗性。這條規定應該是準確的,但是過分簡略,未能展現文學表達之中真理與經驗各自的功能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亦未區分在文學表達中真理話語與經驗話語的深刻歧異。
從浮現於文本表層的關係看,「真理」與「經驗」是互補的。在探討文學真實的時候,強調經驗真實的重要性,乃是為了遠離一味從「真理」的認識論方向去要求、超拔、突顯「文學真實」之際所可能導致的概念化、工具化、反文學的寫作路向,也就是說,經驗真實可祛真理真實的空泛之病。另一方面,經驗真實雖則易於一舉步入審美之域並且可以有效地造成文學敘述質地的經驗感、逼真感(senseofverisimilitude),但是,倘若放縱經驗真實的表達而拒絕真理(尤其是作為人倫真理的道德理性)的制約,則易流於以氾濫為真、以癰潰為美。在此,真理的價值內涵與理性本色有助於節制經驗寫作的流蕩無度。統言之,文學表達若純任真理之真,則失於概念;若盡信經驗之真,則失於恣縱。不離經驗的真實,則真理的宣示方美;不離真理的節制,則經驗的傳遞方善。
然而,「互補」的關係也僅止於文本的技術表層而已。如果縱覽文學真實理論的歷史行程,則可以發現,「真理」與「經驗」其實各有淵源、各有規則、各有所從屬的學科、信仰和「權力」體系,並非總是在文本的技術表層所顯示的那般「互補」。實際上,更深入的研究必須超越文本的技術表層而在話語層面展開,必須在文學真實論域勾勒出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的大致輪廓,並且指明它們之間的關係。
需要先對「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中的話語一詞略作說明。此處所謂的話語概念來自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但是對它的解釋不可避免地有為我所用的取捨和變通。在福柯那裏,追問話語(discourse)為何物並不十分恰當,因為對於反本質主義的福柯而言,話語不宜被明確地定義。不過,福柯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系統而嚴格的」(systematicandrigid),其話語有某種「框架」、「圖式」和「秩序」,因此也可以對他所徵用的話語一詞做出具有一定的有效性的描述。一般地說,福柯的這個用語指的是「知識考古學中各研究領域或各種學科的結構」,「各學科有不同的話語,它們都由許多具體的陳述組成」,「陳述不來源於作者的思考,不涉及個別的主體,也不具有先驗的主體性,而是一種匿名的領域,是一種無意識的結構」,「一個時期的話語的共同特徵即知識型,因而在不同知識型下的同一概念或同一陳述有不同的意義,在不同話語下的相同概念也有不同的意義。」這種對話語的理解,對於「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而言,其關鍵在於揭示了話語、知識型以及概念、陳述的關係。話語的基本單位是陳述,陳述的具體性和知識型的時代性(所謂「大寫的主體,思想的模本和時代的精神走向」)決定了話語本身的具體性、非連續性和實踐性。在此情形下,當把概念納入視野的時候,問題便出現了:話語「是概念出現的地點」,構成話語的一系列陳述離不開、甚至必須大量使用概念;而概念(譬如「真理」之類)在穿過了漫長的歷史和人類主體的經驗之後,一般說來,其內涵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一致性、連續性和經驗性,相對「靜止」的、「理想性」的概念(如果有的話)或者主體直接的、「經驗性」的概念(如果有的話)必然與陳述、話語的具體性、非主體性和非連續性之間產生齟齬。於是,在話語中出現的概念不論是內涵還是外延都必然被徵用它的話語「格式化」,不是「讓陳述的多樣性服從於概念的一致性」,而是相反。對於概念被話語「格式化」的問題,哈耶克(FriedrichHayek,1899-1992)的一些論述可謂佳例:哈耶克曾論及極權主義制度對「自由」、「真理」等「一切普遍應用的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名詞」的詞義的竄改,這種竄改使得「全部語言的意義逐漸被剝奪而文字則變成了空殼,失去了任何具體的內容;它們既可以表示一件事物的正面,又可以表示它的反面」。用福柯的理論,這種竄改的實質便是在極權主義的知識型之下,話語對於概念的「格式化」。實際上,這種「格式化」是必然的,因為概念必然是在陳述、在話語之中形成的,也是以此之故,福柯認為「分析概念的形成,既不應把它們歸結於理想性的範圍,也不應歸結於觀念的經驗性發展」,譬如分析「精神病」這個概念的形成,便既不能根據一個靜止的「定義」,也不能根據個體的經驗,而應該像福柯的《瘋癲與文明》那樣在話語的考察中去發現其在不同的「時代精神」之下、在不同的知識型之下的具體所指。而在文學真實論域,所謂的真實,所謂的真理之真、經驗之真,也應當在話語的層面上作「考古學」的研究即歷史清理,方能洞見其幽微的真相和具體的所指,而對文學真實的探討顯然也可以在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的框架下展開。
福柯著力於揭示潛藏於各科知識、社會文化諸般表像之下的深層結構和控制規則,而所謂「話語」便是為此目的而提出和使用的。「話語」直通人類知識的生產、傳播與使用的內在秘密,即權力,福柯「指出了一個容易為人們所忽略的事實,那就是任何時代的任何話語都不是個人的創造和想像力的成果,也不是自然而然延續的結果,而是權力的產物,權力通過一系列複雜的程序和隱蔽的手段,來控制、選擇、組織和傳播作為話語形式的知識,無論科學、法律、人文科學甚至醫學,莫不如此。」在將所謂的「權力」同文學真實觀念聯繫起來的時候,應當注意的是:此處的「權力」並不固執地指向政治權力,它是廣義的權力,它將顯示的是話語背後結構性的力量和控制性的關係。所謂的文學真實便深陷於這種力量和關係之中,並劃分為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
如果更進一步,則可以看出,真理話語似乎與福柯所謂的「求知意志」(willtoknowledge)或者「求真意志」(willtotruth)相繫,而經驗話語則似乎與出現於「文的自覺」以後的文學學科共識密不可分。而不論是「求知意志」、「求真意志」,還是文學的學科共識,都代表著結構性的力量和控制性的關係,即,都代表著某種權力。
真理話語所關涉到的「求知意志」並不單純是知識追求,「求知意志」也「有賴於體制的支持與流通,它傾向於實施某種壓力,實施一種對其他話語形式的限制權力。」「求知」是通向「求真」的,「求知意志」實際上就是「求真意志」,這是西方文化中追求真理的理性原則。在文學真實論域,真理話語的實質就是所謂「求真意志」或者「求知意志」,真理話語貫徹於對文學真實的理解之後,其他有關文學真實的理解,譬如所謂經驗真實,便作為一種「其他話語形式」而面臨被具體、特定的真理話語限制、壓制甚至取消的處境。真理話語的核心是權力:「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以及其他社會中,有多樣的權力關係滲透到社會的機體中去,構成社會機體的特徵,如果沒有話語的生產、積累、流通和發揮功能的話,這些權力關係自身就不能建立起來和得到鞏固。我們受真理的生產的支配,如果不是通過對真理的生產,我們就不能實施權力。」對此,哈耶克有相似的說法:「真理這個詞本身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它成了要由當權者規定的東西,某種為了有組織的一致行動的利益必須加以信任的東西,並且是在有組織的行動有迫切需要的關頭又必須加以更改的東西。」齊格蒙‧鮑曼(ZygmuntBauman,1926-)也一語中的:「真理觀念屬於權力的修辭學。」真理話語執行的是個體並不自覺的權力規則,它本身就是權力的產物,它是社會對個體實施權力的媒介,並且也是維繫權力關係的工具。在此,必須指出,文學真實理論中的真理話語作為一種權力話語,它貫穿於文學理論之中,依靠從古至今形態不同但是內在相通的政治、倫理、道德、科學、風俗等「體制」持續對文學「實施某種壓力」,按照權力規則和實用規則操縱文學表達。文學寫作主體(包括批評主體)處於真理話語的權力鏈條的不同環節上,他們或者是自覺不自覺地依據權力規則解釋、闡述「真理」,或者接受、表現「真理」,而在解釋、闡述或者接受、表現之中,權力的眼睛無處不在。
與經驗話語相連的文學學科的內在規則或者說學科共識也是一種權力形式。當然,文學學科的內在規則與真理話語背後的權力規則有很大差異:對於文學這一學科而言,尤其是對於現代的、充分強調自身的獨立自足的文學學科而言,真理話語所實施的權力控制是外在的,屬於「外部聯繫」,而文學這一學科的所謂「本質屬性」則是一切「內在規則」的集合,這是一種深刻的內部權力。就文學真實論域觀之,文學學科「內在規則」的最要緊處,乃是經驗話語。先秦的國人把「詩」與真實的、經驗性的「志」聯繫起來,古代希臘人把逼真的「摹仿」與「痛感」、「快感」之類的經驗聯繫起來,這表明,不論中西,經驗話語當然的學科合法性都在文學真實觀念的源頭暗示出來了。但是直到近世,在文學真實觀念中,經驗話語的學科合法性才真正確立,而一旦確立,它就代表了一種學科建制的結構性特徵,一種權力。在二十世紀中國,從胡適所謂「詩的經驗主義」(poeticempiricism)到成仿吾所謂「文藝是以經驗為基礎的創造」,再到袁可嘉所謂詩「是經驗的傳達」,展示了在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工具主義氛圍中,經驗話語企圖以自己的力量搭建文學學科構架、確定學科內在規則的不懈努力。不過,這種努力很快就在新的歷史語境裏中斷了,直到近二十來年才逐漸恢復並顯示出文學的學科權力,才有人明確指出「詩的第一要素就是真,不真無詩,矯飾情感者乃偽詩」。近世西人一直強調經驗話語在文學學科中的地位,在H.派克的體系中,感覺、感情、審美經驗中的「觀念或意義」、「來自各種感官」的「形象」這四類藝術經驗具有重大意義;而貫穿琳賽‧沃特斯《美學權威主義批判》一書的聲音則是「你體驗過了嗎」,他批判了自笛卡爾以來「對於體驗的空前的不信任」的現象,認為當「正確性成為藝術存在的前提條件」以後,「我們用教養來對抗體驗並且讓教養占統治地位」,於是,「我們」便「被精緻的思想觀念敗壞了」,而「我們」本不應如此,因為「我們的目標應該是體驗而不是認識」。實際上沃特斯是以經驗話語「批判」真理話語,而這種批判所昭示的恰是經驗話語的學科權力。在此,應該重申,經驗不等於經驗話語,經驗具有個體性、直接性,而經驗話語則是在經驗的概念背後糾結的學科權力結構,這個結構是在與真理話語的對峙之中形成的,它主要捍衛的是文學學科的屬性而非經驗的重要性。
在話語層面,「真理」與「經驗」從來就是對峙、競爭的關係。真理話語與經驗話語可能顯得「和諧」(此「和諧」的實質是某一時代的文學真實觀念取了中道,意味著兩種話語在對峙之中呈現出一種均勢),但更可能是一方壓倒另一方。它們載沉載浮、此消彼漲,使文學真實觀念的歷史從來就是一場真理話語同經驗話語共處一室而又不斷競逐話語權的歷史。不過,應當看到,在文學真實論域,兩種話語中的任何一種都不可能絕對壓倒另一種。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可以視為一條線段的兩個端點,在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的共同作用下,一個時代的文學真實觀念所處的確切位置永遠在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這兩個端點之間滑動,不同時代的文學真實觀念在這條線段上處於不同的位置。
至此,「文學真實」似乎只能被這樣界定:
在文學寫作之中所傳達的經驗性真實或者真理性真實,便是所謂的「文學真實」。而關於文學真實的理論表述之中則存在著一個對立而又統一的結構,一個關於「經驗之真-真理之真」、「經驗話語-真理話語」的雙重結構。
真實是人類的一種必要的想像。
離開真實,人類的一切表達、從而整個人類文化,都可能意義全消。
文學作為人類對自身精神與境遇的審美表達,同樣應該直面「真」相或者腳踏「實」地。文學當以真實為基座,舍此基座,便可能流於漂浮的游談,喪盡其精神和根據,而所謂的審美追求也將一腳踏空;真實亦當如旗桿,文學之旗在風中自由似夢的捲舒不應離開旗桿的真實挺立,否則,文學這面風中之旗勢將隨風飄逝。在文學敘述中,「真實」可能是經驗之真,質地可以觸摸,也可能是真理之真,給人方向、節制與思索。然而,文學中所謂的「真實」並非一種不言而喻的當然之物,它有時也可能僅僅是一種宣稱,而在所宣稱的「真實」背後還另有真實――於是,真實的也許是崇高的社會理想,或者是堅硬的現實功利,甚至,「真實」可能是鬥爭的口號和工具,是權力的修辭。實際上,在穿過文化規範、權力操縱、功利打算、主觀判斷和語言構造之後,「真實」所呈現的,只能是斑駁的投影,或者說,人類所把握到的「真實」,包括「文學真實」,往往只是一種有根據的想像。
真實、文學真實,乃是一個直逼文學本源的重要論域。這個論域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文化中呈現出不同的景致,各有傳承和新變、增益和減損、發掘和重塑,有進有退,有改道,有折中,遺下豐富的學術資料,以及理論智慧。同時,從古至今的中外文論和批評,有關文學真實的觀念紛然雜陳,不可勝計,有時甚至顯得恍惚不明,讓人困惑未已。
面對這個資源豐富而又令人困惑的重要論域,一般性地建構學者自己的體系誠能揭示一些在學者個人的視點上發現的幽微學理,但更有說服力的探尋應當首先注目於歷史過程,應當首先縱向追索文學真實觀念的歷史,然後方能有根據地橫向建構文學真實的理論體系。實際上,倘若回到具體的語境,在文學真實觀念的演進歷程之中,其暗藏的內在機制和結構將從幽暗的歷史煙雲深處清晰現身。
這裏要做的,就是在歷史清理之中實現學理建構,即對中國從先秦到1949年的文學真實觀念展開一次全面的歷史清理,並在清理過程中勾畫出中國文學真實觀念的內在結構。從二十世紀以前的誠論到二十世紀的文學真實論,在此將做貫通之理解。
1.「真」的意義區劃:經驗與真理
問題出現了:何謂真實?何謂文學真實?
夷考其實,「文學真實」一語並不見諸中國傳統文論表述。作為西方文論概念,「文學真實」在二十世紀全面置換了中國文學真實論域固有的「誠」、「修辭立其誠」、「性情之真」,以及「仁義禮智」所代表的「人倫真理」,並在中國化的同時承擔了近一個世紀以來批評和闡釋中國文學真實的責任。細辨之,「文學真實」顯然不是以「文學」一詞對「真實」一詞作簡單限定,「文學」的「真實」與一般意義上的「真實」相去甚遠。但要回答「文學真實」諸問題,卻應該首先厘清一般所謂「真實」的內蘊。在古代漢語中,「真實」的一個重要的意義指涉是「相符」,即名與實、內與外、言與行、德與位、能與事等的「相符」,唯能「相符」,方可謂之真實。而在現代漢語中,「真實」也以「相符」為意義基礎,所謂「思維內容與客體相符」,亦即觀念、表達符合於客觀事實。顯然,對「文學真實」來說,「相符」的理解模式未可拋卻。不過,僅以所謂「相符」理解「文學真實」似嫌不足,應該進一步探討。
實際上,現代漢語的「真實」一詞乃是源於古代漢語的「真」。而就意義的普遍性觀之,「真」最重要的意義,一是「真實、真誠」,一是所謂「本原、自身」。細考之,可以發現古代漢語的「真」、現代漢語的「真實」確實以此二義為主,即:一是通過感知和表像所直接把握到的人與世界的真切相遇,或者人的誠而不偽的內心狀態――此為經驗意義上的「真實、真誠」,即經驗之真,或曰經驗性真實;一是通過思維的歸納或演繹,或者徑直通過直覺把握到的宇內萬物抽象的運行規律或者隱藏於其後的內在結構、秩序與動因――此為所謂的「真理」,即潛藏於現象背後的「本原、自身」,是為真理之真。直指本質的「真理」乃與「謬誤」、「錯誤」相對,而經驗意義上的「真實、真誠」則與「虛偽」、「虛假」相對。經驗意義上的「真實、真誠」與直指本質的「真理」構成了漢語之中「真實」一詞的兩個主要意義區劃。實際上,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論語境中,「文學真實」一語之中的「真實」也有這兩個意義區劃,即:「文學真實」或者偏於總體性、抽象性的本質真理的揭示,或者趣近個體性、直接性的經驗真實的抒寫。此意義區劃,不僅呈現出了對「文學真實」可能存在的兩種字面解釋,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劃分出了兩種文學真實話語: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學真實」,從具體的寫作技術層面看,所謂真理之真與所謂經驗之真有時呈互補之勢。而在話語層面上,真理話語與經驗話語歧異判然,它們之間實際上一直存在著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的表現即為真理話語與經驗話語在文學真實論域持續展開的話語權競逐。正是這種話語權競逐使得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學真實」忽而偏執於真理話語,忽而傾向於經驗話語,也正是這種話語權競逐引發了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真實論域不休的甚至殘酷的爭訟和無盡的至今無解的問題。而放眼望去,其實中西文學真實觀念的整個歷史也是因為這種話語權競逐而顯得問題叢生、撲朔迷離。當然,話語權的競逐也常在某些歷史時期歸於穩定的和平共處狀態――即兼重經驗之真和真理之真的狀態。於是,「真實」、「文學真實」的意義區劃,以及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的話語權競逐與共處,遂成為此間探討「文學真實」的下手之處。
2.「真理」與文學真實
且說「真理」。漢語中的「真理」一詞初見於南朝《梁昭明太子文集》之中,其後唐三藏的《大唐西域記》、釋道宣的《廣弘明集》等書屢見「真理」,而白居易、宋之問等人的詩中亦每稱「真理」。然考其所指,悉為佛教的教義、正理,不涉文學。唯《法苑珠林》所謂「浮言翳真理,為此沉惡趣」,旁涉「言」與「真」的關係,或可向文學真實觀念稍作引申。
唐以後言及「真理」並以之指稱佛理者亦夥。當然也有以「真理」指稱他事者,譬如王若虛云:「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於自得」,「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缽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真理也哉」。此處所言的「真理」,大抵是為詩之道。通觀古代中國所謂「真理」一詞,殆與現代漢語之中的「真理」含義頗不相類。
到了二十世紀,「真理」一詞在漢語中主要不再指稱佛理或者詩文之道,這個詞的所指逐漸寬泛,並逐漸與西方的「真理」含義合流。而在西方,所謂的「真理」曾有強烈的超驗色彩,從古希臘的柏拉圖到中世紀,從神秘的「理念」到宗教的「太一」,超驗的真理享有不容違拗的權威。不過,與之同時,另一種真理觀、即所謂「符合說」的真理觀或曰真理的符合論(correspondencetheoryoftruth)亦在古希臘開其端緒,其後,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由於「教會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學的威信逐步上升」,一般意義上的真理遂成為「主觀判斷與客觀對象相符合」的人間「真理」,顯得科學而理性。這種「符合說」的真理觀被後世描述為:「1.真理的『處所』是命題(判斷)。2.真理的本質在於判斷同它的對象相『符合』。3.亞理士多德這位邏輯之父既把判斷認作真理的源始處所,又率先把真理定義為『符合』。」在海德格爾的「去蔽說」之前,「符合說」幾乎是常識性的真理觀。產生於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理觀也屬於「符合說」――這也是二十世紀中國主流的真理觀。在二十世紀,對現代漢語中「真理」一詞的通行理解正是基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符合說」,即,「真理」是「認識主體對存在於意識之外、並且不以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實在的規律性的正確反映」。顯然,這裏的真理亦屬認識論範疇,在主客二分的哲學框架下,如果客觀事物與主觀判斷相符合,或者認識符合於事物之本然,那麼認識主體就把握了真理。然而,這種「符合」、「真理」可能是基於認識主體的經驗性實踐和理論性總結,也可能是為了社會進步、為了建構人間秩序或者為了某一群體的利益而被指明的「符合」、被宣稱的「真理」,這種被指明、被宣稱的真理具有工具主義性質,或者說其基礎是一種實用的真理觀(pragmatictheoryoftruth),這種真理之所以被指明、宣稱和確定,其出發點不是認識論的,而是效果論的――雖然這種著眼於效果的「真理」總是朝著認識論或者說符合論的方向而獲得論證。真理作為真理,一旦被指明和確定,它就可能獲得某種正當性甚至權威性。事實上,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語境中,真理往往是超越於個體經驗之外的「宏大敘事」。因為這種真理被指明為符合社會歷史的客觀本質、符合偉大的現實需要,又因為這種指明本身所意味著的某種應當接受的必然性、決定性、客觀性以及進步的、革命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意義,於是,被指明、被確定下來的這種真理往往相似於崇高的超驗真理,享有不可質疑的權威,成為「時代共名」和「權力話語」。中國文論在二十世紀的百年風雲顯示,這種真理觀念對中國的文學真實理論確曾起過結構性的作用。
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總體性、全面性的抽象之物,「真理」塑造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真實觀。在有關文學真實的一系列爭論中頻頻出現的「歷史真實」、「社會生活本質」、「整體真實」、「本質真實」甚至「理想真實」,等等,均屬於甚為抽象的「真理」話語,這樣的「真理」話語一度覆蓋了文學的經驗性,成為檢驗文學表達是否真實的普遍標準。自然,「真理」不是由單個的文學寫作主體自行建構的,對於單個的文學寫作主體而言,「真理」是既定的、前定的、權威的,應該接受之、反映之、表現之。「真理」話語使得文學敘述獲得了一個位於表達主體之外的視點,這個視點更崇高、更正確、更正當。執著於表現「真理」的觀念導致對「文學真實」的追求在很長時期一直偏向目的性、工具性、集體性和正確性,而偏離個體性、審美性,偏離直接的經驗、切身的體驗。在此情形之下,「文學真實」所指者何?其所指乃是以文學形式宣示的社會生活和歷史進程的「本質」、「真理」,一種對於文學寫作主體而言被「給予」的「本質」、「真理」。在文學寫作之中,居於本位的便是「本質」、「真理」,於是,文學的一切鋪陳和所有刻劃,都成為圍繞、服務此「本質」、「真理」的修辭行為,成為一種工具性存在,而對其自身的目的性和規律性的考慮則常被無限延遲。
其實,如果將視野擴大到整個中國文學真實觀念的演化歷史,更可以看到:儒家的人倫真理或者「天之道」、「人之道」,或者「社會本質」、「本質真實」等真理性範疇不但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亦對整個中國文學表達、尤其是經驗性的表達都有過建構、支配、節制和遮蔽的作用,而且從古至今,一以貫之。
3.「經驗」與文學真實
在此,與人倫真理、社會本質、本質真實等真理之真相對應的是經驗之真。如果不避表達的簡單化,則可以說,本質、真理賦予文學敘述以理性的意義和現實的功用,而經驗真實則使文學敘述有血有肉,使之盡呈豐盈之態。離開經驗真實,單純的本質、真理斷難獨力撐起任何文學作品。在中國文論表述中,有所謂「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之論――花木自不可無根,而「義」、或曰「真理」之「實」,亦未可離卻「情」之根本(「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此「情」此「根」,乃屬經驗範疇。倘無真「根」,則「花」無所依;倘無經驗性的真「情」,則真理之「義」何以立?鮑姆嘉通以為美就是「被稱為真理的那種屬性在感覺中的表現」,如無「感覺」的真實、經驗的真實,文學之中所謂的「真理」以及所謂的「美」何處可尋?在黑格爾那裏,也有所謂「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美就是理念,所以從一方面看,美與真是一回事」,「這就是說,美本身必須是真的」,「但是這理念也要在外在世界實現自己,得到確定的現前的存在,即自然的或心靈的客觀存在」。在此,理念即真、即真理,而美是理念,故美亦真,此暫不論;且注目於作為真理的理念所由實現的「外在世界」、「自然的或心靈的客觀存在」――倘離卻經驗,則此外物與心靈何由把握與呈現?倘此把握與呈現並無經驗的真實,則作為真理的理念亦何由實現?可知在作為審美形式的文學中,本質、真理對於經驗性的真實未可暫離。不過,鮑姆嘉通、黑格爾都是以「真理」、「理念」為本位而對經驗性真實作必要的垂顧,這僅是文學表達的一條路徑。文學表達的另一條路徑、也是最重要的路徑乃是以傳遞經驗真實為本位,而一切人間真諦與精神品格自然包蘊於經驗真實的傳遞中。然則不管是為宣示真理之真而反求經驗,還是以傳遞經驗真實而令真諦自明,經驗真實都是文學表達的第一要義。王國維也曾說,「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倘無經驗性的真實,無真切的感受與體驗,則所謂「具體」何由實現?
似乎所謂經驗性真實就是指情感之真、感受之真、體驗之真;然而文學表達之中的經驗真實到底應當如何準確地界定?
實際上,問題的實質是:何謂文學表達論域中的「經驗」?由於經驗必然是身歷的、心歷的、實有的、真實的,否則便不可謂之「經驗」,也就談不上所謂「經驗真實」,所以,這裏所謂的「經驗真實」乃是「經驗性的真實」;之所以用「經驗」一詞修飾、限定「真實」一詞,只因要與「真理性的真實」相區別,非謂「經驗」之中有「真實」亦有「虛造」者也。既為「經驗」,當然真實。
然而「經驗」為何物?「經驗」是指人所感覺和知覺的、「生物的或社會的閱歷」。而在文學論域,「經驗」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純經歷性的」,另一種則是「不但有過這個經歷,而且在這經歷中見出深刻的意義和詩意的情感,那麼這經驗就成為一種體驗了」,「體驗是經驗中的一種特殊形態」,「是經驗中見出深義、詩意與個性色彩的那一種形態」。顯然,「體驗」對文學表達有直接的重要性。但是,「純經歷性」的經驗的重要也是顯而易見的:因為舍此「經歷」,「體驗」無由萌生。在這裏,所謂「經驗」、所謂「經驗真實」,兼含「經歷」與「體驗」二義。
經過感覺、知覺、表像,尤其是經過所謂「自覺的表像運動」,經驗真實或者說體驗遂在文學寫作之中發生實質性的建構作用,形成文學情感、文學形象以及文學化了的各種人生情境。在文學寫作的心理過程中,表像是從心到文的關鍵步驟,因為對於文學寫作主體而言,「美感」、一定的創造性等都形成於表像階段,並且,表像的一端繫連著感覺、知覺到的一切經驗,另一端繫連著被表達的文學情感、文學形象及各種人生情境。表像是經驗性的,從而文學表像的真實即是文學寫作主體的經驗真實。而表像的真實又直接決定文學表達的真實――不但決定文學敘事主幹的真實性、深刻性,尤其決定文學敘事質地的真實感、真切感,因為表像是「最具體的、最主觀的和最豐富的」,而這種具體、主觀和豐富的「表像」只能來自真實、真切的感覺和知覺(感覺、知覺具有顯而易見的生動性、豐富性和直接性),來自經驗真實。文學寫作主體也許可以基於已有的經驗而推論未知的「經驗」,但是卻斷難憑空虛造。魯迅有云:「藝術的真實……只要逼真,不必實有其事也」――「不必實有其事」乃謂不必有某一表達所嚴格對應的具體的確鑿的經驗真實,可以虛設表達之物,只要「逼真」即可;然而,倘無真切的相關經驗以供推論、揣度和移用,何能「逼真」?因此,對於文學寫作、文學真實而言,表像的真實、從而經驗的真實,乃是決定性的。
應該承認,文學寫作對主體的經驗資源有選擇性,文學敘述並不必然是真實存在和發生的具體事物,而常常表現為凌空蹈虛的虛構和想像,文學的審美性質將這種選擇、虛構和想像判定為合法。同時,作為文學敘述媒介、作為文學表達的全部現實的語言,其與外在世界、與人的體受在物理上是異質的,文學表達不可能、也不必要特別地製造出與外在世界、與人的體受同質同構的另一個物理性「真實」。文學寫作主體所建構的必然是一個「虛構的世界、想像的世界」。然而,文學的這種虛構性、想像性卻並不是拒絕文學真實、尤其是拒絕經驗真實的依據。文學史上有許多文學表達具有觸目驚心、出人意表的想像性、虛構性甚至荒誕感,而所謂經驗、所謂真實,似乎將要在這想像、虛構和荒誕之中流失殆盡,但是,閱讀的經驗表明,「當故事變得越來越不可思議的時候,故事本身的真實性不僅沒有削弱,反而增強」,整體形式雖然荒誕,但是「所有的事物被展示時都有著現實的觸摸感和親切感」,寫作主體「認真地和現實地刻劃每一個細節」,精細捕捉「具體事物的真實」。整體表達的虛構、荒誕無礙其局部、細節、敘述質地的可觸可摸的經驗感、真切感,是為此類文學表達能夠長驅直入文學閱讀主體的內心並引出廣闊思索的關鍵。而閱讀主體所獲得的經驗感、真切感,當然源於寫作主體不可須臾失手的經驗真實。
4.真理話語與經驗話語
在真理、經驗以及它們與文學真實的關係被勾畫出來之後,文學真實似乎便獲得了大致的規定――所謂文學真實,即是在文學敘述之中以文學的形式傳達出來的真理性或者經驗性。這條規定應該是準確的,但是過分簡略,未能展現文學表達之中真理與經驗各自的功能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亦未區分在文學表達中真理話語與經驗話語的深刻歧異。
從浮現於文本表層的關係看,「真理」與「經驗」是互補的。在探討文學真實的時候,強調經驗真實的重要性,乃是為了遠離一味從「真理」的認識論方向去要求、超拔、突顯「文學真實」之際所可能導致的概念化、工具化、反文學的寫作路向,也就是說,經驗真實可祛真理真實的空泛之病。另一方面,經驗真實雖則易於一舉步入審美之域並且可以有效地造成文學敘述質地的經驗感、逼真感(senseofverisimilitude),但是,倘若放縱經驗真實的表達而拒絕真理(尤其是作為人倫真理的道德理性)的制約,則易流於以氾濫為真、以癰潰為美。在此,真理的價值內涵與理性本色有助於節制經驗寫作的流蕩無度。統言之,文學表達若純任真理之真,則失於概念;若盡信經驗之真,則失於恣縱。不離經驗的真實,則真理的宣示方美;不離真理的節制,則經驗的傳遞方善。
然而,「互補」的關係也僅止於文本的技術表層而已。如果縱覽文學真實理論的歷史行程,則可以發現,「真理」與「經驗」其實各有淵源、各有規則、各有所從屬的學科、信仰和「權力」體系,並非總是在文本的技術表層所顯示的那般「互補」。實際上,更深入的研究必須超越文本的技術表層而在話語層面展開,必須在文學真實論域勾勒出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的大致輪廓,並且指明它們之間的關係。
需要先對「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中的話語一詞略作說明。此處所謂的話語概念來自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但是對它的解釋不可避免地有為我所用的取捨和變通。在福柯那裏,追問話語(discourse)為何物並不十分恰當,因為對於反本質主義的福柯而言,話語不宜被明確地定義。不過,福柯的觀念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系統而嚴格的」(systematicandrigid),其話語有某種「框架」、「圖式」和「秩序」,因此也可以對他所徵用的話語一詞做出具有一定的有效性的描述。一般地說,福柯的這個用語指的是「知識考古學中各研究領域或各種學科的結構」,「各學科有不同的話語,它們都由許多具體的陳述組成」,「陳述不來源於作者的思考,不涉及個別的主體,也不具有先驗的主體性,而是一種匿名的領域,是一種無意識的結構」,「一個時期的話語的共同特徵即知識型,因而在不同知識型下的同一概念或同一陳述有不同的意義,在不同話語下的相同概念也有不同的意義。」這種對話語的理解,對於「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而言,其關鍵在於揭示了話語、知識型以及概念、陳述的關係。話語的基本單位是陳述,陳述的具體性和知識型的時代性(所謂「大寫的主體,思想的模本和時代的精神走向」)決定了話語本身的具體性、非連續性和實踐性。在此情形下,當把概念納入視野的時候,問題便出現了:話語「是概念出現的地點」,構成話語的一系列陳述離不開、甚至必須大量使用概念;而概念(譬如「真理」之類)在穿過了漫長的歷史和人類主體的經驗之後,一般說來,其內涵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一致性、連續性和經驗性,相對「靜止」的、「理想性」的概念(如果有的話)或者主體直接的、「經驗性」的概念(如果有的話)必然與陳述、話語的具體性、非主體性和非連續性之間產生齟齬。於是,在話語中出現的概念不論是內涵還是外延都必然被徵用它的話語「格式化」,不是「讓陳述的多樣性服從於概念的一致性」,而是相反。對於概念被話語「格式化」的問題,哈耶克(FriedrichHayek,1899-1992)的一些論述可謂佳例:哈耶克曾論及極權主義制度對「自由」、「真理」等「一切普遍應用的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名詞」的詞義的竄改,這種竄改使得「全部語言的意義逐漸被剝奪而文字則變成了空殼,失去了任何具體的內容;它們既可以表示一件事物的正面,又可以表示它的反面」。用福柯的理論,這種竄改的實質便是在極權主義的知識型之下,話語對於概念的「格式化」。實際上,這種「格式化」是必然的,因為概念必然是在陳述、在話語之中形成的,也是以此之故,福柯認為「分析概念的形成,既不應把它們歸結於理想性的範圍,也不應歸結於觀念的經驗性發展」,譬如分析「精神病」這個概念的形成,便既不能根據一個靜止的「定義」,也不能根據個體的經驗,而應該像福柯的《瘋癲與文明》那樣在話語的考察中去發現其在不同的「時代精神」之下、在不同的知識型之下的具體所指。而在文學真實論域,所謂的真實,所謂的真理之真、經驗之真,也應當在話語的層面上作「考古學」的研究即歷史清理,方能洞見其幽微的真相和具體的所指,而對文學真實的探討顯然也可以在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的框架下展開。
福柯著力於揭示潛藏於各科知識、社會文化諸般表像之下的深層結構和控制規則,而所謂「話語」便是為此目的而提出和使用的。「話語」直通人類知識的生產、傳播與使用的內在秘密,即權力,福柯「指出了一個容易為人們所忽略的事實,那就是任何時代的任何話語都不是個人的創造和想像力的成果,也不是自然而然延續的結果,而是權力的產物,權力通過一系列複雜的程序和隱蔽的手段,來控制、選擇、組織和傳播作為話語形式的知識,無論科學、法律、人文科學甚至醫學,莫不如此。」在將所謂的「權力」同文學真實觀念聯繫起來的時候,應當注意的是:此處的「權力」並不固執地指向政治權力,它是廣義的權力,它將顯示的是話語背後結構性的力量和控制性的關係。所謂的文學真實便深陷於這種力量和關係之中,並劃分為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
如果更進一步,則可以看出,真理話語似乎與福柯所謂的「求知意志」(willtoknowledge)或者「求真意志」(willtotruth)相繫,而經驗話語則似乎與出現於「文的自覺」以後的文學學科共識密不可分。而不論是「求知意志」、「求真意志」,還是文學的學科共識,都代表著結構性的力量和控制性的關係,即,都代表著某種權力。
真理話語所關涉到的「求知意志」並不單純是知識追求,「求知意志」也「有賴於體制的支持與流通,它傾向於實施某種壓力,實施一種對其他話語形式的限制權力。」「求知」是通向「求真」的,「求知意志」實際上就是「求真意志」,這是西方文化中追求真理的理性原則。在文學真實論域,真理話語的實質就是所謂「求真意志」或者「求知意志」,真理話語貫徹於對文學真實的理解之後,其他有關文學真實的理解,譬如所謂經驗真實,便作為一種「其他話語形式」而面臨被具體、特定的真理話語限制、壓制甚至取消的處境。真理話語的核心是權力:「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以及其他社會中,有多樣的權力關係滲透到社會的機體中去,構成社會機體的特徵,如果沒有話語的生產、積累、流通和發揮功能的話,這些權力關係自身就不能建立起來和得到鞏固。我們受真理的生產的支配,如果不是通過對真理的生產,我們就不能實施權力。」對此,哈耶克有相似的說法:「真理這個詞本身已失去了它原有的意義……它成了要由當權者規定的東西,某種為了有組織的一致行動的利益必須加以信任的東西,並且是在有組織的行動有迫切需要的關頭又必須加以更改的東西。」齊格蒙‧鮑曼(ZygmuntBauman,1926-)也一語中的:「真理觀念屬於權力的修辭學。」真理話語執行的是個體並不自覺的權力規則,它本身就是權力的產物,它是社會對個體實施權力的媒介,並且也是維繫權力關係的工具。在此,必須指出,文學真實理論中的真理話語作為一種權力話語,它貫穿於文學理論之中,依靠從古至今形態不同但是內在相通的政治、倫理、道德、科學、風俗等「體制」持續對文學「實施某種壓力」,按照權力規則和實用規則操縱文學表達。文學寫作主體(包括批評主體)處於真理話語的權力鏈條的不同環節上,他們或者是自覺不自覺地依據權力規則解釋、闡述「真理」,或者接受、表現「真理」,而在解釋、闡述或者接受、表現之中,權力的眼睛無處不在。
與經驗話語相連的文學學科的內在規則或者說學科共識也是一種權力形式。當然,文學學科的內在規則與真理話語背後的權力規則有很大差異:對於文學這一學科而言,尤其是對於現代的、充分強調自身的獨立自足的文學學科而言,真理話語所實施的權力控制是外在的,屬於「外部聯繫」,而文學這一學科的所謂「本質屬性」則是一切「內在規則」的集合,這是一種深刻的內部權力。就文學真實論域觀之,文學學科「內在規則」的最要緊處,乃是經驗話語。先秦的國人把「詩」與真實的、經驗性的「志」聯繫起來,古代希臘人把逼真的「摹仿」與「痛感」、「快感」之類的經驗聯繫起來,這表明,不論中西,經驗話語當然的學科合法性都在文學真實觀念的源頭暗示出來了。但是直到近世,在文學真實觀念中,經驗話語的學科合法性才真正確立,而一旦確立,它就代表了一種學科建制的結構性特徵,一種權力。在二十世紀中國,從胡適所謂「詩的經驗主義」(poeticempiricism)到成仿吾所謂「文藝是以經驗為基礎的創造」,再到袁可嘉所謂詩「是經驗的傳達」,展示了在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工具主義氛圍中,經驗話語企圖以自己的力量搭建文學學科構架、確定學科內在規則的不懈努力。不過,這種努力很快就在新的歷史語境裏中斷了,直到近二十來年才逐漸恢復並顯示出文學的學科權力,才有人明確指出「詩的第一要素就是真,不真無詩,矯飾情感者乃偽詩」。近世西人一直強調經驗話語在文學學科中的地位,在H.派克的體系中,感覺、感情、審美經驗中的「觀念或意義」、「來自各種感官」的「形象」這四類藝術經驗具有重大意義;而貫穿琳賽‧沃特斯《美學權威主義批判》一書的聲音則是「你體驗過了嗎」,他批判了自笛卡爾以來「對於體驗的空前的不信任」的現象,認為當「正確性成為藝術存在的前提條件」以後,「我們用教養來對抗體驗並且讓教養占統治地位」,於是,「我們」便「被精緻的思想觀念敗壞了」,而「我們」本不應如此,因為「我們的目標應該是體驗而不是認識」。實際上沃特斯是以經驗話語「批判」真理話語,而這種批判所昭示的恰是經驗話語的學科權力。在此,應該重申,經驗不等於經驗話語,經驗具有個體性、直接性,而經驗話語則是在經驗的概念背後糾結的學科權力結構,這個結構是在與真理話語的對峙之中形成的,它主要捍衛的是文學學科的屬性而非經驗的重要性。
在話語層面,「真理」與「經驗」從來就是對峙、競爭的關係。真理話語與經驗話語可能顯得「和諧」(此「和諧」的實質是某一時代的文學真實觀念取了中道,意味著兩種話語在對峙之中呈現出一種均勢),但更可能是一方壓倒另一方。它們載沉載浮、此消彼漲,使文學真實觀念的歷史從來就是一場真理話語同經驗話語共處一室而又不斷競逐話語權的歷史。不過,應當看到,在文學真實論域,兩種話語中的任何一種都不可能絕對壓倒另一種。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可以視為一條線段的兩個端點,在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的共同作用下,一個時代的文學真實觀念所處的確切位置永遠在真理話語和經驗話語這兩個端點之間滑動,不同時代的文學真實觀念在這條線段上處於不同的位置。
至此,「文學真實」似乎只能被這樣界定:
在文學寫作之中所傳達的經驗性真實或者真理性真實,便是所謂的「文學真實」。而關於文學真實的理論表述之中則存在著一個對立而又統一的結構,一個關於「經驗之真-真理之真」、「經驗話語-真理話語」的雙重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