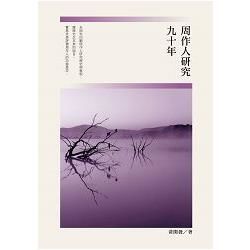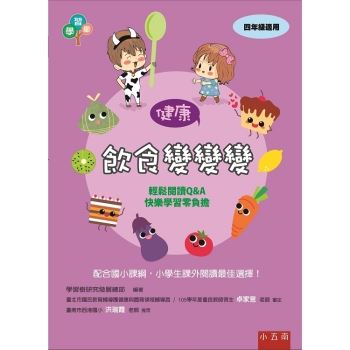周作人是毀譽參半、褒貶不一的焦點人物,身為一個對中國現代文學有著深刻影響的作家,周作人和魯迅一樣,都是新文學運動的發起者和倡導者。只是因為他曾出任汪精衛政權職務,有了「附逆」的負面名聲,使得他的歷史地位受到了影響。然而,研究者不應該以政治的標準代替一切,因人廢言,而應該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實事求是地去評價周作人的功過是非。
本書是第一本全面性回顧中國大陸周作人研究歷史與進程的專著。全書共分六章,將周作人研究以四個時期分別考察:前四章從專書、思想與人生道路研究、文學思想研究、文學創作研究等方面評述;第五、第六章則評述周作人文集的校訂出版與史料工作的建設。本書之研究,結合了歷史評述與理論探討,注重史料之考核,並對研究文獻的歷史語境與研究者個人思想及學術語境,分別做了縝密的分析。
本書特色
★ 周作人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深刻影響,不應因其「附逆文人」評價而被忽視
★ 第一本全面性記錄周作人研究歷史之專著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周作人研究九十年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412 |
中文書 |
$ 435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484 |
華文文學研究 |
$ 495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550 |
文學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周作人研究九十年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黃開發
1963年12月生,安徽霍邱人。文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1989年獲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1997年考入北師大中文系,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學位,2000年7月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2002年在韓國國民大學任客座教授。現為丹麥奧爾堡大學創新學習孔子學院中方院長。主要研究現代漢語散文、現代文學觀念和周作人等。著有《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體》(1999年)、《文學之用——從啟蒙到革命》(2004年,2006年台灣版)、《民國苦魂:周作人的精神肖像》(2013年,台灣版),主編有《中國散文通史•現代卷》(上)等。
黃開發
1963年12月生,安徽霍邱人。文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1989年獲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碩士學位,1997年考入北師大中文系,攻讀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學位,2000年7月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2002年在韓國國民大學任客座教授。現為丹麥奧爾堡大學創新學習孔子學院中方院長。主要研究現代漢語散文、現代文學觀念和周作人等。著有《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體》(1999年)、《文學之用——從啟蒙到革命》(2004年,2006年台灣版)、《民國苦魂:周作人的精神肖像》(2013年,台灣版),主編有《中國散文通史•現代卷》(上)等。
目錄
引言
第一章 周作人研究的開始期(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
第二章 周作人研究的恢復期(一九八○至一九八九)
第三章 周作人研究的成長期(一九九○至一九九九)
第四章 周作人研究的深入期(二○○○至二○○九)
第五章 周作人文集的出版(一九八一至二○一○)
第六章 周作人研究的史料建設(一九七九至二○○九)
結語 周作人研究的價值標準
周作人文集目錄(一九八二至二○一○)
研究資料要目與索引
附錄一 關於周作人的附逆及其他
附錄二 需要一種學術態度
附錄三 關於《沈啟無自述》
附錄四 沈啟無自述
後記
第一章 周作人研究的開始期(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
第二章 周作人研究的恢復期(一九八○至一九八九)
第三章 周作人研究的成長期(一九九○至一九九九)
第四章 周作人研究的深入期(二○○○至二○○九)
第五章 周作人文集的出版(一九八一至二○一○)
第六章 周作人研究的史料建設(一九七九至二○○九)
結語 周作人研究的價值標準
周作人文集目錄(一九八二至二○一○)
研究資料要目與索引
附錄一 關於周作人的附逆及其他
附錄二 需要一種學術態度
附錄三 關於《沈啟無自述》
附錄四 沈啟無自述
後記
序
引言
周作人是一個對中國現代文學有著深刻影響的作家。他和魯迅一樣,都是新文學運動的發起者和倡導者,通過各自的努力,從不同方面,為新文學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只是由於他在抗戰時期未能保持自己的節操,附逆投敵,他的名聲才黯淡下去,以至於到了被遺忘的程度。到了新時期,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周作人以其本身的重要性,又受到研究者和讀者的廣泛關注。
一九八六年,舒蕪在《中國社會科學》第四、五期上連載長篇論文《周作人概觀》,產生了廣泛影響。他指出,在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中,周作人在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方面,在新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建設方面,在思想革命的號召和實行方面,在新詩的創作和理論探索方面,在小品散文的創作方面,「成就和貢獻都是第一流的,開創性的」,「別人無可代替的」,「將永遠成為中國新文學寶庫的一個極重要的部分」。之所以要研究周作人,是因為在他身上「有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史的一半」,因為「魯迅的存在,也離不開他畢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關係」,因為「周作人的悲劇,則是和中國文化傳統、中國知識份子歷史性格有著甚深的聯繫」。對周作人研究意義的肯定其實也就是從另一角度對其自身地位的肯定。在此之前,還沒有人對他做出過如此高的評價。
那麼,舒蕪是不是劍走偏鋒、立異唱高呢?下面來當一次「文抄公」,摘抄幾個重量級人物的評價來看看。早在一九四六年,鄭振鐸就說過與舒蕪類似的話:「假如我們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什麼成就,無疑的,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鎮;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鄭振鐸是新文學的重要參加者,又是一個文學史家,說話的時候周作人已經淪為了階下囚,他的評價應該是可信的。觀點與鄭振鐸相近的還有周氏兄弟的朋友曹聚仁,他在一九五○年代出版的《文壇五十年》一書中說:「近三十年的中國文壇,周氏兄弟的確代表著兩種不同的路向。我們治史的,並沒有抹消個人主義在文藝上的成就;我們也承認周作人在文學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魯迅之下;而其對文學理解之深,還在魯迅之上。但從現在中國的社會觀點說,此時此地,有不能不抉擇魯迅那個路向。」接下來再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具影響力的倡導者之一胡適的評價,陳之藩在《在春風裏‧紀念適之先生之八》一文記述:
胡先生對周作人的偏愛,是著名的。他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說:「到現在還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他在晚年是儘量搜集周作人的東西。
我如果說:「不要打呀!蒼蠅正在搓搓手搓搓腳呢。」(周作人在《蒼蠅》一文中引用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原文為:「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黃按)他似乎就想起了苦茶庵中的老友。在他回憶的茫然的眼光裏,我看出胡先生對朋友那份癡與愛。
在胡適說話之時,到底還有幾個作家值得一讀,姑且不論;他卻單單舉出周作人,可見推重之高。另據周建人回憶,馮雪峰說過:「周作人是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後,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馮雪峰是一個左翼作家,應該不會有吹捧周作人的嫌疑。上述幾個文化名人的立場各個不同,說話的時間和場域也不同,但他們的話都明確無誤地強調了周作人作為中國現代屈指可數的幾個最重要文學家之一的存在。
在中共高層,也有深知周作人的價值的。一九八○年代中期,湖南嶽麓書社的老編輯鍾叔河想重印周作人著作集,然而在當時面臨重重障礙,無法正常獲批,於是直接給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寫信。嶽麓書社的報告最後得到了胡喬木的批准。後來黃裳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致鍾叔河的信中披露:「去年喬木來滬,一次談天,談及周作人,他自稱為『護法』,並告當年吾兄呈請重刊周書事,最後到他那裏,他不顧別人反對批准的,談來興趣盎然。」以周作人的「護法」自居,這在很多人看來可能匪夷所思。其實早在建國初期,周作人就得到過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的胡喬木的照顧和安排。在《胡喬木書信集》裏,有一九五一年致毛澤東的一封信―
主席:
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作為逆產),不當他是漢奸。他另又寫了一封給周揚,現一併送上。
我的意見是:他應當澈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以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
敬禮
喬木
二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大筆一揮,批示了兩個大字:「照辦。」這以後周作人成為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特約翻譯,從一九五五年一月開始,他每月取得稿費二百元,一度增加到每月四百元。正是由於得到了高層關照,他才得以在北京度過相對平靜的晚年生活。
再說對作為散文家的周作人的評價。郁達夫在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時,把十分之六七的篇幅讓給了魯迅(二十四篇)和周作人(五十七篇),這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上是絕無僅有的。他在《導言》中解釋道:「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為最豐富、最偉大,我平時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為最所溺愛。」到了一九九○年代,樓肇明在其所編《八十年代臺灣散文選》的序言中說:「在我看來,『五四』現代散文成就大,優秀作家人數眾多,但真正以完備的審美體系在審美路標意義上影響了同時代及後世作家的,當推魯迅和周作人,而其他作家像郁達夫、朱自清、冰心、許地山、徐志摩等有成就、有風格的傑出散文作家,則是環繞在這兩座高峰之間大小不等的山峰。」著名學者陳平原說:「六十年後,重新引述此段文字,幾乎不必作任何改動。也曾出現不少顯赫一時的散文家,但周氏兄弟始終是兩面不倒的大旗。近百年中國文壇上,小說、詩歌群雄角逐,唯有散文雙峰並峙―周氏兄弟的地位無可爭議。」
類似的重要評語還有不少,不遑遍舉。既然周作人的歷史地位如此之高,那就不應該以政治的標準代替一切,因人廢言,而應該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實事求是地去評價他的功過是非。這其中理所當然地包括對周作人研究學術史的回顧和總結。認真求實地回顧過去,總結經驗和教訓,是為了繼承前人已經取得的成果,並為今天的研究工作提供參照,更好地開拓未來。
一九八○年代以來,每一個現代文學大家的研究都有一種或多種研究評述的專著,而周作人研究還沒有,這與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稱的;而周作人研究的複雜性又遠遠大於一般的文學大家,更需要對研究的本身予以專門、深入的總結和探討。溫儒敏等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中,把「開展周作人研究史的研究」視為周作人研究可能的新增長點之一,並指出:「周作人是毀譽參半、褒貶不一的焦點人物,他的活動貫穿了二十世紀的三分之二時段,回顧周氏的興衰沉浮歷史,可以窺探二十世紀中國的諸多思想命題、文化奧祕。」同樣,一部周作人研究學術史不僅折射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同樣也從特定的方面反映出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的側影。
本書第一次全面回顧中國大陸周作人研究的歷史進程。大致按時間次序把周作人研究分為四個時期加以考察,前四章均分別從專書(專著、論文集等)、思想與人生道路研究、文學思想研究、文學創作研究等方面評述,第五、第六兩章評述周作人文集的校訂出版與史料工作的建設,則根據對象的特點單獨成章。周作人研究的第一篇專門文章是趙景深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周作人的詩》。不過,關於周作人的零散的評論可以上溯到一九一九年傅斯年、錢玄同、羅家倫、胡適等的論文,他們從自己的親身感受出發,高度評價了周作人在新文學運動之初的赫赫功績。如果從一九一九年開始算起,中國大陸周作人研究已經走過了九十多年的風風雨雨。這九十多年大約可以分為四個時期。一九四九年以前為周作人研究的開始期,有關的論文絕大多數是一般性的評論,真正達到學術研究層次的甚少。一九三○年代後期,研究工作因為周作人的附逆投敵而出現了轉折。一九四九年以後又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停滯,周作人在文學史的敘述中基本處於缺席狀態。一直到一九八○年,受益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周作人研究重新起步。一九八○年代的周作人研究成績斐然,然而研究者受到一些「左」的思想觀念的掣肘,於對象還或多或少地有點「隔」,這是周作人研究的恢復期。一九九○年代是周作人研究的成長期,研究者努力地走近周作人,走到他獨特的藝術與精神世界中去;在此基礎上,開始試圖建立他與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思想史以及東西方文化的廣泛聯繫。進入新世紀以後,周作人研究到了深入期。不少重要的方面都有了專攻,而不是泛泛而論,如周作人的「人學」思想、女性思想、文學思想、文學翻譯等。迄今為止,已出版了周作人研究著作四十餘部,這是研究成就的集中體現。隨著研究工作的深入,有幾個重要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周作人是不是一個思想家的問題、對其後期「抄書體」散文的評價問題、周作人與中國文學傳統問題,以及評價他的價值標準問題。因此,本書以這幾個主要問題為「劇情主線」,並對此進行探討。
本書附錄了三篇文章,其中有兩篇是我與別人關於周作人的論爭文字,還有一篇由我整理的沈啟無自述。沈啟無被稱作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後來又被逐出師門。他的自述包括了不少關於周作人和淪陷區文壇的珍貴資料。
在研究方法上,本書力圖做到:歷史評述與理論探討相結合;以辯證求實的態度,堅持政治的標準與思想文化的標準相統一,既充分肯定研究對象的貢獻和歷史地位,又對其附逆行為和消極的思想進行分析、批判;注重考核史料,考察和分析研究文獻的歷史語境和研究者個人思想、學術語境。
周作人是一個對中國現代文學有著深刻影響的作家。他和魯迅一樣,都是新文學運動的發起者和倡導者,通過各自的努力,從不同方面,為新文學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只是由於他在抗戰時期未能保持自己的節操,附逆投敵,他的名聲才黯淡下去,以至於到了被遺忘的程度。到了新時期,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周作人以其本身的重要性,又受到研究者和讀者的廣泛關注。
一九八六年,舒蕪在《中國社會科學》第四、五期上連載長篇論文《周作人概觀》,產生了廣泛影響。他指出,在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中,周作人在外國文學的翻譯介紹方面,在新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建設方面,在思想革命的號召和實行方面,在新詩的創作和理論探索方面,在小品散文的創作方面,「成就和貢獻都是第一流的,開創性的」,「別人無可代替的」,「將永遠成為中國新文學寶庫的一個極重要的部分」。之所以要研究周作人,是因為在他身上「有中國新文學史和新文化史的一半」,因為「魯迅的存在,也離不開他畢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關係」,因為「周作人的悲劇,則是和中國文化傳統、中國知識份子歷史性格有著甚深的聯繫」。對周作人研究意義的肯定其實也就是從另一角度對其自身地位的肯定。在此之前,還沒有人對他做出過如此高的評價。
那麼,舒蕪是不是劍走偏鋒、立異唱高呢?下面來當一次「文抄公」,摘抄幾個重量級人物的評價來看看。早在一九四六年,鄭振鐸就說過與舒蕪類似的話:「假如我們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什麼成就,無疑的,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鎮;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鄭振鐸是新文學的重要參加者,又是一個文學史家,說話的時候周作人已經淪為了階下囚,他的評價應該是可信的。觀點與鄭振鐸相近的還有周氏兄弟的朋友曹聚仁,他在一九五○年代出版的《文壇五十年》一書中說:「近三十年的中國文壇,周氏兄弟的確代表著兩種不同的路向。我們治史的,並沒有抹消個人主義在文藝上的成就;我們也承認周作人在文學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魯迅之下;而其對文學理解之深,還在魯迅之上。但從現在中國的社會觀點說,此時此地,有不能不抉擇魯迅那個路向。」接下來再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具影響力的倡導者之一胡適的評價,陳之藩在《在春風裏‧紀念適之先生之八》一文記述:
胡先生對周作人的偏愛,是著名的。他曾不止一次的跟我說:「到現在還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他在晚年是儘量搜集周作人的東西。
我如果說:「不要打呀!蒼蠅正在搓搓手搓搓腳呢。」(周作人在《蒼蠅》一文中引用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原文為:「不要打哪,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腳呢。―黃按)他似乎就想起了苦茶庵中的老友。在他回憶的茫然的眼光裏,我看出胡先生對朋友那份癡與愛。
在胡適說話之時,到底還有幾個作家值得一讀,姑且不論;他卻單單舉出周作人,可見推重之高。另據周建人回憶,馮雪峰說過:「周作人是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魯迅去世後,他的學識文章,沒有人能相比。」馮雪峰是一個左翼作家,應該不會有吹捧周作人的嫌疑。上述幾個文化名人的立場各個不同,說話的時間和場域也不同,但他們的話都明確無誤地強調了周作人作為中國現代屈指可數的幾個最重要文學家之一的存在。
在中共高層,也有深知周作人的價值的。一九八○年代中期,湖南嶽麓書社的老編輯鍾叔河想重印周作人著作集,然而在當時面臨重重障礙,無法正常獲批,於是直接給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寫信。嶽麓書社的報告最後得到了胡喬木的批准。後來黃裳在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致鍾叔河的信中披露:「去年喬木來滬,一次談天,談及周作人,他自稱為『護法』,並告當年吾兄呈請重刊周書事,最後到他那裏,他不顧別人反對批准的,談來興趣盎然。」以周作人的「護法」自居,這在很多人看來可能匪夷所思。其實早在建國初期,周作人就得到過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的胡喬木的照顧和安排。在《胡喬木書信集》裏,有一九五一年致毛澤東的一封信―
主席:
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作為逆產),不當他是漢奸。他另又寫了一封給周揚,現一併送上。
我的意見是:他應當澈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以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
敬禮
喬木
二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大筆一揮,批示了兩個大字:「照辦。」這以後周作人成為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特約翻譯,從一九五五年一月開始,他每月取得稿費二百元,一度增加到每月四百元。正是由於得到了高層關照,他才得以在北京度過相對平靜的晚年生活。
再說對作為散文家的周作人的評價。郁達夫在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時,把十分之六七的篇幅讓給了魯迅(二十四篇)和周作人(五十七篇),這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上是絕無僅有的。他在《導言》中解釋道:「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為最豐富、最偉大,我平時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為最所溺愛。」到了一九九○年代,樓肇明在其所編《八十年代臺灣散文選》的序言中說:「在我看來,『五四』現代散文成就大,優秀作家人數眾多,但真正以完備的審美體系在審美路標意義上影響了同時代及後世作家的,當推魯迅和周作人,而其他作家像郁達夫、朱自清、冰心、許地山、徐志摩等有成就、有風格的傑出散文作家,則是環繞在這兩座高峰之間大小不等的山峰。」著名學者陳平原說:「六十年後,重新引述此段文字,幾乎不必作任何改動。也曾出現不少顯赫一時的散文家,但周氏兄弟始終是兩面不倒的大旗。近百年中國文壇上,小說、詩歌群雄角逐,唯有散文雙峰並峙―周氏兄弟的地位無可爭議。」
類似的重要評語還有不少,不遑遍舉。既然周作人的歷史地位如此之高,那就不應該以政治的標準代替一切,因人廢言,而應該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實事求是地去評價他的功過是非。這其中理所當然地包括對周作人研究學術史的回顧和總結。認真求實地回顧過去,總結經驗和教訓,是為了繼承前人已經取得的成果,並為今天的研究工作提供參照,更好地開拓未來。
一九八○年代以來,每一個現代文學大家的研究都有一種或多種研究評述的專著,而周作人研究還沒有,這與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稱的;而周作人研究的複雜性又遠遠大於一般的文學大家,更需要對研究的本身予以專門、深入的總結和探討。溫儒敏等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中,把「開展周作人研究史的研究」視為周作人研究可能的新增長點之一,並指出:「周作人是毀譽參半、褒貶不一的焦點人物,他的活動貫穿了二十世紀的三分之二時段,回顧周氏的興衰沉浮歷史,可以窺探二十世紀中國的諸多思想命題、文化奧祕。」同樣,一部周作人研究學術史不僅折射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同樣也從特定的方面反映出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的側影。
本書第一次全面回顧中國大陸周作人研究的歷史進程。大致按時間次序把周作人研究分為四個時期加以考察,前四章均分別從專書(專著、論文集等)、思想與人生道路研究、文學思想研究、文學創作研究等方面評述,第五、第六兩章評述周作人文集的校訂出版與史料工作的建設,則根據對象的特點單獨成章。周作人研究的第一篇專門文章是趙景深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周作人的詩》。不過,關於周作人的零散的評論可以上溯到一九一九年傅斯年、錢玄同、羅家倫、胡適等的論文,他們從自己的親身感受出發,高度評價了周作人在新文學運動之初的赫赫功績。如果從一九一九年開始算起,中國大陸周作人研究已經走過了九十多年的風風雨雨。這九十多年大約可以分為四個時期。一九四九年以前為周作人研究的開始期,有關的論文絕大多數是一般性的評論,真正達到學術研究層次的甚少。一九三○年代後期,研究工作因為周作人的附逆投敵而出現了轉折。一九四九年以後又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停滯,周作人在文學史的敘述中基本處於缺席狀態。一直到一九八○年,受益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思想解放運動的興起,周作人研究重新起步。一九八○年代的周作人研究成績斐然,然而研究者受到一些「左」的思想觀念的掣肘,於對象還或多或少地有點「隔」,這是周作人研究的恢復期。一九九○年代是周作人研究的成長期,研究者努力地走近周作人,走到他獨特的藝術與精神世界中去;在此基礎上,開始試圖建立他與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現代思想史以及東西方文化的廣泛聯繫。進入新世紀以後,周作人研究到了深入期。不少重要的方面都有了專攻,而不是泛泛而論,如周作人的「人學」思想、女性思想、文學思想、文學翻譯等。迄今為止,已出版了周作人研究著作四十餘部,這是研究成就的集中體現。隨著研究工作的深入,有幾個重要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周作人是不是一個思想家的問題、對其後期「抄書體」散文的評價問題、周作人與中國文學傳統問題,以及評價他的價值標準問題。因此,本書以這幾個主要問題為「劇情主線」,並對此進行探討。
本書附錄了三篇文章,其中有兩篇是我與別人關於周作人的論爭文字,還有一篇由我整理的沈啟無自述。沈啟無被稱作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後來又被逐出師門。他的自述包括了不少關於周作人和淪陷區文壇的珍貴資料。
在研究方法上,本書力圖做到:歷史評述與理論探討相結合;以辯證求實的態度,堅持政治的標準與思想文化的標準相統一,既充分肯定研究對象的貢獻和歷史地位,又對其附逆行為和消極的思想進行分析、批判;注重考核史料,考察和分析研究文獻的歷史語境和研究者個人思想、學術語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