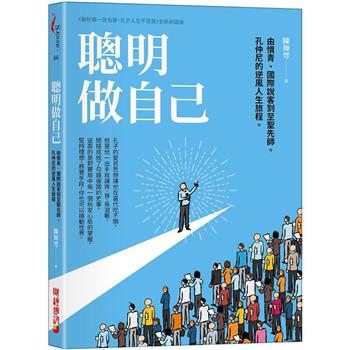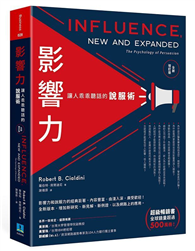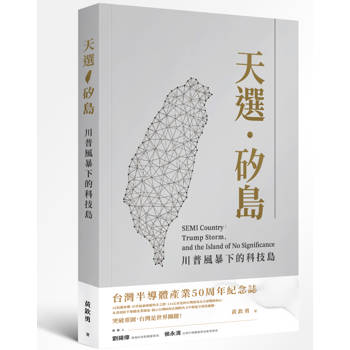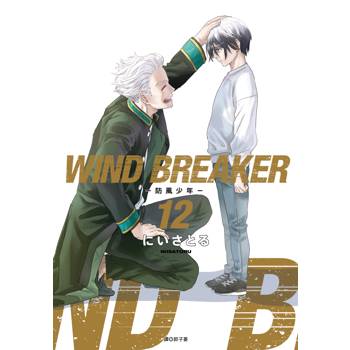臺灣自1895年依「馬關條約」割離清國,至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段期間,屬於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每當遇上敏感的「認同問題」時,研究者自身所謂的「中國/臺灣民族意識」,往往成為詮釋日治時期人物的民族認同的標尺。有趣的是,臺灣歷史中有些被稱為「協力者」的人物,經由不同民族史觀的詮釋,竟有著全然不同的面貌。早期中國民族主義強調「反帝、反封建」,與臺灣相關的研究也必須依循此準則為人物定位。臺灣意識興起後,研究者或站在相反的角度,一定程度地肯定日本統治者的功績;或是站在「反抗史觀」評價當時的人物與事件。站在「反抗史觀」看待「協力者」,則可能得出兩種不同的評價:一是一味地指責「協力者」是統治當局的棋子,一則是尋求「協力者」有功於臺灣的蛛絲馬跡而將之詮釋為「協力者」的反抗意識。
然而,某人是否具有某意識,是我們透過對他的生命歷程、所處的時代、他的著述、行動、甚至是交友網絡等等的分析,得到的結論。再透過結論,檢視他生命歷程的每個細節。也就是說,這是一個辯證的過程,而非絕對的標準。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二十世紀初,由於新思潮的激盪,臺灣人開始追問:「我是誰?」受日本統治期間,臺灣人開始認識「異與己」,並尋求認同。
筆者認為,這個牽涉殖民結構的問題,必須從日本與臺灣各自的社會脈絡談起。日本展開海外拓殖行動的背景是什麼?當臺灣人遇上新的統治政權,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如何面對?作為亞洲第一個殖民帝國,日本如何進行對臺灣的同化策略?臺灣與日本同屬儒學文化圈,殖民統治者如何利用文化作為溝通的橋樑?臺灣人又如何面對日本統治下「文化」與「文明」的變革?透過史料的耙梳,將「協力者」的身分與行動,放在殖民歷史的脈動中反覆思考;經由反覆的探問,讓「認同」的矛盾在「異與己」的辯證下更加明晰。
首先,我們從日本帝國興起乃至於對亞洲拓殖的需求談起。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形成國家意識的前提是「對內的統一」與「對外的獨立」。眾所周知,受西方列強的壓迫,日本為強調國家主體性,因而在抵抗西方侵略的過程中形成日本民族主義。此即「對外的獨立」。接著,為了發展國家實力,日本開始積極地向西方學習。社會自由與平等化,以及富國強兵的觀念,成為日本施政的焦點。同時,為了達到「內部的統一」,日本採取鞏固中央集權體制、加強天皇權威的「天皇制絕對主義」。支撐天皇制的兩大聖典即為「帝國憲法」和「教育敕語」。「帝國憲法」強調「臣民」而不用「國民」,是明治年間建立人民與君主的臣屬關係的必要論述;而「教育敕語」則是融合了儒學與西方思想,使臣民透過「道德實踐」為天皇克忠盡孝。
西風東漸,日本的民族危機意識促成民族主義運動,繼而轉向亞洲拓展其民族勢力。這使得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近代帝國,也是歷史上唯一非西方的殖民勢力。相較於西方「一手拿槍,一手拿著聖經」的殖民擴張,日本帝國的東亞策略可說是「一手拿槍,一手拿著教育敕語」。面對原始居民對土地、資產的捍衛而興起的反抗,西方利用宗教的力量「教化」「野蠻」的原始住民,也就是透過宗教的道德觀與近代文明的結合,賦予殖民統治政權絕對的正當性。而新興的日本帝國,在「教育敕語」中結合儒學與西方思想,鞏固天皇制之下的臣民道德準則,成為建構統治正當性的重要依據。臺灣是日本在亞洲的第一個殖民地。在臺灣,建立在「教育敕語」基礎之上的殖民策略可分為兩大方向:其一,透過同屬儒學文化圈的文化資產,籠絡臺灣士紳;另一方面,透過近代教育的拓展,教化新附之民。經由此二途徑,使「新民」歸順,繼之產生殖民地可用的人力資源。
「教育敕語」頒布於明治23年(1890),是日本近代教育的基準。由代表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1841~1909)路線的井上毅(1843~1895)起草,經「儒教」主義者元田永孚(1818~1891)修正,再採納內閣閣員及天皇的意向編製而成。即便存在著日本內地頒行的「教育敕語」不適用於帝國新領地的爭議,自近代教育在臺灣開始推行到1945年日本戰敗,「教育敕語」對日治時期的臺灣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觀察「教育敕語」在臺灣流布的時機,或許可窺見「教育敕語」在形式上所具有的意義。明治29年(1896)第一批學習日語的臺灣人在芝山岩舉行畢業典禮。典禮上,臺灣人柯秋潔被指派捧讀「漢譯」的「教育敕語」。翌年,訓令第15號規定,今後官公私立各學校,除了捧讀「教育敕語」外,還要加以漢文解釋,以貫徹聖旨。大正元年(1912)公學校規則改正,規定在祝祭日舉行儀式,並且在儀式中合唱「君之代」,對天皇、皇后的照片行最敬禮並由校長捧讀「教育敕語」。大正8年(1919),在臺灣第一次頒布的「臺灣教育令」,更明確規定「教育基於教育敕語之旨趣,以育成忠良國民為目的」(第二條),要求臺灣人符合「教育敕語」的基本精神。所謂「教育敕語」的基本精神,融合了儒學「克忠克孝、博愛及眾」以及近代文明中「重國憲、遵國法」的精神。除了透過儀式加強「教育敕語」神聖不可違的形象,也經由課程加強學童對「教育敕語」的理解。大正8年(1919)臺灣教育令公布後隨之修正的「公學校漢文讀本」卷六之最後一課,即為「教育敕語」。此外,亦有論者指出,許多曾受日治教育的長者,現在仍可一字不漏地背誦「教育敕語」。我們由此看出,形式上,「教育敕語」與日治時期臺灣近代教育確實有著緊密的扣連。
除了形式上的關聯,「教育敕語」的儒學思想,更是值得注意的關鍵。日本與臺灣同屬於「儒學文化圈」。先從日本的角度來談。日本在近代國家意識興起後,國內的「國學」及西方「洋學」取代「儒學」(或作「漢學」)原有的地位,「儒學」經歷了一番改革,其意義因而產生了質變。質變後的「漢學」與「教育敕語」中用以確立國體的「儒教」思想,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初的策略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成為與臺灣傳統文教環境嫁接的橋梁。另從臺灣的角度來看。改隸之前臺灣屬於清國統治。晚清時期,國內有志之士對於積弱不振的國勢提出許多諫言,科舉取士制度的存廢備受爭議,傳統的教育方式面臨考驗。臺灣在這時候被割讓給日本,山河易主。面對新的統治政權,臺灣士紳原以為只能將過去所學束之高閣,對傳統文學在臺灣的存廢感到絕望。正對著棄地遺民的景況感慨萬千,新政府的文化策略卻讓臺灣士紳看到傳統文學存續的希望。包括形式上有漢文「教育敕語」的頒布,以及利用「儒學文化圈」的共通性對臺灣文士的籠絡。臺灣士紳甚至期待傳統文學可能與日本國內一樣經歷漢學的改革,使其成為更具有實用性質的經世濟民之學。綜上所述,日本明治維新後內涵變革的漢學與「教育敕語」中隱含的「儒教」思想,正因為這樣的背景才與臺灣傳統文教環境產生嫁接的可能。
臺灣改隸日本後,官方為取信於前清士紳,在明治33年(1900)3月15日於總督府舉行「揚文會」,邀請全臺具有科舉功名的士紳參與,並鼓勵士紳對臺灣文教方針提出意見。會議期間,除了討論日本在臺的文治策略,官紳詩文唱和亦是活動內容。更重要的是,士紳們在會後獲邀參觀日本近代教育機構。我們可藉由前清碩儒吳德功於揚文會後撰寫的《觀光日記》中對近代文明的讚嘆、對新政權的肯定,看出此次揚文會對於漢學嫁接以及近代教育推廣的成功。緣此,筆者認為,以具有漢學素養也接受近代教育的臺灣士紳為研究對象,是釐清或突顯認同矛盾的重要關鍵。他們是如何看待過去所學?對漢學的未來有什麼期待?而在形塑國民意識的近代學校中,他們的學習是否影響其對漢學的看法?當臺灣傳統漢學遇上日本漢學,產生什麼火花?臺灣漢學脈絡如何延續、變異或產生新的內涵?更重要的是,解決以上問題後,我們是否能夠為認同議題提供不同的思考面向?並以辯證「具有漢學素養及接受近代教育的臺灣士紳對認同之矛盾」為基礎,嘗試探問:我們是否能夠回到文學發展脈絡,觀察日治時期傳統漢學活動存在的意義、形式及其價值?
經歷過清代儒學、書房等教育,也有機會在日治後接受近代教育的士紳,大約生在同治10年(1871)到光緒16年(1890)間。日治時期雖然有書房存在,但因官方對書房教育的控管,所學已經和前清時期大不相同。生於1871到1890年間的臺灣士紳又可依考取功名與否再進行更細緻的分類,此外,這段時期出生者,並非人人皆在改隸後進入近代教育體系就讀。比方說,生於同治10年(1871)的謝汝銓,光緒18年(1892)年入泮,日治後選擇進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國語部學習「國語」;而生於光緒2年(1876)的連橫,擁有紮實的漢學基礎,但在前清時期並未考取功名,日治後也未進入近代教育體系學習。過去有關於這類具有漢學素養又有近代教育經驗的人物研究,如前所述,無論人物本身的認同傾向,討論面向仍多以反抗意識的「有無」、反抗的「程度」為焦點。而筆者則希望能透過具有漢學及近代教育經驗的人物,觀察他們對近代教育乃至於同化的態度,分析人物對日治時期漢學存續的立場、理想及實踐。站在文學發展的立場觀察文學內涵的改變。
為釐清「同化政策」、「近代教育」以及「漢學」三者之間包含的民族問題,史料帶領我找到一位未曾被研究者重視的臺灣籍教師―劉克明。劉克明,號篁村,新竹人。生於清光緒10年(1884)。10幼時,其父劉廷璧(1857~1892)應新竹宿儒鄭如蘭(1835~1911)之聘,在北郭園授課。劉克明亦寄學於北郭園,從竹塹文士張鏡濤(1850~1901)、曾逢辰(1853~1928)學習。劉父逝世後,劉克明隨張鏡濤寄學於潛園及北郭園。改隸之際,劉克明12歲。明治30年(1897)10月,進入新竹國語傳習所就學。明治33年(1900)入臺北師範學校就讀,該校二年後併入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明治36年(1903)劉克明以第一名畢業後,歷任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囑託(1903-1907)、總督府國語學校助教授(1908-1921)、臺北師範學校教諭(1922-1926)、臺北第一師範學校兼第二師範學校教諭(1927-1931)、臺北第一師範學校囑託(1932-1939)及臺北第三高女囑託(1932-1936)、總督府評譯員翻譯官(1928-1931)、文教局編修課教材書調查委員(1932-1933)等職。除了擔任教員,劉克明與同窗友人共同商議,成立了「本島人國語學校同窗會」。劉氏並於大正元年(1912)創立時擔任總幹事至戰後,此團體為臺灣社會中相當具有影響力的「本島人群體」。
明治41年(1908),劉克明開始擔任臺灣教育會之機關刊物《臺灣教育》漢文報編輯,與教師職務相輔相成。期間除了擔任會況報告的通訊記者,也曾經在明治41年(1908)於該報發表臺灣俚言與修身科結合的相關教案。大正元年(1912)明治天皇駕崩,劉克明譯註〈明治天皇聖藻〉系列文章刊於漢文報之首,大正2年(1913)專欄介紹「祝祭日及國民記念日」,更從大正6年(1917)開始發表漢文教案。18由於漢、日語能力均佳,劉克明亦曾編修數種臺灣語教材,方便日、臺人使用,如《國語對譯臺語大成》(1916)、《廣東語集成》(1919)、《教科摘要―臺灣語速修》(1925)、《實業教科―臺灣語及書翰文》(1926)等等。上述教材皆長期被總督府編定為「教諭試驗檢定受驗者參考書」。從以上資歷可以看出,劉克明具有一定程度的漢學涵養,對於日文運用也相當嫻熟,甚至可說是日治時期頗受當局重用的臺灣籍教師。身為日本殖民教育系統中的一員,劉克明不遺餘力地投入工作,使得他在大正10年(1921)獲臺灣教育會表彰,大正14年(1925)獲得臺灣總督府頒授勳章。
教師的身分之外,劉克明更是北臺文壇重要成員。曾參與詠霓吟社(1903-1906)、瀛東小社(1910-1911)的成立,亦是瀛社大正7年(1918)到大正15年(1926)間的總幹事。除此之外,劉克明曾獲邀評選其他詩文社團的詩作,並長期擔任《臺灣教育》及《專賣通信》漢詩欄的編輯。劉克明在世時,雖未出版詩文集,但他八十大壽時,哲嗣為其祝壽,邀請劉克明親自將所著數十卷詩稿中選錄珠璣,預計編成《寄園詩葉》。然未及出版,劉克明仙逝。該文稿於1968年編印,2009年由龍文書局復刻出版。26除了語言教材以及後來出版的詩文集,劉克明還曾出版關於臺灣史地的雜著《臺灣今古談》(1930),以及應中和庄長江讚慶之邀撰寫的《中和庄誌》(1932)。《臺灣今古談》單元式的記錄臺灣改隸前後的轉變,特別著重在文教設施。本書不但反映劉克明對臺灣漢學維繫的態度,更是臺灣文學史上的重要史料。
瀏覽劉克明畢生的著作,將會發現「我等新民」、「皇恩」、「同化」、「本島」、「一線斯文」、「翰村補筆」、「買山結廬」是他的著作中頻繁出現的關鍵字。然而,這幾個關鍵字彼此是否有思想內涵的衝突?更具體的說,具有漢學素養,並接受近代教育,而後又成為殖民教育體系一員的劉克明,究竟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教育界,站有什麼樣的位置?他在教育界的位置,如何影響他對漢學存續的態度?這與他高倡同化的立場是否衝突?漢學存續的問題,與他的詩社參與有什麼關聯?以上皆是筆者企圖在本論文解決的問題。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島民、新民與國民:日治臺籍教師劉克明(1884~1967)的同化之道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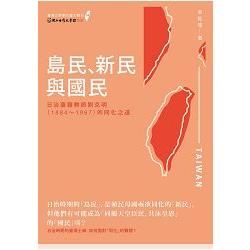 |
島民、新民與國民: 日治臺籍教師劉克明 (1884~1967) 的同化之道 作者:吳鈺瑾 出版社: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5-01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2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25 |
中文書 |
$ 326 |
台灣研究 |
$ 333 |
社會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島民、新民與國民:日治臺籍教師劉克明(1884~1967)的同化之道
日治時期的「島民」,是殖民母國亟欲同化的「新民」,
但他們有可能成為「同屬天皇臣民、共沐皇恩」的「國民」嗎?
日治時期的臺灣士紳,如何面對「同化」的難題?
★當歷史成為過去,觀看的角度更為重要!
破除民族意識的藩籬,重新觀看、解讀日治時期台灣教育的歷史
日治時期的臺語教育,竟是為了消滅臺灣人的民族意識、加速殖民地對日本的認同?
協助日本統治者的臺灣士紳,究竟是當權者的棋子,還是真正為臺灣人民謀福利?
本書以日治時期臺灣籍教師劉克明(1884~1967)為研究對象,關注具有漢學素養也接受近代教育的臺灣士紳之認同矛盾。
具有漢學素養,並接受近代教育,而後又成為殖民教育體系一員的劉克明,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教育界,佔有什麼樣的位置?他如何看待過去所學?劉克明在教育界的位置,如何影響他對漢學存續的態度?這與他提倡同化於日本的立場是否衝突?漢學存續的問題,與他參與詩社活動有什麼關聯?
根據研究,劉克明將「與『母國人』同化」之途徑視為振興漢學之道。然而,「文化上『種族』的融合」就像潘洛斯階梯(Penrose stairs)──劉克明以為每一步的實踐能夠更接近成為「臣民」的條件,但實際上卻是被排拒在日本國體「血統的」論述之外──島民,並無法在從「中原」到「橿原」的論述中成為真正的帝國臣民。本書拋卻「漢民族主義」乃至於「本質性的反抗意識」,根據劉克明的生命經歷、著作以及詩社參與,透過詳盡的史料分析,從交流與變異的角度貼近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人。
作者簡介:
吳鈺瑾
新北市新店人,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研究方向以臺灣古典文學為主,曾發表〈清代噶瑪蘭設廳建城的官方敘述:以古典詩文為分析對象〉。現旅居美國。
章節試閱
臺灣自1895年依「馬關條約」割離清國,至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段期間,屬於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每當遇上敏感的「認同問題」時,研究者自身所謂的「中國/臺灣民族意識」,往往成為詮釋日治時期人物的民族認同的標尺。有趣的是,臺灣歷史中有些被稱為「協力者」的人物,經由不同民族史觀的詮釋,竟有著全然不同的面貌。早期中國民族主義強調「反帝、反封建」,與臺灣相關的研究也必須依循此準則為人物定位。臺灣意識興起後,研究者或站在相反的角度,一定程度地肯定日本統治者的功績;或是站在「反抗史觀」評價當時的人物與事件。站在「...
»看全部
目錄
館長序/翁誌聰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概念釋義
第四節 章節架構
第二章 劉克明生平概述與詩作分析
第一節 生平概述
第二節 詩作分析
第三章 「我等新民」的同化之路:臺籍教師的同化論述與實踐
第一節 臺灣語權威教授
第二節 理念與實踐之道:《臺灣教育》發表之分析
第三節 從「新民」到「臣民」
第四章 《臺灣今古談》中的「臺灣」
第一節 關於《臺灣今古談》
第二節 談臺灣古今‧話本島故事
第五章 「同文」的美麗錯誤:從劉克明看「漢學」與「同化」的關聯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概念釋義
第四節 章節架構
第二章 劉克明生平概述與詩作分析
第一節 生平概述
第二節 詩作分析
第三章 「我等新民」的同化之路:臺籍教師的同化論述與實踐
第一節 臺灣語權威教授
第二節 理念與實踐之道:《臺灣教育》發表之分析
第三節 從「新民」到「臣民」
第四章 《臺灣今古談》中的「臺灣」
第一節 關於《臺灣今古談》
第二節 談臺灣古今‧話本島故事
第五章 「同文」的美麗錯誤:從劉克明看「漢學」與「同化」的關聯
...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吳鈺瑾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5-05-06 ISBN/ISSN:978986326336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10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台灣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