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realism一詞,在華文語境中有「寫實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兩種譯/義/異況。其中,「現實主義」自1932年馬克思主義者的中譯定調後,幾乎成為「左翼限定」用法;因此,本書以「寫實主義」名之,同時囊括殖民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左、右翼立場的想像。
隨著社會的變遷和理論思潮的譯介,臺灣的「寫實主義」在日治時期有張我軍、黃石輝、楊逵等的建構,以及賴和、翁鬧、張文環等的小說實踐;戰後則有張道藩、夏濟安、夏志清、顏元叔、陳映真、葉石濤、林耀德等的批評建制,與王藍、白先勇、王禎和、黃春明、宋澤萊、黃凡、李喬、朱天文等的小說展演。寫實意識流變,小說變形化身,千姿百態,終不離對於「現實」的回應。
本書特色
*本書為榮獲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學位論文出版徵選」補助之優秀論文
名人推薦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向陽 專序推薦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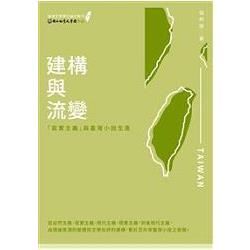 |
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 出版社: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6-03-3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448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55 |
小說/文學 |
$ 398 |
文學 |
$ 466 |
中文書 |
$ 530 |
華文文學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張俐璇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博士,現職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小說與散文創作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時報文學獎等獎項。研究興趣為戰後臺灣小說、電影與文學、數位人文研究。兩度執行國藝會計畫:「臺灣文學理論批評建制調查研究」(2008)以及「新世紀臺灣長篇小說評論」(2015)。著有專書《兩大報文學獎與台灣文學生態之形構》(2010)。
張俐璇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博士,現職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小說與散文創作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時報文學獎等獎項。研究興趣為戰後臺灣小說、電影與文學、數位人文研究。兩度執行國藝會計畫:「臺灣文學理論批評建制調查研究」(2008)以及「新世紀臺灣長篇小說評論」(2015)。著有專書《兩大報文學獎與台灣文學生態之形構》(2010)。
目錄
館長序/陳益源
一個具有新視角的文學史論的可能:讀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向陽
本書各章摘要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一、從兩項文學獎評審談起
二、「寫實主義」的建構性
三、戰後臺灣小說的「寫實」意/異識
第二節 先行研究與文獻回顧
一、Realism在西方
二、現實主義在中國
三、寫實主義在臺灣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第四節 章節架構與內容安排
一、第一章 序論
二、第二章 殖民主義與リアリズム(Realism)
三、第三章 現/寫實主義及其想像
四、第四章 現代主義及其寫實轉向
五、第五章 現實主義及其不滿
六、第六章 結論
第二章 殖民主義與リアリズム(Realism)
第一節 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
一、反自然主義的大正文壇
二、以自然主義改革舊小說的臺灣
三、大正思潮與臺灣小說
第二節 昭和前期寫實觀念與現代小說語言
一、五四寫實觀念與「殖民地漢文化」的中國白話文小說
二、鄉土寫實意識與「帝國漢文化」的臺灣話文小說
三、「真實的寫實主義」與「振假名註記」的日文小說
第三節 決戰時期的文體與國體─日本思想史的嫁接
一、浪漫寫實主義:回歸「日本美好傳統」
二、觀念現實主義:超克西方的大東亞意識形態
三、糞現實主義:不「同一」於日本的「差異」臺灣
第三章 現/寫實主義及其想像
第一節 現實主義與寫實主義
一、進步左翼與現實主義
二、民族右翼與三民主義
第二節 戰後初期現實主義在臺灣的角力
一、三民主義現實主義的匯入
二、族群與階級:小說書寫的分化
三、新現實主義文學論爭:國統區與解放區的歧義延長
第三節 三民主義寫實主義及其長篇小說生產
一、反共成長小說:第一人稱與二元敘事
二、戰爭歷史書寫:去差異化的民族想像
三、 健康寫實小說:民生建設與家在臺北
第四章 現代主義及其寫實轉向
第一節 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
第二節 「美援」與「中華」文化主導下「寫實」觀念之移轉
一、自由主義文藝:美援年代的黨國威權侍從
二、批評建制:從《文學雜誌》到《中外文學》
第三節 理論翻譯與內向性寫實小說生產
一、小說理論與心理學的接引
二、精神分析與冷戰意識形態
三、存在主義與個體反思
第四節 寫實的「美」「援」:現代小說的美學挪用
一、化用中外經典的「寫實」策略
二、音響與字質:新批評與短篇小說生產
第五章 現實主義及其不滿
第一節 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
一、日據時代臺灣小說的重返
二、鄉土小說:從露骨寫實主義到反諷現實主義
三、 美學判準與意識形態
第二節 鄉關何處:植有玫瑰與麥的土地
一、土地與社會:兩種論述基點與小說生產
二、政治小說的「現實」分歧
第三節 後現代及其超越
一、後現代小說
二、新鄉土小說
三、「新寫實主義」與絃歌不輟的土地之歌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被建構的「寫實主義」
第二節 下一輪小說研究的備忘錄
參考資料
Becoming-Realism: The Production of Taiwan Fiction
RESULTS AND DISCUSSION
2014年博士論文謝誌
一個具有新視角的文學史論的可能:讀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向陽
本書各章摘要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一、從兩項文學獎評審談起
二、「寫實主義」的建構性
三、戰後臺灣小說的「寫實」意/異識
第二節 先行研究與文獻回顧
一、Realism在西方
二、現實主義在中國
三、寫實主義在臺灣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第四節 章節架構與內容安排
一、第一章 序論
二、第二章 殖民主義與リアリズム(Realism)
三、第三章 現/寫實主義及其想像
四、第四章 現代主義及其寫實轉向
五、第五章 現實主義及其不滿
六、第六章 結論
第二章 殖民主義與リアリズム(Realism)
第一節 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
一、反自然主義的大正文壇
二、以自然主義改革舊小說的臺灣
三、大正思潮與臺灣小說
第二節 昭和前期寫實觀念與現代小說語言
一、五四寫實觀念與「殖民地漢文化」的中國白話文小說
二、鄉土寫實意識與「帝國漢文化」的臺灣話文小說
三、「真實的寫實主義」與「振假名註記」的日文小說
第三節 決戰時期的文體與國體─日本思想史的嫁接
一、浪漫寫實主義:回歸「日本美好傳統」
二、觀念現實主義:超克西方的大東亞意識形態
三、糞現實主義:不「同一」於日本的「差異」臺灣
第三章 現/寫實主義及其想像
第一節 現實主義與寫實主義
一、進步左翼與現實主義
二、民族右翼與三民主義
第二節 戰後初期現實主義在臺灣的角力
一、三民主義現實主義的匯入
二、族群與階級:小說書寫的分化
三、新現實主義文學論爭:國統區與解放區的歧義延長
第三節 三民主義寫實主義及其長篇小說生產
一、反共成長小說:第一人稱與二元敘事
二、戰爭歷史書寫:去差異化的民族想像
三、 健康寫實小說:民生建設與家在臺北
第四章 現代主義及其寫實轉向
第一節 現代主義與寫實主義
第二節 「美援」與「中華」文化主導下「寫實」觀念之移轉
一、自由主義文藝:美援年代的黨國威權侍從
二、批評建制:從《文學雜誌》到《中外文學》
第三節 理論翻譯與內向性寫實小說生產
一、小說理論與心理學的接引
二、精神分析與冷戰意識形態
三、存在主義與個體反思
第四節 寫實的「美」「援」:現代小說的美學挪用
一、化用中外經典的「寫實」策略
二、音響與字質:新批評與短篇小說生產
第五章 現實主義及其不滿
第一節 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
一、日據時代臺灣小說的重返
二、鄉土小說:從露骨寫實主義到反諷現實主義
三、 美學判準與意識形態
第二節 鄉關何處:植有玫瑰與麥的土地
一、土地與社會:兩種論述基點與小說生產
二、政治小說的「現實」分歧
第三節 後現代及其超越
一、後現代小說
二、新鄉土小說
三、「新寫實主義」與絃歌不輟的土地之歌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被建構的「寫實主義」
第二節 下一輪小說研究的備忘錄
參考資料
Becoming-Realism: The Production of Taiwan Fiction
RESULTS AND DISCUSSION
2014年博士論文謝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