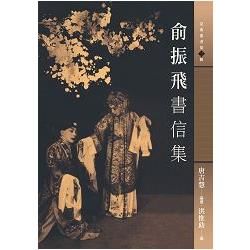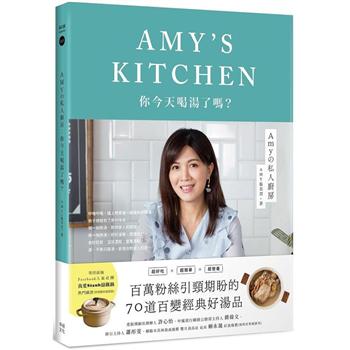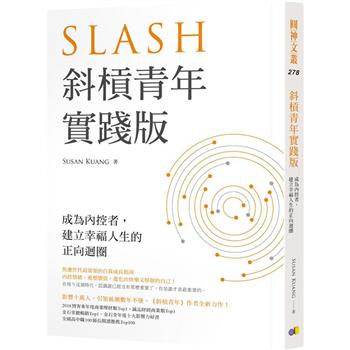本書收錄俞振飛先生與友人往還的書信,時間跨度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歷經文革,直至八十年代後期。俞振飛於信中敘述了崑曲諸多劇目的唱腔、身段,在演出需要注意的要點及其藝術心得,並論及其與梅蘭芳、程硯秋、張君秋、馬連良等名人的交往掌故;最爲重要的是記錄了他數十年的個人生活,包含日常交遊、家庭變遷、從藝經歷等,真實呈現崑曲名家的真實面貌。
本書特色
彙集諸多曲家前輩珍藏的俞振飛書信,以及中央大學戲曲研究室收藏的俞振飛給宋鐵錚的十三封信,是研究俞振飛及現代崑曲史與崑曲藝術的珍貴史料。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俞振飛書信集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1 |
二手中文書 |
$ 238 |
小說/文學 |
$ 270 |
中文書 |
$ 284 |
表演藝術 |
$ 317 |
戲劇 |
$ 324 |
各類戲劇 |
$ 324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60 |
藝術總論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俞振飛書信集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編選:唐吉慧
上海寶山人。崑曲業餘愛好者。十八歲學書法,二十歲學篆刻,二十五歲寫散文,二十六歲致力於近現代名人文獻的收集、研究。著有散文集《舊時月色》、《舊時相識》。現爲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上海青年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上海青年文聯理事、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
編選:唐吉慧
上海寶山人。崑曲業餘愛好者。十八歲學書法,二十歲學篆刻,二十五歲寫散文,二十六歲致力於近現代名人文獻的收集、研究。著有散文集《舊時月色》、《舊時相識》。現爲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上海青年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上海青年文聯理事、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
目錄
崑曲叢書第三輯總序/洪惟助
自序/唐吉慧
致蔡正仁
致方家驥
致顧篤璜
致顧兆琪
致陸兼之
致羅錦堂
致梅蘭芳
致宋鐵錚
致孫堃鎔
致孫天申
致王守泰
致吳新雷
致辛清華
致徐希博
致許姬傳
致葉劍英
致朱復
致鄒家沅
自序/唐吉慧
致蔡正仁
致方家驥
致顧篤璜
致顧兆琪
致陸兼之
致羅錦堂
致梅蘭芳
致宋鐵錚
致孫堃鎔
致孫天申
致王守泰
致吳新雷
致辛清華
致徐希博
致許姬傳
致葉劍英
致朱復
致鄒家沅
序
自序
痴迷名人信件的集藏不容易,入門之初見識淺薄,積累的過程磕磕跘跘,幾年下來雖然數量可觀,到底魚龍混雜:有的重書法,有的重史料,有的只為一張別致的小花箋。在這些信件中,最為珍貴的要數崑曲泰斗俞振飛的一批書信了。
我是在二○○八年接觸崑曲的,緣由崑曲名票孫天申奶奶的厚愛,得以結識較多崑曲界資深曲友和老師,這幾年大家時常往來,我聽他們講關於崑曲的故事,和他們一起唱曲子看戲,在這棵六百年的老樹下享受著一片快樂的綠蔭。我是幸運的,在較短的時間裡便對崑曲有了較深的認識。有位老前輩與我打趣,誇我扮相好,不如學俞振飛,做個小生演員粉絲一定多。俞振飛票友下海能成名角,那是家裡有淵源,老先生又有學問,詩做的好,畫畫得好,字寫得好,崑曲泰斗當之無愧:「學戲太辛苦,我這一身骨頭都硬了,怕是經不住練腰腿、打把子了,不如收收他的書信,為俞老、為崑曲做點貢獻也好。」我對老前輩說。
二○一○年,有好友告知海上某位老曲家有意轉讓一批俞振飛書信。在好友的安排下,有天晚上我們與老曲家見了面。三人圍坐在老曲家小客廳的茶几前,邊喝茶,邊聊崑曲,邊看書信。我粗粗看了看,這些信的書寫時間集中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共有一百多封。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正值國內浩劫動蕩不安,老輩人惋惜,俞老的書信大部分毀在了「文革」,當然那個年代,對於文化,毀掉一些信根本算不上什麼。同為俞老學生的蔡正仁和岳美緹各有俞老寫給他們的信件一百多封,「文革」時,蔡正仁的全部上交文化局,岳美緹的部分自己燒毀,部分上交文化局。「文革」結束,兩位老師曾去文化局要過幾次,但毫無結果,只得作罷。如今已步入七十的正仁老師每每說起此事總有不甘,因為那些信裡多的是俞老對他的殷殷寄望、諄諄教誨,和對崑曲各齣戲細節的解讀。岳老師則滿懷傷感,說:「俞老師當年寫的許多信,已經化作一個個畫面,一個個鏡頭,時常回閃在我的眼前,把我帶回那充滿理想的青年時代……」現在這些信身在何處沒人知道。有人抱怨,「文革」中不知換了多少批管理材料的人,現在去找誰,誰會對這事負責任?也有人猜測,信可能在一九七○年文化廣場的一場大火中燒掉了。老曲家有點得意,他的信是他在「文革」中偷偷藏下的。我細細讀了讀,信裡,俞老跟老朋友傾訴苦悶、斟酌劇情、鑽研演技,無疑是近代崑曲表演藝術史的稀世文獻。老曲家讓我留意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一封信,內容談到了俞振飛從藝的小掌故,信上說:「我所遇到的崑班老演員,只有沈月泉老師(傳芷之父),我所能表演的崑曲劇目,絕大多數是沈老師教給我的。當時他的年紀已六十左右,但不是『食古不化』的保守派,他自己有一定的創造。及至後來到北京拜了程繼先老師,他的表演藝術,有些是和沈老師異曲同工的,但程老師由於武工底子好,因此在表演上有他的獨特風格。而且程老師幼年在科班時,據說是先學崑曲,後學京戲,因此在『咬字』方面,崑味很濃,我能得到他的悉心教導,其原因也就在於此。」這是研究俞老不可或缺的珍貴記錄了。
那晚老曲家沉浸在懷舊的氣氛中。幾分喜悅,說及小時候與梅蘭芳的交往,幾分自豪,說及第一次登臺唱戲,幾分惆悵,說及一位位昔日的友人。我望著八十好幾的老人家,往事漂浮在他年華轉眼消歇的臉上像煙像水:花事凋離,知己零落,經了兩次中風,他說他這副臭皮囊是再經不住折騰了。偶爾他和老伴閑話幾句,終究忘不了當年給俞振飛熬的那碗雞湯。那是文革末期,上海市文化局奉文化部指示,集中了一批京崑老藝人在泰興路文藝俱樂部(今上海市政協)拍攝傳統京崑影片,俞振飛拍攝的是崑劇「太白醉寫」。俞振飛在信上說:「泰興路又來催我把『太白醉寫』全齣詞句和樂譜寫給他們,他們馬上就要刻蠟紙分發給大家……由於『醉寫』是我把崑曲的『吟詩脫靴』作了一些增刪,這個劇本,任何曲譜裡沒有,必須由我一點一點想起來,因此更加費事。我從十日到十四日共五個晚上,雖然我怕失眠,每日工作到八點半,但這五個晚上都失眠了,今天上午劇本交去,可能精神可以鬆弛一下。這種情況我不講,別人是猜想不到的。」等到正式排練更辛苦,老先生極為焦慮,幾次信上都擔心自己左支右絀,要請老朋友為他打聽提神的藥品,「請您向醫生朋友瞭解一下,除了『ATP』、『輔酶A』之外,有沒有吃的藥片或者打的針,使我身體內部增加一點『能量』,問到後,請即日來函告知,切盼切盼!!」哪怕是有毒性的:「我要一種針藥,打一針,就能比較精神振作一點,這是臨時的,略有一點毒性,關係不大(屬於這些藥品,恐怕還要急診間配得到,也要懇託您代想辦法)。」老曲家心疼他的俞伯,為他問藥配藥送藥,還特意為他熬雞湯補身子。那天俞振飛正在排練,老曲家沒打擾他,留下一只盛滿了雞湯的保暖瓶悄悄走了。俞振飛排練完畢回到屋裡,見到那只保暖瓶,激動地沒說出話來,「我就認得是您家的!」他在信上寫,「我老實告訴您,這次的雞湯,我打開瓶蓋,撲鼻噴香,湯清味鮮,您加入一點青菜,不僅營養好,而且在淡黃色濃湯中漂著幾葉青菜,又漂亮,又好吃,可謂色、香、味俱全,這裡向您表示由衷地感謝!」那麼稀鬆平常的往事,兩代人的情誼,今晚顯得格外珍貴,格外溫暖。「這些信跟著我蹉跎到今天數十年,該做個了斷了。」望著沉沉的夜色,老先生淡淡地言語讓我頓感悲涼。我買下了這些信。
文革結束不久,有回俞老到蘇州西山遊玩,在一塊寫著壽字的巨石前留影,沒多久巨石竟然滑落摔裂,蘇州人說,這石頭的壽是讓俞振飛帶走了。俞振飛果然長壽,一九九三年九十二歲辭世。老人家一生喜歡寫信,寫了多少無從計算。我陸陸續續收集了有兩百封了,寫給梅蘭芳的,寫給許姬傳的,寫給羅錦堂的,等等,原件、影印件都有,我想編一本《俞振飛書信集》,喜愛崑曲的陳佩秋先生、戴敦邦先生高興地先為我寫了書名題了字。陳佩秋先生寫了「俞振飛書信」,戴敦邦先生題了「瀟湘雁飛來」,字都認真,字都深情,是一份對俞老的致敬,更是一份對崑曲的致敬。我做不了小生演員,能為俞老、為崑曲做點貢獻,也好。
唐吉慧
痴迷名人信件的集藏不容易,入門之初見識淺薄,積累的過程磕磕跘跘,幾年下來雖然數量可觀,到底魚龍混雜:有的重書法,有的重史料,有的只為一張別致的小花箋。在這些信件中,最為珍貴的要數崑曲泰斗俞振飛的一批書信了。
我是在二○○八年接觸崑曲的,緣由崑曲名票孫天申奶奶的厚愛,得以結識較多崑曲界資深曲友和老師,這幾年大家時常往來,我聽他們講關於崑曲的故事,和他們一起唱曲子看戲,在這棵六百年的老樹下享受著一片快樂的綠蔭。我是幸運的,在較短的時間裡便對崑曲有了較深的認識。有位老前輩與我打趣,誇我扮相好,不如學俞振飛,做個小生演員粉絲一定多。俞振飛票友下海能成名角,那是家裡有淵源,老先生又有學問,詩做的好,畫畫得好,字寫得好,崑曲泰斗當之無愧:「學戲太辛苦,我這一身骨頭都硬了,怕是經不住練腰腿、打把子了,不如收收他的書信,為俞老、為崑曲做點貢獻也好。」我對老前輩說。
二○一○年,有好友告知海上某位老曲家有意轉讓一批俞振飛書信。在好友的安排下,有天晚上我們與老曲家見了面。三人圍坐在老曲家小客廳的茶几前,邊喝茶,邊聊崑曲,邊看書信。我粗粗看了看,這些信的書寫時間集中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共有一百多封。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正值國內浩劫動蕩不安,老輩人惋惜,俞老的書信大部分毀在了「文革」,當然那個年代,對於文化,毀掉一些信根本算不上什麼。同為俞老學生的蔡正仁和岳美緹各有俞老寫給他們的信件一百多封,「文革」時,蔡正仁的全部上交文化局,岳美緹的部分自己燒毀,部分上交文化局。「文革」結束,兩位老師曾去文化局要過幾次,但毫無結果,只得作罷。如今已步入七十的正仁老師每每說起此事總有不甘,因為那些信裡多的是俞老對他的殷殷寄望、諄諄教誨,和對崑曲各齣戲細節的解讀。岳老師則滿懷傷感,說:「俞老師當年寫的許多信,已經化作一個個畫面,一個個鏡頭,時常回閃在我的眼前,把我帶回那充滿理想的青年時代……」現在這些信身在何處沒人知道。有人抱怨,「文革」中不知換了多少批管理材料的人,現在去找誰,誰會對這事負責任?也有人猜測,信可能在一九七○年文化廣場的一場大火中燒掉了。老曲家有點得意,他的信是他在「文革」中偷偷藏下的。我細細讀了讀,信裡,俞老跟老朋友傾訴苦悶、斟酌劇情、鑽研演技,無疑是近代崑曲表演藝術史的稀世文獻。老曲家讓我留意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一封信,內容談到了俞振飛從藝的小掌故,信上說:「我所遇到的崑班老演員,只有沈月泉老師(傳芷之父),我所能表演的崑曲劇目,絕大多數是沈老師教給我的。當時他的年紀已六十左右,但不是『食古不化』的保守派,他自己有一定的創造。及至後來到北京拜了程繼先老師,他的表演藝術,有些是和沈老師異曲同工的,但程老師由於武工底子好,因此在表演上有他的獨特風格。而且程老師幼年在科班時,據說是先學崑曲,後學京戲,因此在『咬字』方面,崑味很濃,我能得到他的悉心教導,其原因也就在於此。」這是研究俞老不可或缺的珍貴記錄了。
那晚老曲家沉浸在懷舊的氣氛中。幾分喜悅,說及小時候與梅蘭芳的交往,幾分自豪,說及第一次登臺唱戲,幾分惆悵,說及一位位昔日的友人。我望著八十好幾的老人家,往事漂浮在他年華轉眼消歇的臉上像煙像水:花事凋離,知己零落,經了兩次中風,他說他這副臭皮囊是再經不住折騰了。偶爾他和老伴閑話幾句,終究忘不了當年給俞振飛熬的那碗雞湯。那是文革末期,上海市文化局奉文化部指示,集中了一批京崑老藝人在泰興路文藝俱樂部(今上海市政協)拍攝傳統京崑影片,俞振飛拍攝的是崑劇「太白醉寫」。俞振飛在信上說:「泰興路又來催我把『太白醉寫』全齣詞句和樂譜寫給他們,他們馬上就要刻蠟紙分發給大家……由於『醉寫』是我把崑曲的『吟詩脫靴』作了一些增刪,這個劇本,任何曲譜裡沒有,必須由我一點一點想起來,因此更加費事。我從十日到十四日共五個晚上,雖然我怕失眠,每日工作到八點半,但這五個晚上都失眠了,今天上午劇本交去,可能精神可以鬆弛一下。這種情況我不講,別人是猜想不到的。」等到正式排練更辛苦,老先生極為焦慮,幾次信上都擔心自己左支右絀,要請老朋友為他打聽提神的藥品,「請您向醫生朋友瞭解一下,除了『ATP』、『輔酶A』之外,有沒有吃的藥片或者打的針,使我身體內部增加一點『能量』,問到後,請即日來函告知,切盼切盼!!」哪怕是有毒性的:「我要一種針藥,打一針,就能比較精神振作一點,這是臨時的,略有一點毒性,關係不大(屬於這些藥品,恐怕還要急診間配得到,也要懇託您代想辦法)。」老曲家心疼他的俞伯,為他問藥配藥送藥,還特意為他熬雞湯補身子。那天俞振飛正在排練,老曲家沒打擾他,留下一只盛滿了雞湯的保暖瓶悄悄走了。俞振飛排練完畢回到屋裡,見到那只保暖瓶,激動地沒說出話來,「我就認得是您家的!」他在信上寫,「我老實告訴您,這次的雞湯,我打開瓶蓋,撲鼻噴香,湯清味鮮,您加入一點青菜,不僅營養好,而且在淡黃色濃湯中漂著幾葉青菜,又漂亮,又好吃,可謂色、香、味俱全,這裡向您表示由衷地感謝!」那麼稀鬆平常的往事,兩代人的情誼,今晚顯得格外珍貴,格外溫暖。「這些信跟著我蹉跎到今天數十年,該做個了斷了。」望著沉沉的夜色,老先生淡淡地言語讓我頓感悲涼。我買下了這些信。
文革結束不久,有回俞老到蘇州西山遊玩,在一塊寫著壽字的巨石前留影,沒多久巨石竟然滑落摔裂,蘇州人說,這石頭的壽是讓俞振飛帶走了。俞振飛果然長壽,一九九三年九十二歲辭世。老人家一生喜歡寫信,寫了多少無從計算。我陸陸續續收集了有兩百封了,寫給梅蘭芳的,寫給許姬傳的,寫給羅錦堂的,等等,原件、影印件都有,我想編一本《俞振飛書信集》,喜愛崑曲的陳佩秋先生、戴敦邦先生高興地先為我寫了書名題了字。陳佩秋先生寫了「俞振飛書信」,戴敦邦先生題了「瀟湘雁飛來」,字都認真,字都深情,是一份對俞老的致敬,更是一份對崑曲的致敬。我做不了小生演員,能為俞老、為崑曲做點貢獻,也好。
唐吉慧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