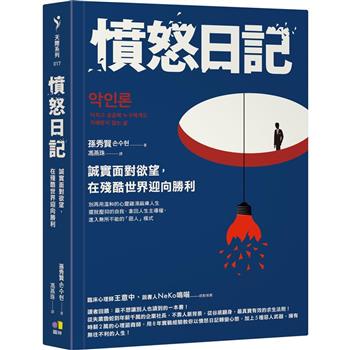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浮塵戀影:獻給年輕世代的執拗低語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52 |
小說 |
$ 270 |
中文書 |
$ 284 |
中文現代文學 |
$ 306 |
小說/文學 |
$ 317 |
小說 |
$ 324 |
小說 |
$ 324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6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浮塵戀影:獻給年輕世代的執拗低語
「文學一如人之生命體。作者要設法把自己的生命觀表達、解釋出來。如對天、對人、對社會種種的看法和意見,如此才算成全圓滿。寫作只是在妄圖喜悅,盼得人們之瞭解,以另外的方式渴求溫暖、尊嚴、受人誇讚、肯定自我的途徑。」──王幼華
本書根據作家王幼華年輕時的日記改寫而成,其內容包括兩大部份:其一為日記,紀錄作者離開學校後成為專業作家的心路歷程。其二為小說,作者用自傳體小說的方式,描述服兵役時因適應不良而進入療養院療養的特殊經歷。全書透過日記與小說的方式,勾勒出一位作家對知識的追求、愛情的碰撞、心靈的徬徨與掙扎、創作的挫敗與歡愉等感悟,過程裡充滿了意志的燃燒,精神的試煉和理想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