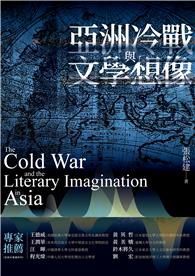【序章】
早晨,一個漫長休眠的結束,電流會溫順地在身體內流淌,散亂的訊號會在腦中舞蹈,最終交織成雙眼所見的影像。我能透過它看見宇宙的樣貌,每一次都不盡相同,每一次都能使我知道,自己仍然在這宇宙的某個地方旅行。
我緩慢地呼出一口氣,察覺到諾夫曼先生已經將茶水泡好放在一旁,深藍色的液體在杯中透著微光。通常這個時間他會在樓下悠閒地翻閱雜誌,用手觸摸那些刻在金屬頁面上,由程式代碼組成的文字。半瞇著眼,遐想在遠方發生的事。
我與他也不算特別熟識,真要說,就只是在酒館喝了兩杯小酒、互相說起往事的那種關係。對他來說我只是一個旅人,而他只是一個居住在巨大金屬森林中的獵人。
「早安,諾夫曼先生。」
我在他一旁的椅子上坐下,與他一同看向窗外正飄落的星塵。那些是宇宙裡隕石經過漫長的時間,相互撞擊消磨所剩下的塵埃。它們會成為星球上植物的養分,或是逐漸聚集成為下一個星球的雛形。
「你確定要在這麼糟糕的天氣中離開嗎?」他低沉的話語透過電磁波傳達到我的腦中,一邊又用力地眨了眨眼,我猜他是想調整瞳孔的焦聚,好讓他可以看得更遠,但似乎並不怎麼有用。諾夫曼雖然看起來約莫五十多歲,但我很難用一個人外表的年齡,來推測他實際生活過的歲月,那是不現實的。
「是的,恐怕要讓我在那麼柔軟的床上再多睡一天,我都會忘卻旅行的煩憂。」
「是嗎?」諾夫曼停頓一會,他放下手中的雜誌,並在空蕩的屋內轉了一圈, 「看來我也沒什麼好給你的。」他顯得有些失落。
「喔,不需要了,在這裡的這幾天我真的很愉快。」我半瞇著眼,腦海中閃過一些零星的回憶,很難說旅行本身總是美好的,但像這樣悠閒的時光卻不常見。
「你是指狩獵野兔的事情嗎?」諾夫曼興奮的轉過身來看著我,他做出拉滿弓箭的動作像個孩子般,彷彿在我之前已經很久沒有人來過此地。
「不,那個可不算在內。」我苦笑道,沒有什麼比兩個大男人在充滿星塵的森林中,追逐野兔還要累的事情,更別提我們除了搞得滿身都是星塵外,根本沒有狩獵到半隻兔子。
而且諾夫曼會提出狩獵野兔的事情,我本以為他是一時興起,沒想到他真當一回事。
「嗯,我真希望你可以待久一些,這樣我就可以再聽到更多有趣的故事,還有……」諾夫曼停止了自己的話,他盯著自己的腳發愣,或許是有什麼回憶從記憶體的深處被喚醒。
我沒有多作猜測,就如同過往我所待過無數的地方,與相處的人一樣,我拿起掛在一旁厚重的斗篷,拍拍諾夫曼微微顫抖著的肩膀向他告別。屋外的星塵積累的很深,就像別人常說起的雪,可我沒有實際見過,也不認為踩起來時會聽見細微的沙沙聲響。
我走得遠,四周都快要被星塵覆蓋,這是非常難得的場景,但對我來說並不是一件好事,畢竟我可不想要在這裡迷失方向。正當我想把斗篷裹的更加緊實,好讓星塵不會沾黏在衣服或身上時,卻意外發現斗篷內襯柔軟蓬鬆的兔毛,我想是諾夫曼趁我不注意時縫上的。處理獸毛並非容易之事,雖然有柔軟的地方,但卻仍然有金屬的尖銳與韌性,要不是相當好的手藝,是無法做到這麼好的。儘管這不會給我在如此冰冷的宇宙裡帶來溫度,卻有著另一種層面的溫暖。
我卻很難想像他逮到野兔的瞬間,尤其是在這種惡劣環境下生長的野兔,有時候快跑起來都看不見蹤影,更不用說找到蹤跡與巢穴都是不容易的。當然我或許是小瞧他的狩獵技巧,不然他又是怎麼能待在這裡生活這麼長久。
我停下自己的腳步,將視線拉遠,企圖從飄落的星塵之中,看向那更加遙遠的宇宙,直到超過影像捕捉最為極限的距離,散亂成過多繁雜的訊號。
這是很神奇的一瞬間,我是指不論經過多長的時間,多少次的旅行,我總是難以從複雜的程式代碼中,尋找出能拼湊,或是能說明自己當初行動的理由,恐怕今後也依然如此。
【第一章 長路漫漫】(節錄)
宇宙列車無疑是跨越星系之間,最好的移動方式,除去漫長的移動時間外,我難以挑出它不好的地方。更不用說打從我開始旅行以來,宇宙列車的車廂就好比我的家一樣,我在那裡待過的時間,遠勝過一次又一次的旅行。
「午安,坤特爾先生。」列車的服務員薩姆叫喚著我的名字,她與她無數個姊妹們有著相同的圓潤臉蛋,還有那一身乾淨又整齊的制服,如果她能在說話中添加些情感那就更好了。
當然,這也只是我不經大腦的說詞。
我踢了踢身上的毯子,翻了個身,就像是從蟲子般。我從毯子的縫隙中向外窺視,一名看起來約二十多歲的男子正站在她的身邊,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放在前方的行李占據他的位子。
「喔,讓他去別的車廂坐吧。」我抱怨著,但薩姆並沒有理會我,而是強硬的把行李塞到我的身邊,使我被迫坐了起來。
「喬拉頓先生,我已經幫你把位子空出來,祝您有個愉快的一天。不論有任何事情,隨時都可以按旁邊的按鈕呼喚我。」薩姆熟練地說道,並向他行禮後才轉身離開。
我仰著頭,由於我是中途被叫醒的,所以我覺得自己大腦中的程式還無法反應過來,甚至雙腿還處在未通電,沒有半點感知的狀態。
真是糟糕透了。
我企圖想讓自己再次睡去,但卻沒有半點效果。我開始觀察眼前名為喬拉頓的男子,體型瘦高,長像普通,穿著相當隨性,甚至沒有帶任何行李,如果在任何地方見到都不奇怪。
可是這並非一般的列車,是一站便要橫跨數個星系,數天才會抵達的長途列車。那麼一個二十多歲,沒有帶任何行李的普通男子,要不是有計畫性的逃家,就是沒有任何想法的出走。
這個年代中想要離開自己星球的人並不算少數,理由大多也相當荒謬。有些人會覺得離開自己所居住的星系便會有所不同,也有些人費盡時間抵達另一個星系中的某個星球,只為了驗證他的幻想。誰知道他們的運算程式到底哪裡出了問題,不過這種事情要我來說還是有些可笑的。
幸好這樣尷尬的氣氛並沒有維持太久,一如往常只要坐在我對面的人,都會好奇的問我即將要去哪裡,不過他並不同,而是問了一個相當有意思的問題:「坤特爾先生,您有見過狼嗎?」
「狼?或許有吧,不過我沒有什麼太深刻的印象。」
大多數的旅行中,我不會刻意在未開發的星球上旅行,也不會選擇人較多的人造星球。前者有太多不安定的因素與危險,後者則是我本來就不喜歡過於熱鬧的地方。儘管多數我都無意識的持續旅行,但或多或少都會避開這些。
如果真的能遇到狼,那也只是在很遠的地方聽見,或是從其他旅行者的口中得知。
「在我故鄉附近的星球上,居住著一隻巨大的狼,它銀白色的毛會在眾星下閃耀,使它奔馳的時候如流星一般。」喬拉頓半瞇著雙眼,他試著回憶起記憶深處那頭美麗的巨狼,而我則是陷入了另一個困惑之中。
我記得某個旅行者告訴我,他說多半遇見猛獸的故事都不會是真的,哪怕真的遇見,若不是經歷瀕臨死亡之人,那便是一心求死之人,唯獨這樣他們才能在沒有任何食物與水分的曠野中行走,試圖穿越各種惡劣的氣候。哪怕他們遇見也不見得能活著回來,即使他們活著回來,也不會樂於分享給別人。
我退去身上的毛毯,從一旁的行李中拿出能咀嚼的菸草,它刺激著我的大腦,好讓那些散亂的訊號源可以有所集中。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呢?」
喬拉頓露出靦腆的笑容,他抓了抓自己散亂的頭髮:「能的話我還想要再見到她一面。」
「她?」
「嗯,是的,或許你會認為我在開玩笑,不過我總覺得她就像是我逝去的母親, 儘管已經過了這麼長久的日子,我真的很希望能在某個星球上再次與她相遇。」
「她已經不在那個星球上了?」
喬拉頓沉重的嘆了一口氣,他所發出的電磁波變得散亂與不安定:「很抱歉,我也希望她就在那一個星球上,可是父親一直都不肯告訴我關於那星球的事情,他總說我應該從母親的死亡中釋懷。」
「你沒有試著回到那個星球上去嗎?」
「那是我很小時候的事情,儘管我記得她奔跑的身姿,與她溫柔的眼神,可很多事情我早已忘記,難道你也能記得住自己旅行的事情嗎?」
「我會將記憶的資料備份在專屬的容器中。」儘管我很少會再去閱覽那些過去。
「那麼你自己又為何旅行呢?」
「我不知道,不過某個旅行者曾這麼說過,正因我們有所行動,這個宇宙才不會像是冰冷的金屬。」
「是嗎?」喬拉頓點了點頭。
「那麼你要到哪裡去呢?」我問,儘管我多少能猜出這個問題的答案。
「哪裡也不去,我只是搭上這班列車到某一站後再返回,對我來說這樣就算是旅行吧。」喬拉頓露出了微笑,他顯得相當的愉快,就像是一個愛聽別人說故事的孩子。
「你不會想要再見到她嗎?」
「我會到她的墳墓前祈禱,父親說她是生我後死去的,我想也因為如此她才多次出現在我面前,我希望她真的生活在某個寬闊的星球上,我想你應該能明白我的意思。」
「這恐怕有些困難。」我尷尬的笑了一笑,「我很少會想起他們的事情。」
「喔,那真是抱歉,坤特爾先生,我應該沒有讓你想起不愉快的回憶吧。」
「當然沒有,宇宙的時間是難以估算的,我們會定期的睡去,把大量的程序重新計算與處理,所以每天的開始我們能想起的事情很少。我不會花時間讀取過去,或猜想此時他們在做些什麼,但也或許終有一天我會再次與他們相遇。」
「我恐怕無法像你一樣,搭乘這班列車已經算離開我星系最遙遠的距離。」
「我想你應該可以試著在車站附近看看。」
「不,我怕要是我那麼做,我肯定會控制不住我的好奇心。」喬拉頓眨了眨眼, 如果有機會,他恐怕會像我或是其他旅人踏上自己的旅行。
「能離開自己所居住的星球,我覺得那已經相當厲害。」我在借宿於他人星球時,經常會看見那些放棄生活,每天只是仰望星空的人。他們已凹陷下的眼窩,就好比迷失方向的旅行者。
「我們很難不會變成那樣,就好比我們吃下去的東西,是一塊冰冷的金屬,還是大腦編寫出的一串程式;我眼前所看見的你或是列車外的宇宙,那會是真實的,亦或只是一種多層的影像。我們是不可能有所答案的,那就好比你的旅行,或是我夢中的那隻白狼一樣,而我們依然前行。」喬拉頓抬起頭,他有堅定的眼神,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個二十歲,實際只經歷過可能萬年不到的日子裡,就有著自己的想法,實在並不容易。
我將口中的煙草吐近一旁的小垃圾桶中,它就像是一團乾癟的草球,不,嚴格來說是團金屬渣子也不為過。
很少有機會我能想起,甚至說我已經不曾想起,那一段清澈明亮的日子。
我翻找著行李箱內的深處,試圖尋找那裝載我大量記憶的裝置,很快我的手便停止下來,我轉身面向喬拉頓:「時間還多著,你想要聽我說一個故事嗎?」
「喔,那當然沒有問題。」
「不過,與狼無關,甚至不是什麼特別的傳奇。」那卻清晰的出現在我的眼前,宛如昨日。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航向星海的列車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4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168 |
其他科幻/奇幻小說 |
$ 180 |
中文書 |
$ 190 |
科幻/奇幻小說 |
$ 211 |
科幻小說 |
$ 216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240 |
奇幻\科幻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航向星海的列車
☆有的人想在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有的人只想在宇宙列車上碰上一隻貓;從宇宙的中心到盡頭,你的旅行精彩嗎?你還記得自己踏上旅途的初衷嗎?
☆遙遠的星啊,請帶著我前行。穿越險峻的深谷,走過荒蕪與死亡。如果有人問我要望何處去,我便指著自己的腳。如果有人問我旅行的目的,我便指著前方的星。
大部分的旅行者都不太相信傳說,
他們多數願意相信自己腳下走過的事。
只有冒險者才會把希望投注在既瘋狂又不見得可能發生的事情上,
他們從不在乎當下遇到的困難。
你想成為漫步在星球之上的旅行者呢?
還是不畏懼生死,勇於前進的冒險者?
有的人想在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有的人只想在宇宙列車上碰上一隻貓
從宇宙的中心到盡頭,你的旅行精彩嗎?你還記得自己踏上旅途的初衷嗎?
坤特爾是一位乘著宇宙列車旅行的旅人,在與車上不同旅客短暫相處的過程中,交換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看到了各式各樣的宇宙與人生:有人窮盡一輩子,只為穿越無法穿越的電子風暴,一窺背後的風景;有人尋覓著傳說中能帶給人幸福的太空鯨魚,遊蕩在浩然的宇宙中;還有的人,只想做一隻不會在列車上迷路的貓。隨著旅途逐漸接近尾聲,坤特爾開始回想起自己踏上這班列車的動機、內心的遺憾與那未完成的旅途。
作者簡介:
羽尚愛
本名汪玉川,現居桃園,27歲,喜愛日本純文學或類型文學,目前主要寫作方式以寫實與科幻為主。
我在文字的深海裡迷航。我在宇宙的盡頭替自己的靈魂哀悼。
TOP
章節試閱
【序章】
早晨,一個漫長休眠的結束,電流會溫順地在身體內流淌,散亂的訊號會在腦中舞蹈,最終交織成雙眼所見的影像。我能透過它看見宇宙的樣貌,每一次都不盡相同,每一次都能使我知道,自己仍然在這宇宙的某個地方旅行。
我緩慢地呼出一口氣,察覺到諾夫曼先生已經將茶水泡好放在一旁,深藍色的液體在杯中透著微光。通常這個時間他會在樓下悠閒地翻閱雜誌,用手觸摸那些刻在金屬頁面上,由程式代碼組成的文字。半瞇著眼,遐想在遠方發生的事。
我與他也不算特別熟識,真要說,就只是在酒館喝了兩杯小酒、互相說起往事的那種關係。對...
早晨,一個漫長休眠的結束,電流會溫順地在身體內流淌,散亂的訊號會在腦中舞蹈,最終交織成雙眼所見的影像。我能透過它看見宇宙的樣貌,每一次都不盡相同,每一次都能使我知道,自己仍然在這宇宙的某個地方旅行。
我緩慢地呼出一口氣,察覺到諾夫曼先生已經將茶水泡好放在一旁,深藍色的液體在杯中透著微光。通常這個時間他會在樓下悠閒地翻閱雜誌,用手觸摸那些刻在金屬頁面上,由程式代碼組成的文字。半瞇著眼,遐想在遠方發生的事。
我與他也不算特別熟識,真要說,就只是在酒館喝了兩杯小酒、互相說起往事的那種關係。對...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將此書贈與所有喜愛旅行之人。」―布蘭亞
TOP
目錄
序章
第一章 長路漫漫
第二章 如夢似幻
第三章 勇往直前
第四章 嚮往之地
第五章 告別的日子
終章 在旅行之後
後記
第一章 長路漫漫
第二章 如夢似幻
第三章 勇往直前
第四章 嚮往之地
第五章 告別的日子
終章 在旅行之後
後記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羽尚愛
- 出版社: 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17-12-11 ISBN/ISSN:978986326476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192頁 開數:14.8*21 cm
- 類別: 二手書> 中文書> 類型文學> 科幻小說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
|


 2018/02/21
2018/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