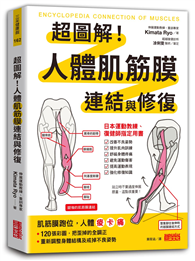【第一章】 這個雪夜如夢似幻
一
一九八○年的最後一天,整個白天都陰霾沉沉,藩城彷彿還浸淫在昨夜的夢裡。但給人的感覺還是相當溫暖的。風很微弱,蒼白的冬陽上午還短暫地露過幾次臉,中午起就深囚於逐漸增厚的雲層中,掙不出來了。天色因此比平時暗得早,到秦義飛從食堂吃過晚飯回寢室的時候,大院裡已經黑透了。
他坐在岑寂的辦公桌前,發了好一會呆,不知道該怎麼打發接下來的漫漫長夜。每天的這個時候都是最讓他感覺到無聊和孤獨的。頭腦有點昏沉,心裡空落落的,但睡覺時間還早得很。看點書吧,一時還打不起精神。走親訪友吧,對於一個剛從下面縣裡借調上來沒多久的孤家寡人,亦無從談起。
這時,秦義飛忽然注意到窗玻璃上細微的沙沙聲,和漆黑的院子裡那翻飛在昏黃路燈光暈中微弱的亮點。他俯向窗玻璃,詫異而又有幾分欣喜地發覺外面正在下雪。而且那雪的來頭還不算小。往上看,窗外的天空更陰沉了,彷彿有誰拿墨汁將天幕瞎塗亂染了一氣。
家鄉該也在下雪吧?秦義飛悶悶地想:雪花就像一條大被子,把屋子和世界都包裹得嚴嚴實實啦。哦,這樣的夜晚!這麼靜,這麼美,連一絲半點風聲都聽不到。要是整個世界就此讓雪給凍住了,從此永遠定格在這個時間,這個樣子上,那冰雕玉砌,玉樹瓊花,普天銀光,豈不就成了個(未免有些陰森的)夢幻世界了嗎?而人也定格了,定格於此時此刻的那個年齡,老到七老八十的從此得以不死,小到牙牙學語的從此不會長大,因而也不用去上學、做工,永遠做年輕父母懷抱中的乖寶寶。其他人呢?該上班的上班,該享受的享受,該當總統的還當總統,該當叫花子的還當叫花子,總之一切都永久維持在原狀上。那局面,雖然遠不夠公平,遠不能皆大歡喜,其實也還是相當理想的呢──起碼,誰都不用再吃苦、受罪,更不必再惶恐於衰老乃至死亡的威脅,豈不真成了不是夢幻、勝似夢幻的人間天國?
他驀地打了個寒顫,為自己的念頭感到一絲古怪。可是,剛離開窗前,卻意外地聽到寢室門上似乎被人敲了兩下。聲音怯怯的,若有若無。這時候會有什麼人上門來呢?怕是自己的錯覺吧?可是,門聲又響起來,還是兩下,卻比先前響了些,而且分外真切。
「誰呀?」問話的同時,他上前擰開了門。但隨即又本能地倒退了一步。
門口出現一個穿著件紫紅底、黑隱條布質棉襖的女孩,笑吟吟而又帶著幾分羞澀地看定了他。而她那烏亮的瞳仁裡,剛好清楚地映現出吊在頭頂的白熾燈溫暖的光澤,和秦義飛有幾分迷惑的臉龐。她那有些蓬鬆的頭髮上還沾著幾絮未融的雪花,蒼白的面頰和鼻翼上,則如晨露般凝著幾點雪花融化而成的小水珠。
秦義飛的心呼呼作響:「你是找我的嗎?」
話出口的剎那,他已經認出了她:「徐曉彗!」
女孩微微點了點頭,秦義飛不由自主便側過身子,將她讓進了門。同時,他下意識地探出頭去,向樓道兩旁飛速地掃了一眼。樓道裡黯寂如故,只是他門前的地板上留下一小灘淺淺的水漬和幾個殘存著雪跡的淡淡的腳印。
秦義飛腦海中倏地閃亮了一下──今晨他出門時,曾注意到門前有一小灘泥跡和一長溜蔓延開去、深淺不一的腳印。當時他十分迷惑,昨天下過點毛毛雨,外面是比較濕滑的。但卻並沒有任何人來找過自己,怎麼會有腳印留在自己門前?難道就是眼前這多少有幾分神祕的女孩的?
他想關門,卻又遲疑了一下;不關,又覺得不太妥當,於是將門輕輕掩上。不料,那女孩的胳膊似乎不經意地往後一靠,喀嗒,門鎖被她碰上了。
二
粉碎四人幫後第一年,一九七七年夏天,國家恢復了高考。而此時的秦義飛剛好從藩城地區師專物理系畢業。儘管熱愛自己的專業,並且學習成績相當突出,但他留校的願望還是落了空。按照哪裡來哪裡去的原則,他被一刀切分配回澤溪縣去,在城郊中學教初中物理。
本來,他也沒什麼奢望,打算就在家鄉平靜地混一輩子算了。父母都吃了一輩子粉筆灰,自己也算是子承父業吧。然而,畢竟時代已是如此地不同了,風生水起的改革開放大勢,恰如潮水一般,給年輕人裹挾來無窮的機遇。中央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又如春風化雨,催生了地區科技局的誕生。
科技局設立了旨在普及科學知識,煥發群眾尊重知識、學習科技熱情的科技館。從小就崇拜高士其、迷戀《十萬個為什麼》和儒勒.凡爾納系列作品等科幻、科普類作品的秦義飛,授課之餘曾嘗試著寫過幾篇科幻小說和科普小品,有一篇科幻小說還上了省科技館出版的《科普天地》,並被《藩城日報》選用了好幾篇科普小品。沒想到就此引起地區科技館的重視,一九八○年元旦剛過,一紙公文發到了澤溪縣城郊中學,將秦義飛借調到科技館宣傳科工作。
雖然科技館初創不久,編制尚緊,但汪館長在試用了他幾個月之後,明確向秦義飛承諾,向行署編辦申請的新編制隨時會下來。到時候,將優先辦理秦義飛的調動。
草創之初的科技館和地區科技局都擠在同一座頗有些年頭的老院落裡。據說這裡原先是晚清一位藩城著名畫家的私宅。院子倒是不小,新粉刷的圍牆圈出一塊上百畝的天地和一座長方形的四層大樓──這就是科技局和科技館的辦公大樓。寬敞的院門後有東西兩排廂房,現在是科技局的傳達室和後勤科用房。局裡有兩名炊事員的小食堂和水房也設在這裡。
前院最美麗的風景是那兩棵至少有百多年樹齡的老樟樹,翁鬱挺拔,歷經滄桑依然活得生機勃勃,且終年飄溢著特有的清香。後院小一些,卻相當精緻。花窗假山一如既往,一小溜粉牆雖然青苔斑駁,反襯出一種特別的韻味。花草滿徑的碎石小道曲曲彎彎地漫上一座小土丘,丘上的「清秋亭」有待修葺且已塌了一個角,但老畫家手書的那三個蒼勁飽滿的大字依然清晰可辯。
平時,在食堂吃過晚飯後,秦義飛常常獨自登上後院的清秋亭,有時還攀上亭後的土山頂端,久久眺望院牆外的風光,心中隱約驛動著蠢蠢的豪情。
科技館樓房不高,院落裡的樹木又很密集,因此樓裡的採光就成了問題,白天都常常需要開燈的樓道,陰冷而潮濕,其長度差不多相當於兩三節連接在一起的火車車廂。「車廂」的通道尚算寬敞,面對面排列著兩排每間二十平米左右的房間。
秦義飛就棲身於西邊倒數第二間朝南的辦公室裡。房間靠窗處放著張辦公桌,邊上有兩張黃褐色的舊皮沙發和一個漆皮差不多磨盡了的木茶几。緊挨沙發處安了一張床,床對面則是兩個鐵皮文件櫃。床自然是秦義飛的,那張辦公桌卻是汪館長的。秦義飛所在的宣傳科連他共擠了三個人,加上資料櫃之類,因此不可能再放下一張床。秦義飛初來的兩個月睡的都是地鋪。後來汪館長就讓他在自己獨用的辦公室安了張木床。白天他把被褥卷起來放上檔櫃頂,汪館長下班後再拿下來鋪在床上。館長辦公室就成了他的「家」。
三
三天前的下午,因為是週末,手頭沒什麼事,汪館長又出差不在,秦義飛就溜回住處看書。就在這時,那女孩出現在門口。
聽到響動,秦義飛轉過身來,兩人的目光剛好撞在一起。女孩明顯怔了一下,隨即哈了哈腰:「館長,你好。」
秦義飛趕緊聲明館長不在,自己是宣傳科的,暫住在這裡而已。並問女孩找館長有什麼事。女孩的神情輕鬆了許多,她吐了下舌頭,眸子閃閃地嬉笑道:「我說這個館長怎麼這麼年輕呢。」
秦義飛招呼她坐,她也就大大方方地在秦義飛對面坐了下來,說:「我來這裡是想看看,你們有沒有什麼科普方面的資料。天文、地理,或者百科知識之類,隨便什麼都可以;有的話我想借一些,或者買一些……不,雖然我平時也喜歡看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想些怪七怪八的問題,但我今天是為我父親來的。他在廠裡出了工傷,躺在床上兩個多月了。你可以想像他有多麼無聊。他平時什麼愛好也沒有,就是特別喜歡這類知識,而且還寫了不少科普文章。他還在《藩城日報》發表過好些篇作品呢。」
「哦,請問你父親叫什麼名字?說不定我也看過他的文章呢?」
「他叫徐方向。發表文章時就叫方向。」
哦!秦義飛立刻想起了方向這個名字。《藩城日報》的科技版他是常看的,方向這個名字又很大氣,所以容易記住。但印象中這個方向。發表的似乎都是些有關生活或科技類的小知識,如吃蘋果削皮好還是不削皮好,扇子或房子是誰發明的,一年二十四節氣的來歷之類。但他還是表示讚許地點頭道:「是有印象,我看過他不少文章。」
「這麼說,你又是科技館的,一定也寫過好多文章吧?你能告訴我你的名字嗎?說不定我也看過你的文章呢?」
「我叫秦義飛。文章嘛,倒也算是寫過點。筆名就叫義飛。」
女孩一下子挺直起了身子:「真是太榮幸了,原來你就是義飛老師啊?一點不騙你,我就是看過你的文章。你寫的才真叫科普文章呢。尤其是一篇關於彗星的文章,我還把它剪下來了。因為我從小就對彗星有一種特別特別的感情。我的名字叫徐曉彗。原來不是彗星的彗,而是智慧的慧。高一時我自作主張把它改成了彗星的彗……你還不能理解嗎?彗星的形象多麼美妙呵?其他星辰看上去都亮晶晶的,其實卻傻傻地、一覽無餘地天天待在原地,千年萬年,寸步不移,太沒勁了……」
「我可以插你一句嗎?星辰可不是一動不動的。浩瀚宇宙中就沒有靜止的物體。所有星辰,一切天體,不管是恆星還是行星,還有哪怕是細小到肉眼根本無法辨識的塵埃,每時每刻都在劇烈地永恆地運動著,旋轉著、變化著,分裂著或積聚著,循環往復,乃至無窮。所謂不動,只是我們觀察者的一種錯覺或者無知而已……」
「這個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說的是從表面現象上看,它們不是都好像一動不動的嗎?可彗星就不是那樣的啊,我特別喜歡的就是她自由自在,特立獨行,來如風去如電的瀟灑形象。而且,你不覺得彗星特別美麗、特別清高,特別自由、而且還特別神祕而孤傲嗎?一個人要能活得像彗星那樣,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不是特別有意思嗎?」
彗星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乃至普通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歷來是很不妙的,諸如掃帚星、會帶來晦氣或厄運等等無稽之談由來已久。而眼前這個看起來個子矮小卻頗有心氣的女孩,獨能有這樣一種很不一般的認識,不由得讓秦義飛刮目相看。
但也許是出於對科學的尊崇感,又多少也有些賣弄的欲望在吧,他還是忍不住又給徐曉彗潑了點冷水:「我很欣賞你的浪漫,可是……彗星可不像你想像的那樣浪漫、瀟灑;甚至,它和別的星辰一樣,是決無所謂自由可言的。首先,她也有固定的運行軌道,受制於星球間的引力,因而她的來去也有軌道和週期限制的。還有,彗星在古人眼裡可不是個討人喜歡的形象。你應該知道,她就是所謂的掃帚星,是不吉利的象徵;古人由於缺乏天文知識,總是將她與地球上的災難、戰爭等聯繫起來……」
「我才不信這一套呢!」徐曉彗略顯蒼白的臉上泛起兩酡紅暈,纖細的雙手也大幅度地比劃起來:「老實說,我才不管它什麼好的壞的呢,我就想要做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秦義飛對她的想法和率直頗覺驚訝,但臉上沒有流露出來:「像你這樣有個性的女孩,我還是第一次遇見呢。」
徐曉彗更加眉飛色舞,幾乎不假思索便地接道:「像你這樣有知識又……那個的人,我也是第一次遇見呢。我可以問問你是哪一年出生的嗎?」
「我是一九五四年出生的。」
「哦,我是一九六○年出生的。秦老師你這麼有知識,有思想,起碼應該是大學畢業生吧?」
「應該算是吧。你呢?」
「唉,現在後悔也不及了。從小我爸就怪我太愛幻想,好高騖遠,對周圍的生活和俗人從來都看不上眼,也太不把學習當回事了,結果讀到高中也勉勉強強……不過也有個原因是,我媽退休了,按政策可以頂替一個子女,家裡就讓我頂替她進了人民商場。我一點也不喜歡這個工作,更不喜歡周圍那些婆婆媽媽的小市民,我簡直厭煩透了。今天能碰見你,真是太幸運了!」
四
門鎖碰上的聲音很輕微。但那堅定的喀嗒一響,卻如引信般,驟然引爆秦義飛胸中某種久抑的欲望。周身的血液突然被一股神祕的火苗點燃般,呼呼騰湧,頭腦裡也彷彿灌下一大口烈酒般溫和而暈眩起來。
當時兩個人靠得是那麼近,以至徐曉彗轉過頭來的時候,那幾根輕輕掠過他鼻翼的髮絲,那一縷久違的、令他分外渴望又有幾分畏懼的異性的體息,也讓他不多一會前還彷彿已虛無而枯萎的情懷,突然像春花怒放的山谷般繁華而絢爛。
這麼個岑寂的夜晚,這麼個神祕的雪夜,這麼個精靈般熱情而率真、大膽地突然降臨的女孩!
秦義飛差點就伸出手去,將徐曉彗攬入懷中。但實際上,他卻是大大地後退了一步,轉身到桌上抓起暖水瓶,要給徐曉彗倒茶。「外面一定很冷吧?」他的嗓音也多少有些顫抖起來。
「不要不要。我不喝水。」徐曉彗緊跟著他來到桌前,伸手按住暖瓶不讓他倒水。兩人的手相距那麼近,差點就碰在一起了。秦義飛只要一翻掌就能輕易地握住她的手。秦義飛也注意到她的手是那麼的纖細嬌嫩,只是上面明顯有兩朵早春初綻的紅梅般的凍斑。他的心又悸動了一下,憐愛之情油然:「你穿得太少了吧?看都生凍瘡了。」
徐曉彗縮回手去,輕輕撫揉著,卻不說話,又像那天下午一樣,熱烈而專注地凝視秦義飛。灼灼目光裡分明吐露著無窮的意味。秦義飛有些發窘地避開她的注視,一時也不知再說什麼好,竟又下意識地伸出手去。但手掌在半路上又轉了個向,直接掠過徐曉彗的頭頂,又收回自己的頸前。似乎他是要比劃一下兩人的身高:「你好像有……」
「一米六。」徐曉彗順勢站到秦義飛身前:「我是不是太矮了點?」
「不矮不矮。我也只有一米七八。」
徐曉彗似乎有點不相信,她誇張地掂起腳來,抬手按在秦義飛頭上,往自己身上一劃,兩人變得差不多高了。徐曉彗咯兒一聲笑了,秦義飛心裡又湧過一陣暖流,卻仍然有些拘謹,平時的伶牙俐齒像是被什麼風給吹走了,只會再一次請徐曉彗坐下來。徐曉彗卻還是搖搖頭站著不動,並且又不說話了,只是一個勁地盯著他微笑。秦義飛這才注意到她的面頰兩面,也各有一個角幣般大小的凍瘡斑,在發燒般紅潤的臉色和柔和的燈光襯映下,兩朵桃花般別有種異樣的魅力。他的心也因此而又哆嗦了一下:「你真要多穿點衣服呢。外面在下雪呢。」
徐曉彗卻不出聲了。
「一會兒你怎麼回去呢?哦,我是說,我真沒想到……你找我有什麼事嗎?」
身後還是沒有回音。秦義飛偏過頭來,目光正好撞在徐曉彗灼亮的眸子上,那麼熱切而灼烈的目光,那麼純真而動人的笑容──
「那天我回家後,一直都想你的……」徐曉彗的聲音很輕,吐字卻分外清晰,剎時像一根高舉的鼓捶重重地擂在了秦義飛的心坎上。但他更加不知所措了,半晌才期期艾艾地哦了一聲。
徐曉彗又逼近他一步:「你不相信嗎?」
秦義飛還是回避著徐曉彗的目光,卻點了點頭。
「你呢?」
秦義飛猛地張開雙臂,將徐曉彗攬入了懷中。這才發現,徐曉彗的臉頰火一般發燙,身子也觸了電般一瞬瞬地痙攣著,以至她那細碎而白潔的牙齒也在發出輕微的磕碰聲。
窗外的雪花好像在竊竊地笑。雪片裡夾著細碎雪粒,撲簌撲簌地打在窗玻璃上的聲音,在這萬賴俱寂的靜夜,聽起來分外真切、多情。
這個雪夜如此溫馨。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無語凝噎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301 |
華文創作 |
$ 322 |
中文書 |
$ 340 |
中文現代文學 |
$ 378 |
小說 |
$ 387 |
小說 |
$ 387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43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無語凝噎
◆ 改編自真人真事,卻有著超現實的衝擊性結局,幾乎令人無法想像!
◆ 從戲劇化的人設,借鏡真實生活中的你我他:當逆來順受的軟弱性格,遇上極致佔有的侵略型人格──最具勸世效果的對比組合。
◆ 劇情媲美翻譯小說《控制》,真實呈現兩性關係當中最驚悚、最糾葛的一面。
一段絕無僅有、結局完全出人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的都市愛情故事,時間跨度長達30年,這是最糾葛也最真實的愛。
「我——愛——你」
她那從一開始就顯露無遺的明快、果敢,並由此而形成的理所當然的姿態,以及她性格中某種似乎是先天即具的獨斷特質,對始終不認為自己軟弱或黏糊的他來說,卻形成一種無形的制約力。
他雖已隱隱感覺到,表面看去天真無邪、嬌柔而率真的她,其性格的內層或許並不柔軟或簡單。但此時他仍然沒有意識到,她實質上個性及意志中的剛烈、執拗與頑韌,決不亞於那些飽經風吹浪打的礁岩,或裸露於浪灘邊那些久經磨礪的老樹的氣根。
那些扭曲、晦暗、如霧裡看花的精心布局,原來是她的愛。
作者簡介:
姜琍敏
中國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協會員。原任江蘇作協小說創作委主任、《雨花》主編。現為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江蘇省散文學會會長。江蘇作協理事、《江蘇散文》主編。1976年迄今,在《人民文學》、《當代》、《十月》等全國各地報刊發表各種文學作品約500萬字。部分作品被新文學大系及各種選刊、年選本廣泛選載。
主要出版品: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隨筆集《不幸的幸運兒》、《憤怒的樹林》、《美麗的戰爭》、《叫我如何不執著》、《紅蝴蝶》等14部;長篇小說《多伊在中國》、《女人的宗教》、《華麗洋商》、《泡影》等10部。
得獎紀錄:散文集曾獲中國冰心散文獎;長篇小說曾獲省五個一工程獎、並曾獲紫金山文學獎中篇小說獎、長篇小說獎及其它各類獎勵數十項。有作品譯介國外。
章節試閱
【第一章】 這個雪夜如夢似幻
一
一九八○年的最後一天,整個白天都陰霾沉沉,藩城彷彿還浸淫在昨夜的夢裡。但給人的感覺還是相當溫暖的。風很微弱,蒼白的冬陽上午還短暫地露過幾次臉,中午起就深囚於逐漸增厚的雲層中,掙不出來了。天色因此比平時暗得早,到秦義飛從食堂吃過晚飯回寢室的時候,大院裡已經黑透了。
他坐在岑寂的辦公桌前,發了好一會呆,不知道該怎麼打發接下來的漫漫長夜。每天的這個時候都是最讓他感覺到無聊和孤獨的。頭腦有點昏沉,心裡空落落的,但睡覺時間還早得很。看點書吧,一時還打不起精神。走親訪友...
一
一九八○年的最後一天,整個白天都陰霾沉沉,藩城彷彿還浸淫在昨夜的夢裡。但給人的感覺還是相當溫暖的。風很微弱,蒼白的冬陽上午還短暫地露過幾次臉,中午起就深囚於逐漸增厚的雲層中,掙不出來了。天色因此比平時暗得早,到秦義飛從食堂吃過晚飯回寢室的時候,大院裡已經黑透了。
他坐在岑寂的辦公桌前,發了好一會呆,不知道該怎麼打發接下來的漫漫長夜。每天的這個時候都是最讓他感覺到無聊和孤獨的。頭腦有點昏沉,心裡空落落的,但睡覺時間還早得很。看點書吧,一時還打不起精神。走親訪友...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這個雪夜如夢似幻
第二章 一步錯步步錯
第三章 恭喜你,你做父親了
第四章 「芳草盡成無意綠」
第五章 「夕陽都作可憐紅」
第六章 慈母手中線
第七章 崩潰
第八章 恭喜你,你當爺爺了
第九章 叫兒子太沉重
第十章 天哪天哪我的天哪
第二章 一步錯步步錯
第三章 恭喜你,你做父親了
第四章 「芳草盡成無意綠」
第五章 「夕陽都作可憐紅」
第六章 慈母手中線
第七章 崩潰
第八章 恭喜你,你當爺爺了
第九章 叫兒子太沉重
第十章 天哪天哪我的天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