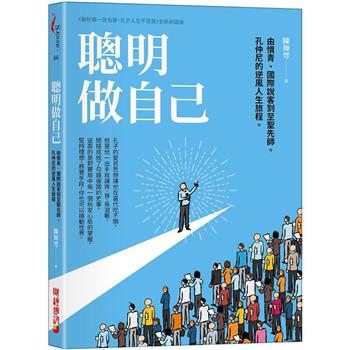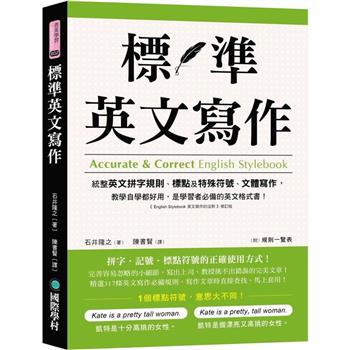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我的精神病姊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38 |
小說 |
$ 255 |
中文書 |
$ 269 |
中文現代文學 |
$ 299 |
小說 |
$ 299 |
Literature & Fiction |
$ 306 |
小說 |
$ 306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40 |
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我的精神病姊姊
真人真事改編:一對情同手足的姐妹,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一段為了至親而奮鬥的故事。
余家大姊韻亞自幼心地善良、外貌出眾。她不只是眾人矚目的校花,更拿了獎學金出國深造,本以為一切能從此平步青雲,卻沒有想到一切都在韻亞到了美國後變調。韻亞開始變得瘋瘋癲癲、不受控制,既難以溝通也無法照顧自己。醫生診斷她得了嚴重的精神疾病:花癲。面對韻亞愈發加重的病情,房東只想趕她走、朋友也紛紛疏遠她,親戚與家人們更都避之唯恐不及。
願意承擔照顧韻亞責任的,只有小她十一歲的妹妹醒亞。醒亞從此開始了照顧姊姊的美國生活,這一照顧就是數十年。在老公的不諒解與兒子成長過程需要陪伴的雙重壓力下,她該如何在自身的家庭與長期照顧姊姊的無底洞中抉擇?她又該如何追尋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