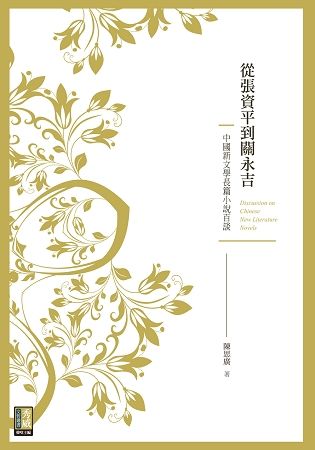▍從《沖積期化石》到《貓城記》,從《財主底兒女們》到《子夜》,選取具代表性的近八十部作品,剖析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年間中國新文學長篇小說呈現的歷史樣態及文學意涵。
中國新文學肇始於一九一五年的新文化運動,自一九二二年出現現代文學第一部白話長篇小說:張資平《沖積期化石》,至一九四九年王林出版的《腹地》這段期間,共出版了新文學長篇小說三百餘部。
作為時代生活重要載體之一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反映著不斷變化的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時代訴求。《沖積期化石》將「人的文學」這一新文學的革命主張真切地落實在長篇小說,表現人面對命運與既有秩序的抗爭態度與不屈精神。「革命加戀愛」小說一度成為二○年代末三○年代初左翼文學的創作主潮,藉此可瞭解革命文學的書寫模式。《科爾沁旗草原》、《財主底兒女們》等作品更反映出三○至四○年代不斷上升的民族及階級矛盾。《戰血》、《大上海的毀滅》、《間諜夫人》等書則忠實記錄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那段戰火紛飛的時代。
本書選取新文學中具代表性的近八十部作品,以個案分析形式,分「文學‧時代」、「戰爭‧歷史」、「借鏡‧融創」、「傳播‧接受」、「文體實踐」及「文學徵文」六大部分,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向讀者介紹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在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這二十七年間所呈現的歷史樣態及文學意涵。
本書特色
從《沖積期化石》到《貓城記》,從《財主底兒女們》到《子夜》,選取具代表性的近八十部作品,剖析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年間中國新文學長篇小說呈現的歷史樣態及文學意涵。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從張資平到關永吉:中國新文學長篇小說百談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73 |
華文文學研究 |
$ 292 |
中文書 |
$ 308 |
中國文學總論 |
$ 308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43 |
華文文學研究 |
$ 351 |
文學作品 |
電子書 |
$ 390 |
文學研究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從張資平到關永吉:中國新文學長篇小說百談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思廣
文學博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文系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小說及作家作品研究。著有:《戰爭本體的藝術轉化──20世紀下半葉中國戰爭小說創作論》、《審美之維──中國現代經典長篇小說接受史論》、《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四川抗戰小說史(1931-1949)》、《身份的印跡──中國文學論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傳播與接受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鑒識》、《現代長篇小說邊緣作家研究》等。
陳思廣
文學博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文系教授,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小說及作家作品研究。著有:《戰爭本體的藝術轉化──20世紀下半葉中國戰爭小說創作論》、《審美之維──中國現代經典長篇小說接受史論》、《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四川抗戰小說史(1931-1949)》、《身份的印跡──中國文學論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傳播與接受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鑒識》、《現代長篇小說邊緣作家研究》等。
目錄
序「秀威文哲叢書」/韓晗
引言
【第一輯 文學‧時代】
《沖積期化石》:新文學第一部長篇小說
新文學第二部長篇小說:王統照的《一葉》
革命浪漫主義文學的濫觴之作:張聞天的《旅途》
張資平的代表作《苔莉》
《最後的幸福》:張資平小說的滑坡信號
孫夢雷和他的《英蘭的一生》
《老張的哲學》:寂寞之餘的收穫
一部不該忽略的長篇小說:談黃心真的《罪惡》
一個畸形的有違倫理的戀情故事:洪靈菲的《轉變》
章克標和他的獵豔小說《銀蛇》
《二月》:1920年代最出色的長篇小說
兩部表現南洋教育生活的長篇小說
楚洪的《愛網》
《地泉》:「『不應當這麼樣寫』的標本」
《貓城記》:老舍的轉向之作
《新生代》:活的歷史
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
詩意的與感傷的:談《呼蘭河傳》
蘆焚‧師陀‧《結婚》
青春的詩:《財主底兒女們》
【第二輯 戰爭‧歷史】
《蝕》之思,《蝕》之惑
被魯迅誤讀的《大上海的毀滅》
東北抗戰文學的先聲之作《萬寶山》
《戰血》:血淚寫就的一部義勇軍抗敵史料
戰爭是可以感化人的:談歐陽山的《戰果》
《鴨嘴澇》:抗戰初期民眾覺醒的心靈史詩
報業人的小說:崔萬秋的《第二年代》
「被色情」的小說:談荊有麟的《間諜夫人》
《三年》:華北淪陷區長篇小說的破寂之作
《蘋果山》啊,蘋果山
《蓉蓉》:華北淪陷區最優秀的長篇小說
「古城文學家」趙蔭棠和他的《影》
吳調公‧丁諦與《前程》
《霧都》:陪都另類生活的歷史鏡像
《女兵自傳》是這樣寫成的
【第三輯 借鏡‧融創】
《飛絮》:張資平的「起飛」之作
天之故?人之禍?:談陳銓的《天問》
大膽的嘗試與最後的絕唱:談蔣光慈的《麗莎的哀怨》
《愛力圈外》:張資平的另一部改寫之作
《八月的鄉村》:中國的《毀滅》
《馬丹波娃利》與《死水微瀾》
康拉德的恩惠:《駱駝祥子》的影響探源
三讀契訶夫之後:談《寒夜》的師法與融創
【第四輯 傳播‧接受】
福緣與福分:魯迅與葉永蓁的《小小十年》
儁聞‧沈從文‧《幽僻的陳莊》
差點被「腰斬」的《家》
《子夜》的刪節本
「削除濟」與偽滿刪禁的兩部長篇小說
《駱駝祥子》的版次及其意涵
《綠色的穀》:險遭日偽查禁的鄉土小說
《圍城》出版初期的臧否之聲
《困獸記》的初版本與修訂本
寫什麼與怎樣寫:談柳青的《種穀記》
反常的與正常的:王林《腹地》的命運
【第五輯 文體實踐】
黃俊與他的《戀愛的悲慘》
抑鬱兒童‧愚昧惡母‧短制長篇:談超超的長篇小說《小雪》
一部對話體長篇小說:黃中的《三角戀愛》
「往下寫」會如何:談沈從文的《阿麗思中國遊記》
《曼娜》:第一部書信體長篇小說
一部宣洩個人不幸情感的愛的癡狂曲:彭芳草的《落花曲》
開一代文風的《橋》
萬迪鶴和他的《中國大學生日記》
文獻體寫作:優乎?劣乎?──談李劼人的《大波》
似巧實拙之作:列躬射的《白莎哀史》
【第六輯 文學徵文】
創造社的長篇小說徵文與獲獎小說
良友文學獎金徵文與獲獎長篇小說
文協長篇小說徵文與獲獎小說
鮮為人知的「朱胡彬夏文學獎金」
「盛京文學獎」的獲獎長篇:《北歸》
《大地的波動》:徹頭徹尾的漢奸小說
沒有頁碼的長篇小說:《路》
門生和老婆的代表們:談「大東亞文學獎」的爭議之作《貝殼》
特定歷史階段即生即滅的藝術泡沫:《國民雜誌》第一次長篇小說徵文的獲獎作品
矮子裡的將軍:《牛》
引言
【第一輯 文學‧時代】
《沖積期化石》:新文學第一部長篇小說
新文學第二部長篇小說:王統照的《一葉》
革命浪漫主義文學的濫觴之作:張聞天的《旅途》
張資平的代表作《苔莉》
《最後的幸福》:張資平小說的滑坡信號
孫夢雷和他的《英蘭的一生》
《老張的哲學》:寂寞之餘的收穫
一部不該忽略的長篇小說:談黃心真的《罪惡》
一個畸形的有違倫理的戀情故事:洪靈菲的《轉變》
章克標和他的獵豔小說《銀蛇》
《二月》:1920年代最出色的長篇小說
兩部表現南洋教育生活的長篇小說
楚洪的《愛網》
《地泉》:「『不應當這麼樣寫』的標本」
《貓城記》:老舍的轉向之作
《新生代》:活的歷史
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
詩意的與感傷的:談《呼蘭河傳》
蘆焚‧師陀‧《結婚》
青春的詩:《財主底兒女們》
【第二輯 戰爭‧歷史】
《蝕》之思,《蝕》之惑
被魯迅誤讀的《大上海的毀滅》
東北抗戰文學的先聲之作《萬寶山》
《戰血》:血淚寫就的一部義勇軍抗敵史料
戰爭是可以感化人的:談歐陽山的《戰果》
《鴨嘴澇》:抗戰初期民眾覺醒的心靈史詩
報業人的小說:崔萬秋的《第二年代》
「被色情」的小說:談荊有麟的《間諜夫人》
《三年》:華北淪陷區長篇小說的破寂之作
《蘋果山》啊,蘋果山
《蓉蓉》:華北淪陷區最優秀的長篇小說
「古城文學家」趙蔭棠和他的《影》
吳調公‧丁諦與《前程》
《霧都》:陪都另類生活的歷史鏡像
《女兵自傳》是這樣寫成的
【第三輯 借鏡‧融創】
《飛絮》:張資平的「起飛」之作
天之故?人之禍?:談陳銓的《天問》
大膽的嘗試與最後的絕唱:談蔣光慈的《麗莎的哀怨》
《愛力圈外》:張資平的另一部改寫之作
《八月的鄉村》:中國的《毀滅》
《馬丹波娃利》與《死水微瀾》
康拉德的恩惠:《駱駝祥子》的影響探源
三讀契訶夫之後:談《寒夜》的師法與融創
【第四輯 傳播‧接受】
福緣與福分:魯迅與葉永蓁的《小小十年》
儁聞‧沈從文‧《幽僻的陳莊》
差點被「腰斬」的《家》
《子夜》的刪節本
「削除濟」與偽滿刪禁的兩部長篇小說
《駱駝祥子》的版次及其意涵
《綠色的穀》:險遭日偽查禁的鄉土小說
《圍城》出版初期的臧否之聲
《困獸記》的初版本與修訂本
寫什麼與怎樣寫:談柳青的《種穀記》
反常的與正常的:王林《腹地》的命運
【第五輯 文體實踐】
黃俊與他的《戀愛的悲慘》
抑鬱兒童‧愚昧惡母‧短制長篇:談超超的長篇小說《小雪》
一部對話體長篇小說:黃中的《三角戀愛》
「往下寫」會如何:談沈從文的《阿麗思中國遊記》
《曼娜》:第一部書信體長篇小說
一部宣洩個人不幸情感的愛的癡狂曲:彭芳草的《落花曲》
開一代文風的《橋》
萬迪鶴和他的《中國大學生日記》
文獻體寫作:優乎?劣乎?──談李劼人的《大波》
似巧實拙之作:列躬射的《白莎哀史》
【第六輯 文學徵文】
創造社的長篇小說徵文與獲獎小說
良友文學獎金徵文與獲獎長篇小說
文協長篇小說徵文與獲獎小說
鮮為人知的「朱胡彬夏文學獎金」
「盛京文學獎」的獲獎長篇:《北歸》
《大地的波動》:徹頭徹尾的漢奸小說
沒有頁碼的長篇小說:《路》
門生和老婆的代表們:談「大東亞文學獎」的爭議之作《貝殼》
特定歷史階段即生即滅的藝術泡沫:《國民雜誌》第一次長篇小說徵文的獲獎作品
矮子裡的將軍:《牛》
序
引言
中國新文學肇始於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發端於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反帝反封建的吶喊,使中國新文學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迅速邁向了與世界融合的步伐,中國現代文學也因之翻開了偉大而嶄新的一頁。
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與時代同脈,雖然1922年才開始出現現代文學第一部白話長篇小說,但27年的發展實績證明,它毫無愧色地成為20世紀最為顯赫的文學部門之一。不過,談到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卻首先要面臨一個如何界定現代長篇小說的問題。也就是說,什麼樣的小說才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對此,筆者採用目前較為通行的斷定方式予以認定,即:以文體的形式與長度作為判斷長篇小說的核心標準。也就是說,凡作者用現代白話文的形式創作的有一定長度的小說就被認可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而通常人們所說的長篇章回小說與通俗小說就不作為本書的敘述範圍了。
我們知道,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新文學關於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並無明顯的界限,早期的出版者常常將五-六萬字以上的小說均標注為長篇小說出版,如小雪的《超超》(1926)、黎錦明的《蹈海》(1929)等,也有將超過六萬字的小說當作中篇小說來印行的,如芳草的《管他呢》(1928)等。不過,在1927年創造社進行長篇小說徵文時,對長篇小說的合格字數要求是:「六萬字以上」。這一文體長度在今天看來顯然只是一個小中篇,但在當時卻是一部長篇了。而1936年「良友文學獎金徵稿」與1939年「文協」徵文時,對長篇小說的合格字數要求則是:「十萬字以上」。因此,為尊重歷史起見,也充分考慮新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文體長度統一大體為,1920年代以創造社長篇小說徵文的約定字數為限,1940年以後以「文協」長篇小說徵文所約定的字數為據,中間的年份(1930-1939)則取其中,也就是說,從六萬字起,每一個十年增加二萬字。即:1922-1929年:六萬字以上;1930-1939年:八萬字以上;1940-1949年:十萬字以上。當然,這並非絕對的一刀切,如果字數相差不大,或略少於規定字數,但只要具備長篇小說的審美特徵,也認可為長篇小說。這樣,依此標準,自1922年2月15日張資平出版《沖積期化石》至1949年9月30日王林出版《腹地》期間,新文學共出版長篇小說近三百部(三部曲若合名出版則以一部計,如茅盾的《幻滅》、《動搖》、《追求》不作為三部長篇小說,而認作一部《蝕》等)。雖然年均十餘部左右的數量在今天看來有些不可思議,而它們中的大部還將最終走入歷史的深處,但作為一個時代的忠實記錄,卻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學價值,其中的經典則彰顯出新文學偉大的歷史功績,矗立起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文學豐碑。
文學是時代的晴雨錶。作為時代生活重要載體之一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當然反映著不斷變化的20世紀上半葉的時代訴求。從第一部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開始將「人的文學」這一新文學的革命主張真切地落實在長篇小說領域以來,表現人生,表現人面對命運與既有秩序的抗爭態度與不屈精神,就成為現代長篇小說家們的自覺追求。有個性的複雜人物的描寫,雙重人性的透示特別是對人的自身弱點所釀成的悲劇的批判,人的多重意識世界的揭示以及在雙重文化的燭照中透視國民的靈魂等藝術特質,使它和舊文學徹底區別開來,並真正邁開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現代化的步伐。《一葉》、《苔莉》、《英蘭的一生》、《罪惡》、《二月》等可視為其中的代表。受國際國內環境的影響,「革命加戀愛」小說一度成為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翼文學的創作主潮,我們這裡選擇了《旅途》、《轉變》、《地泉》等作為個案,既可瞭解革命文學的書寫模式,也可瞭解革命文學有待總結的經驗與教訓。這一時期還值得關注的是域外題材的小說創作,它們所呈現出的廣闊的時空背景,無疑擴大了新文學的表現視閾。馬仲殊的《太平洋的暖流》和林參天的《濃煙》,即可作如是觀。當然,30-40年代也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不斷上升的時代,也是革故鼎新、自強新生的時代,《新生代》、《科爾沁旗草原》、《財主底兒女們》等作品,就是這一時代鏡像的文學再現。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戰火紛飛,戰爭考驗著時代,歷練著人心,也鍛造著文學。從「九‧一八」東北事變到「七‧七」盧溝橋事件,抗戰的烽火點燃了中華民族爭取獨立,保家衛國的堅強決心,點燃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捍衛民族尊嚴的不屈意志。在血與火的洗禮面前,在靈與肉的搏戰時刻,各民族、各黨派、各武裝力量紛紛集結在抗日的旗幟下,開始了長達十四年艱苦卓絕的團結禦侮、浴火重生的大決戰,也譜寫了中華民族邁向新生、走向自強的偉大篇章。《戰血》、《大上海的毀滅》、《萬寶山》、《鴨嘴澇》、《蘋果山》、《戰果》、《間諜夫人》、《第二年代》等,就是這一輝煌歷史的忠實記錄。當然,由於中國國力的衰落以及其他諸種因素,中國戰區在這場反法西斯戰爭中,形成了東北淪陷區、華北淪陷區和華東淪陷區及以重慶陪都為中心的西南大後方的戰時格局,也因之形成了不同地區獨特的文學風貌。《三年》、《蓉蓉》、《影》、《前程》、《霧都》等就反映了各自戰區不同的文學特徵,也成為那個特殊時代的文學略影。當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戰火還包括震動世界的中國革命戰爭,我們頭尾各選取了一部在現代文學史上影響較大的作品──《蝕》與《女兵自傳》,意在留住那個時代的一側面,也留住那個時代的文學一側影。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開放進取,充滿活力,各種思想紛至遝來,長篇小說家們以西方現代思想與文學觀念為借鏡,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現代化注入了生機。不過,最初一段時間的借鑒往往帶有模仿、橫移的痕跡,如《八月的鄉村》,雖然也不乏《天問》那樣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下有所創新者,但畢竟是少數。至於像張資平這樣的作家以改寫代替創作以博文名,如《飛絮》、《愛力圈外》等,更是文學界的敗類。這只能糊弄一時而不能糊弄一世。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作家則在借鑒世界文學大師豐富營養的基礎上吐故納新,創作出屬於他們自己同時也屬於中國甚至屬於世界的傑作。《死水微瀾》、《駱駝祥子》、《寒夜》、《圍城》即是其中的代表。這也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邁向現代化征程的必然之旅。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文學生態環境複雜多樣,長篇小說的傳播與接受也各顯特點。我們在這裡選取了四種類型:獎掖扶持型、官方查禁型、文藝爭鳴型、《講話》轉軌型予以透視,以使讀者對當時的傳播接受生態有初步的瞭解。我們知道,對於初出茅廬的青年作者而言,由於寫作技巧較為粗淺,藝術水準較為稚嫩,往往容易遭受歧視,他們自然渴望得到文壇名宿的慧眼相識,以邁出走向文壇的第一步甚至脫穎而出。王林、葉永蓁等就是其中的幸運兒與佼佼者,他們的長篇小說創作也因之顯出成色。查禁是歷代統治者鉗制文化的一種官方策略,國民黨也不例外。據統計,27年間,《子夜》、《綠色的穀》等約有四十部長篇小說遭到不同程度的查禁,它們對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由於被禁毀,《子夜》的刪節版到底是怎樣的,無人知曉,以至於成為現代文學界版本研究中一個懸而未決的疑案。《〈子夜〉的刪節本》一文徹底解決了這一懸案,也算是解決了茅盾研究界的一個重要問題。《駱駝祥子》與《圍城》堪稱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發展史上重要收穫,對它們的不同解讀本是正常的文學批評,但由於特殊的時代語境與文學生態環境,它們的某種有價值的視野或被遮蔽,或被噤聲,在去魅的時代當然應該還歷史以本來面目。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文藝工作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以後,延安解放區的文藝工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寫什麼與怎樣寫在隨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黨的文藝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反常的與正常的也就成為創作轉型期一種最為常見的接受樣態。《種穀記》與《腹地》就是這一類型具有代表性的一個樣板。不過,它們留給我們的教訓也極為深刻。
現代長篇小說應該如何寫?現代長篇小說究竟有沒有統一的文體樣態?先驅者在努力嘗試著,實踐著。初期的寫作者並沒有明確的長篇小說文體意識,甚至以為一般的日記彙編成長的小說就是日記體長篇小說,有的作者以整體人物對話的方式構建長篇小說新文體,還有的作者嘗試以童話的文體續寫批判性的長篇小說等。30年代後,書信體小說蔚然成風,許多作者將書信有機地彙集在一起,穿插於一定的人物與情節,組構成一部書信體長篇小說,有的還頗有文學意味,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文體實踐潮。故而有的作者嘗試以文獻體的方式補充長篇小說的文體構成,有的作者以混合體的方式即將全書分為上中下三部,第一部是散文,第二部是書簡,第三部又是日記;或分為上下兩部,上部為書信,下部為敘述文體,拓新長篇小說的文體疆域。只是,這類文體實驗的失遠大於得。那麼,這一時期文體實踐的最大亮點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嘗試是什麼呢?是詩體長篇小說的實踐。典型的代表是廢名的《橋》。《橋》詩境,畫意,禪趣,交相輝映,相得益彰,開一代文風,對中國抒情小說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僅就長篇小說而言,蕭紅的《呼蘭河傳》、艾蕪的《豐饒的原野》以及孫犁的《風雲初記》等,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美麗的風景。當然,如何以詩的方式藝術地精湛地構建以敘事為主體的長篇小說,需要長篇小說家不懈的探索。
同樣,在1922-1949年間,不同組織與機構還舉辦了大量的長篇小說徵文活動,對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復興與發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從最初創造社的長篇小說徵文到之後的良友、文協徵文以及個人名義舉辦的「朱胡彬夏文學獎金」等,都對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當然,30年代後,在東北淪陷區與華北淪陷區,日偽統治者也先後舉辦了多種形式的長篇小說徵文活動,也評選出了幾部獲獎作品。但客觀地說,這些作品除個別小說外,大部分作品均是替日偽統治者塗脂抹粉之作,是典型的漢奸小說,是特定歷史階段即生即滅的藝術泡沫。不過,它們作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應為人們所探討,為歷史所總結。這也是我們專列「文學徵文」為一板塊的重要原因。
所有這一切,構成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歷史長河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也反映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演變發展的基本史貌。也因此構想,本書選取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近八十部作品,以個案分析的形式,分「文學‧時代」、「戰爭‧歷史」、「借鏡‧融創」、「傳播‧接受」、「文體實踐」及「文學徵文」六個板塊,以圖文並茂、返歸歷史現場的方式,向讀者介紹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在1922至1949這27年間所呈現的歷史樣態,所走過的歷史道路,所彰顯的審美意涵。在介紹過程中,筆者力求點面結合,雅俗共賞,為學界也為收藏界及廣大文學愛好者提供史的印痕,美的啟迪。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具有某一特質的文學作品不獨是該板塊的這幾部作品,只是為了更好地使讀者瞭解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全貌,也為了全書各章節的相對均衡,筆者將其分置於相應的板塊中了。如果讀者朋友們能從中窺一斑而知全貌,那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
序「秀威文哲叢書」
自秦漢以來,與世界接觸最緊密、聯繫最頻繁的中國學術非當下莫屬,這是全球化與現代性語境下的必然選擇,也是學術史界的共識。一批優秀的中國學人不斷在世界學界發出自己的聲音,促進了世界學術的發展與變革。就這些從理論話語、實證研究與歷史典籍出發的學術成果而言,一方面反映了當代中國學人對於先前中國學術思想與方法的繼承與發展,既是對「五四」以來學術傳統的精神賡續,也是對傳統中國學術的批判吸收;另一方面則反映了當代中國學人借鑒、參與世界學術建設的努力。因此,我們既要正視海外學術給當代中國學界的壓力,也必須認可其為當代中國學人所賦予的靈感。
這裡所說的「當代中國學人」,既包括居住於中國大陸的學者,也包括臺灣、香港的學人,更包括客居海外的華裔學者。他們的共同性在於:從未放棄對中國問題的關注,並致力於提升華人(或漢語)學術研究的層次。他們既有開闊的西學視野,亦有扎實的國學基礎。這種承前啟後的時代共性,為當代中國學術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動力。
「秀威文哲叢書」反映了一批最優秀的當代中國學人在文化、哲學層面的重要思考與艱辛探索,反映了大變革時期當代中國學人的歷史責任感與文化選擇。其中既有前輩學者的皓首之作,也有學界新人的新銳之筆。作為主編,我熱情地向世界各地關心中國學術尤其是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的人士推薦這些著述。儘管這套書的出版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但我相信,它必然會成為展示當代中國學術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窗口。
中國新文學肇始於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發端於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反帝反封建的吶喊,使中國新文學以前所未有的姿態迅速邁向了與世界融合的步伐,中國現代文學也因之翻開了偉大而嶄新的一頁。
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與時代同脈,雖然1922年才開始出現現代文學第一部白話長篇小說,但27年的發展實績證明,它毫無愧色地成為20世紀最為顯赫的文學部門之一。不過,談到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卻首先要面臨一個如何界定現代長篇小說的問題。也就是說,什麼樣的小說才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對此,筆者採用目前較為通行的斷定方式予以認定,即:以文體的形式與長度作為判斷長篇小說的核心標準。也就是說,凡作者用現代白話文的形式創作的有一定長度的小說就被認可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而通常人們所說的長篇章回小說與通俗小說就不作為本書的敘述範圍了。
我們知道,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新文學關於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並無明顯的界限,早期的出版者常常將五-六萬字以上的小說均標注為長篇小說出版,如小雪的《超超》(1926)、黎錦明的《蹈海》(1929)等,也有將超過六萬字的小說當作中篇小說來印行的,如芳草的《管他呢》(1928)等。不過,在1927年創造社進行長篇小說徵文時,對長篇小說的合格字數要求是:「六萬字以上」。這一文體長度在今天看來顯然只是一個小中篇,但在當時卻是一部長篇了。而1936年「良友文學獎金徵稿」與1939年「文協」徵文時,對長篇小說的合格字數要求則是:「十萬字以上」。因此,為尊重歷史起見,也充分考慮新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文體長度統一大體為,1920年代以創造社長篇小說徵文的約定字數為限,1940年以後以「文協」長篇小說徵文所約定的字數為據,中間的年份(1930-1939)則取其中,也就是說,從六萬字起,每一個十年增加二萬字。即:1922-1929年:六萬字以上;1930-1939年:八萬字以上;1940-1949年:十萬字以上。當然,這並非絕對的一刀切,如果字數相差不大,或略少於規定字數,但只要具備長篇小說的審美特徵,也認可為長篇小說。這樣,依此標準,自1922年2月15日張資平出版《沖積期化石》至1949年9月30日王林出版《腹地》期間,新文學共出版長篇小說近三百部(三部曲若合名出版則以一部計,如茅盾的《幻滅》、《動搖》、《追求》不作為三部長篇小說,而認作一部《蝕》等)。雖然年均十餘部左右的數量在今天看來有些不可思議,而它們中的大部還將最終走入歷史的深處,但作為一個時代的忠實記錄,卻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學價值,其中的經典則彰顯出新文學偉大的歷史功績,矗立起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文學豐碑。
文學是時代的晴雨錶。作為時代生活重要載體之一的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當然反映著不斷變化的20世紀上半葉的時代訴求。從第一部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開始將「人的文學」這一新文學的革命主張真切地落實在長篇小說領域以來,表現人生,表現人面對命運與既有秩序的抗爭態度與不屈精神,就成為現代長篇小說家們的自覺追求。有個性的複雜人物的描寫,雙重人性的透示特別是對人的自身弱點所釀成的悲劇的批判,人的多重意識世界的揭示以及在雙重文化的燭照中透視國民的靈魂等藝術特質,使它和舊文學徹底區別開來,並真正邁開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現代化的步伐。《一葉》、《苔莉》、《英蘭的一生》、《罪惡》、《二月》等可視為其中的代表。受國際國內環境的影響,「革命加戀愛」小說一度成為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翼文學的創作主潮,我們這裡選擇了《旅途》、《轉變》、《地泉》等作為個案,既可瞭解革命文學的書寫模式,也可瞭解革命文學有待總結的經驗與教訓。這一時期還值得關注的是域外題材的小說創作,它們所呈現出的廣闊的時空背景,無疑擴大了新文學的表現視閾。馬仲殊的《太平洋的暖流》和林參天的《濃煙》,即可作如是觀。當然,30-40年代也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不斷上升的時代,也是革故鼎新、自強新生的時代,《新生代》、《科爾沁旗草原》、《財主底兒女們》等作品,就是這一時代鏡像的文學再現。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戰火紛飛,戰爭考驗著時代,歷練著人心,也鍛造著文學。從「九‧一八」東北事變到「七‧七」盧溝橋事件,抗戰的烽火點燃了中華民族爭取獨立,保家衛國的堅強決心,點燃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捍衛民族尊嚴的不屈意志。在血與火的洗禮面前,在靈與肉的搏戰時刻,各民族、各黨派、各武裝力量紛紛集結在抗日的旗幟下,開始了長達十四年艱苦卓絕的團結禦侮、浴火重生的大決戰,也譜寫了中華民族邁向新生、走向自強的偉大篇章。《戰血》、《大上海的毀滅》、《萬寶山》、《鴨嘴澇》、《蘋果山》、《戰果》、《間諜夫人》、《第二年代》等,就是這一輝煌歷史的忠實記錄。當然,由於中國國力的衰落以及其他諸種因素,中國戰區在這場反法西斯戰爭中,形成了東北淪陷區、華北淪陷區和華東淪陷區及以重慶陪都為中心的西南大後方的戰時格局,也因之形成了不同地區獨特的文學風貌。《三年》、《蓉蓉》、《影》、《前程》、《霧都》等就反映了各自戰區不同的文學特徵,也成為那個特殊時代的文學略影。當然,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戰火還包括震動世界的中國革命戰爭,我們頭尾各選取了一部在現代文學史上影響較大的作品──《蝕》與《女兵自傳》,意在留住那個時代的一側面,也留住那個時代的文學一側影。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開放進取,充滿活力,各種思想紛至遝來,長篇小說家們以西方現代思想與文學觀念為借鏡,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現代化注入了生機。不過,最初一段時間的借鑒往往帶有模仿、橫移的痕跡,如《八月的鄉村》,雖然也不乏《天問》那樣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下有所創新者,但畢竟是少數。至於像張資平這樣的作家以改寫代替創作以博文名,如《飛絮》、《愛力圈外》等,更是文學界的敗類。這只能糊弄一時而不能糊弄一世。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作家則在借鑒世界文學大師豐富營養的基礎上吐故納新,創作出屬於他們自己同時也屬於中國甚至屬於世界的傑作。《死水微瀾》、《駱駝祥子》、《寒夜》、《圍城》即是其中的代表。這也是中國現代長篇小說邁向現代化征程的必然之旅。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文學生態環境複雜多樣,長篇小說的傳播與接受也各顯特點。我們在這裡選取了四種類型:獎掖扶持型、官方查禁型、文藝爭鳴型、《講話》轉軌型予以透視,以使讀者對當時的傳播接受生態有初步的瞭解。我們知道,對於初出茅廬的青年作者而言,由於寫作技巧較為粗淺,藝術水準較為稚嫩,往往容易遭受歧視,他們自然渴望得到文壇名宿的慧眼相識,以邁出走向文壇的第一步甚至脫穎而出。王林、葉永蓁等就是其中的幸運兒與佼佼者,他們的長篇小說創作也因之顯出成色。查禁是歷代統治者鉗制文化的一種官方策略,國民黨也不例外。據統計,27年間,《子夜》、《綠色的穀》等約有四十部長篇小說遭到不同程度的查禁,它們對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由於被禁毀,《子夜》的刪節版到底是怎樣的,無人知曉,以至於成為現代文學界版本研究中一個懸而未決的疑案。《〈子夜〉的刪節本》一文徹底解決了這一懸案,也算是解決了茅盾研究界的一個重要問題。《駱駝祥子》與《圍城》堪稱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發展史上重要收穫,對它們的不同解讀本是正常的文學批評,但由於特殊的時代語境與文學生態環境,它們的某種有價值的視野或被遮蔽,或被噤聲,在去魅的時代當然應該還歷史以本來面目。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文藝工作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以後,延安解放區的文藝工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寫什麼與怎樣寫在隨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黨的文藝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反常的與正常的也就成為創作轉型期一種最為常見的接受樣態。《種穀記》與《腹地》就是這一類型具有代表性的一個樣板。不過,它們留給我們的教訓也極為深刻。
現代長篇小說應該如何寫?現代長篇小說究竟有沒有統一的文體樣態?先驅者在努力嘗試著,實踐著。初期的寫作者並沒有明確的長篇小說文體意識,甚至以為一般的日記彙編成長的小說就是日記體長篇小說,有的作者以整體人物對話的方式構建長篇小說新文體,還有的作者嘗試以童話的文體續寫批判性的長篇小說等。30年代後,書信體小說蔚然成風,許多作者將書信有機地彙集在一起,穿插於一定的人物與情節,組構成一部書信體長篇小說,有的還頗有文學意味,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文體實踐潮。故而有的作者嘗試以文獻體的方式補充長篇小說的文體構成,有的作者以混合體的方式即將全書分為上中下三部,第一部是散文,第二部是書簡,第三部又是日記;或分為上下兩部,上部為書信,下部為敘述文體,拓新長篇小說的文體疆域。只是,這類文體實驗的失遠大於得。那麼,這一時期文體實踐的最大亮點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嘗試是什麼呢?是詩體長篇小說的實踐。典型的代表是廢名的《橋》。《橋》詩境,畫意,禪趣,交相輝映,相得益彰,開一代文風,對中國抒情小說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僅就長篇小說而言,蕭紅的《呼蘭河傳》、艾蕪的《豐饒的原野》以及孫犁的《風雲初記》等,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美麗的風景。當然,如何以詩的方式藝術地精湛地構建以敘事為主體的長篇小說,需要長篇小說家不懈的探索。
同樣,在1922-1949年間,不同組織與機構還舉辦了大量的長篇小說徵文活動,對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復興與發展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從最初創造社的長篇小說徵文到之後的良友、文協徵文以及個人名義舉辦的「朱胡彬夏文學獎金」等,都對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當然,30年代後,在東北淪陷區與華北淪陷區,日偽統治者也先後舉辦了多種形式的長篇小說徵文活動,也評選出了幾部獲獎作品。但客觀地說,這些作品除個別小說外,大部分作品均是替日偽統治者塗脂抹粉之作,是典型的漢奸小說,是特定歷史階段即生即滅的藝術泡沫。不過,它們作為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應為人們所探討,為歷史所總結。這也是我們專列「文學徵文」為一板塊的重要原因。
所有這一切,構成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歷史長河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也反映了中國現代長篇小說演變發展的基本史貌。也因此構想,本書選取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近八十部作品,以個案分析的形式,分「文學‧時代」、「戰爭‧歷史」、「借鏡‧融創」、「傳播‧接受」、「文體實踐」及「文學徵文」六個板塊,以圖文並茂、返歸歷史現場的方式,向讀者介紹中國現代長篇小說在1922至1949這27年間所呈現的歷史樣態,所走過的歷史道路,所彰顯的審美意涵。在介紹過程中,筆者力求點面結合,雅俗共賞,為學界也為收藏界及廣大文學愛好者提供史的印痕,美的啟迪。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具有某一特質的文學作品不獨是該板塊的這幾部作品,只是為了更好地使讀者瞭解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展全貌,也為了全書各章節的相對均衡,筆者將其分置於相應的板塊中了。如果讀者朋友們能從中窺一斑而知全貌,那我的努力就沒有白費。
序「秀威文哲叢書」
自秦漢以來,與世界接觸最緊密、聯繫最頻繁的中國學術非當下莫屬,這是全球化與現代性語境下的必然選擇,也是學術史界的共識。一批優秀的中國學人不斷在世界學界發出自己的聲音,促進了世界學術的發展與變革。就這些從理論話語、實證研究與歷史典籍出發的學術成果而言,一方面反映了當代中國學人對於先前中國學術思想與方法的繼承與發展,既是對「五四」以來學術傳統的精神賡續,也是對傳統中國學術的批判吸收;另一方面則反映了當代中國學人借鑒、參與世界學術建設的努力。因此,我們既要正視海外學術給當代中國學界的壓力,也必須認可其為當代中國學人所賦予的靈感。
這裡所說的「當代中國學人」,既包括居住於中國大陸的學者,也包括臺灣、香港的學人,更包括客居海外的華裔學者。他們的共同性在於:從未放棄對中國問題的關注,並致力於提升華人(或漢語)學術研究的層次。他們既有開闊的西學視野,亦有扎實的國學基礎。這種承前啟後的時代共性,為當代中國學術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動力。
「秀威文哲叢書」反映了一批最優秀的當代中國學人在文化、哲學層面的重要思考與艱辛探索,反映了大變革時期當代中國學人的歷史責任感與文化選擇。其中既有前輩學者的皓首之作,也有學界新人的新銳之筆。作為主編,我熱情地向世界各地關心中國學術尤其是中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發展的人士推薦這些著述。儘管這套書的出版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但我相信,它必然會成為展示當代中國學術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窗口。
韓晗
2013 年秋於中國科學院
2013 年秋於中國科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