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車亭〉(節選)
這雨已經下了很久了。幾天前我到達這個城的時候它就是這麼下著,沒有更大也沒有變小。客運司機是一個留著落腮鬍的壯年男子,身材維持的不錯,沒有洋人的啤酒肚,皮膚也不是純粹的白種人,但一看就知道是白人,沒有黑色或黃色的成分。一路上他都跟前排座位的一位肢體殘障者交談,那位殘障者的左臉及唇顎部分好像被嚴重燒傷過,所以說起話來發音非常不清楚,我坐在他左後方三排的位置,雖然聲音很大,想聽懂卻非常困難,但無論如何這個人顯然非常健談,即使客運駕駛有許多次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他仍然可以把談話繼續下去。從HOBART到LAUNCESTON的公路車程約三小時,扣掉我四十分鐘的昏睡,這位肢障者足足說了一百四十分鐘。不過更令我驚異地是這位有著燒灼面孔的男人出奇的年輕,被火皺硬成深褐色的臉部線條上端,一雙湛藍的眼睛始終帶著笑意,和他彎曲下垂的嘴角拼合成一種無可奈何的感覺。也許這樣無邪的眼睛就是駕駛肯和他繼續交談的原因,但這卻使我無法分辨他的種族。
雨並不是從HOBART開始下的,這點我非常確定,在進入LAUNCESTON地界以前,陽光還透過玻璃直直刺進眼睛,天空沒有一片雲,也沒有大風,我從車窗看出去,道路兩邊的植物都像沙漠蜃樓冒著氤氳的熱氣。然後突然車窗就被雨水給封住了,就如同有人從正面用黑色塑膠袋把你的頭罩住一樣,我甚至來不及喘息或發出一聲尖叫,胸口就整個窒悶了起來。但是就在我心跳呼吸恢復正常且大大吐出一口氣的時候,客運車駕駛便告訴我們終站已到,引擎才熄火,他隨即就跳下車從咖啡色的旋轉門消失。那時雨也像這樣下著,雖然還不到瀑布傾洩的程度,但始終不是飄飄黏黏總也不濕的細雨。肢障者晚我一步下車,他萎縮的右手靈活地調動一條彈性繃帶,很像高空彈跳繫的那種繩子,把扭曲的左腳像操偶一樣的提起,然後彷彿知道我在看似的,他用左腳腳掌做了一個頷首的姿勢,便快速的離開車體。這男人身上有一個小帆布包斜掛在左肩上,一下車,一跳一跳地毫不猶豫地也走進咖啡色的旋轉門裡。除了空無一人的大客車,這個有著加油站般廊簷的兩尺見方,便只剩下我,以及讓人什麼也看不清的雨。
一開始我是站在計程車候車處等待的,這裡沒有任何招牌或文字足以確定是計程車候車處,不過根據經驗研判這介於快車道與客運總站建築間的半月形安全島,大多是出站旅客的候車處,就和加油站分隔的車道一樣,這個區塊有濃厚的轉接意味,可以讓旅客輕易的分別出等待和離開的安全地帶。一般情形下這類計程車候車處的地上會有白色油漆畫成的小客車形狀,但是雨大的很,我沒辦法探頭看清楚地下,更何況我也沒有傘。
對了,就是這個,沒有傘,在雨這樣下的地方我竟然沒有一把傘。原本這也沒有什麼,這幾十年飛過許多城市,行李箱裡從來沒有一把傘,也從來沒有任何一件事或物讓我想起傘這個東西。可事實上,我去過的每一個城市都有雨,INNSBRUCK那次還在阿爾卑斯山遇上大雨冰雹,只當時我也沒想起需要一把傘。不知道為什麼雨和傘就像電車和方塊酥一樣,沒有引發聯想的可能。站在半月形安全島上等計程車,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因為前後都被雨給隔斷了,所以視線只好不斷向狹長的左右移轉,無法靜置凝視前方又不願不斷轉身時,便只好低頭看著自己的腳。那天我穿的是一雙墨綠色的休閒鞋,深灰色絨布休閒褲,腰際特別打了縐折,半月形上開口袋兩個。左腳邊上放著我的旅行箱,不是一般商務人士的手提箱,也不是背囊客的帆布包,我的旅行箱有一個黑色的拉桿,手提大小的咖啡色小牛皮製成,裡面就幾件換洗的衣服,牙刷毛巾之類。
我一直很喜歡這個旅行箱,就尺寸來說是小了些,不過它不像我原來用的那個黑色的大型旅行箱,每次都要在登機前麻煩的秤重托運,下機後還得緊張地從一大堆黑的旅行箱裡把它找出來。最重要的是這個小巧軟皮的拉桿旅行箱可以和我搭乘任何交通工具,而且讓我少帶了許多東西。當然,另外一個不在料想的收穫則是在使用它之後出現的,那就是提著這個旅行箱,沒有人能弄清楚我是一個為工作奔波的商務代表還是一個刻苦或優渥的旅人、是來尋訪些什麼還是為了拋棄些什麼、是一個短暫的過客還是一個自我流放的人?這使得我的旅行有一些樂趣。所以,即使每次我離開一個地方都會把箱中的一切丟棄卻還是會拉著空箱子回家,把它靜靜立在客廳那套嶄新的牛皮沙發後面。
下車後我也許等了許久,但也許沒有我想像的久,總之,我似乎聽到了不遠處傳來救護車的聲音,這世界雖然被上帝用語言分成無數的區塊,每個人都可以自顧自地呆坐在屬於自己的地方。但是救護車的聲音卻到哪裡都一樣,它不會理會你的房子有多麼寬厚的牆,即使沒有一扇窗,它也總是能肆無忌憚的闖進你的耳膜,讓你不自覺的開始緊張起來。不過這次也許是雨下的太大了,救護車的聲音一開始只像是一頭絕望的野獸遠遠斷續的哀嚎,彷彿正背對著這裡逐漸消失,然而就在我心緒逐漸適應而趨向平穩的時候,它又突然朝著我大聲鳴呼起來。這個刺耳的聲音雖然很快越過我看不見的前方消失,卻使我安心不少,畢竟這個地方還有車和人經過,我不至於和日本導演北野武電影中的菊次郎一樣在廢棄的公車牌下等幾個日夜。
雨水濺濕我大半褲管的時候,身後客運總站廊簷的日光燈倏地亮了起來,我這才想起時間。顯然,這灰濛濛的雨把天時都給混亂了。這時咖啡色旋轉門有了動靜,一種金屬觸及水泥地的聲音雖然不比雨聲來的大,卻還是能讓人清楚地聽見它規律研磨地面的姿態。突然像是有所期待的似的,我意識到有另一個人一直在我沒有進去的旋轉門裡也許等待著看顧著陪伴著或監視著取笑著我,車還不來這件事變的無足輕重,至少有人跟我同時滯留在這個地方,在相同境遇裡沒有選擇,因而將我帶離了被無邊際的等待而質疑等待的意志和可能。
我專注地等待著他,仔細分辨尖銳的金屬以一又二分之一的拍子觸地,而且在每一次敲擊結束前那個粗糙的摩擦音,總讓我以為他要停下或轉移方向。我神經緊繃,直到一個彷彿重物摔落地面的聲音出現,這才暫時脫離耳朵的牢籠大大的鬆了一口氣。那個人就在廊簷邊的木椅坐下,而我則站在一個車道之隔的這邊,雖然同屬候車亭的領地,但他顯然佔據了比較優越的位置。我有些懊惱,質問自己為什麼一開始就急急忙忙地來到這個狹窄的安全島,而錯失了那樣一個空曠無雨的位子。而且這樣的距離顯然是無法交談的,甚至想接觸他的眼神也不可能,更何況還有雨,尤其令人沮喪的是從他舒攤成大字的坐姿,我也不能期待他會走過來或看我一眼。於是我決定暫時留下我的行李箱衝過雨簾來到他身旁坐下。像許多無聊的搭訕一樣,故做氣定神閒開始自語:
「這雨好大,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停?」
「應該不會停吧!天色還是黑的。」男人經驗老道的說。
「出來旅行?」
「算是。」
「住哪?」
男人舉起左手朝雨中指一指:「雨停了就看的到。」
我盯著他手指的方向,除了從屋頂上飛濺下來的雨,後面什麼也沒有。在移回眼光的同時,我順便斜瞥了一眼獨自呆在安全島上的行李箱。男人蜷曲的右手從帆布包裡取出一根菸,閑閑咬含在右邊的嘴角,左手把打火機遞給我,不一會兒一個個煙圈就冒了出來。
「你呢?也是旅行!」
「算是。」
「第一次來?」
「嗯。」
「為什麼?」男人把左手架放在椅背上,毫不在乎地說。
「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來這裡?」
……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候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0 |
中文書 |
$ 190 |
Literature & Fiction |
$ 211 |
現代散文 |
$ 216 |
文學作品 |
$ 216 |
中文現代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候
希臘神話裡酒神的伴護西勒諾斯說:「可憐的浮生啊!無常與苦難之子,你為什麼逼我說出你最好不要聽到的話呢?那最好的東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為虛無。不過對於你還有次好的東西——立刻就死」(尼采《悲劇的誕生》),對於已經降生且不知何時會死的我們,等候並不是宿命,它恰恰普羅米修斯對抗命運的意志。
本書收錄〈我只是借停一下〉、〈候車亭〉、〈我家門前有小河〉、〈假日〉、〈裹〉、〈下水道結構補強工程〉、〈期中預警通知〉、〈早安〉、〈謎〉等共9篇短篇小說,大多為作者許琇禎獲獎之作品。
作者簡介:
許琇禎,1963年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台北市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專攻文學理論與現代文學研究。
小說作品曾獲教育部文藝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
著有《解嚴前後(1977-1997)台灣當代小說縱論》、《沈雁冰文學研究》、《朱自清及其散文》等。
章節試閱
〈候車亭〉(節選)
這雨已經下了很久了。幾天前我到達這個城的時候它就是這麼下著,沒有更大也沒有變小。客運司機是一個留著落腮鬍的壯年男子,身材維持的不錯,沒有洋人的啤酒肚,皮膚也不是純粹的白種人,但一看就知道是白人,沒有黑色或黃色的成分。一路上他都跟前排座位的一位肢體殘障者交談,那位殘障者的左臉及唇顎部分好像被嚴重燒傷過,所以說起話來發音非常不清楚,我坐在他左後方三排的位置,雖然聲音很大,想聽懂卻非常困難,但無論如何這個人顯然非常健談,即使客運駕駛有許多次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他仍然可以把談話繼續...
這雨已經下了很久了。幾天前我到達這個城的時候它就是這麼下著,沒有更大也沒有變小。客運司機是一個留著落腮鬍的壯年男子,身材維持的不錯,沒有洋人的啤酒肚,皮膚也不是純粹的白種人,但一看就知道是白人,沒有黑色或黃色的成分。一路上他都跟前排座位的一位肢體殘障者交談,那位殘障者的左臉及唇顎部分好像被嚴重燒傷過,所以說起話來發音非常不清楚,我坐在他左後方三排的位置,雖然聲音很大,想聽懂卻非常困難,但無論如何這個人顯然非常健談,即使客運駕駛有許多次並沒有回答他的問題,他仍然可以把談話繼續...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我只是借停一下
候車亭
我家門前有小河
假日
裹
下水道結構補強工程
期中預警通知
早安
謎
後記
候車亭
我家門前有小河
假日
裹
下水道結構補強工程
期中預警通知
早安
謎
後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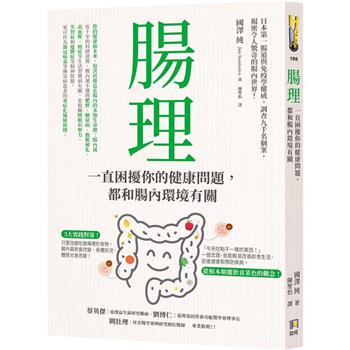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