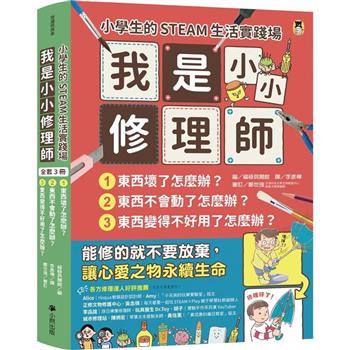〈莊家的餐桌〉
莊懂先生有一個老婆和三個小孩。老婆本姓賈,當年嫁給他的原因是不想繼續被人家叫做賈小姐,雖然當了莊太太也好不到哪裡去,不過女人家最忌諱被人說是假的,不論指的是身材還是其他。莊懂的三個兒子全在唸大學,從好的一方面來說,莊懂的教育成功,全家都是知識分子,從壞的一面來說,莊懂家的開銷實在驚人,雖然莊懂不用擔心兒子會像女兒一樣成了賠錢貨,可是光是三個兒子搞出來的遮羞費也非常驚人。
莊懂家的財政赤字最先是由莊太太的治裝費裡顯示出來的,從賈小姐到莊太太,唯一不可變的就是衣服一定要是貨真價實的名牌貨,要不裝啊假的還去用仿冒,那可就真成了人家的笑柄。莊太太嚴謹持家犧牲奉獻,就只有這點是誓死捍衛的。於是莊家為此開了一次家庭會議,選的就是晚餐的時候。
三個大學生難得同時坐在餐桌上,莊太太今兒個給大家加了菜所以還在廚房裡忙,莊懂這就先說了要旨。他說:「兒子們!你們知道老爸我是最最開通的人啦!向來尊重你們的意思,處處為你們著想。今天這會就是要你們想個辦法,共體時艱,咱家的收入是月不敷出,已經動到了你們老媽的治裝費上了,所以大家如果還想在這餐桌上有飯吃,就得想想辦法。」
學古文的大兒子莊古斜斜瞥了旁邊坐沒坐相的老二,慢條斯理端足了大哥的架子說:「照理誰的開銷大,誰就得減的多。我讀古文是祖宗們的學問,最不花錢又最要緊,也沒買什麼閒書,對家裡的經濟貢獻已經很大了,更何況我既身為長子,原本就比弟弟們多扛了一份責任,說什麼也不該減我的零用。」學白話文的老二莊洋立時挺直了背脊,把煙頭在煙灰缸裡使盡地扭了扭說:「咱學白話文的可一點都不輕鬆,算算看不只要讀漢字還得讀洋文,論難處可一點都不比古文少,書雖然買的多,可本本都唸,不像老大明擺著幾本精裝的字書,專門用來撈灰塵用。」
莊懂眼見兩個兒子誰也不讓,心裡也直冒火,不過他為了保有開明的頭銜,只得硬按下想各給兩巴掌的手,轉頭問那個正忙著啃雞翅膀的老三莊傻。
學教育的莊傻是最得莊家二老歡心的,莊傻小時候不知是跟誰學了變臉的絕活,打從他進學校唸書起,就沒人見過他真正的長相。此時他用手揩了揩嘴角的肉屑,先朝爸爸哥哥鞠了個躬,然後笑嘻嘻的說:「咱什麼都學什麼都會,不過你們說的咱都不懂,但凡咱不懂就不重要。」
莊懂這下也沒了轍,所幸莊太太端著今晚的大菜佛跳牆出來了。莊太太一坐下來,就開宗明義的說:「今兒這頓飯算是給你們補償補償,打明兒起每個人的零用都減一半,就這樣定了。」話才說完,莊古第一個不服氣,他手背在身後原地直轉圈圈,既不敢直接違背古訓頂撞他的娘,只好嘴裡直唸著:「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哀哉痛哉我的零用。」一旁的莊洋拿出和學校老師擺龍門鎮的氣勢,直接對著他的老媽說:「你獨裁,你不分青紅皂白,為啥我要和那個搞大別人的肚子就縮起頭的老大拿一樣的零用?咱跟咱女友光明正大同居,也沒給家裡長開銷,咱女人還到處兼家教賺錢,說什麼也比那個窩囊廢強。」
莊太太在還是賈小姐的時候,還會為了形象輕聲細語的說話,但自從成了莊太太後,除非在人前,否則她一貫的是晚娘臉金錢豹,誰要想改她的決定,那真是連什麼都沒有。於是就在莊太太要使出殺手鐧的時候,莊懂說話了:
「咱是最最開明的老爸,既然大家對一起減零用沒法兒服氣,那這樣,咱就讓你們三個交出個心得報告,誰要寫的好,零用就減的少。」
三小時後,在同一個餐桌上莊古交出了他的心得報告:「減,損也,從水咸聲。動詞。零,徐雨也,從雨令聲。名詞。用,可施行也,從卜中,衛宏說凡用之屬皆從用。動詞。減零用者即損徐雨可施行也。採替代修辭法言之。」莊洋的心得報告是:「零用錢雖然不是生活費,但是從後設的立場來看它卻提供了人在維生之外更重要的精神消費,所以除非是殖民主義剝削,零用錢是萬萬不可減的。」老三莊傻是最後一個交的,他寫的是:「爸爸說的對,媽媽說的好,哥哥們都沒有錯,我都懂得但是我不知道。爸媽萬歲,教育千歲。」
莊懂實在不知道這三個兒子寫的是什麼東西,但是既然他們的老師都這樣教,想必這也就是重要的學問。不過他和莊太太討論後,還是一致認為莊傻寫的最好,莊古再怎麼樣也還吊了書袋,只有這莊洋什麼精神精神個沒完,壓根就沒見出他學了什麼。於是零用錢最後做了這樣的調整:莊傻在原有之上再加一倍,莊古減去原有一半,莊洋則全數取消,讓他和他的女友去自立自強。這樣加加減減,總算多了一點錢可以補莊太太的治裝費,雖然還是不太夠,但既然還有兩個有出息的兒子可以寄予厚望,講求投資報酬率的莊家二老,這回也就沒有異議,安然渡過一次經濟危機。
不過,沒多久莊傻就搞上了一個黑妞一個白妞和一個黃妞。付不出遮羞費的莊家餐桌,現在就像聯合國一樣,莊古繼續一邊唸著聖賢古訓一邊偷看黃色書刊,莊傻持續夜不歸營來充實餐桌上的國籍,而照理說當莊家應該絕對不會輸錢的莊家二老,太太的名牌卻全進了二手衣商店,莊先生則再也沒有機會用中文在餐桌上說他有多麼開明了。
〈獨木舟〉
森林之所以是森林,正由於它們並不知道彼此的不同。這片由挺拔堅實樹木所構成的林子也是一樣,每一粒種子在離開枝頭之前,都抱著延續並拓展森林生命與領地的夢。
春天的風吹過樹梢,從偶爾見到的白雲裡,樹苗們努力向上,以便抹去那一點自由的暗示。由夏而冬、年復一年,白雲和天空更顯得少見了,雖然風迴旋的空間卻多了起來。樹苗們並不在意,成長原是為了爭取擁有天空的權力,並向下延伸,作永生的固著。它們因為森林而生而死,也成就了更濃密更擁擠的森林。
不過凡事總有例外,這片林子的樹有其他的選擇。除了探出頭去領略天空或拼命佔穩地盤外,它們由於質地堅實、輕巧又不易腐爛,所以常在還能向上或向下發展的壯年,就被作成獨木舟。對它們而言,如果開花是成年禮,那麼下水的那一刻,就是無限悲淒的參與自己的告別式。
告別式其實比成年禮熱鬧許多,每一艘獨木舟脫離了「森林」這個名字,有了與樹木完全無關的稱呼。身上的色調、曲線、年輪被全新的東西所取代。這些被作成獨木舟的樹木,稱這個儀式為「犧牲」。它們知道離開了森林的完整就是死亡,而且這種死亡其實是一種無止境的飄泊。沒有根、沒有了供養和傳承,還有什麼能超越這個命運中最大的咒詛呢?
每一艘獨木舟的憂傷都滅頂。它們在水影裡自憐、在槳聲中悲歎。那些森林中曾熟識的面孔,一但成了獨木舟,就再也不相識。它們哀悼自己的早殤,見證自己的死亡,獨木舟、風、雲或任何存在都失去意義,於是每艘獨木舟給自己取了一個孤絕的名字──「我」。
我的生活其實並不如預期的漂泊,它常常漫游在森林旁的河岸邊上,而且靜止的時間居多。岸上的樹木既不會看它一眼,它也忘了自己是什麼。只依稀記得,變成獨木舟之後,就失去了掀起狂瀾般風聲、承擔滿身青綠的能力。現在,我只負載一個人,和一個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除了那雙握槳的手、纜繩和舟底的水外,我大體上覺得這種死亡是自由的。但是它無法對死亡滿意,因為離開既然是失去,而失去總是死亡,自然沒有對死亡滿意的道理。
這一天,我撞上了另一個我。它們正沉緬於死亡憂傷的永無結束。嘎吱一聲,身上的油彩被磨掉了一些。我同時在對方身上看到了一片黃白的木皮,而且自己的身上也有一塊。我頓時從死亡的悼念裡,憶起曾為樹木的生前。它開始思索:如果世上還有另一個我,而且這個我可以見到我,那麼究竟孰生?孰死?
懷疑死亡的明確性不是一件好事。意外過去了很久,我也沒有再遇見另一個我。但是它開始抱著希望來觀察尋找,就是一件頂壞的事。它不斷從那塊磨掉油彩的木頭揣想:我是什麼?我和樹是什麼關係?它開始注意水中倒影的全像,並且尋找河岸邊與我相同的樣子。這段時間,它有點興奮,既然有這麼多和我一樣的我,我們就是一座森林了。我並沒有死,一切都和以前一樣,我只要努力地向我靠近就好了。
太過自信常常帶來致命的打擊。我終於發現我們永遠不會是森林了。每一艘獨木舟都有自己的去處,連停泊的地方都不一樣。更要命的是:那些看起來一樣的油彩和曲線,其實完全不同。我畢竟是真的死了,沒有森林的夢和根,樹木就失去了價值,更何況獨木舟根本就不是樹。
維持對死亡的認知有一種安全感。我回歸到繼續執行自己死亡的軌道上,只是不再這麼悲淒了,反正死就是死,沒什麼可想的。它偶爾看看周圍的東西,竟然弄懂了雲不一定是白色的事實。老實說,它甚至於覺得日子有點愉快,尤其是在那些熟悉的水道行進時,也許說奔馳會更恰當吧!當然,如果那揮之不去的孤獨可以離開的話,生死、森林和獨木舟的生活,還真沒有什麼不同。我就是我,獨一無二而且完整的。
但是,完整意味著什麼呢?
我的航行其實並不遠,大部份的時間它都在平滑的河面上划行,偶爾風強了些,也只是晃的厲害一點罷了。熟悉增添了自信,它幾乎感覺不出土與水的不同。不過,人生總有第一次,這天它來到瀑布下,水掀起了和風聲一樣的狂瀾,超過了它的負載,「翻了」我聽到有人說。它於是慢慢地漂著,心想:「翻」是什麼意思?翻了還是沒翻,我不是都有一半泡在水裡又浮又沉嗎?
不知道漂了多久,水面又平滑起來,不過這次它卻停住不動了。這時它看到身邊有一些像葉子的東西浮在水面,葉下還長了些像根一樣的東西。基於一種無聊的好奇,我和這些似動不動的浮萍說起話來:
「你下面那些像根的東西是什麼?」我問。
「就是根。」浮萍說。
「胡說,根是長在泥土裡,用來吸取養分、固定自己的。你那些東西根本沒有這些條件。」
「你認為吸收養分和固定自己哪一種比較重要?」
「沒有固定怎麼吸收養分呢?」
「如果養分不在一個地方,那麼固定能吸取到養分嗎?」
「你的意思是,根是為了吸收而不是為了固定?」
「差不多是這樣。」
「那所有活的東西都會有根嘍!不拘在水裡或土裡,根不一定要固定住,對不對?」
「大致是如此。」
「那我已經死了,我已經沒有吸收養分的根。」
「那要看你認為自己是什麼東西而定。」
「我是獨木舟呀!」
「獨木舟的根是水,只要還能碰到水,它就是活的。」
「可是我是樹木造的,我不可能離開我的本質呀!」
「樹木的本質是什麼?」
「我不知道。」
「所有生命的本質不是土就是水,不是嗎?」
「如果獨木舟與樹木的本質都一樣,為什麼要將樹木造成獨木舟?又為什麼給它們不同的根呢?」
「你喜歡森林嗎?」
「喜歡。」
「為什麼?」
「因為在那裡我知道自己是什麼、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呢?」
「長得比別人高比別人壯。」
「為什麼?」
「這是作為一棵樹的責任。」
「誰告訴你的?」
「以前就這樣,大家都這麼想。」
「你知道樹可以被很多生物寄生或寄居嗎?」
「那不是樹的志向。」
「你認為長高長壯比讓一種生命延續下去來得重要神聖?」
「好吧!就算你說的對,這和獨木舟與樹有什麼關係?」
「你何不想想你在成為獨木舟後,生活有什麼不同?」
「孤單、不定、危險。」
「還有呢?」
「自由吧!」
「你在森林的時候不自由嗎?你現在得受水、欖繩和搖槳的手控制哦。」
「大概是森林太固定了吧!」
「其實當樹或是獨木舟都有不自由的地方,但是存在的價值卻沒有輕重。」
「死亡會有什麼價值?」
「你認為自己死了嗎?」
「不太確定。」
「你確實不是長在森林裡的樹木了,但是你現在是獨木舟啊!」
「獨木舟泡在水裡不能航行,就是真的死了。對不對?」
「不當獨木舟還能當泥土呢!你擔心什麼。」
風大了些。
「你不會跟我一樣留下來,對不對?」
「我們一定會再見,當我們看起來沒有不同的時候。」
浮萍漂走後,我慢慢吸吮著獨木舟特有的根,終於順利的生成泥土,而且不再孤獨。
當然,春天又來了,種子仍以它們特有的告別式離開枝頭。令人驚異的是,那個關於尋根的夢竟然還在上演。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獨語術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50 |
中文書 |
$ 158 |
中文現代文學 |
$ 176 |
現代散文 |
$ 176 |
Literature & Fiction |
$ 18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獨語術
坐在井底看到的天空也許就那麼小小的,不過即使是井底的天空也有千變萬化,也是天空。更何況井底是每個人必要的處境,跳出去的時候,要想當一隻獨特的青蛙就不太可能了。
本書收錄〈湖〉、〈寄居蟹〉、〈雞排男孩的甜甜圈〉、〈羅盤〉、〈莊家的餐桌〉、〈想像一個冬夜〉、〈城堡〉、〈向日葵〉、〈獨木舟〉、〈石頭〉、〈請在秋天寫信給我〉、〈三個包包與三個女人和男人們〉、〈閱讀˙旅途˙村上春樹〉、〈井〉等共14篇散文。
作者簡介:
許琇禎,1963年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台北市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專攻文學理論與現代文學研究。
小說作品曾獲教育部文藝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
著有《解嚴前後(1977-1997)台灣當代小說縱論》、《沈雁冰文學研究》、《朱自清及其散文》等。
章節試閱
〈莊家的餐桌〉
莊懂先生有一個老婆和三個小孩。老婆本姓賈,當年嫁給他的原因是不想繼續被人家叫做賈小姐,雖然當了莊太太也好不到哪裡去,不過女人家最忌諱被人說是假的,不論指的是身材還是其他。莊懂的三個兒子全在唸大學,從好的一方面來說,莊懂的教育成功,全家都是知識分子,從壞的一面來說,莊懂家的開銷實在驚人,雖然莊懂不用擔心兒子會像女兒一樣成了賠錢貨,可是光是三個兒子搞出來的遮羞費也非常驚人。
莊懂家的財政赤字最先是由莊太太的治裝費裡顯示出來的,從賈小姐到莊太太,唯一不可變的就是衣服一定要是貨真價實的...
莊懂先生有一個老婆和三個小孩。老婆本姓賈,當年嫁給他的原因是不想繼續被人家叫做賈小姐,雖然當了莊太太也好不到哪裡去,不過女人家最忌諱被人說是假的,不論指的是身材還是其他。莊懂的三個兒子全在唸大學,從好的一方面來說,莊懂的教育成功,全家都是知識分子,從壞的一面來說,莊懂家的開銷實在驚人,雖然莊懂不用擔心兒子會像女兒一樣成了賠錢貨,可是光是三個兒子搞出來的遮羞費也非常驚人。
莊懂家的財政赤字最先是由莊太太的治裝費裡顯示出來的,從賈小姐到莊太太,唯一不可變的就是衣服一定要是貨真價實的...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湖
寄居蟹
雞排男孩的甜甜圈
羅盤
莊家的餐桌
想像一個冬夜
城堡
向日葵
獨木舟
石頭
請在秋天寫信給我
三個包包與三個女人和男人們
閱讀‧旅途‧村上春樹
井
後記
寄居蟹
雞排男孩的甜甜圈
羅盤
莊家的餐桌
想像一個冬夜
城堡
向日葵
獨木舟
石頭
請在秋天寫信給我
三個包包與三個女人和男人們
閱讀‧旅途‧村上春樹
井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