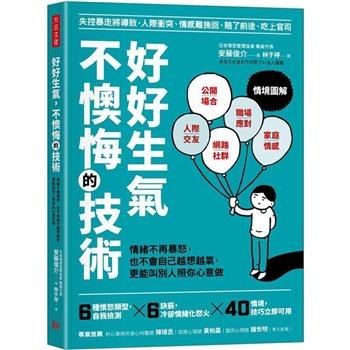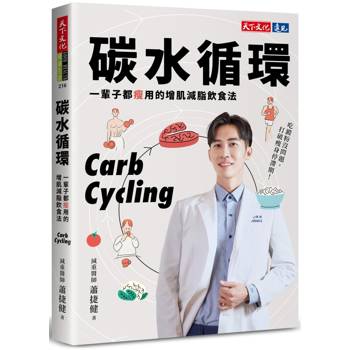以女性為中心的寫作──論嚴歌苓《第九個寡婦》
一、前言─女作家寫女性的故事
嚴歌苓作品從來不乏注意,2006年出版的小說《第九個寡婦》,即受到不少研究者垂青。先是陳思和為此書撰寫後跋,內容篇幅雖簡短,對後來論者卻不無啟發。嚴歌苓向來不找人作序跋,這次特別請來專家學人執筆,多少可見對作品的重視。《第九個寡婦》以女主角王葡萄從七歲至五十多歲的遭遇為敘述內容,涵蓋的歷史事件包括日本侵華、土改、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嚴歌苓作品,向偏重女主角,亦著重反映歷史,其長篇小說尤能體現此特色。早期《雌性的土地》,後來《扶桑》,以至近年《寄居者》、《金陵十三釵》、《小姨多鶴》及《一個女人的史詩》等均為佳例。《第九個寡婦》值得注意,便因能細緻表述歷史洪流中個人的立身處世。女主角王葡萄立於大地,順應自然,觀照歷史,除可被新歷史主義者視作同道外,大概亦足讓女性主義者引為知己。嚴歌苓以女性為中心的書寫策略,相當符合女性主義的立場,本文討論亦主要由此角度切入。男性主義慣常看法是︰男性積極創造「他的女人」。《第九個寡婦》讓我們一睹的是︰女作家如何在文本中創造「她的女人」。
二、命名的意義─從「第九個寡婦」的題目說起
嚴歌苓以「第九個寡婦」為書題,引來評者意見紛紜。陳思和首先提出異議,指出題目與整體故事及意象並無必然關係。他認為以「鞦韆」命名會更富表現力,因為人的命運一如盪鞦韆,唯有緊抓鞦韆架上的繩子,才不會被拋落。不錯,鞦韆在故事中確是上佳意象,折射了女主角王葡萄動盪世界裡求生的頑強意志。然而,這是否就是命名唯一或最佳選擇,實有商榷餘地。鄭民娟便認為陳思和忽略嚴歌苓民間、非精英的創作立場,並引述了嚴歌苓「九是一個大數」的說法。她最後更指出歷史成了王葡萄的故事背景,而《第九個寡婦》是︰
「一個鄉土中國女人的生存故事,而這個女人就像她的名字一樣,多汁而又甜蜜,極具生命力。」
鄭民娟雖提出一定看法,但仍顯得較為籠統空泛,未能針對題目本身詳加解釋,讀者必須從行文中自行聯想體會。女主角「王葡萄」名字蘊含的意義,固可從水果本身多汁香甜的特色得到更豐富的解讀,但《第九個寡婦》這題目本身,並沒把王葡萄三字加上。如此看來,以「第九個寡婦王葡萄」命名,似能引發更多藝術想像,而「九」這一數字,在中國語文傳統習慣裡,可視為虛指,一方面既為嚴歌苓所說的大數,但亦有無限延伸的意義。《第九個寡婦》演繹的,正是王葡萄無限的生命力。小說以王葡萄為軸心,鋪演開拓的也是在固有政治環境框囿下,個人突破的種種可能。附以寡婦這一名稱,亦可從反面敘述意義上加以說明。中國傳統社會對寡婦的要求往往嚴苛,克己守節常為無形思想桎梏。在王葡萄身處的年代,寡婦容易招惹「是非」(頁111)的說法,仍切實反映社會一貫對寡婦的道德要求。王葡萄為寡婦,但她的行為表現,並不同於前八個,亦即一般的寡婦;她是第九個寡婦,有著無限潛能。劉思謙則在論文中除同樣肯定王葡萄的「獨特性」外,更反過來把陳思和的說法轉化應用,指出「第九個寡婦」這樣的標題正好緊扣「整體故事和意象」。
其實,從命名意義來看,正可見嚴歌苓對「第九個寡婦」的重視,小說情節重心也確實落在她守寡以後的遭遇。這樣的題目本身便頗具張力。故事一開始便這樣戲劇化地展開︰
「她們都是在四十四年夏天的那個夜晚開始守寡的」(頁5)
而內容發展同樣沒讓人失望,劇情引人入勝之餘,卻從沒偏離王葡萄的生活經歷。這一守寡婦人無論任何惡劣環境仍活得精彩的故事,反映的正為題目所標示「第九個」的獨特含義。
三、「女人好看」─以女性為中心的寫作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關注的是女性的命運與處境。從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強調「自己的房間」到伊萊恩‧蕭沃爾特(Elaine Showalter)的「荒野」 探索,以至呂斯‧伊加里(Luce Irigaray)意圖建立的「流動」女性文體 ,女性作家對性別的自覺意識均為其中重要課題。在企圖扭轉神話中美杜莎(Medusa)刻板形象的專文中,埃萊娜‧西蘇(Helene Cixous)更向姊姊妹妹呼籲︰要寫作,寫自己,寫女性。她認為女性的寫作猶如一己身體般,一直被排斥。因此,女性必須付諸行動,把自身寫進文本裡,走入世界、歷史。
其實無論中外,以女性為書寫對象,一直是女作家從未忘懷的使命。在男作家壟斷文壇年代,女性心事只能由男作家代言。中國方面,以傳統閨怨文體為例,思婦形象恆常成為男作家筆下一廂情願的想像。由「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到「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如蓮花般開落」,時代迭變,這一以男性為中心的落想仍然清晰可見。詩歌內容雖是女性心事,但對男性不能割捨的依戀才是至欲傳達的訊息。女作家時思反抗的,是男作家以自我為中心的越俎代庖。在女性主義思潮影響下,近年不少女作家已經意識到性別身分與寫作的關係。中西兩地均曾居停的嚴歌苓,雖從沒打起女性主義旗號,但對女性角色的鍾情及敘寫方式,不啻也是以女性為中心,有著明顯性別意識的寫作姿態。嚴歌苓受訪時,從不諱言自己愛寫女性,認為男性沒有寫頭。《第九個寡婦》編者在引述嚴歌苓認為「女人好看」的話後,更進而指出王葡萄為一「『好看』的女人」。所謂「好看」,可從不同層面詮釋。首先,廣義地引申,不妨是指以王葡萄為重心開展的故事好看,這亦即嚴歌苓一直在作品中追求的藝術面向。其次,從字面含義看,明顯直指王葡萄樣貌體態悅目。這方面作者不僅從客觀敘述中表達,更往往通過別人的視角說明。此外,可把「好看」解釋為愛看人。在故事中,王葡萄常常在看人,從她的視點觀察外面世界,以她的看法詮釋政治人事的變遷。這種女性視角正是貫串全書脈絡所在,而此一性別觀照,正是女性自我意識的體現。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人性反思與敘述魅力──嚴歌苓小說論評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99 |
中文書 |
$ 299 |
華文文學研究 |
$ 306 |
文學作品 |
$ 306 |
中國文學論集/經典作品 |
$ 340 |
Literature & Fiction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人性反思與敘述魅力──嚴歌苓小說論評
本書從不同層面解讀嚴歌苓不同時期,不同篇幅的小說。嚴歌苓一向愛為讀者說故事,其小說的敘述魅力不但見於樸直、鮮活而細緻的語言,也在於情節的設計以及內容的鋪陳,這一切都令其訴說的故事引人入勝且獨具韻味。歷年來嚴歌苓筆耕不輟,移居國外後,筆下始終離不開中國人的故事,或許歷經他鄉再回望故土,最牽動她的仍是舊地的種種。
本書以「人性反思」為題,展現了政治與人性糾葛的紛紛擾擾,因為嚴氏小說所演繹的,正是嚴苛的政治環境以及顛簸的國族命運中人性的陰晴明晦。她以其獨特的敘述技巧,娓娓述說著一個又一個人心的陰暗與光輝重疊交錯的故事。
作者簡介:
李仕芬,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現職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師。著作為《女性觀照下的男性──女作家小說析論》、《愛情與婚姻──臺灣當代女作家小說研究》,論文散見於各期刊。
章節試閱
以女性為中心的寫作──論嚴歌苓《第九個寡婦》
一、前言─女作家寫女性的故事
嚴歌苓作品從來不乏注意,2006年出版的小說《第九個寡婦》,即受到不少研究者垂青。先是陳思和為此書撰寫後跋,內容篇幅雖簡短,對後來論者卻不無啟發。嚴歌苓向來不找人作序跋,這次特別請來專家學人執筆,多少可見對作品的重視。《第九個寡婦》以女主角王葡萄從七歲至五十多歲的遭遇為敘述內容,涵蓋的歷史事件包括日本侵華、土改、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嚴歌苓作品,向偏重女主角,亦著重反映歷史,其長篇小說尤能體現此特色。早期《雌性的土地》,後...
一、前言─女作家寫女性的故事
嚴歌苓作品從來不乏注意,2006年出版的小說《第九個寡婦》,即受到不少研究者垂青。先是陳思和為此書撰寫後跋,內容篇幅雖簡短,對後來論者卻不無啟發。嚴歌苓向來不找人作序跋,這次特別請來專家學人執筆,多少可見對作品的重視。《第九個寡婦》以女主角王葡萄從七歲至五十多歲的遭遇為敘述內容,涵蓋的歷史事件包括日本侵華、土改、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嚴歌苓作品,向偏重女主角,亦著重反映歷史,其長篇小說尤能體現此特色。早期《雌性的土地》,後...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以女性為中心的寫作──論嚴歌苓《第九個寡婦》
細節解讀──嚴歌苓《寄居者》對寄居的反思
一個女子的革命體驗──嚴歌苓《一個女人的史詩》探析
親密與疏離──嚴歌苓〈老人魚〉解讀
沒有名字的人──嚴歌苓《人寰》試論
拖著長辮的中國男人──嚴歌苓的〈橙血〉
女性觀照下的賭徒──析嚴歌苓《媽閣是座城》
講故事與聽故事──嚴歌苓〈老囚〉試論
男性敘述下的女性傳奇──讀嚴歌苓〈倒淌河〉
錯失的青春歲月──讀嚴歌苓〈我不是精靈〉
審醜──嚴歌苓〈審醜〉解讀
扶桑與克里斯的愛情神話──嚴歌苓的《扶桑》故事
敘述...
細節解讀──嚴歌苓《寄居者》對寄居的反思
一個女子的革命體驗──嚴歌苓《一個女人的史詩》探析
親密與疏離──嚴歌苓〈老人魚〉解讀
沒有名字的人──嚴歌苓《人寰》試論
拖著長辮的中國男人──嚴歌苓的〈橙血〉
女性觀照下的賭徒──析嚴歌苓《媽閣是座城》
講故事與聽故事──嚴歌苓〈老囚〉試論
男性敘述下的女性傳奇──讀嚴歌苓〈倒淌河〉
錯失的青春歲月──讀嚴歌苓〈我不是精靈〉
審醜──嚴歌苓〈審醜〉解讀
扶桑與克里斯的愛情神話──嚴歌苓的《扶桑》故事
敘述...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