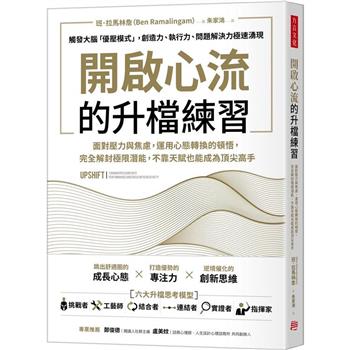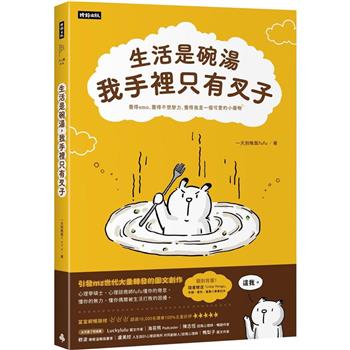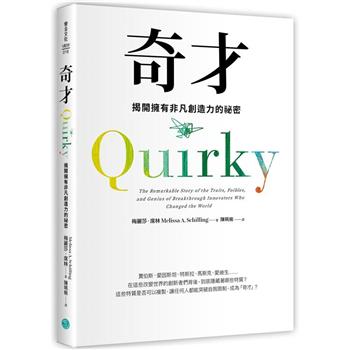相公生得俊美無比又腹黑無敵,她孫錦娘也不差,
宅鬥速速上手,如今更能使計設陷阱,一步步靠近幸福將來……
宅鬥其實不難,看她孫錦娘就知道;經歷了內院外院的風波,
身邊丫鬟婆子的陷害與各種伎倆,她也練就一身本事,
何況相公雖然不良於行,但論心思深沈及詭計,
他冷華庭要說第二,也沒人敢搶第一,肚子裡壞水可是多得很,
倒也彼此呵護,情意綿綿滋長,小日子過得可滋潤了~~~~
但也不能永遠關起門來過自己日子,不問世事,
尤其疼愛自己的王妃院內小事不斷,二房太太又生事,
好不容易找到了些證據能讓奸人就範,偏又讓對方找了縫隙逃過一劫!
加上自家姊姊這時又不情不願地嫁到簡親王府,給大伯當了側室,
既是不情願,自然會生事;她要幫王妃掌家,又要應付別有心思的嫡姊,
人生真是一刻不得閒,幸好她逐漸在王府站穩位置,
小夫妻齊心合力,看來要揪出王府幕後黑手的時刻也不遠了……
本書特色
既有穿越,又是重生,
女主角不但要活得比別人好,還要善用頭腦,
為自己在重男輕女的古代社會掙一席之地,
雖然結婚,也不做丈夫身邊的小女人,
而是能與丈夫並肩而行、互相扶持的一對夫妻;
本文除了女主角的自立,還有婚後戀愛、生情,
加上宅鬥及宮鬥,內容豐富精采、高潮迭起,非常黏手吸睛。
作者簡介
不游泳的小魚
瀟湘書院宅鬥文代表作家之一,著有《名門庶女》、《望門閨秀》等作品。加入瀟湘後的第一篇新文便以銳不可擋之勢衝進總訂榜前三,其功底紮實,細筆寓大,筆下人物聰慧生動,如鮫珠璀璨,光不可斂。
雖是平凡的家庭主婦,雖已過了愛作夢的年紀,但內心還是有小女人的心態,愛作夢愛幻想,喜歡把夢裡出現的場景用樸實的文字記錄下來,永久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