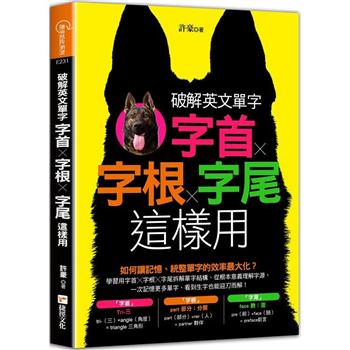第一回 紅芍藥聞聽大家族 梅蓮英魂還深宅門
盛夏,蟬兒在樹上狂鳴,荷塘間微風陣陣,擺動碧葉,傳來陣陣荷香。紅芍托著一碗藥,穿了荷塘邊的抄手遊廊直走到浣芳齋,入內室掀開簾子一看,只見柳婉玉躺在床上雙目緊閉,面色慘白。夏婆子正坐在繡墩子上,頭靠著床欄打盹。
紅芍將藥碗放在床邊梅花几子上,拍了拍夏婆子的肩,夏婆子猛一醒過來,看見紅芍,用手搓搓臉輕聲道:「天太燥熱,守著守著就犯了睏了。」
紅芍道:「夏嬤嬤幫我一把。」說完去扶柳婉玉的頭。夏婆子忙過來將婉玉上半身扶起,紅芍將藥一勺一勺灌進柳婉玉口中,又用帕子給她擦了嘴。
夏婆子將柳婉玉放躺下來,看著那張桃花面,坐在床邊歎了口氣道:「婉姐兒長得冰雪可愛模樣,可是氣性太大,好端端的投什麼湖,幸虧死活給救回來了,但鬧那麼一齣,姑娘怕以後難做人了。」
紅芍拿了針線笸籮出來,坐在夏婆子身邊,對床上一努嘴低聲道:「就這位小祖宗,難做人的事兒還少嗎?也不怕添這一樁。」
夏婆子忙掩了紅芍的口道:「沒輕沒重的東西,亂嚼舌頭,若是讓太太知道,仔細妳的皮!」
紅芍也知自己說話衝撞了,哼一聲低頭做起針線來。
夏婆子靜了半晌,忽然道:「聽說了沒?昨日還有個人墮湖,竟是楊府的大奶奶梅氏!聽說是不小心滑到湖裡去的,救上來的時候人已經斷了氣。梅府那邊炸了營,梅家老爺帶著人就趕去了,梅家太太哭暈了頭,兩家正商議著如何辦這層白事。」
紅芍繡著一朵菊花,聽夏婆子說得鄭重,便抬起頭道:「這梅氏墮湖難道是什麼了不起的新聞?楊府又是什麼來歷?」
夏婆子失笑道:「我竟忘了,妳剛從外省買過來,不知道我們金陵的事情。我且說與妳聽,這金陵城中有四個大戶,梅、楊、柳、柯,人稱『金陵四木家』,咱們柳家便位列其中。」
紅芍忙道:「夏嬤嬤,妳快將梅家和楊家的事說與我聽聽。」
夏婆子道:「『四木家』中梅家因是詩書傳家,故排名為首。梅家祖上三代做官,傳到這一輩,老爺梅海泉是此地巡撫,二品大員,自是顯赫風光。膝下有兩子一女,大兒子梅書遠金榜高中,入了翰林院,做了京官;二兒子梅書達年紀雖小亦是個秀才。梅家大小姐閨名喚作蓮英,是個知書達禮的大家閨秀,長相卻平庸,這也罷了,竟天生是個瘸子。四年前配與了楊府大少爺楊昊之。那楊大官人真個兒一副好相貌,英俊倜儻的,早年頗惹了些風流債的。這梅蓮英過門第二年便生了個大胖小子,有娘家撐腰,又得了兒子,在楊家哪個不讓她三分?」
紅芍歎道:「真真兒是這梅蓮英的造化!雖生得殘廢,長得亦不漂亮,但娘家聲勢顯赫,還嫁了個如意郎君。」
夏婆子道:「誰說不是,只可惜命薄,無福消受,竟掉進荷塘死了。」說到此處,誰都沒留意婉玉悄悄側過臉對著牆,眼淚順著眼角靜靜滑了下來。
那夏婆子接著道:「這楊家來歷亦不簡單,祖上便是皇商,慣做絲綢生意,自是闊綽,金銀珠寶享受不盡。楊老爺子前年病死,楊老太太健在,二人只有一個兒子喚作楊崢,娶了婉姐兒的姑姑柳氏,育有三子兩女。大兒子楊昊之跟著楊崢做了商賈;二兒子楊景之,聽說是個怯懦性子,媳婦兒是柯家大小姐,閨名喚作穎鸞,精明強悍,玲瓏八面,過門後一無所出,卻不讓楊景之納妾,去年楊老太太發話,把身邊一個大丫鬟配給了楊景之,開了臉做了姨娘。柯氏明裡頭未說什麼,到年底那小妾便不明不白死了,可見她手段厲害了。」
紅芍聽到此處,因自己也是個丫鬟,不由兔死狐悲歎了一聲。夏婆子道:「這楊家老三楊晟之卻是個頂不起眼的庶子,在家裡唯唯諾諾的。一心想走仕途,讀書讀得一股書呆子傻氣;這楊家的大女兒楊蕙蘭嫁了外省大戶,二女兒楊蕙菊還待字閨中,但已和梅家小兒子訂了親。」
紅芍道:「這兩家倒是親上加親了。」
夏婆子道:「可不是,那梅家的小兒子也是個文武雙全的俊俏兒郎,且前程遠大得很,楊家是要死死抱住梅家這棵大樹了。」
婉玉心中冷笑,腦中思緒紛紛,藥力上湧,不由昏沉沉睡了。迷迷糊糊間作了一個夢,夢裡她還年幼,不過六、七歲光景,一日在書房對著爹爹將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她爹爹喜得將她舉起來道:「此等聰慧,男子亦不及也!」說罷又面帶疼惜,摸著她的頭憐愛道:「可惜是個女兒家,若是男子,有這般學識,又何懼身殘?」
夢又轉變,轉眼間她長到十五歲。在家中後園子裡看書,忽而一陣風起,將她放在石桌上的幾張花箋吹遠,直吹到一雙青皂靴旁,那人俯身將花箋拾起,看了一遍,而後含笑望著她道:「這是姑娘做的文章?真是好文采。」她抬眼望去,那男子十六、七歲年紀,長身玉立,身穿雪青色長衫,風度翩翩。她素來深居簡出,幾乎不怎麼見人,如今被這樣清俊的人物一讚,臉兒瞬間紅了,低著頭。她素性淡然,但此刻不知怎的,心裡頭突然因為自己是瘸子而難堪羞愧起來。
過了幾日,她娘親拉著她的手兒笑道:「我兒好福分,楊家派人來提親了!那楊家大公子妳幾天之前在園子裡碰見過,斯文儒雅的。我原本想著多備嫁妝把妳嫁給個家世清白的讀書人家便好,誰想還能結到這樣一門親,那楊昊之說,他就仰慕妳的文章錦繡、滿腹詩書……阿彌陀佛,看著妳出嫁,我也便知足了……」
她爹爹卻皺著眉道:「那楊昊之風流自賞,他的事情我是有所耳聞的。我怕他此番攀親不過看上咱們家世,英兒嫁過去受苦。」她垂下眼,心中酸楚,只覺若是能嫁如斯俊偉丈夫,即便是憑藉家世也無有不可。
夢境之中轉眼間又過了一年。她懷了孩子,夫君恐她寂寞,便將她從小的玩伴柯穎思接到楊府小住,陪她說話。她因著自小殘疾,故而身邊沒什麼夥伴,唯有柯家的二小姐柯穎思自小陪著她一同說話,做做針線。如今柯穎思的姊姊又成了府裡的二奶奶,與她成了妯娌,於是二人走動便越發頻繁了。這一日她將下人打發了,一個人清清靜靜的去書房看書,不多時便聽外間傳來推門聲和腳步聲響。只聽她夫君楊昊之的聲音道:「有話就這兒說吧,這裡素來清靜無人。」
柯穎思聲音尖銳道:「楊昊之,我今日便要問你個痛快話兒!總說讓我等,這如今要等到什麼時候?爹爹已經給我定了王家那門親,可……可我早就把清白給了你了!你個挨千刀的陳世美,你說,這可怎麼辦?」之後便是嚶嚶哭泣之聲。一席話,直將她劈得五雷轟頂,整個人僵直成石頭一般。
楊昊之溫言軟語道:「思妹妹,妳我二人青梅竹馬,是從小的情分,我對妳的心妳還不知道嗎?只是爹爹的意思,我不得不娶了梅蓮英,如今她又有了孩子,在這節骨眼上,妳我之事我自是不好提出來,妳且等上一等吧!」
柯穎思哭道:「我雖是個庶出的,但好歹也是個大家小姐,如今都願意忍氣吞聲的給你做二房,你又擺什麼架子、拿什麼喬?那梅蓮英不過托生得好,鑽進了大戶人家的正妻肚子,論相貌、身段、女紅手藝,在這一輩的女孩兒裡我也算是個尖兒,她一個瘸子哪一點強過我來著?昊哥兒,我對你一片癡心,你萬不能負了我!」
楊昊之柔情款款道:「思妹妹,我若負妳便死無葬身之地,但眼下不是好時機,妳且再等上一等吧。」
屋外男女柔情密意,她縮在牆角裡手足俱冷。成親以來,夫妻二人相敬如賓,好似待客一般,她本以為夫君素性淡薄,原來……自己夫君一腔的柔情已盡數給了別人!若是早知道他有了心尖兒上的人,她斷不會答應提親!
她怔怔坐了良久,原先她偷看過幾本才子佳人的話本,看罷曾癡想著與有情郎君長相廝守。原來,才子早就有了佳人,兩人之間自有愛恨糾葛,她只是多餘人罷了。忽然腹中劇痛,她捂著肚子,死死咬著嘴唇,竟一直忍到那對男女離去才搖著輪椅出門。她受此番刺激,孩子未足月便生了出來。楊家見是個男孩兒,全府上下不由喜氣盈腮,給她道喜的絡繹不絕。她臉上笑著,心裡卻是苦的。
她的夫君每日都來探望她,只坐一坐就走。柯穎思得了風寒,他卻一日之間探望五、六回。她知道夫君來坐上一坐俱是為了表面工夫,或許也因為心中可憐她——這一切只不過是她任性,無自知之明,妄想了檀郎佳偶,有此般下場也活該自作自受。
然而她又作妄想,現如今不如便裝傻,蒙混過關,只作不知道那檔子情事。孩兒都有了她又能如何?況且那夫君是她心心繫繫的人兒,她只要一心體貼,即便是顆石頭,揣在懷裡也能捂熱了,更何況人非草木孰能無情?自己又是他的結髮之妻,明媒正娶進來的,日子一長,夫君會念及她的好處,回心轉意與她相守吧?!
夢境又變了變,似乎又回到了昨日。她心緒憂悶,在府裡荷塘邊閒坐,命丫鬟去給她端壺茶來。就這片刻的工夫,背後忽有一雙手將她直直推入荷塘之中!她腿不能動,只胳膊撲騰兩下,看見柯穎思臉色煞白的站在湖邊,心中頓時雪亮,嗆了水連救命都來不及喊一聲便沉入湖底。恍忽間身子越來越輕,竟飄到湖面上頭。只見楊昊之匆匆而來,對著柯穎思滿面通紅道:「妳瘋了!人都掉下去了還不趕緊喊人!」說著便要縱身而入,柯穎思忙扯住他的衣袖道:「昊哥,你萬不能救她!她知道是我將她推入湖的,若是將她救活,我便要見官了!」
楊昊之登時呆住,跺腳道:「妳這是……妳這是為什麼啊?!」
柯穎思哭道:「還不是為了咱們!我今日上午特地來求她,說我已懷了你的骨肉,求她讓我進門做個二房。我跪了半日,她連眼皮都沒抬一下……那瘸子娘家勢力大,她不讓我進門,我們家和楊家是萬不敢得罪她的,我又是個庶出……昊哥,我真沒辦法了,我已為了你打了兩胎,大夫說這胎再打了,今後便懷不上孩子了!」
楊昊之一沉吟,咬著牙跺腳道:「莫叫旁人瞧見,妳快隨我走吧!」說完扯了柯穎思的手忙不迭的逃了。
她心中又哀又痛又恨,直想衝過去拽著那對男女陪葬。四年的夫妻恩情,十幾年的朋友情誼,竟就這般下了殺手。她飄在荷塘邊欲哭而無淚,天上彤雲密佈,雷聲大作,忽而驚天一道霹雷打下來,她便什麼都不知了。
再醒來,她從梅蓮英變成了柳家小妾之女柳婉玉。
她滿面淚水的睜開雙眼,十幾年的愛恨一晃而過,再回憶恍若隔世一般,真好似長長的作了一場夢。
紅芍和夏婆子絮絮說了半晌,忽聽門外傳來一陣說笑聲,兩人忙止住話頭,只見門被推開,七、八個丫鬟簇擁著五個女子走進來,為首的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婦人,眉眼清秀,高身兆身材,頭綰金鳳釵,身穿墨綠纏枝桃花刺繡鑲領粉綠短襦,同色長裙,手捏一條藍色宮紗帕子,品格大器。這幾個人一走入,立時便把屋子擠得滿滿當當。夏婆子和紅芍趕緊起身,滿面堆笑道:「大奶奶、姑娘們好。」
那婦人道:「婉姑娘的病怎樣了?」
紅芍忙道:「剛餵姑娘吃過藥,現如今還睡著。」婦人聽著屋中鶯鶯燕燕雜亂,便讓丫鬟出去等候,自己則坐到床邊,伸手摸摸婉玉的臉,歎道:「婉姐兒作著夢怎的就哭了?唉,這孩子,想來也是心裡委屈。」說著拿帕子給婉玉拭淚。
只聽得有人冷哼道:「她心裡委屈?瑞哥哥心裡說不定還更委屈!聽說被他爹狠狠打了一頓,還關在祠堂裡兩天不給飯吃。分明是她沒羞沒臉,連累了旁人,這會子怎又說她委屈了?!」
此時又有人道:「妍姊姊,妳這話說得不妥,是柯家二公子先辱婉妹妹在先的,若不是他背後說婉妹妹『繡花的枕頭,粗魯悍婦,天下的女子都死絕了也不會娶她』,妹妹又怎麼會一賭氣跳了湖?」
那人爭辯道:「是她巴巴的貼過去,又送鞋又送荷包,瑞哥哥才……」
話音未落,便聽那婦人道:「都少說兩句吧!」屋中頓時靜了下來。
婉玉暗想:「原來如此,這柳婉玉是因著這個緣故才投了湖,世上悲歡皆是因這一個『情』字罷了。」心中默默一歎,微睜開眼睛,只見屋子裡站了三個姊妹,第一個十六、七歲年紀,鵝蛋臉,杏子目,纖腰盈盈,飄逸清高;第二個十四、五歲,瓜子臉,春水眸,身形嫋娜,粉面含嬌;第三個年紀與第二個相仿,修眉俊眼,膚若凝脂,合中身材,帶著一股英氣。三人均是一色海棠紅衣裙,連釵環絹花也俱都相同。這幾個人婉玉原先都是見過的,她微微瞥了一眼,便又閉上了眼睛。
原來這柳家也頗有來歷,祖上曾封過爵,根基在京城。柳老爺柳壽峰入江寧織造局,做了四品員外郎,品級雖不高,卻是個肥缺。夫人孫氏生了大爺柳禛,今年二十五歲,捐官做了同知,娶了京城官宦小姐張氏,閨名喚作紫菱。其妾周氏生了次子柳祥,方才六歲。柳府中有五個小姐,大小姐柳婧玉入宮為嬪;二小姐柳娟玉嫁給了柯府大公子柯琿;三小姐柳姝玉乃是周姨娘所生之女;四小姐柳妍玉是嫡出之女;五小姐柳婉玉也是庶出,母親卻早亡了,她母親花氏原先是個唱越劇的戲子,生得閉月羞花一般,將柳壽峰迷住了,放在外宅養著,直到私出孩子才帶回家做了姨娘。府裡人嘴上不說,但心裡到底看輕幾分。花姨娘死後,孫氏便把婉玉帶在身邊一直教養。
今日這房中被喚作「大奶奶」的婦人便是柳家大兒媳張紫菱,那氣質高潔的是柳姝玉,嬌俏的是柳妍玉,那英氣的女孩是張紫菱的妹妹張紫萱,如今暫住在柳府。
紫菱見婉玉醒了,忙道:「五妹妹醒了?身子哪裡不舒服,頭還疼不疼?」婉玉閉目不語,妍玉冷笑道:「瞧瞧,自己做了丟人的事,如今還跟嫂嫂使上性子了。」此話一出,旁人俱倒抽一口冷氣,眼睛齊唰唰盯著婉玉,等她跳起來衝向妍玉哭鬧時好將她攔住,卻見婉玉靜悄悄的躺在榻上,眉毛都不曾動上一動。人人心中納罕,只道她身上不爽利。
正在此時,只聽門外有丫鬟道:「大奶奶,太太請您過去,說楊府大奶奶沒了,這層白事怎麼隨禮,要您過去商議。」
紫菱道:「知道了。」說罷握了婉玉的手道:「五妹妹放寬心吧,妳如今病著,爹也不會責罰於妳,安心調養身子,若有什麼要的,直接派人跟我說一聲便是。」說罷帶著人散了。
婉玉側過身,眼淚又簌簌滑了下來。
如此這般過了三、四日,婉玉只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柯家日日派人來問候,送了燕窩、人參等名貴補藥。到了第五日早晨,一個大丫鬟進屋對她道:「姑娘,柯家二爺親自登門給您賠不是,太太命我叫妳去正房。」
婉玉強打精神道:「知道了。」而後起身,命紅芍及小丫頭子打水洗漱淨面。婉玉坐在床上,小丫頭子端了銅盆站在她面前,婉玉等人給她拿毛巾掩住前襟,卻見紅芍垂著眼皮不動,少不得自己將衣襟掩了,用青鹽擦了牙。斜眼一看所用之物不由微微皺眉,原先她還是梅蓮英的時候,每日淨面必用自家製的茉莉皂,那香皂是用茉莉花搗碎配著幾味中藥和珍珠粉製成的,芳香四溢,且滋潤皮膚,而現今用的香皂卻是市面上的常見貨色,用起來不免澀重。婉玉知挑剔不得,便草草洗了臉,接過紅芍遞來的毛巾將臉上的水拭了,換了件月白色的衣裳,站起身走到妝檯跟前。
她自小腿殘,重生為人竟得了具健全的身子,只是她連日來心中苦楚,這層喜悅便被沖淡了不少,這幾日對這身子熟悉了,走起來倒也穩妥。紅芍站在她身後,拿起梳子道:「姑娘想梳什麼頭?」
婉玉道:「簡單些便好,不要太繁複的,也不要插花。」紅芍暗暗稱奇,她這小主人平日裡仗著貌美,最愛扮俏賣嬌,雖沒幾套衣裳,但梳的頭卻是天天變著樣,如今卻像轉了性子。心中納罕,手裡頭卻麻利起來。
婉玉抬頭,只見鏡子中的女孩不過荳蔻年華,兩彎遠山眉,雙目若秋水,紅唇雪膚,榮耀春華,已隱隱有了國色。婉玉看了呆了一呆,暗道:「這柳婉玉倒有個好皮相。」
不多時,紅芍將頭髮梳好了,門外的丫鬟早已等候多時,紅芍道:「白蘋姊姊,我家姑娘已準備停當了。」白蘋道:「姑娘隨我去吧。」說完在前頭引路。
婉玉蓮步輕移緩緩跟在後頭,出了浣芳齋走過抄手遊廊,往西北方穿過一道拱門,旁邊便是下人們住的裙房(編註:指與高層建築相連的建築,高度不超過二十四米的附屬建築,亦稱裙樓),沿著石子路拐一道彎,便能看到西花牆開的一道角門,進去後繞過福祿壽喜字樣的影壁,一排軒麗的正房就在眼前了。
房門口守著個抱著貓咪的小丫鬟,見婉玉等來了,忙起身到門前挑簾道:「等候姑娘多時了。」
婉玉邁步走了進去,此處正是孫氏常居的休息處,靠窗一處大炕,鋪著雲蟒妝花緞子的大條褥,正面設四合雲地柿蒂窠蟒妝花羅靠背,同色引枕。左右兩旁皆是一溜四張梨花木椅子,搭秋香色椅搭,椅旁的菱花洋漆高几上擺著瓜果茗碗等物。
只見炕上坐兩個婦人,正拉著手親熱的說話兒。東側椅子上坐了個十四、五歲的少年,生得面如冠玉、唇紅齒白,頗為俊俏,好似金童一般。那少年繃著臉端坐,垂著眼皮看都不看婉玉一眼。婉玉飛快打量一遍,認得其中濃眉大眼、長臉高鼻的婦人是柳府夫人孫氏,忙恭敬行禮,垂首而立。
那炕上的另一個婦人忙召喚道:「五姑娘,我的兒,快讓我看看。」婉玉低著頭走過去,手便立刻被人握了,婉玉抬頭一看,那婦人頭戴鳳釵,身穿藕色盤金襦裙,身材微胖,五官端莊,此人正是柯府的夫人馮氏。
這梅、楊、柳、柯並稱「四木家」,柯家排最末一位,因這家只是坐享祖蔭罷了。祖上是開平王的手下大將,後封了爵位,雖不是世襲,但從大明開國起便在金陵扎根,至今仍有朝廷俸祿,自有一方勢力。柯家老爺柯旭,膝下二子二女。大兒子柯琿雖捐了個官,卻鎮日在家賦閑,娶了柳家的二小姐娟玉;次子柯瑞十五歲,已有秀才功名。柯家大女兒柯穎鸞嫁給楊家次子楊景之。二女兒柯穎思是庶出,前年出嫁,成親一年便守了寡。
馮氏拉著婉玉的手連連歎道:「水靈靈的姑娘,如今清減憔悴多了。」說完眼睛一瞪那兒坐著的柯瑞道:「都是因為你這混帳小子!還不快給你五妹妹賠不是!」
柯瑞心中煩悶至極,不情不願的起身,作揖行禮道:「妹妹我錯了,給妳賠不是了!」
婉玉忙道:「瑞哥哥哪有錯,是我年紀小不懂事,讓太太、夫人平白擔心,牽連瑞哥哥受罰。」
此言一出,四下皆靜。滿屋人都不可思議的盯著婉玉猛瞧。孫氏也不由大訝,瞇著眼打量婉玉幾眼,板著臉道:「既知道自己平素讓人操心,怎還做出這等事情?大家小姐,本就該文文靜靜,端莊賢淑,妳看妳的嫂嫂和幾個姊姊,哪一個像妳鬧了這麼一齣!」
婉玉忙低頭道:「太太別氣,是我錯了。」
馮氏道:「五姑娘身子還沒大好,就莫要訓斥她了。這件事都怨瑞哥兒,幸好沒鑄成大錯。」說完拿出一個赤金彌勒墜子塞到婉玉手中道:「這個物件是請高僧開過光的,保佑五姑娘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婉玉一迭聲的道謝,退兩步便要行禮,馮氏一把攔了,又一陣噓寒問暖。婉玉一一應答,說太太關心、嫂嫂體貼、姊姊們知疼著熱,下人也辛苦盡力,總之人人俱好,說到最後,孫氏也露出淡淡笑容。
聊了片刻,馮氏帶著柯瑞告辭。孫氏命人相送,而後便坐在炕上靜靜發呆。婉玉站在旁邊,屏聲靜氣的候著,心中暗想:「柳婉玉是個小妾之女,娘親還死了,平素又是個不招人待見的,在這家要處處小心才是。所幸此處還算是個宅門旺族,不至於受凍受餓,還有下人使喚。」
正思索的當兒,孫氏忽然抬起眼皮,看著婉玉不冷不熱道:「婉玉,妳可知道妳給柳家丟盡了臉了?現如今街頭巷尾的誰不在議論咱家的事兒?妳小小年紀就為個男人尋死覓活,將來可怎麼做人?昨個兒老爺還來信,責怪我沒有將妳好好教養,可妳憑良心想想,妳雖不是我親生的,可我待妳一直跟親生女兒一般,吃穿用度哪一點虧了妳了?妳如今鬧到這般田地,讓我……讓我……」說到此處再講不下去,用帕子拭起淚來。
婉玉忙跪下磕頭道:「太太,是我錯了,妳責罰我吧!」
孫氏灑了幾滴淚,一把將婉玉拉起來,拽到身邊語重心長道:「婉兒,我不是怪妳,而是怨我自己。妳在我心裡跟親生的一般,等過兩年必要給妳尋一個好婆家,多備些陪嫁把妳風風光光嫁了……婉兒,柯家二爺那裡妳便死了心吧,人家一則要大戶人家嫡出的女兒,二來馮氏心裡也有了妥帖的人兒。妳如今也不小了,須記著男女大防,今後那些外眷,能不見便不見了吧。」
婉玉低頭道:「太太說的是,往日裡我淘氣,淨惹太太生氣,如今我都改了。」
孫氏道:「我的兒,妳若都改了,不但是妳的造化,也是我的一番造化了!」又跟婉玉說了片刻,方派白蘋將她送走了。看著婉玉的背影,孫氏沈著臉暗思道:「那戲子生的孩子竟突然懂事伶俐起來了,莫非真的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又想:「不管怎樣,如此這般一鬧,柯家是萬不會再看上她了,柯瑞這般人品本是我給妍兒相中的夫婿,怎能讓那戲子的孽種攪壞了這門好親。」
想到這裡,孫氏心中又嘲笑婉玉一個庶出的女兒竟想嫁入豪門大戶,平頭正臉的做妻,不由輕輕笑了一聲。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春濃花開(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1 |
中文書 |
$ 181 |
文學作品 |
$ 207 |
穿越文 |
$ 207 |
華文羅曼史 |
$ 252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春濃花開(上)
可恨哪!
只因愛了個虛情假意的男人,她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雖獲重生,卻有家不能回,有仇不能報,有子不能認……
文創風074《春濃花開》上
前生,她是一品大官的掌上明珠,才情學識都不輸男兒,
雖然容貌平庸,加上自小腿殘,但憑藉著娘家的權勢,
她得以嫁給芳心暗許的男人,帶著滿心喜悅,一心與子偕老。
沒想到卻是遇人大不淑,夫君勾搭上她的好姊妹已是殊可恨,
竟還眼睜睜看著小三殺害她,將她推入荷塘……
再睜開眼,她成了同一日裡投湖的柳府五小姐柳婉玉,
可幸的是,如今換了具健全的身子,還擁有絕色嬌顏,
可悲的是,身分卻換成小妾之女,在家不受待見,在外受人非議,
眼下她只能忍氣吞聲,日日看人臉色,處處小心討好,先掙扎著活下來,
再來想方設法報仇雪恨,讓那對奸夫淫婦血債血償!
還有那前生遺下的心肝寶貝兒,如今是娘死爹不理了,
有什麼辦法能將幼兒護個周全,並重回她懷抱……
本書特色:
本書類型屬於重生報仇雪恨+豪門世家宅鬥。
描述梅家大小姐梅蓮英,容貌平庸、腿殘,卻出身大戶,婚後遭到丈夫背叛和小三陷害,被推入荷塘之中溺死,人雖死但一縷芳魂重生到柳家小妾之女身上。自此她要在錯綜複雜的新環境裏求生存,又想著回去報仇,同時又面臨新的情愛和生活突發狀況;伴隨著無窮無盡的八卦瑣事和歡樂煩惱,人生的悲喜劇就在轟轟烈烈與平淡無波之間悄悄上演了……
本書參加2010年第一屆晉江文學城和悅讀紀合辦
「悅讀紀女性原創網路小說大賽」,獲古代組第一名
作者簡介:
禾晏
禾晏,大陸筆名禾晏山。80後,天秤座。 喜歡閱讀、藝術、旅行以及寫小說自娛自樂。 性格幽默,隨和,好溝通。 內心堅定的樂觀主義者。
章節試閱
第一回 紅芍藥聞聽大家族 梅蓮英魂還深宅門
盛夏,蟬兒在樹上狂鳴,荷塘間微風陣陣,擺動碧葉,傳來陣陣荷香。紅芍托著一碗藥,穿了荷塘邊的抄手遊廊直走到浣芳齋,入內室掀開簾子一看,只見柳婉玉躺在床上雙目緊閉,面色慘白。夏婆子正坐在繡墩子上,頭靠著床欄打盹。
紅芍將藥碗放在床邊梅花几子上,拍了拍夏婆子的肩,夏婆子猛一醒過來,看見紅芍,用手搓搓臉輕聲道:「天太燥熱,守著守著就犯了睏了。」
紅芍道:「夏嬤嬤幫我一把。」說完去扶柳婉玉的頭。夏婆子忙過來將婉玉上半身扶起,紅芍將藥一勺一勺灌進柳婉玉口中,又用帕子...
盛夏,蟬兒在樹上狂鳴,荷塘間微風陣陣,擺動碧葉,傳來陣陣荷香。紅芍托著一碗藥,穿了荷塘邊的抄手遊廊直走到浣芳齋,入內室掀開簾子一看,只見柳婉玉躺在床上雙目緊閉,面色慘白。夏婆子正坐在繡墩子上,頭靠著床欄打盹。
紅芍將藥碗放在床邊梅花几子上,拍了拍夏婆子的肩,夏婆子猛一醒過來,看見紅芍,用手搓搓臉輕聲道:「天太燥熱,守著守著就犯了睏了。」
紅芍道:「夏嬤嬤幫我一把。」說完去扶柳婉玉的頭。夏婆子忙過來將婉玉上半身扶起,紅芍將藥一勺一勺灌進柳婉玉口中,又用帕子...
»看全部
目錄
序言
第一回 紅芍藥聞聽大家族 梅蓮英魂還深宅門
第二回 怒柳父痛打假嬌女 苦閨秀急智避災禍
第三回 傳喜訊婧玉升品儀 訴苦情娟玉忍醋意
第四回 柯二少拾帕惹風波 柳五姐遭戲動干戈
第五回 慶壽辰楊府迎嬌客 偷幽會楊大暗謀劃
第六回 評美人仇人初相見 私相授楊三勇相幫
第七回 楊大郎偷贈前人物 柯二姐苦墮腹中肉
第八回 柳姝玉暗藏一段意 楊晟之悄懷兩樁情
第九回 處處為難貴女受屈 種種不肖孽子遭打
第十回 愚姨娘存心爭臉面 敏婉玉設計阻情思
第十一回 綃帕子惹來姻親禍 冰蓮粥引出雲雨情
第十二回 呆混人欲娶...
第一回 紅芍藥聞聽大家族 梅蓮英魂還深宅門
第二回 怒柳父痛打假嬌女 苦閨秀急智避災禍
第三回 傳喜訊婧玉升品儀 訴苦情娟玉忍醋意
第四回 柯二少拾帕惹風波 柳五姐遭戲動干戈
第五回 慶壽辰楊府迎嬌客 偷幽會楊大暗謀劃
第六回 評美人仇人初相見 私相授楊三勇相幫
第七回 楊大郎偷贈前人物 柯二姐苦墮腹中肉
第八回 柳姝玉暗藏一段意 楊晟之悄懷兩樁情
第九回 處處為難貴女受屈 種種不肖孽子遭打
第十回 愚姨娘存心爭臉面 敏婉玉設計阻情思
第十一回 綃帕子惹來姻親禍 冰蓮粥引出雲雨情
第十二回 呆混人欲娶...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禾晏
- 出版社: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3-28 ISBN/ISSN:978986328019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88頁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