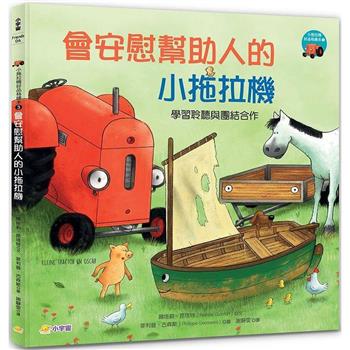錢會咬手燒得慌,糊味兒能熏了天—這說的就是焦家!
焦家不僅是豪門中的豪門,她焦清蕙更是貴女中的貴女,
他們家那是有名的火燒富貴,吃穿用度全是精心挑選,尖子裡的尖子啊……
因著一場惡水,焦家全族數百人全淹在黃湯裡死絕了,僅餘幾個活口,
於是,她焦清蕙自小被祖父當作招婿承嗣家業、延續香火的守灶女將養起來,
聰明才智自是不在話下了,最難得的是她還有男子的果敢作派,
然而,在父親出殯那日,五姨娘給摸出了身孕,之後更生下了焦家獨苗,
想當然耳,她這個名滿京城的守灶女也只得安排出嫁了,
然則當年連先帝想索要她成為太子嬪都沒能成了,如今誰配得上她?
說來這事也實在不需她操心,祖父心中早有人選—良國公府的二子權神醫。
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這個權仲白是名滿天下的神醫,連皇帝后妃都離不開他,
偏偏他超然世外、不爭世子位的態度,與她未來要走的爭權大道不同,
看來想扳倒大房之前,她得先收服了二房這個不成器的夫君才行吶……
本書特色
新婦剛入門就得勞心勞力?幸好她也非省油的燈!
妯娌、叔嫂內鬥只是小菜一盤,夫妻不和亦是三兩下就解決的事,
令小倆口隱隱擔憂的是, 除了皇帝,暗處的敵人也正磨牙伸爪地逼近,
而這一切,似乎都肇始於她的驚天巨富……
作者簡介
玉井香
機關算盡、局中有局之絕妙好手
新世代作夢專家,沈迷於編造故事、創造屬於自己的世界。在我的世界裡,愛情有點bittersweet,有現實的苦也有夢幻的甜,只有最強大的女戰士,才能披荊斬棘,斬惡龍收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