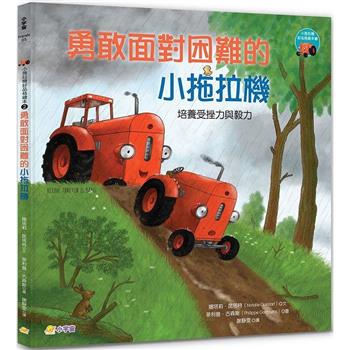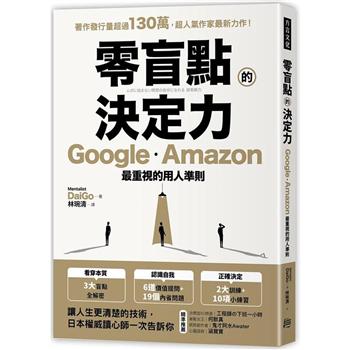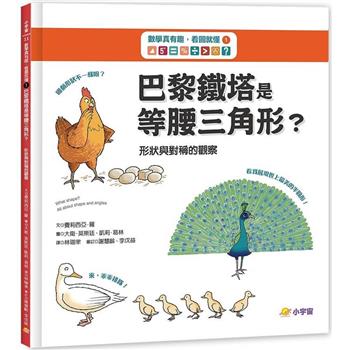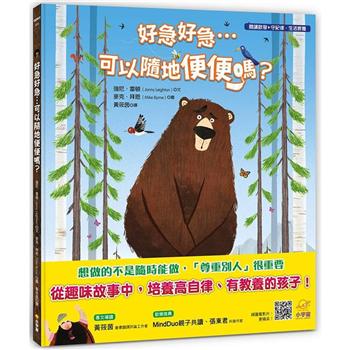第二十四章
四太太心裡有事,自然一整晚都沒睡好,她躺在床上,想一想就是後怕,一則恐怕蕙娘不在,將來失去一大臂助;二則恐懼萬一蕙娘中毒,這對老爺子會是多大的打擊!
喬哥年紀太小,指望不上;文娘是個不懂事的性子,家裡要靠她也難……要是蕙娘和老爺子都沒挺過去,這潑天的家業,要敗起來也就是一、兩年的事—不管誰動的手,這都是在挖焦家的命根子!
可又有誰會動手呢?五姨娘?她倒也許不是沒這個心,可有這個能耐嗎?也所以,她一開始壓根兒就沒往家裡人身上猜疑,直接就猜到了朝廷那傳說中能耐通天的組織燕雲衛身上去,可看老爺子的意思,似乎不置可否,並不這樣認為……
老爺子就是這樣,年紀越大,出事就越藏著。家下鬧出了這麼大的事,他倒還是那八風不動的老樣子,倒顯得自己一驚一乍的,失了沈穩……可四太太心裡已經很久沒有裝著這麼大的事了,她一個晚上都在納悶:就為了一點錢,至於嗎?可要不是為了錢,又為了什麼呢?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令人上後園遞了話—這幾天老太爺心緒不好,在玉虛觀清修,沒有謝羅居的話,哪個院子無事都不要出門走動,有誰敢犯了老人家的脾性,立刻就攆出去打死!
到底是正太太,儘管已經有幾年沒有發威了,這番話傳下去,也依然是唬得人人戰戰兢兢的。幾個心腹丫頭去園子裡巡視過,回來了都說:「幾個院子都關門落鎖的,咱們就只用中午安排人送個飯就成了。」
四太太這才鬆了口氣,她卻不便再去前院了:老太爺今兒照常入閣辦事,國事第一,還不知道要忙到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藥渣被他留在小書房,看來老人家是要把這事攬到自己頭上……
為免其餘各院得到風聲,她連自雨堂都是一視同仁。自雨堂也安靜得不得了,蕙娘就像是個死人,竟沒有一點情緒,綠松昨晚回去,想必是把老太爺的態度給詳細描摹了一番的。四太太心亂如麻之餘,也不禁佩服蕙娘的城府:自己在她這個年紀,簡直比文娘也許還有不如呢!要知道有人想害自己,怕不是早哭成了淚人兒,她卻能沈著冷靜若此。權子殷正月裡和她傳的消息,整整半年了,她是一點都沒有露出端倪。想必外鬆內緊的,私底下,還不知做了多少工夫……
有了這樣的認知,四太太再去回想蕙娘這幾個月的行動,就覺得處處都有了解釋:把自雨堂管得風雨不透的,恐怕連自己都插不進手去;上個月四處遊蕩,卻很少回自家院子裡用飯……甚至和太和塢都忽然友好起來,原來是應在了這裡!她還納悶呢,以蕙娘的性子,就算要出嫁了,將來也是娘家靠她更多,她犯得著和五姨娘眉來眼去、禮尚往來嗎?卻原來,還是為自己的性命著想,想要與人為善,或者就能把禍患消弭於無形了。
四太太是厚道人,前思後想,越想越覺得為蕙娘委屈,也就越想越是生氣。彷彿有一種久違的激動,從她身體裡慢慢地醞釀了出來,倒令她的精神頭要比往日好了許多。老太爺沒從皇城回來,她就自己坐在窗前冥思苦想,把這幾個月府裡的行動、局勢掰開來揉碎了在心頭慢慢地咀嚼,想了半日,又叫過綠柱來,同她細細地說了許多話,綠柱均都一一答了。
等老太爺回了閣老府,從前院傳話過來請她去相見時,四太太的臉色真的很沈,她的心情,也真的很壞。
「試過藥了—」老太爺開門見山,四太太一進屋,他就衝著下首扶膝而坐的老者點了點頭。「小鶴子,你來說吧。」
閣老府大管家焦鶴,跟隨老太爺也已經有五、六十年了,他一家人一樣毀於水患,同三姨娘一樣,因是經過當年慘事的家人,在主子跟前都特別有體面。聽老太爺這麼一說,他顫顫巍巍地站起身來,作勢要給四太太見禮。
四太太忙側身避開了,笑道:「鶴老不要客氣,您快坐吧!老胳膊老腿的,還跟我折騰。」
焦鶴雖然比老太爺小了十來歲,看著卻比老太爺更老邁得多,鬚髮皆銀,滿面皺紋,看著就像是個鄉間安居的老壽星。四太太才這麼一客氣,他也就順勢坐下,沒有絲毫客氣寒暄,便交代起了試藥經過。
「因是配好的藥方,藥材全是搗過切過的,光從藥渣,看不出什麼來,大夫說恐怕是斷腸草,只不知道用量。因貓狗畢竟和人不同,我便使了些銀子,在順天府尋了個死囚犯,拿藥渣重又熬了一碗藥灌他喝了……」他沈默了一下,才道:「一整夜都沒有事,還當是姑娘多想了,就是午時前後,忽然吐了血,話也說不清了。在地上就只是抽抽,摁都摁不住……抽了兩個時辰,人暈過去了。這還是熬過一水,藥力還這麼足,要是第一道,怕是沒救了。」
四太太費力地吞嚥了幾下,心頭到底還是一鬆,她看了公爹一眼。「斷腸草、發作得這麼急……我看,不像是天家的手筆。」
「是。」老太爺頭也點得很爽快。「他們慣用的毒藥,可要比這個隱密得多了。」
焦鶴撚了撚鬍鬚,說得更直接。「除了家賊,誰有那麼大本事,能往主子頭上下藥?我們家可不是隨隨便便的道台、巡撫,連江湖殺手都能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這擺明了是在譏刺楊閣老。當年他還是江南總督時,就曾鬧過刺客潛進後宅的事。雖說背後有一定文章,但楊家因為此事,在高門中落了不少話柄,就連選秀時,都不是沒人拿來說嘴的:隨隨便便,就能讓人潛進後宅,主人還茫然不知,誰知道家裡的姑娘,平時是不是也能隨意出入深閨?更有人思維很發散—家裡人口這麼少,還顧不過來呢,他楊海東有心思去為整個天下盤算嗎?
楊家人口少,焦家人口就更少了。就這麼幾個主子,吃的用的,肯定都是經過層層審核,不知來歷的東西,不要說被主子吃進去了,就連要進後院都難以辦到。雖說僕役如雲,但管理嚴格,馭下嚴厲,這些年來,在後院從沒有出過一點么蛾子。除非是燕雲衛這樣有官方背景的特務組織,外人想要把手插進焦家後宅,簡直是癡人說夢。
四太太長長地嘆了口氣,也不禁生出了幾分惋惜,她望了公爹一眼,輕聲說:「爹,我看這事,太和塢難逃嫌疑。」
「喔?」老太爺神色不動,只聲調抬高少許。「巧了,就剛才小鶴子還和我說,這家裡要有誰會動佩蘭,也就只有五姨娘了。」
「這幾個月,梅管事和太和塢走得滿近的。」焦鶴咳嗽了一聲。「本來嘛,未雨綢繆,也是人之常情。前陣子他來找我談他女兒石英的去向……」
他看了老太爺一眼,老太爺動也不動的,可焦鶴竟不知是從哪兒得到了暗示,他跳過了焦梅要陪房的消息。「我聽其意思,是不大想令石英陪嫁過去的。要在府中找,那肯定是想和太和塢攀親了……就是喬哥兒的養娘,不還有個小子是沒成親的?」
這沒板沒眼的事,從焦鶴口中說出,就透著那樣入情入理。四太太聽住了。「鶴老意思,是焦梅從蛛絲馬跡中,推測出了我們給蕙娘定的嫁妝,扭頭就給太和塢遞了話?」
「無憑無據的事,不好胡說。」焦鶴猶豫了一下。「但那麼一筆大得驚人的財富,要動,肯定是有動靜的……他說知道也行,說不知道也行,就是嚴刑拷打,恐怕也都很難逼出準話,只能說有這個可能吧。」
蕙娘的陪嫁,即使以焦家豪富來說,也算是傷筋動骨了。四太太自己可能還不大在乎,但五姨娘是有兒子的人,想得肯定就不一樣……她雙眉緊蹙。「可這才是近半個月的事,她的動作,有那麼快嗎?」
正說著,又想起來向老太爺解釋。「這件事,按理來說是該問問您的,但當時過年,您實在是太忙了,我也就自作主張……麻氏找我說了情,想收她一個親戚進府,我想她一家自然是身家清白,便答應了下來,也沒有多做過問。今兒問了綠柱,才知道……」她的聲音低了下去。「他人就在二門上當差。不過,始終也還是太快了一點吧?嫁妝定下來到現在,說真的也就是十天多一點兒……」
焦家門禁森嚴,就拿自雨堂裡的丫頭來說,小丫頭不必說了,哪有她們回家探親的分?除非病了、笨了,主子打發出去了就再不能進來,否則沒有回家的道理。有臉面的大丫頭,一年有兩、三次能回家看看,身邊也都跟了服侍人,一來,也是彰顯身分,二來最主要,多少起到一點監視的作用。凡是在內院服侍的大丫頭,就沒有例外的。五姨娘就是想往裡頭弄點藥,也沒有那麼簡單。她守孝三年沒有出門,到現在連娘家都沒回過,就假設真是她所為,斷腸草那也不是那麼好弄到的,從傳話到設法神不知鬼不覺地弄到毒藥,再往裡送,她還要找機會放進蕙娘的藥湯裡……這事哪有這麼簡單?
焦鶴點了點頭。「太太說得是,麻家的家世還算清白,一家子也沒有什麼地痞無賴,要弄到毒藥,雖也不是不能,但他們沒那麼大的能耐……」他輕輕地咳嗽了一聲,面無表情地說:「不過,這也不是五姨娘第一次有機會和外頭聯繫。太和塢的丫頭婆子,雖然都經過特別甄選,絕不會做出不該做的事,但……去年臘月裡,幾位姨太太去承德莊子小住的時候,五姨娘倒是出去過一次,和她娘家兄弟見了一面,說了幾句話。她有個兄弟就在承德開了間米店。」
四太太越聽越是生氣,她銀牙緊咬。「小門小戶的女兒,因為生了個兒子,這幾年來家裡是雞犬升天,她還有什麼不足夠的?平時挑唆著喬哥和兩個姊姊疏遠,我體諒她也就喬哥這個獨苗,再怎麼小心都不過分的—」
老太爺神色一動,打斷了四太太,聲音一沈。「挑唆喬哥?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我怎麼連一點都不知道?」
四太太吃驚地看了焦鶴一眼,見焦鶴神色篤定並不說話,她心頭一突。「還以為您知道……當時讓她帶著喬哥,就是因為她畢竟是喬哥生母,對孩子是最上心的,平時連一個點心,都要自己吃過了再給喬哥吃。可也就是她的這個小心過分……因蕙娘身分,難免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此平素不喜歡喬哥和姊姊親近,我也就沒開口。這親事一定,她倒也知趣,就經常抱著子喬去自雨堂作客了。」
家裡除了謝羅居,幾處院子都有老太爺的眼線。老人家也無甚特別用意,不過意在掌握府中大小事務而已,四太太對這點,心頭也是有數的。她甚至還知道往常負責聽取消息、過濾彙報的正是焦鶴……可這幾年來,鶴老年紀大了,精力漸漸不濟,看他表現,似乎這差事已經換了人做。就不知是誰那樣著急討好未來的主子,竟瞞報了消息—五姨娘的用心,幾番都有體現,要說漏報,那是不可能的,這麼敏感的事,肯定要同上頭一提,也就是在消息過濾這一層上,被人給卡住了沒往上說而已。這是拿準了以蕙娘的傲氣,絕不會私底下和老太爺告太和塢的刁狀,第一她不屑,第二,這也不是她能做的事……
老太爺倒真是第一次聽說這麼一回事,他尋思了片刻,不禁微微冷笑,卻並不再提,反而冷靜逾恆地為五姨娘說了幾句話。「就是她拿到了藥,要怎麼下毒?小庫房她可伸不進手去,那不是她可以經常過去串門的地方……要下毒,也就是到自雨堂裡去了。但自雨堂是什麼情況,妳也是知道的。從小養成的習慣,要緊的地方幾乎不離人。麻氏就有通天本領,又怎能把毒給下進去?」
這一點,焦鶴肯定是答不上來的。四太太也有點抓瞎,她越想越覺得迷惑:此事疑點重重,可議之處頗多。最可怕的是,焦家人就這麼幾個,如不是五姨娘,又不是燕雲衛,難道是誰家還有這樣的能耐,悄無聲息地把手伸進了焦家來……可要如此,他們又何必用這樣的毒藥呢?光是四太太所知,可以無聲無息置人於死地的鴆毒之物,就已經有十幾種了,這還是她根本無心此道,只是從前聽丈夫閒談間提起而已……
「那,唯一的可能,也就是她最近去自雨堂的時候,乘機把藥材給混進去了吧……」四太太自己囁嚅了幾句,也有點暈乎了。
老太爺卻還是那樣泰然,他「嗯」了一聲,轉向焦鶴道:「去把自雨堂的雄黃,太和塢的透輝叫來吧。」
雄黃是老太爺的眼線心腹,這四太太是不吃驚的,她父親也是焦家產業裡有數的大帳房了,當時會進來服侍,其實多少是為蕙娘日後接管家業打個伏筆,她的身分,在自雨堂裡都算是比較特出的,即使是蕙娘對她也很尊重。倒是太和塢最有臉面的透輝竟是老太爺的人,這多少令她有幾分吃驚,再一想,卻又心悅誠服:處處埋著伏筆,永遠防患於未然,老太爺就是老太爺,即使這樣的細節上,也都透了名家風範。
雄黃和透輝很快就被帶進了小書房,焦鶴會辦事,他把兩個人分頭帶進來。第一個進門的是雄黃,這位眉清目秀、身材姣好的大丫鬟默不作聲地給兩位主子行了禮—即使是在相爺跟前,她也顯得從容不迫,面上雖有些嚴肅,但四太太和老太爺都明白:和她父親一個樣,他們一家子,都是這麼不苟言笑。
「五姨娘最近是常來太和塢。」即使兩個主子忽然要查問這麼敏感的一回事,雄黃面上也看不出絲毫猶豫,她回答得平靜而機械,就像是一雙不含偏見的眼—老爺子用人,一向是很到位的。「十三姑娘也很給她面子,大家笑來笑去的,看著倒很和睦,我們底下人自然也都有些議論……每次五姨娘過來,石墨都躲出去,孔雀也一樣,從不給五姨娘好臉色,除此之外,倒沒什麼特別的事。幾次過來,奴婢都在屋內、院中當差,並未見到、聽說什麼可說之事。」
老太爺一手撫著下唇,他看了焦鶴一眼。
焦鶴便問:「五姨娘過來的時候,可有沒有單獨在裡屋逗留?」
「這……」雄黃面現遲疑,想了想才道:「倒是有一次,六月裡,她過來的時候,正好撞見姑娘又犯了噴嚏,進淨房去了,令我進來服侍五姨娘。當時裡頭人也不多,孔雀本來是一直在小間裡的,可自從她因五姨娘來要首飾沒給後,次次五姨娘過來,姑娘總就給她找些差事,令她出去,當時就是令她去浣洗處催姑娘的手帕,因此屋內就我招呼姨娘同喬哥。過了一會兒,綠松令我進去找帕子,也就這麼一會兒工夫,整個東翼都沒有人。後來我們出來的時候,喬哥在玩姑娘平日裡收藏的古董盒子,五姨娘彎在喬哥身邊,瞇著眼想從縫隙裡看進去……彼此還都有些尷尬—」
「這一會兒工夫,究竟多久?」老太爺打斷了雄黃的敘述。
雄黃回想片刻後,肯定地回答。「總有個一炷香時分吧。」
一炷香時分,孔雀人又短暫離開……估計是沒有鎖上小間門,五姨娘要是手腳快一點,也可以進去動點手腳了。
老太爺點了點頭。「妳們姑娘的太平方子,幾天吃上一次?」
「一向是十天上下吃一次。」雄黃面露驚容,回答得卻還是很謹慎、很快速。說完了這句話,她猶豫了一下,又補充。「姑娘這幾次喝的藥也多,前陣子還喝了專治噴嚏的湯藥,幾次喝藥的日子,分別是六月十八、六月二十九……」便說了幾個日期出來。
這一次不等老爺子,四太太都知道問:「那五姨娘上個月是什麼時候去的太和塢?」
雄黃屈指算了算,她的聲音有點抖了。「大、大約是六月二十八。」
四太太猛地一拍桌子,她才要說話,老太爺已一擺手—
「妳可以出去了。」
遣走了微微發顫的雄黃後,他疲憊無限地搓了搓臉,倒是搶在媳婦跟前開口了。「我知道妳要說什麼……小庫房每個月給自雨堂送東西,就是在月中。」
也就是說,當時還有兩包藥在小間裡放著,恐怕臨近熬藥的日子,孔雀也就沒有收納得很密實,只是隨意撂在屋裡……
四太太牙關緊咬,幾乎說不出話來。
老太爺卻還未失卻鎮定,他若有所思地將手中兩個核桃捏得哢哢作響,等透輝進了屋子,便開門見山地問透輝。「五姨娘最近,可有什麼異動?」
透輝就沒有雄黃那麼上得了臺盤了,她顯得格外侷促,在兩重主子灼灼的逼視之下,聲若蚊蚋。「還是和從前一樣,和胡養娘走得很近。除了悉心教養喬哥之外,得了閒也就是往自雨堂走動走動,再、再同南岩軒、花月山房爭些閒氣……」
「喔?」老太爺微微抬高了調子。「比如說呢?」
比起雄黃那樣鎮定自若的表現,透輝如此驚惶,反而使得她的說辭更加可信—明眼人一望即知,她完全是被這場面給嚇怕了,別說玩心機,怕是連氣氛都讀不出來,老太爺這一問,她倒是竹筒倒豆子一樣,從臘月裡「聽說了橘子的事,當時沒說什麼,第二天就哄著喬哥多睡一會兒,後來,聽說在謝羅居……」、「花月山房得了自雨堂的東西,她也去要,回過頭和胡養娘說起來『再不殺一殺自雨堂的威風,這府裡還有我落腳的地兒嗎?』」、「幾次和南岩軒見面,都不大客氣……」一路說到了最近「還是不許喬哥同花月山房親近,十四姑娘幾次送東西來,都沒讓喬哥見到,私底下說『誰知道她安了什麼心!』」。
雖面目可憎,但畢竟都是無關緊要的小事,老太爺聽得幾乎打起了呵欠,透輝越看臉色就越是恐慌,最終她住了口,咬住了嘴唇。「也就是去年年前,姨娘不知從哪兒得了風聲,像是知道了奴婢的身分,從那時候起,很多話都不當著奴婢說……常令奴婢在外跑腿兒,連同娘家兄弟見面,都沒令奴婢在一邊服侍。奴婢知道的,也就是這些了,倒是胡養娘,也許知道得更多些……」
四太太至此,反而不再吃驚憤怒了,她甚至嘆了口氣。要是心中沒鬼,又何必如此防備?雄黃擺明車馬就是老太爺的眼線,這些年來也沒見蕙娘對她如何。還有花月山房,文娘不喜歡藍銅的作派,可還時常令她在身邊服侍……家裡這麼大,一個小姑娘住一個院子,長輩不放心,指派個人過來看著,那是人之常情,有什麼需要避諱的?南岩軒兩個姨娘,也從來沒有做出過這樣的事。五姨娘這個人,處事也實在是太淺薄了,稍微一經查問,就已經破綻百出。
打發走了透輝後,她和老太爺商量。「爹,您看這事該怎麼處理?」
「妳的意思呢?」老太爺不置可否,他摸著下巴反問了一句。
「這賤婢竟如此狠毒,人是留不得了。」再怎麼樣,蕙娘也是在四太太眼皮底下長大的,四太太難得地下了狠心,她一咬牙。「娘家人心術不正,留在京城,對喬哥將來,恐怕也是弊大於利……索性一併清理了。把喬哥……」她再三猶豫,最終下了決心。「把喬哥抱到謝羅居來吧!」
老太爺眼底神光一閃,他過了好半晌,才慢慢地吁了一口長氣。
多少複雜的情緒、多少長年積累下來的擔憂,竟都在這一口氣裡體現了出來,老太爺的欣慰,誰都能看得出來。「妳早該這麼辦啦……」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豪門守灶女(2)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1 |
中文書 |
$ 181 |
文學作品 |
$ 196 |
社會人文 |
$ 207 |
穿越文 |
$ 207 |
華文羅曼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豪門守灶女(2)
她怕死,因為她已然死過一回,經歷過那種痛苦。
重生後的她,一心想找出害死她的凶手,不想再這麼死去,
家裡這些親人中,是否就有人非要她死不可呢?
文創風103《豪門守灶女》2 (拆封不退)
從小祖父焦老太爺就是這麼教她焦清蕙的—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有錢有勢,自然就有人覬覦。
潑天的富貴看著是好,可要沒有撐天的實力,那也只有被淹死的分。
天下的富貴就那麼多,他們焦家硬是獨攬了幾分去,
若說焦家是豪門中的豪門,那她無疑是貴女中的貴女,
她被養得嬌貴,平時吃的用的直是比宮裡的娘娘們還要好,
這輩子她沒嚐過第二的滋味,到死她都是第一。
不過,人都死了,就算生前是第一又有什麼用?
這輩子她也就輸這麼一次,甚至連死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她不想再死一回,所以重生後就得好好活,活得好,並揪出凶手來!
本書特色
新婦剛入門就得勞心勞力?幸好她也非省油的燈!
妯娌、叔嫂內鬥只是小菜一盤,夫妻不和亦是三兩下就解決的事,
令小倆口隱隱擔憂的是, 除了皇帝,暗處的敵人也正磨牙伸爪地逼近,
而這一切,似乎都肇始於她的驚天巨富……
作者簡介:
玉井香/機關算盡、局中有局之絕妙好手
新世代作夢專家,沈迷於編造故事、創造屬於自己的世界。在我的世界裡,愛情有點bittersweet,有現實的苦也有夢幻的甜,只有最強大的女戰士,才能披荊斬棘,斬惡龍收王子。
章節試閱
第二十四章
四太太心裡有事,自然一整晚都沒睡好,她躺在床上,想一想就是後怕,一則恐怕蕙娘不在,將來失去一大臂助;二則恐懼萬一蕙娘中毒,這對老爺子會是多大的打擊!
喬哥年紀太小,指望不上;文娘是個不懂事的性子,家裡要靠她也難……要是蕙娘和老爺子都沒挺過去,這潑天的家業,要敗起來也就是一、兩年的事—不管誰動的手,這都是在挖焦家的命根子!
可又有誰會動手呢?五姨娘?她倒也許不是沒這個心,可有這個能耐嗎?也所以,她一開始壓根兒就沒往家裡人身上猜疑,直接就猜到了朝廷那傳說中能耐通天的組織燕雲衛身上去,可看...
四太太心裡有事,自然一整晚都沒睡好,她躺在床上,想一想就是後怕,一則恐怕蕙娘不在,將來失去一大臂助;二則恐懼萬一蕙娘中毒,這對老爺子會是多大的打擊!
喬哥年紀太小,指望不上;文娘是個不懂事的性子,家裡要靠她也難……要是蕙娘和老爺子都沒挺過去,這潑天的家業,要敗起來也就是一、兩年的事—不管誰動的手,這都是在挖焦家的命根子!
可又有誰會動手呢?五姨娘?她倒也許不是沒這個心,可有這個能耐嗎?也所以,她一開始壓根兒就沒往家裡人身上猜疑,直接就猜到了朝廷那傳說中能耐通天的組織燕雲衛身上去,可看...
»看全部
目錄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玉井香
- 出版社: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7-18 ISBN/ISSN:978986328101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96頁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