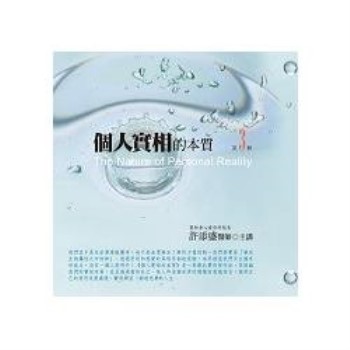第四十九章
蕙娘還真沒接觸過這個桂家少奶奶—先不說夫家是外地望族,本身丈夫品級也還低,距離蕙娘所在的交際圈,還差了那麼半步,就她在京城的時間可也不長。但她是聽說過桂少奶奶的名氣的—她丈夫自從進京,擺明車馬絕不納妾,甚至連通房都不收用,幾乎因此不見容於整個社交圈,善妒的名聲就這麼傳開了。就是前幾年,因她不知如何得罪了太后,太后藉口數落她妒忌,給她姑爺桂含沁賞了一位溫柔大方、極是可人的宮女子,可桂含沁受少奶奶轄制慣了,根本就不敢收用,因少奶奶當時還不在京裡,為怕說不清楚,頭天納妾,第二天就把人給賣到窯子裡去了!這件事在京城激起軒然大波,連太后都氣病了!桂含沁本來出身世家,為皇上看重,簡直是前程似錦,因為這事,鬧得遠配廣州……成了天下知名的「怕老婆少將軍」。在軍隊中,不知道新一代將星許鳳佳的人多,可不知道這個桂含沁的,恐怕真是鳳毛麟角。
就是這麼一個妒忌出了名的女兒家,人緣卻並不差,進京才一年不到,就得了她娘家幾個族姊的喜愛,連皇后都頻頻抬舉,可謂是出盡了風頭。就是在楊家壽筵上,她還聽到楊四少奶奶和閣老太太念叨她呢,閣老太太都那樣喜歡地說「可惜她下廣州去了,這一年多家裡是真冷清」,要說心裡沒有些好奇,那是假的—蕙娘雖不是好事性子,卻也不是死人。可她沒想到,連對著後宮妃嬪都沒有一句好話,提到楊寧妃、牛美人這樣的絕色,好像在談一對老頭子的權仲白,對她的評價居然這樣高……
小夫妻相處,就像是在打仗,誰也不會貿然就把情緒給露在面上。蕙娘從前被權仲白氣得再厲害,基本風度總是能保持的。可這回權仲白把話說得這麼過分,她也有點吃不消了,眉宇一凝,就要回擊,可究竟又強行把話給嚥下去了。
權仲白看了她一眼,語氣並未放緩。「京城傳她妒忌,傳她姑爺桂含沁懼內,很多話都說得不大好聽,那是一般人無知好事,得了一點八卦,便滿世界胡說取樂。可若連妳都輕信傳言,胡亂說嘴,這真是一大笑話了。閣老府獨女、守灶的千金,妳以為市面上沒有妳的故事嗎?」
這話真利得似一把刀,正正地戳中了蕙娘的軟肋:她身分且高,過的還是天人一般的日子,即使知道內情的親友,沒有相信那些個傳聞的,可在一般富戶心裡,焦清蕙連鼻子都不用擤,有了涕淚,是要讓老媽子來親自吸出來的!更有些事情,傳得幾乎都不堪入耳了……世人好以訛傳訛,她難道還不夠清楚?她難道沒有吃過口舌是非的虧?
只是一句說笑而已,就惹來權仲白正色說教,蕙娘垂下頭去,要服軟又不甘心,不服軟又覺得自己理虧,倒是罕見地體會到了權仲白被她堵得無話可說的滋味。僵了半天,才軟綿綿地道:「這麼說,你是知道內情的嘍?」
權仲白究竟是個君子,不如她次次都要捏個夠本,見蕙娘自己難堪起來,便放過了她,緩緩道:「有些事外人不清楚,實際上桂家家事,並不是她在作主。桂含沁此人心機深沈、天才橫溢,一旦遇有機會,將來成就如何,我是不敢說的。這樣的人,哪裡會因為懼內,就隨妻子擺弄,甚至不惜得罪牛家?他是自己情願一生都不納妾,只因為痛惜妻子。坊間不知底細,胡亂傳說,妳不要跟著亂傳。」
這裡頭一聽就是有故事的,蕙娘更好奇了,見權仲白不想往下說,竟是要起身出去用飯的意思,她有些發急,竟學了文娘,一跺腳。「唉,你就說個開頭,又不細談!他們遠在西北,是成了親才進京的吧?你怎麼就知道得那樣清楚?」
權仲白只好略略告訴她。「就只提幾句,妳便明白了:當年成親的時候,三姑娘是二品大員、巡撫家的嫡女,伯父是朝野聞名的清知州,父親是陜甘巡撫……桂含沁呢,當時只有一個世襲的四品銜,那還是虛職,實職是一樣沒有,家裡田地都只得一點點。這門親事,實在是三姑娘本人執意方能成就,桂含沁當時親自進京跑媒人,我還幫了他一把……這世上有情人多了,真能成就眷屬的又有幾個?似三姑娘這樣慧眼識英雄的就更少見了,當時見到她,我就覺得她特別坦誠可愛,膽子又大、心思又細,同桂含沁之間很有默契。可畢竟她年紀還小,也沒往深想,沒想到她居然能有這樣大勇、這樣的決心,竟真能排除萬難,說得娘家許嫁。就是桂含沁,能成就這門親事,花的心思也是絕不少的。」
這番話說得閃閃爍爍的,多少故事,似乎都能隨之敷衍出來。蕙娘想到前些年他進西域採藥的事,心中多少也有個數了。想來當時西北戰亂,楊三姑娘沒準真和權仲白打過照面—那是八、九年前的事,當時自己年紀還小,可權仲白卻已經是喪偶身分了……
她忽然間又想到權仲白退親時所說—
「我並不覺得存在此等想望,有什麼非分。」
唉,只看他如此稱賞桂家這一對,就能看得出來了,他是真正在追逐著所謂的真情誼……
「道不同不相為謀,您不但和我不是一條道上的人,而且也還似乎不大看得起我。人生在世,總是要搏上一搏,您不為自己的終生爭取,難道還要等到日後再來後悔嗎?」
他真正是說得不錯,她是挺看不起他的,而他和她,也真的就不是一條道上的人……
「那,」蕙娘不知為什麼,心緒竟有些微微的浮動,她雖然輕聲細語,可詞鋒之銳利,卻不下於片刻前的權仲白。「你為什麼娶我呀……光會羨慕別人,你自己呢?還不是光說不練,口中的把式。」
權仲白瞟了她一眼,竟並未生氣,他淡淡地道:「妳又知道我沒有爭取過?如沒有,妳前幾天拜的墳是哪裡來的?」
他在蕙娘跟前,總是顯得那樣不鎮定,隨意挑勾幾句就動了情緒,每每被氣得俊臉扭曲,那樣子別提有多可樂了。蕙娘幾乎都沒想到他還會有這麼一面,一點情緒不動,那張俊秀風流的面孔,就像一片深幽的海,所有的情緒都被吞了進去,所有的故事都沈在下頭,竟似乎再沒有什麼事物,能引動他的潮汐……
「你不是沒回來嗎?這都知道了……」她輕聲嘀咕,雙眸遊走,竟是頭一回不敢和權仲白眼神交接。「奶公前幾天進城辦事……是他告訴你的?」
「他說了妳很多好話。」權仲白沒有否認。「讓我得了空就趕緊回來,別在京城逗留了,妳一個小姑娘在香山待著寂寞。」
會籠絡張奶公,不過是題中應有之義,沒想到他竟這樣上心,說是進城辦鋪子裡的事,如今看來,竟是專程去催權仲白回來的……蕙娘不是容易被打動的人,心頭也不禁微微一暖,她的語氣緩和了下來。「我就說,以你的身分,元配怎麼會是她的出身……原來這門親事,還真是你爭取回來的。」
見權仲白望著自己,若有所指,蕙娘有點不高興,她一攤手,人倒又潑辣起來了。「看我幹麼?我要是和楊三姑娘一樣有幾個兄弟,我也一樣去爭,誰還要嫁你呀?難道我就沒有別的心上人?就是你,爭取來爭取去,還不是沒能爭取不娶我嗎?咱們一樣爛鍋配爛蓋,都沒能耐!」
「我一句話沒說,妳就又來堵我!」權仲白滿不高興地說,可那大海一樣的深沈畢竟是消退了。「我就奇怪,妳和我一樣沒能耐,可妳還老看不起我做什麼?」
「我是女兒身呀,姑爺!」蕙娘要堵他,哪裡沒有理由?「我但凡是個男人,早都鬧得天翻地覆了!您要是不歡喜做男人,我同你換!」
兩人大眼瞪小眼,又沒話說了,可不知為何,氣氛卻輕鬆下來,要比一開始權仲白放下臉數落她時鬆快得多了。權仲白沒說話,只是若有所思地把玩著茶杯。倒是蕙娘,她有點好奇:這個人心裡,一般是存不住事的,起碼對她,他有不滿都一定會表現出來,可……
「我早想問你了。」她輕聲說。「那天在宗祠,『吾家規矩、生者為大』,我只行了姊妹禮……你心裡,沒有不高興呀?」
「那又和妳沒關係。」權仲白倒有幾分吃驚。「就是生氣,我也是衝著爹娘。不過,這又有什麼要緊呢?」
也許是因為要說服蕙娘,也許是因為被蕙娘勾動了對前人的思念,也許是因為,蕙娘今天的語氣畢竟要比從前緩和,態度畢竟要比從前坦誠,就連嫌棄他,都嫌棄得不是沒有道理,因此即使談到的是達氏這麼敏感的話題,權仲白也一點都沒有露出別樣的情緒,他就像是在和蕙娘談別人家的事。「妳和她本不相識、素未謀面,又沒有任何交情,別說姊妹禮,就是不行禮、不上香,我看也沒有任何問題。」
他的別出機杼,還真是一視同仁,就連達氏都沒能逃得過這獨特的邏輯。蕙娘啼笑皆非,她不無試探。「香都不上,我也怕你生氣呀……」
「妳還會怕?」權仲白不由得失笑。
這句話,他說得很好,蕙娘面上一紅,無話可說了。
也許是她難得的窘態取悅了權仲白,他沒有再繼續調侃蕙娘,多少也有幾分感慨。「人都死了,沒有什麼生氣不生氣的。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凡是去世者,都已經輸了這最重要的一局,早晚會被沖到再看不見的地方去。生者為大,這規矩是有道理的,死人又哪能和活人爭呢?」
這話似有深意,可以權仲白的作風,又像是單純的感慨,但聽在蕙娘耳中,卻不禁勾動了她的心事。她輕輕地搖了搖頭,低聲道:「唉,又有誰是甘願去死的呢?這世上沒有誰不是奮力求活的……」
「就因為這世上誰都在奮力求活,」權仲白順著她的話往下說。「哪管生前權勢滔天,死後也一樣是黃土一抔,不論是躺在歸憩林裡,還是躺在亂葬崗上,其實於死者有什麼差別?死後哀榮,告慰的都是生者。這話只能在私下說,可條條人命都關天,生死實在是最公平的事。我知道妳的心思,妳還是想要爭一爭……妳未必真願意納妾,這世上沒有哪個女人是願意納妾的,可就因為妳想要爭,妳不能讓人捉住妳的痛腳,就是現在不抬舉,妳留那個什麼綠松在家裡,是有別的用意,可將來妳也還是要抬舉的。妳要抬舉,就要提防著她們不能太受寵、不能威脅妳,而她們也難免會有別的想頭。大戶人家,妻妾相爭鬧出多少條人命,我是最清楚的。這些年來,看得難道還不夠多?」
蕙娘眉眼一動,她還有點不死心,尤其權仲白竟站在如此高度來教她——她畢竟是有些不服氣的,沒話找話都要回一句。「你知道這個,就別太寵著不就完了唄……」
「不寵著,我晾著她一輩子,一輩子不進她的門、上她的床?」權仲白眉宇再沈,他越說語氣越冷。「小姑娘一輩子就這麼消磨了,這糟踐的不是人命嗎?這世上可不獨妳的命是命,人家的一輩子不是一輩子嗎?別人院子,我管不著,可這樣血淋淋的事情,我絕不會做。」他的失望是如此明顯,瞎了眼都能看出來。「妳好歹也是守灶女出身,就看在從小受的教育分上,也不至於還想著抬舉通房……就是人家三從四德教出來的女兒家,還想辦法捏著丈夫不給抬舉呢!唉……」
嘆了一口氣,畢竟是沒說下去;再說下去,這話就有點不好聽了。權仲白拍了拍蕙娘的肩膀,放緩了語氣。「這件事以後別再提了,立雪院那裡,妳把石英換過去吧,或者就乾脆不要留人,免得日後傳出去,她也不好找婆家。我自個兒慣了,不用人服侍。」
「這不行……」蕙娘眉眼都是木的,微微一動,反射性地回絕了權仲白。「她是我手下最得用的人,留在京城,我是有用處的。」她到底還是找回了慣常的理智和做派,輕輕地吁了一口氣,又裝出笑來。「姑爺就放心吧,沒想著把她給你……你就別自作多情了!」
換在往常,這一刺必定能鬧得權仲白好生無趣,可今日,卻是蕙娘自己都能聽出其中的軟弱。
雖說小別勝新婚,可昨天晚上,蕙娘特別沒有胃口,一個晚上,她也都沒有怎麼睡好,在床上翻來覆去,睡意都一直不來,澇得眼圈都黑了。
第二天早上權仲白起來看見,都有點過意不去。
「妳的心事怎麼就這麼沈啊?」他一拿蕙娘的手腕,指尖壓在蕙娘腕間,又令她感到一陣煩躁。「說妳幾句而已……不知實情,以訛傳訛、背後臧否,本來就是妳的不對,妳還真上心了。」
說著,便給蕙娘寫了一張條子。「山上夜裡涼,妳又存了心事,被子又不好好蓋,倒鬧得夜風入體,喝一副發發汗,免得存了病根。」
他也真是說過就算,今早起來又沒事人一樣了。蕙娘訕訕然的,要和他認真賭氣,到底是有點心虛,只好發嬌嗔。「一句話說錯,你那麼認真幹麼……這叫我能不往心裡去嗎?」
說著,也是半真半假,眼圈兒都委屈得紅了,倒唬得一群丫鬟,本來都進了屋子,一下全潮水般地退了出去。
權仲白不吃她這一套,又虎起臉。「君子不欺暗室,為人處事,細節上是最要注意的,以後妳也要從心底就要求得嚴點兒,就不至於一鬆口說這樣的話了。」
要他不是君子,蕙娘也多得是話回他,可從頭回見面到現在,權仲白被她激成那個樣子了,到底都還是沒有丟失自己的君子風度。他自己說話直接大膽是一回事,那些話終究頂多算是不看場合,要說私德,還是無可挑剔的。她被噎得難受極了——權仲白又到底比她大了那麼多呢,這麼一虎臉,蕙娘真有點吃不消了,偏偏她又也有自己的風度,究竟這一回是她不謹慎,被抓住了錯處,要豎起刺來,也不那麼占理……
「我本來就不是君子!」她只好蠻不講理。「我是小人,我沒皮沒臉,行了吧?」
這麼一張如花俏臉,委屈得珠淚欲滴,權仲白看著也覺得可憐,又想到她十七、八歲年紀,就算平時表現得再強勢,究竟一個人跟他住在香山,偌大的園子,就她和她的那些下人,自己一走就是好幾天,她也沒半句抱怨,反倒是把沖粹園上上下下,已經安排得井井有條的……
「這可是妳自己說的。」他放鬆了聲調,又嚇唬焦清蕙。「不許哭,掉一滴眼淚,就給妳開一兩黃連吃!」
但凡是人,沒有不怕喝苦藥的,蕙娘一點抽噎,都被嚇回嗓子裡去了,她怕是未能想到權神醫居然出此絕招,一時呆呆地瞪著姑爺,倒是顯出了符合年紀的稚氣。權仲白看了,心情不禁大好,他刮了刮蕙娘的鼻頭,施施然站起身。「快起來吃早飯吧!」
權仲白下回進京城的時候,蕙娘讓他把白雲捎帶過去。「讓她和綠松作個伴吧。」
白雲雖然知書達禮,琴棋書畫上都有造詣,但也不是沒有缺點:她生得不大好看。
二公子很滿意,他雖然進城辦事,但還是盡量趕在當晚回來,免得蕙娘一人獨眠,的確寂寞。
一場小小風波,於是消弭於無形。
※※※
第五十章
承平六年的春夏,事情的確是多,才辦完了孫太夫人的喪事,朝野間就再起了紛爭,總之說來說去,還是兩黨相爭,楊閣老一派的新黨數次逼宮,想要把舊黨代表人物老太爺給掀翻下馬,可這一次,誰的動靜也都不敢鬧大。
孫太夫人去世,孫家全員回家守孝,除了出海在外的孫立泉之外,皇上竟沒有奪情留用任何一個子姪,這著實有些不合常理。皇后緊跟著又鬧病了,整個六月不斷用醫用藥,本來權神醫是半個月進宮請一次平安脈的,最危險的那段日子,他竟是三天進宮一次……這還是因為他身分尊貴,年紀也輕,後宮不敢隨意留人,不然,怕不是要長期居留宮中,隨時照料皇后了。
皇后病、太子病、不奪情,這三個消息,對孫家來說是比太夫人去世還沈重的打擊。
蕙娘隨權仲白回府請安的時候,權夫人談起來都有點感慨。「真是說不清的事,就前幾個月,那還是鮮花著錦的熱鬧呢,現在真是門庭冷落,一下就由紅翻黑了。」
因為蕙娘現在畢竟是在香山住,隔三差五回來請安時,大少夫人就把她當個客人待,總是要陪坐在一邊,有時候連瑞雨得了空都過來尋她說話,這天人就很齊全,一大家子人圍坐著吃西瓜,連權季青、權叔墨、權伯紅三兄弟都坐在一處說話,只得權仲白,和蕙娘一道進了城,他就直接入宮去給皇后扶脈了。
太夫人、權夫人都說:「自從昭明年間到現在,也就是今年他入宮最勤,在宮裡待得最久。」
像權家這樣身分地位的豪門巨富,就算沒有女兒在宮裡,和皇家也都是沾親帶故的,家裡人不可能不關心宮中的風雲變幻,蕙娘沒開聲,大少夫人都要問權夫人。「眼下這宮中的境況,究竟是怎麼樣?難道娘娘的情況,真有這麼糟嗎?」
權夫人未曾就答,反倒是先看了蕙娘一眼,見蕙娘神色怡然,似乎毫不知情,又似乎是胸有成竹,她不禁便在心底輕輕地嘆了口氣。
守灶女就是守灶女,太夫人只看到她反手抽大嫂那一掌,抽得的確是有些過分沈重,沒有掌家主母的氣度,可老人家就沒有想到,現在她人雖然離開良國公府,可立雪院的人在府裡辦事,照樣是處處都給臉面,這就是下馬威給得好了—此消彼長,臥雲院的人在立雪院跟前,就沒那樣有底氣啦……
再說現在,大少夫人這一問,問的哪裡是她?分明就是焦氏。娘娘情況,最清楚的還是仲白,只要焦氏露一點端倪,哪怕一句話不說,就是表情上稍微變化一點兒呢,仲白和她的關係也就一目瞭然了:是已經被小嬌妻給迷得神魂顛倒,該說不該說的全都說了呢;還是同府裡暗暗流傳的一樣,兩人的好,那都是面上做出來的,其實回了屋子,誰都不理誰……
其實宮中情勢,和焦氏娘家也有極大的關係,一旦太子被廢,寧妃所出的皇三子,是有很大機會定鼎東宮的,屆時人心向背,很多事,也就不那麼好說了……仲白的性子,她是瞭解的,不該說的一句話都不會亂說。本以為焦氏聽說局勢,怎麼都要追問幾句,沒想到她繃得這麼緊,連她這個做婆婆的,都有些拿不準了。
「這種事,我們也就是聽說一點風聲罷了,」權夫人答得多少有些哀怨。「哪敢隨意詢問?畢竟是天家密事,怎麼說,都要諱莫如深的。」
大少夫人吃了這一個軟釘子,卻並不生氣,她笑著衝蕙娘道:「前幾天中冕遣人送了一批西洋來的夏布,也是巧,去年才從西洋泊來的新鮮花色,又有一批俵物從天津過來,都不是什麼稀罕東西,唯獨鮑魚還能入眼。正好弟妹今日過來,一會兒回去就坐一車帶走,倒也便宜些。」
自從蕙娘去了香山,兩房之間倒是越來越和氣了,大少夫人待蕙娘體貼,蕙娘也待嫂子恭敬,她笑了。「次次來都不空手回去,我們著三不著兩的,也不知道帶點東西過來,都偏了嫂子了。」
太夫人和權夫人都笑。「你們才成家多久!自然是只有你們偏家裡的,難不成家裡還要偏你們?」
一家人便不談宮事,只說些家常閒話。
權夫人說起沖粹園。「太大了真也不好,我們去過一次,冷清得很!到了晚上怕得都睡不著覺,沒幾天也就回來了。」
倒是權季青有點好奇,他眨了眨眼睛,蝶翅一樣濃而密的睫毛落在臉頰上,竟能投出影子來。「聽說晚秋時節,山上紅葉是最好看的,到時候,少不得要叨擾二哥、二嫂,我也住過去領略領略。」他一推權叔墨,要拉個同伴。「三哥也與我一同去?」
權家四個兒子,就數權叔墨在長輩跟前話最少,就是遇到蕙娘,他也都沒有一句多餘的話,這個悶葫蘆,有了事也全往心裡吞,一開腔甕聲甕氣的。「我事情那麼多,哪能有空?你拉雨娘和你一同去—噢,雨娘要繡嫁妝,那你同大哥一起去。」
瑞雨面上一紅,狠狠地道:「三哥盡會說瞎話!」
一邊說,一邊投入母親懷裡,嬌聲央求。「娘,您也不罰他!」
一家人都笑了,蕙娘一邊笑一邊說:「就是繡嫁妝,也能到香山來繡嘛,風景好,手上活計就做得更快了。妳同四弟什麼時候想來了就來,反正也不怕沒地兒住。」
權瑞雨眼神一亮,可看了母親一眼,神色又黯然下來,嘆了口氣。「要學的東西太多了,沒空……」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豪門守灶女(3)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1 |
中文書 |
$ 181 |
文學作品 |
$ 207 |
穿越文 |
$ 207 |
華文羅曼史 |
$ 225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豪門守灶女(3)
一般富貴女子的陪嫁品,有幾車的金銀珠寶、古董字畫已算了得,
可她焦清蕙的陪嫁卻硬是比人強—一個分紅驚人的金雞母票號!
所以她一心要爭得世子位,讓夫婿承襲國公位,以保護她的命及票號……
文創風104《豪門守灶女》3
權仲白這個人實在是有趣得緊哪!
外表一副魏晉公子模樣,講話直來直往又任憑自己的意思而活,
焦清蕙承認,一開始自個兒的確是小瞧了他,以為他好拿捏得很,
但仔細想想,能在詭譎多變的皇宮中自由來去多年又深得君臣后妃看重,
他,又怎麼可能會是個頭腦簡單、不懂揣度人心的平凡人物呢?
權家規矩,承襲國公位的世子是立賢能不立嫡長,因此人人都有機會,
但權家老三是個武癡、老四尚未成家、老五年紀又甚為幼小,
這一度量,可不是只有老大和他們二房最有機會爭奪世子位嗎?
何況大嫂進門多年都無孕,眼下只要先一步產子,她的地位就穩得多,
然則這個不爭位的二爺能不明白她的心思嗎?就不知美人計對他管不管用了?
本書特色
新婦剛入門就得勞心勞力?幸好她也非省油的燈!
妯娌、叔嫂內鬥只是小菜一盤,夫妻不和亦是三兩下就解決的事,
令小倆口隱隱擔憂的是, 除了皇帝,暗處的敵人也正磨牙伸爪地逼近,
而這一切,似乎都肇始於她的驚天巨富……
作者簡介:
玉井香/機關算盡、局中有局之絕妙好手
新世代作夢專家,沈迷於編造故事、創造屬於自己的世界。在我的世界裡,愛情有點bittersweet,有現實的苦也有夢幻的甜,只有最強大的女戰士,才能披荊斬棘,斬惡龍收王子。
章節試閱
第四十九章
蕙娘還真沒接觸過這個桂家少奶奶—先不說夫家是外地望族,本身丈夫品級也還低,距離蕙娘所在的交際圈,還差了那麼半步,就她在京城的時間可也不長。但她是聽說過桂少奶奶的名氣的—她丈夫自從進京,擺明車馬絕不納妾,甚至連通房都不收用,幾乎因此不見容於整個社交圈,善妒的名聲就這麼傳開了。就是前幾年,因她不知如何得罪了太后,太后藉口數落她妒忌,給她姑爺桂含沁賞了一位溫柔大方、極是可人的宮女子,可桂含沁受少奶奶轄制慣了,根本就不敢收用,因少奶奶當時還不在京裡,為怕說不清楚,頭天納妾,第二天就把人給賣到...
蕙娘還真沒接觸過這個桂家少奶奶—先不說夫家是外地望族,本身丈夫品級也還低,距離蕙娘所在的交際圈,還差了那麼半步,就她在京城的時間可也不長。但她是聽說過桂少奶奶的名氣的—她丈夫自從進京,擺明車馬絕不納妾,甚至連通房都不收用,幾乎因此不見容於整個社交圈,善妒的名聲就這麼傳開了。就是前幾年,因她不知如何得罪了太后,太后藉口數落她妒忌,給她姑爺桂含沁賞了一位溫柔大方、極是可人的宮女子,可桂含沁受少奶奶轄制慣了,根本就不敢收用,因少奶奶當時還不在京裡,為怕說不清楚,頭天納妾,第二天就把人給賣到...
»看全部
目錄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玉井香
- 出版社: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7-25 ISBN/ISSN:978986328102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96頁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