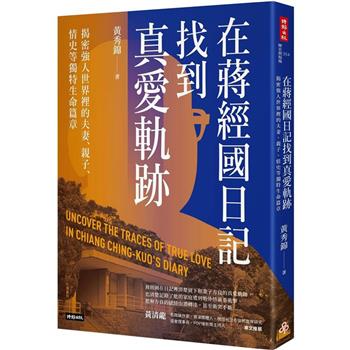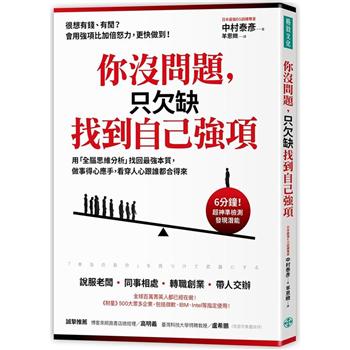她要的不多,只求一家子衣食無虞,平安度日,
可這旱災、澇災接連著來,生活怎就這麼難?
老天爺啊,拜託拜託,賞口飯吃吧~~
別人穿越不是吃香喝辣,生活起碼也過得不賴,
可她不知是否前世把老天爺給得罪慘了,
穿到張小碗這個八九歲的小女孩身上也就罷了,
偏偏這女孩家裡一窮二白,自個兒就是生生給餓死的呀!
好吧,她前世好歹是個頗為出色的服裝設計師,
有一雙能化腐朽為神奇的雙手,養活自己應不成問題,
豈料,她上有體弱父、懷孕母,下還有兩幼弟,
重點是,家裡只剩下一咪咪向別人借來的糙米可吃啦!
要靠憨直的爹娘餵飽一家六口實在太強人所難,
看來得想法子覓食了,否則她肯定得再死一回啊!
本書特色
他寵著她、護著她,會為她醋勁大發,甚至與皇帝對峙,
這男人愛上她了,她知道,但她並不愛他,他也知道。
呵,相較於他的冷酷,狠心絕情的她,其實也不是個好人啊……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娘子不給愛 1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99 |
華文羅曼史 |
$ 197 |
中文書 |
$ 197 |
文學作品 |
$ 213 |
小說/文學 |
$ 223 |
羅曼史 |
$ 225 |
古代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娘子不給愛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