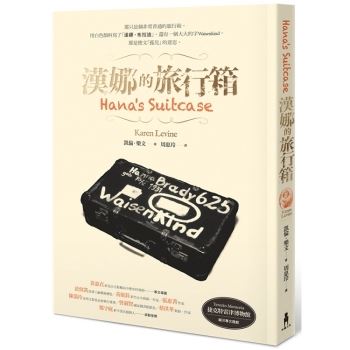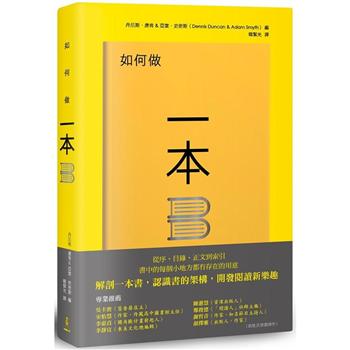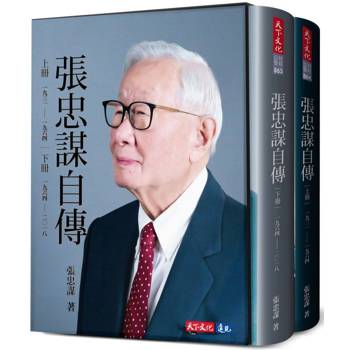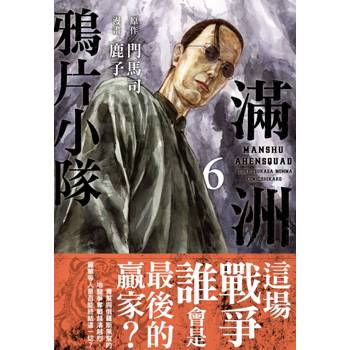第二十一章
張小碗在初四那天回了葉片子村,剛回,世子府那頭就來人接了她過去。
世子妃接見了她,房內無其他人,張小碗還未朝她行禮,世子妃便扶住了她,那威嚴的圓臉一沈,道:「我現下跟妳說件事,妳定要答應我,一定要挺住。」
張小碗不是無知之人,一聽她這口氣,頓時腳都軟了,慌忙中她扶住了桌,坐到了凳子上,喘了好一會兒的氣,才朝世子妃說:「您說。」
世子妃在她身邊坐下,拉了她的手,讓她再緩了兩口氣,才以一種更沈穩的口氣說道:「前方已有人來報,妳兒已在回來途中,但在前日他受了追殺,身受了一劍,因劍上有毒,他此時尚在昏迷中。」
張小碗連氣都喘不出來了,她用牙咬了舌根,疼得很了,才把話從喉嚨裡擠了出來。「我兒何時回來?」
「今日午夜子時。大夫說,昏迷中,他口口聲聲喚的都是娘,到時,就讓妳灌他的藥。」
「可是無礙?吃了藥就無礙了嗎?」
「世子已準備好了猛藥。」
世子妃這話一罷,張小碗的眼淚就從眼眶裡大滴大滴地掉了下來,她怔忡地重複著那兩字。「猛藥?」
「世子找了最好的大夫,得了那最好的藥,猛歸猛,但能救他一命。」
「什麼猛藥?」
世子妃搖了搖頭,拿出帕子拭上她臉上已經氾濫成災的眼淚。「我不知,世子只讓我告知妳,妳家小公子給他立了大功,他定會救他過來。妳無須信我,信世子吧。」
「我信。」張小碗從喉嚨裡擠出了這幾個字,待丫鬟領著她去房中安置時,世子妃見她像是眼睛看不見東西一般,沒有看見門前那道門檻,就這麼被絆倒,狠狠栽在了地上。
丫鬟們都驚呼出了聲,世子妃卻見她若無其事地站了起來,還回過頭朝著她福了福腰,告罪般地笑了一下。
這時,她的鼻血已滴在了她那衣裳上,她卻渾然不覺似的。
「好好領汪夫人下去,扶著她的手。」世子妃輕搖了搖頭,等她走後,感慨地說了一句。「可憐天下慈母心。」
張小碗走後,世子妃匆匆去拜見了世子,說道她已把汪懷善的母親請來。
世子聽得她說了那婦人的表現後,便嘆道:「他所說竟然全都不假,說要幫我把金庫帶回來,他就帶了回來;說是他娘沒了他會活不下去,聽妳所說,那婦人確也是如此。這世上,竟還真有這般一句假話也不予我說的人。」
世子妃聽後也嘆道:「您都不知,饒我這般鐵石心腸的,見著張氏那悽愴的臉,我這心都酸了起來。」
這夜深夜午時,世子府後門悄無聲息地大開,一輛馬車緩緩駛入,馬車一進,那門便又被悄無聲息地快速關上,那快開快關的速度,快得就似那門從未打開過一般。
後院這時燈火通明,來往之人手腳都極快,待一位高大的武夫把一個小孩從馬車上小心地用兩手抱下後,跟隨在他身邊的兩隊侍從便緊跟著他,亦步亦趨地朝那內院快速穩步走去。
張小碗在明亮的門口看到此景,只一刻,她的眼睛就盯到了那人手上的人兒身上去了,從他的頭到他的腳,再從他的腳到他的頭,等人再近一點,她看到了他那紅得異常的臉……
她沒有出聲,更是沒有撲過去喊他,她只是跟著人進了屋,看著那人把她的孩子放在了床鋪上。
「我說好的藥。」那屋子裡這時進入一白鬚老人,對著屋內便道。
「這裡!」屋外,已然有人把剛熬好的熱湯倒入到碗中,快步走來,放置在他面前。
白鬚老人用手探了探,放到舌邊一嚐,便道:「灌。」
張小碗未出聲,她先未接碗,只低頭在她的小老虎耳邊輕輕地說:「娘替你先嚐了一點點,藥苦又割喉,但你得喝下去,你可知?你要喝下去,才活得過來見娘。」
說完,她直起了身,把眼淚眨回了眼內,伸手端過碗,另一手掐住了他的下巴,在兩人壓住他的腿和肩膀後,她咬著牙,把藥灌了進去。
奇異地,那躺著之人竟似有了意識,慢慢地一口一口把藥吞嚥了下去,那白鬚之人見狀,喃喃了一聲。「奇了怪了……」
「何奇?何怪?」靖世子這時也已站在了門口。
「這是狼虎之藥,藥過喉嚨時有刀割之感,豈會這般平靜?」
「那你是小看我這小將了。」靖世子說到這兒,嘴上勾起了一抹殘忍的笑。「他可是踏著百人之軀趕著回來的,以後定會是我劉靖的虎將,豈會連這點疼都忍不得?」
一碗藥竟安穩地餵了進去,那老者過來探了脈後,對世子道:「辰時要是醒來,就無事了。」
「如此便好。」靖世子朝他輕輕一頷首,便對那婦人道:「張氏,妳候在這兒。」
說罷領人而走,留下了一干人等伺候。
這日天亮了一會兒,差不多快到辰時,張小碗見得了床上的人眼睛眨了眨,她屏住了呼吸,過了好一會兒,才見人完全睜開了眼睛。
汪懷善一睜開眼睛,看到他娘,那小小年紀的人竟笑嘆道:「我就知,一睜開眼,就能看到妳。那夢裡,妳說我要是好好回來,妳定會好好給我烙幾張餅,揹著我去那山間打獵,帶著狗子,去尋那群猴兒。」
「嗯。」張小碗朝他笑笑。
「妳別哭。」汪懷善伸出手,拭著她眼邊那蜿蜒而下的淚,卻是越拭越多。
張小碗點頭。「娘不哭,你不說話了,嗯?」她伸出手,摀住了他的嘴,深吸了兩口氣,才不疾不徐地說:「大夫說了,喉嚨要半個月才養得好,這半個月你就別開口了,可好?」
汪懷善看著她那張滿是淚的臉,輕輕地點了點頭。
他很是疲倦,便把張小碗的手拿起貼在臉邊,似乎這樣,他就又可以撐下去了。
在世子府休養了近十日,見過世子後,張小碗揹著汪懷善準備回村裡,同時回去的還有世子派的人,說也是懷善的手下──兵小柒、兵小捌、兵小玖。
三人身材高大,相貌醜陋。
汪懷善背地裡跟張小碗說過黑狼營裡的人,說那營裡的人好多都是身世坎坷之人,加之那與常人不同的外表,除黑狼營外的士兵不喜之餘,尋常人見著他們了也常會被他們嚇一跳。
但他跟他們很合得來,他們也頗為照顧他。
張小碗也沒少烙餅讓他帶去予他們吃,讓他們交流感情。
現下見到他們,她便也是溫和地朝他們笑笑。她未語,但平靜溫和的神情表明了她對他們的接納。
跟隨過去,這時身上無偽裝的三人一見到她此等神情,都抱拳朝她鞠了一躬,喊道了一聲「夫人」。
見到此景,汪懷善在他娘背上無聲地笑著,手還嬉鬧地扯了扯離得他最近的兵小柒的頭髮。
兵小柒被他扯了一下,小嚇了一跳,見他在作怪,便苦笑道:「小公子別胡鬧,好好讓你娘揹著。」
汪懷善又咧開嘴巴笑,也不以為然,轉過身,在他娘背上寫字,告知她,回去他們要做得什麼。
張小碗微微笑著,離開世子那處後,帶了這三人去了世子妃那兒,跟她告別。
世子妃見了他們母子,也未讓他們行禮,她先是摸了摸汪懷善的臉,誇獎道:「真是個小英雄。」
汪懷善得意一笑,從他娘懷裡掏出一條帕子,塞給了世子妃。
「是這幾日繡的,懷善說勞您這些日子照顧我了,特讓我繡了塊帕子給您,我也就只會這個了,望您不要嫌棄。」張小碗頗有些羞赧地笑了笑。「待他能好好說話了,我就讓他過來磕頭給您道謝。」
世子妃聽得忍俊不禁,拿帕子掩了嘴笑了幾聲,才說道:「我道汪家的這小公子這麼小便會做人是從哪兒學來的,如今看來,確是從妳肚子裡出來的!才這般小小年紀,竟如此通人情世故,這上上下下的,可沒幾個人不喜他的。」
張小碗聽得便笑了一下,她身後還讓她揹著的汪懷善此時從她背上下來,問過世子妃,便拿了桌上的筆墨寫道──
待我好了,我就回來服侍世子爺與您,還給您捎件我娘做的新衣裳!
世子妃看罷,又笑了好幾聲,這才叫著婆子、丫鬟,把給他們的什物都收拾好,搬到馬車上去。
汪懷善看得了如此多的好東西,又跟世子妃打了好幾個一揖到地的禮,逗得世子妃摸著臉,笑嘆著說:「這嘴又給你逗得笑疼了。」
說罷,看著在一旁微微笑著看他的張小碗,她頓了一下,便走到她面前,輕聲地與她說道:「以後有為難之處,便著人去後院跟門房報一聲即可。」
張小碗感激地朝她福了福身。「勞您記掛了。」
世子妃聽罷微微一笑,笑道:「妳養了個好兒子。」
汪懷善聽到此話,朝著世子妃又作了個揖,這才拉著張小碗的手,讓他娘揹了他,娘倆跟世子妃就此告了別,踏門而出。
他們走後,沒得多時,世子爺過來找世子妃一道去忠王府用膳,待到了馬車上,世子妃小聲地跟靖世子說:「我看那張氏也不是個一般的婦人。」
「怎講?」
「我看她那手心,硬是被生掰出了一塊肉,可我看她那臉,竟像無事之人一般,一點苦楚也無。」
「嗯。」靖世子沈吟了一下,便說道:「我聽懷善說過,當初有人著人去他們家鬧時,是他娘挺著一口氣,才用了火棍子趕了出去。」
世子妃聽後思忖半晌,小聲地嘆道:「這婦人不易啊!」
「別道別人不易了……」靖世子伸手摟過她的腰,讓她的頭枕在他的肩上,淡道:「妳也不易。先歇一會兒,等會兒就得妳不易了。」
世子妃聽得笑出聲,她靠著他,雙手抓過他的手,用雙手把那粗大男人的手包合在她的掌心,緩緩地閉上了眼睛。
是啊,不易啊,可憐這世上的女子,不是為子,就是為夫,得不了片刻真正的安寧。
馬車一停下,孟先生已扶著大門站在那兒候著,汪懷善一下馬車,就一把跪在了他的面前,「砰砰砰」地磕了三個響頭。
孟先生扶了他起來,看著他那帶笑的臉,聽得他用還有一點沙啞的喉嚨喊了句「先生」。
「歸家了啊……」半會,孟先生只說了這句話。
「是啊,歸家了呢。懷善,扶了先生進屋吧。」張小碗在身後溫和地說著,同時讓家中的老僕去幫著兵小柒他們把馬牽到後院。
等一切歸置好後,張小碗又帶了兩個老僕去做飯。
那柳綠、柳紅這兩個丫鬟她未帶回,汪永昭也沒強迫給她塞人,張小碗也就做好了靜候著他下一步動作的準備。
這男人的好壞,都是有目的的,她只要等著他的動作即好,無須猜太多,因為該來的總會來,躲是躲不了的。
忙完一家的吃食,在夜間,張小碗終是得了空,招呼著還在練劍的汪懷善洗澡、就寢。
這近十天不能說話,也不能下床,確實憋壞了汪懷善,回家練了一通劍,這才把心中的憋悶發散掉了,待洗完澡,他娘給他擦頭髮時,他已有些昏昏欲睡。
等張小碗幫他擦乾,他就睡著了。
張小碗不禁有些失笑,正要把坐在她面前的小兒放在炕上躺平,卻發現她那小兒的手緊緊地抓著她衣角的一端。
她扯了兩下,竟扯不出來,而那在夢中的小兒這時又把頭往她的肩上挪,喉嚨裡輕聲地喚了一聲「娘」。
張小碗抬起了頭,把眼眶中的眼淚忍了回去,但就算是忍回了,她還是心如刀割般疼痛……
隔日,汪家來了人,是汪永重送了些滋補的藥材過來。
「聽得懷善受了些傷,爹與大哥著我先送些藥材過來。」待見過禮,在堂屋坐下,汪永重才說道:「大哥這幾日在兵營練兵未歸家,他讓我送信過來,等這幾日忙完後,他就過來看望你們。」
「勞老爺、大公子費心了。」張小碗頗為感激地道。
汪永重看了看他大嫂那感激的臉,頓了一下,只得硬著頭皮又說:「父親說了,要是村中不便,您可攜懷善回家養傷。」
「就不必如此麻煩了,」張小碗淡笑了一下,依舊和和氣氣地說:「世子爺派了好些人來照顧懷善,眼看這幾日也就好了,就不必回去了。」
「爹說,在家有祖父、父親的看管,這病情許是會……」汪永重猶豫地頓住了。
張小碗笑意盈盈地看著他,不疾不徐地說道:「說來,這也是無須的,是懷善定要回村裡的這處宅子,世子爺才准了他著家養病;要不,按世子爺的意思,他這傷還是在世子府養的好。」
汪永重聞言皺眉。他知他這大嫂根本無回汪家的意願,現話中又搭上了世子,他這話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說下去了,便出聲告辭。
張小碗送了他出了堂屋的門,又叫來兵小捌,讓他送汪永重到村口。
兵小捌一見到這汪家的人,那眼一瞪,手一揚。「請!」
聽著他那咬牙切齒從嘴裡擠出的「請」字,汪永重笑了一下,待到了村口,兵小捌不在身後,他跑馬了一陣,就又改了道,往他大哥的銀虎營方向跑去。
汪永昭得了他的報信,也說了院中現下住的人員後,輕笑了數聲,就又拿了槍桿繼續操練士兵。
汪永重說罷消息後,就又回了家,與他父親稟報實情去了。
現眼下,他那小姪,儼然確也得了世子的重視,加入了黑狼營,打算與他們銀虎營一別苗頭去了。
汪永重這時也才明瞭他大哥過年時,為何要與大嫂一道點鞭炮了。
她是汪家婦,而他那小姪也是汪家人,他竟加入黑狼營,與他父親的銀虎營互別苗頭,這說來,就不是他們家的不是了。
這廂汪永昭操練完士兵,當夜與手下眾將議過事後,換了兵袍,未帶一個隨從,騎馬便往那葉片子村跑去。
到時已是子時,他拍了門,有老僕過來開門。
「夫人呢?」汪永昭牽馬而入,吹亮火摺子四處看了看,待看到那小兒練武的樹樁處,他牽馬過去,把他的馬拴在了那處。
「是汪大人?」那守夜的老僕老眼昏花,看過幾眼才看清行動不是一般乾脆俐落的人是誰,這才忙回道:「這般時辰了,夫人已就寢了。」
「嗯。」汪永昭說話時,已往那後院走去。
老僕看他熟門熟路的,心驚不已,忙關上了大門後就跟在了他身後,可他腳力委實是跟不上那總兵大人,就算提著燈一路小跑著過去,他也沒跟到人,等他跑到了那後院,還未進門,就聽得門內那小公子還稍帶點沙啞的大吼,在夜晚石破天驚地響起──
「哪來的毛賊,竟敢闖你爺爺家的大門!」
聽到喊聲,汪永昭未出聲,朝那堂屋快步走去,途中躲過小兒那支帶著殺氣的箭,推門而入,甩出火摺子點燃了油燈。
黑暗陡地光亮了些許起來,那小兒一見他,訝異出聲。「原來是父親大人?!」說罷收攏了手中的弓,彎腰低頭。「孩兒拜見父親大人!不知您大駕而來,望您恕罪。」
汪永昭掃了他一眼,端坐在了椅子上。
自這小兒進世子府大半年的所作所為,他要是還不知這小兒對他是陽奉陰違,那他便真是個傻的。
那老僕也提著燈籠趕來,見到此景,便對那連鞋都未著的汪懷善說:「小公子,總兵大人來了,您快快穿好衣裳出來拜見。」
汪懷善聽了一笑,眼睛看向那一言不發的汪永昭。
汪永昭未語,靜待半會,就聽得門外傳來了腳步聲。
隨之,那穿戴整齊的婦人走了進來,朝著他施了一禮。
「大公子。」
「免。」汪永昭這才抬眼去看汪懷善,淡淡地說:「穿好出來。」
汪懷善應了聲「是」,但沒離去,只是抬臉看了看那門外的天色。
汪永昭見狀,勾了勾嘴角。居然還想怪他深夜闖入?真是膽大包天的小兒。
「去吧,穿好了再過來給父親大人請安。」婦人此時開了口,語氣溫婉得很。
那小兒便就此退下,而那老奴看過她之後,也提了燈籠下去了。
「妳知我為何而來?」
「請大公子明示。」
看著張氏嘴邊那抹淡漠,汪永昭冷靜地說:「他去了何處?受的何傷?我是他父親,這些總該知道。世子不告知我,妳作為他的母親,是否要給我一個交代?」
「婦人確實不知。」
「不知?」汪永昭冷哼了一聲。「當真不知?張氏,他加入別營,不入我營,我未多語,但並不見得別人不會有什麼看法。妳當真以為他入了世子的眼,就能高枕無憂了?妳當外面人的眼睛都是瞎的?!」汪永昭大拍了下桌子,桌子抖動了好幾下。
張小碗聽得話後,冷靜地想了一會兒,才直視汪永昭道:「婦人愚鈍,請大公子把話說得更明白一些。」
「他就算與我不和,也至少把表面功夫給做全了!」汪永昭忍了忍,站起身往那門邊站了一會兒,待確定那老奴站在了門外,旁邊皆無人之後,他才回頭看著張小碗,目光冰冷,聲音卻輕得不能再輕地說道:「回頭待陛下問我,我這兒子幹甚去了,忠王爺問我,我這兒子幹甚去了,我一個字都答不上!張氏,妳這是置妳、置我、置汪家於何地?世子這事瞞了皇上,連他父王都瞞了,妳道這是什麼好事?
*預知精采後續,敬請期待8/12上市的【文創風】210《娘子不給愛》3。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娘子不給愛(3)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65 |
華文羅曼史 |
$ 197 |
中文書 |
$ 197 |
文學作品 |
$ 213 |
小說/文學 |
$ 223 |
古代小說 |
$ 225 |
古代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娘子不給愛(3)
她看著性子綿軟,實則剛毅堅強,心比誰都狠,
事情一旦牽涉到兒子,便是要殺人,她眼也不會眨一下,
想來,這就是所謂的為母則強吧……
文創風210《娘子不給愛》3 溫柔刀◎著
她懷孕生子了!一次就中,該說她張小碗倒楣到家嗎?
老天爺對她真是太壞了,這苦難的日子就沒一刻消停,
什麼母以子貴這種鬼話,她是完全沒在信的,
雖說她這當娘的出身不高,她的兒子八成也不得人疼,
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她產子一事還是能瞞就瞞吧,
不料,這事最終還是透了風,教她公公給知道了,
迫於無奈,她只得帶著兒子,千里迢迢回汪家認祖去,
她沒啥奢望,只求平安度日便好,但卻事與願違,
進了汪宅後,風不平浪不靜的,兒子還發狂險些殺了她!
唉唉,怎麼這世上就沒一件事能讓她省心的啊?
本 書 特 色
他寵著她、護著她,會為她醋勁大發,甚至與皇帝對峙,
這男人愛上她了,她知道,但她並不愛他,他也知道。
呵,相較於他的冷酷,狠心絕情的她,其實也不是個好人啊……
作者簡介:
溫柔刀,晉江文學城簽約作者。本人是個性格多變的人,愛好也很簡單,喜歡看書,一個人歷險,喜歡創作,不寫自己喜歡的故事就會死星人……
章節試閱
第二十一章
張小碗在初四那天回了葉片子村,剛回,世子府那頭就來人接了她過去。
世子妃接見了她,房內無其他人,張小碗還未朝她行禮,世子妃便扶住了她,那威嚴的圓臉一沈,道:「我現下跟妳說件事,妳定要答應我,一定要挺住。」
張小碗不是無知之人,一聽她這口氣,頓時腳都軟了,慌忙中她扶住了桌,坐到了凳子上,喘了好一會兒的氣,才朝世子妃說:「您說。」
世子妃在她身邊坐下,拉了她的手,讓她再緩了兩口氣,才以一種更沈穩的口氣說道:「前方已有人來報,妳兒已在回來途中,但在前日他受了追殺,身受了一劍,...
張小碗在初四那天回了葉片子村,剛回,世子府那頭就來人接了她過去。
世子妃接見了她,房內無其他人,張小碗還未朝她行禮,世子妃便扶住了她,那威嚴的圓臉一沈,道:「我現下跟妳說件事,妳定要答應我,一定要挺住。」
張小碗不是無知之人,一聽她這口氣,頓時腳都軟了,慌忙中她扶住了桌,坐到了凳子上,喘了好一會兒的氣,才朝世子妃說:「您說。」
世子妃在她身邊坐下,拉了她的手,讓她再緩了兩口氣,才以一種更沈穩的口氣說道:「前方已有人來報,妳兒已在回來途中,但在前日他受了追殺,身受了一劍,...
»看全部
目錄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商品資料
- 作者: 溫柔刀
- 出版社: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8-15 ISBN/ISSN:978986328337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6頁 開數:正25開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