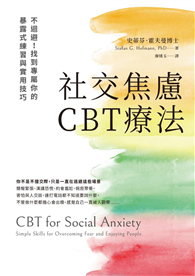第三十一章
兩日後,汪觀琪醒了過來。
父子倆談話時,張小碗就站在那外屋,她清楚地聽得裡屋的汪觀琪口口聲聲說要親手把那惡毒的婦人碎屍萬段。
他那充滿著惡毒意味的口氣讓外面的張小碗聽得不寒而慄,饒是她強自鎮定,身上的寒毛也因他那滿是惡氣的聲音而倒豎,沒得多時,背後已一片冷汗。
張小碗未聽得汪永昭的聲音,一會兒後,在汪觀琪發狂的聲音中,張小碗聽得一道凌厲的巴掌聲響起,還有那劍被抽出鞘的聲響;又過了一會兒,汪永昭走了出來,他那額頭還纏著布條的臉上有著一個清晰五指的巴掌印,脖子間還有一道血痕。
張小碗朝他福了福腰,沈默地走過去,拿著帕子拭了拭,從懷裡掏出準備好的傷藥,打開壺蓋,用小指沾了點藥塗抹了一道,止住了那血,又給他的臉上抹了些藥,才輕聲地說:「咱們回吧。」
「嗯。」汪永昭淡淡地應了一聲,便帶著她出了門。
半夜,見得他還是未睡,張小碗便起了床,點亮了油燈,讓他躺在她的腿上,她輕撫著他的頭髮。
饒是如此,汪永昭也還是一夜無眠,睜著眼睛看著床頂,一言不發。
汪府的事未完,他們也回去不得,而在汪府的四日裡,汪永昭竟連半炷香的時辰都未睡過。
張小碗在第二天的日間讓江小山暫時替他們看著汪府裡的事,然後硬拉了汪永昭上了馬車,回了尚書府。
一到府中,把人安置在房裡,她就去找了在書房的懷慕。
抱得他回的路上,她細細地跟他說了些事,懷慕聽了懂事地直點頭,最後與張小碗拉了勾,答應定會陪爹爹好好地睡。
一回到房,見得汪永昭,汪懷慕便朝汪永昭直伸手,大聲著急地叫著。「爹爹,懷慕在這兒呢!爹爹快來抱我!」
躺在床上的汪永昭聽得這聲音,嘴角竟有了一點淡淡的笑,他撐著床面起身,緩了一下,便下床大步前來,從張小碗手裡把汪懷慕抱到了懷中,用沙啞得不成形的嗓子笑著問他。「這幾日在家中可有好好聽先生的話?」
「有!」懷慕大聲地道:「習得了好幾個字,也寫了好幾張紙!」說到這兒,他哽咽了起來,把手輕輕地放到他爹爹的額頭上,生怕他疼似的,哭著道:「爹爹怕是好疼的吧?不疼、不疼,懷慕親親便不疼了!」
說著他就小心翼翼地往汪永昭的頭上碰去,輕輕地親了好幾口,又呼了好幾次氣,卻把眼淚、鼻涕蹭了汪永昭一臉。
汪永昭卻是笑了起來,抱著他在床上玩耍,跟他問著他這幾日在家中習得了哪幾個字、吃得了多少飯菜等事,不多時,他便抱著懷慕垂下了頭,就此睡了過去。
看得他睡了過去,一直在跟父親童言童語的懷慕便噤了聲,朝得一旁坐著的張小碗看了過去。
張小碗朝他笑了笑,走了過去,彎下腰在他臉邊輕聲地道:「懷慕乖。」
「嗯,懷慕乖。」懷慕說罷此言,小小的孩子不自覺地輕嘆了口氣,把頭依在了汪永昭的肩上,閉上眼睛。
他要陪疼愛他的父親好好地睡覺。
夕間,汪永昭醒了過來,懷慕正趴在他的懷裡玩著翻繩,那婦人就坐在旁邊,看到他,便是一笑。
「申時了,您用點食,便過去吧。」婦人目光柔和地道。
汪永昭便頷了下首。
懷慕這時過來看著他,輕輕地用小臉蹭了下他的臉,軟軟地叫道:「爹爹……」
汪永昭翹起了嘴角,摸了下他的頭髮。
這時婆子過來抱他,汪永昭看著懷慕跟他與那婦人揮了下手,看著懷慕出了門,這才收回了眼神,下地讓那婦人給他著衣。
當她給他穿好衣,拿過她端來的參粥喝得一口後,突道:「妳留在家中吧。」
那婦人笑了笑,未語。
只是當他提步出了門,就看得她跟在了身後。他略微苦笑了一下,等了她幾步,讓她跟上他。
罷了,那府裡,哪裡少得了她?有她在,他才放心,她不去,還不知要多增多少事端。
他們一回,候在大門邊等他們的江小山硬是鬆了一大口氣,待他們進了屋,便上前跟他們稟報了這一天間的事情。
後院還是出了亂子,有三個朝廷敵對黨派安插進來的奸細被揪了出來,他們不在,汪家的三位老爺和夫人也不敢在這時自作主張,要等到他們回來才能成事。日間為此事,他們已催過江小山兩回,此事關係重大,江小山硬是頂住了壓力,這才候著了他們回來。
隨即,汪永昭就去了前院。
張小碗便去了後院,與汪余氏見了個面,處置起了府中的事。
這時的汪府已不是以前住在葉片子村時只有幾個丫鬟、婆子、護院的汪府了,光是丫鬟,整府就有一百三十餘人,婆子四十位,這大大小小的正主子二十七位,那姨娘稱得上號的,就有三十來位。
人數和身後背景昨日就全部著人摸清了,只是今日耽擱了一天,沒在上午處置。這時張小碗也不多浪費時間,叫了各房的夫人過來。
汪杜氏、汪申氏、汪余氏行過禮都落坐後,張小碗便淡然地道:「這時我也不跟妳們拐著彎說話了,大老爺先前也發話了,讓妳們把後院的人都收拾個清爽樣子出來,妳們現在跟我說說,妳們是怎麼辦的?」
幾個婦人都未語,靜得了一會兒後,汪杜氏先開了口,不輕不重地淡然道:「我家二老爺說,他那幾個姨娘規矩得很,待回頭再叮囑她們一番便行了。」
張小碗聽得冷冷地看向她,汪杜氏被她看得垂下了眼,不想對視。
「說吧,哪幾個是不對的?說出來,看跟我這冊子上的對不對得上號。」
「對得上號又如何?對不上號又如何?」汪杜氏垂著頭輕聲地道。
「對得上,那就不是妳我說如何便得了的事了。」張小碗輕描淡寫地道:「這事,大老爺自會叫人處置。」
「是大老爺作主?」汪杜氏看得她一眼,不禁咬了咬嘴,輕輕地問。
「是。」
「那我便……說了。」汪杜氏又咬了咬嘴唇,半抬起頭,輕聲地說了幾個名字。
而她所說的,跟張小碗手裡冊子上的名字都對上了,只是張小碗這冊子裡寫的只有兩個,汪杜氏卻說了四個。
「全寫上。」張小碗便朝汪余氏輕頷了下首。
汪杜氏這裡對過後,便是三夫人汪申氏。汪申氏先前聽得汪杜氏口裡說的那幾位,輪到她,她猶豫了一下,比汪杜氏還多說了一位,她這裡的人數有五位。
汪余氏這裡記上了人數後,這兩人便帶著丫鬟走了,走到門邊時,這兩位婦人相互看了一眼,又看了在主位上看著手中冊子、根本未看向她們的張小碗一眼,朝得張小碗福了福身,拿著帕子掩了嘴,這才走開。
門被人掩上,等到屋內全然安靜了,汪余氏才開了口,她淡淡地與張小碗說道:「這舊的就算去了,總還會有新的。」
張小碗聽得漫不經心地輕應了一聲,一會兒,待她把名字全用自己的筆跡謄寫了一遍,才抬頭對汪余氏淡淡地道:「大老爺說了,汪家的庶子、庶女已經有得八子四女了,嫡子、嫡女那也是有得十來位,咱們家算得上是那子息長的人家了,以後這些姨娘們要是能再給汪家開枝散葉,便是好事,要是不能,也無大礙,主要的還是妳們要多添嫡子,那才叫好。」
汪余氏聽得「喔」了一聲,抬頭認真地看向張小碗。
「這些年間,永安、永莊和永重,姨娘們也娶得了不少,光永重房裡的就有那八位,這要是再娶下去,怕是得給她們再置宅子才夠吧?」張小碗說到這兒,像是說玩笑話般地說:「這是大老爺先前跟我說的話,聽來是不會再給妳們宅子住姨娘了,妳們便死了這條心吧!」
汪余氏聽得這話,眼睛都瞪大了起來,手裡的帕子一時沒注意,竟掉在了地上。
這時,她一回過神,帕子也未去撿,拿了毛筆,又重添了兩人到了紙上。
寫罷,跪到地上,雙手把紙張恭敬地送到了張小碗的面前。
張小碗接過紙,隨口說了句。「起來吧。」
說罷,她重拿起毛筆,把那兩人的名字又謄寫在她的冊子上。
「她們都會去往何處?」在她一筆一劃寫字間,汪余氏輕聲地問。
「咱們家,在鍾暮縣的光華山上要修一座寺廟,那裡就是她們的去處。」張小碗淡淡地道。
「大嫂慈悲心腸。」汪余氏說得了這麼一句。
「呵……」張小碗聽罷笑了一下,搖了一下頭,不再接話。
她哪有什麼慈悲心腸?這不過也是汪永昭的決定罷了。
那寺廟,不僅是要把這些私通外敵、把奸細帶進門的有嫌疑的姨娘們關過去,連汪韓氏,也是要住進去的。
只可惜,婧姨娘她們早了那麼幾天被送走了,要是晚點,便不會去那地了。
去汪家的寺廟,再如何,總比去那寡婦盤踞、必少不了爭衣奪食的棲村要好些。
她又哪是什麼好人?要真是好人,不會為了讓汪府安寧點,以後她事少些,就默許著她們三個把看不順眼的姨娘給寫了進去。
汪府的整頓花了近半月的時間,怕是汪家那幾兄弟,各自都跟自己房裡的正妻透露了不會再納新妾的口風,後院的那幾位正頭夫人一高興,這汪府竟一掃之前的沈鬱,多了幾許輕鬆的氣息。
就算汪觀琪成日陰陽怪氣,她們少不了在去問安之時被他喝斥、找碴,但她們眉目之間還是多了幾許輕快。
這日張小碗要回去之前,一家人吃了頓飯,在女桌這邊,汪杜氏還下跪給她敬了杯酒,接下來那兩位亦然。張小碗未語,接過酒杯就一口喝下。
一桌的四位夫人,誰也沒就此說過隻字片語,這時她們交談都寥寥,但她們共同坐在一桌的氣氛,竟是從來沒有過的平和,甚至稱得上祥和。
張小碗回府後,汪永昭便又回了兵部辦差,日日不著家,也不知是出了什麼事,接下來有得數日,他竟是夜間都不回了。
因著自家媳婦有了身子,江小山被特准留在了府中辦差,這日他去了外頭送信回來,拉了聞管家到了一邊,小聲地跟他說:「你說咱們爺不會不准他兄弟納新妾,他自個兒倒要添新美人了吧?」
「你這是從何聽來的?」聞管家刮了他一眼。
「外邊聽來的唄,就是上午給秦大人送信時聽來的。」江小山撓撓頭,困惑地道:「想來也不應該啊,他現下跟夫人好得跟一個人似的,怎可能要新美人?」
聞管家聽罷,抽了下他的腦袋,罵道:「少聽外人胡說八道!」說罷,又意味深長地看了他一眼,道:「主子們的事,你少亂說。」
江小山不服氣地橫了他一眼。「我這是為了咱們府的家宅安寧,你懂什麼?」說著就搖頭走了。
聞管家看得他走遠,這才長嘆了口氣,雙手合掌,朝得天空拜了拜,唸叨了一句。「老天保佑。」
這邊江小山為著張小碗擔憂不已,每每看見張小碗就不由自主地嘆口氣,張小碗看得幾次,有些好笑,但也不問。
看得她不問,江小山更想嘆氣了,想提幾句讓她注意點的話都無從出口,只得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過得幾日,這日白日間汪永昭便回來了,一回來身上就是老大的脂粉氣,江小山跟著他進後院,急得滿頭都是包,想跟汪永昭提醒幾句,但他話往往還沒尋思好怎麼開口,那急步往後院走的大老爺就又把他甩下了一大截路,他只得急忙跑過去接上,這話是怎麼樣都沒法想好,再好好出口了。
不得多時,他們就到了後院,看到大夫人那笑意盈盈迎過來的樣子,江小山差點都要急哭了。
可當夫人靠近,笑臉還是那張笑臉,臉上一點波動的情緒也無,只一刻,江小山那滿腔的熱血便冷了下來。
等到夫人把大老爺迎進了屋,江小山才重重地抽了下自己的臉,罵自己道:「抽你這個不長記性的!都忘了夫人才懶得理會大老爺有多少美人呢!」
說罷,他那心又偏到了大老爺身上去了。他伸手擦了擦眼角,自言自語道:「大老爺也是個可憐的,待到善王一回來,夫人做的那第一套新裳,必是善王的,不是他的。」
「可是要先沐浴?」進了屋,張小碗解了他身上的披風,嘴邊有著淺淺笑意。
「嗯。」
說罷,張小碗手上的披風在他身前閃過,那道媚俗的暗香也隨之飄過,汪永昭忍不住皺了下眉。「拿出去。」
「咦?」張小碗回頭,稍有些不解。
「衣裳都拿出去。」汪永昭解了身上的外袍,扔到了地上,隨即解開了裡衣,拿到鼻間聞了聞,沒聞到異味,這才扔到了屏風上。
「是。」張小碗應了一聲。
汪永昭看了她一眼,垂眼看著她的手把他的外袍撿了起來,這才淡淡地道:「邊疆有幾個武將回京,都是兄弟,這幾日陪得他們在外邊喝了幾天酒。」
張小碗微笑點頭,見狀,汪永昭冷冷地翹了翹嘴角,就提步往內屋走去。
熱水很快提來,洗到一半,汪永昭拉了她進了浴桶。
事畢,他摸著她的肚子,微微有些不快。「要何時才能有?」
張小碗還在輕喘著氣,聽到這話,抬手摸了摸他的臉,淡淡地道:「有時自然就有。」
汪永昭聽得冷哼了一聲。「再找個大夫過來瞧瞧。」
皇帝的御醫都被他弄來過了,還找什麼別的大夫?沒有就是沒有,這事哪能勉強得了。
不過,這種實話,張小碗是不可能說給他聽的,她聽過後也只當他是說說,回他個微笑就是。
汪永昭說是陪兄弟喝酒的話不假,隔天,那幾個武將帶著家眷就過來拜見張小碗了,其間有兩個是沒帶人來的,他們倒不是沒有家眷,只是不是正妻,汪永昭嫌丟人,不許他們帶來。
有正妻的在張小碗面前露了個臉,得了她不少回禮,他們回去時還沒出汪府的門,得了禮的就去嘲諷沒得禮的,這一言不合,就在汪府裡大打了起來。
汪永昭提了軍棍過去,一人打了十大板子,才把這五人給打踏實了。
男人打架,婦人是被嚇得不輕的,不過這幾個武將裡頭,有個都指揮史的夫人膽兒特別大,拉了其他兩位夫人一起看架,還在旁兒拍著手板格格笑著,天真爛漫得很。
前來看熱鬧的張小碗見著心喜,又把這幾個夫人招到手邊,又一人賞了兩個金鐲子,還封了包打頭飾的銀子,美得這幾個婦人的夫君,哪怕在一旁被棍子打得齜牙咧嘴,也喜得眼睛冒光。
這幾個窮武將,邊疆一向沒得多少油水可撈,夏朝那些吃的、穿的都被大軍帶回來,更別說銀子了,這些都給摳門得緊的靖皇關到國庫裡頭了,他們回來述職都是汪永昭給的盤纏,這時又得了銀子回去,自然是心喜的。
沒得張小碗打發的,私下就來跟汪永昭哭窮,汪永昭一人踢了一腳,卻還是各自給了他們五百兩的私銀。
他們一走,汪永昭就找來張小碗算帳,這一算,算出了近萬兩的支出。
這幾個都指揮史自個兒得了,汪永昭還得給他們另外一些,讓他們發給手底下的兵,這一萬兩,還只是他給他們這次來京回去的打賞,待到年底,又得另拉一批過去私下發給他們。
汪家在邊疆的經營,日後也少不了這些人的幫忙與扶助,說來,待過幾年,這些人也終會被他養成他的人。
現下,汪永昭讓親信騰飛成立的馬幫,這時已經在大夏、雲、滄兩州這幾地跑了起來,再有其他各行各業布下的暗樁,待過些年壯大了起來,誰知那又會是怎樣的一幅景象?
儘管現在老往那邊填銀子,但汪永昭卻知,那銀子有朝一日是收得回的,而眼下,他只得懷慕一個愛子,往後那麼大的家業,只得懷慕那一個眼睛長在腦殼頂上的兄弟相幫,怕是辛苦得緊。
所以無論如何,這婦人還是得至少再生兩個。
汪永昭求子心切,凡是關於這方面醫術高明的大夫,都被他請了過來給張小碗探脈,每個大夫的說辭其實都差不多,就是張小碗年齡已大,有子無子,都是送子觀音的事了。
汪永昭聽得煩躁,著人去打聽那些四十多高齡還能產子的婦人的妙方,結果,還真讓他找來了幾種,拉著張小碗試了個遍。
張小碗被他折騰得怕了,心裡厭煩,但嘴間還是示了弱,他一強要她就哭,哭得多了汪永昭也被她哭怕了,不敢再折騰她。
不過,有時他難免也想不開,要多往她的肚子看幾眼,眉目間皆是不快,似是嫌棄張小碗無用之極,連懷個孩子也不會。
這段時日,朝廷間出了大事,當朝太尉在太平殿撞傷了腦袋,語指御史大夫誣陷他貪了邊疆武官的餉銀。
御史大夫更是憤怒,當天就把他貪污的證據呈稟了上去。
而老太尉當天在家就一病不醒了。
太尉夫人上了兵部尚書府過來哭訴苦楚,張小碗怯怯懦懦地陪著她抹眼淚,太尉夫人哭就哭,太尉夫人問她話,她就茫然地抬起頭,搖頭道「妾身不知」。
太尉夫人左一句,右一句,得的都是她的「妾身不知」,偏生張小碗比她還能哭,她那整個人都似是水做的一般,眼淚掉得比她還多,話說到了後頭,她也只得悻悻離去。
*預知精采後續,敬請期待8/12上市的【文創風】211《娘子不給愛》4。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娘子不給愛(4)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65 |
華文羅曼史 |
$ 197 |
中文書 |
$ 197 |
文學作品 |
$ 213 |
小說/文學 |
$ 223 |
古代小說 |
$ 225 |
古代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娘子不給愛(4)
她知道他不喜她生的兒子……準確的說法,是厭惡。
可在兒子振翅高飛的戰場上,她需要他豐厚的羽翼擋住利箭,
因此,她戴上溫婉的假面,當起他要的可人妻子……
文創風211《娘子不給愛》4 溫柔刀◎著
汪永昭,一個令歷任皇帝都忌憚不已、欲殺不能的大臣。
他不僅聰明絕頂,而且心腸比誰都狠,不喜的便是不喜,
即便那人是她這正妻所出的嫡子,或是美妾所生的庶子,
兒子自小便恨極了他,因為他的存在對他們母子倆只有磨難,
然而張小碗卻清楚明白一點——違抗他是沒有好果子吃的!
兒子的前程他可以不施援手,卻絕不能痛下殺手,
因此在他跟前,再低的腰她都彎得下去,他的話也必定服從,
對她而言,他從不是什麼良人,只是一個可怕而強大的對手,
她必須打起十二萬分的精神,一步步都得謹慎小心地踏出,
畢竟,一步踏錯,迎來的不是滿盤皆輸,而是粉身碎骨!
本 書 特 色
他寵著她、護著她,會為她醋勁大發,甚至與皇帝對峙,
這男人愛上她了,她知道,但她並不愛他,他也知道。
呵,相較於他的冷酷,狠心絕情的她,其實也不是個好人啊……
作者簡介:
溫柔刀,晉江文學城簽約作者。本人是個性格多變的人,愛好也很簡單,喜歡看書,一個人歷險,喜歡創作,不寫自己喜歡的故事就會死星人……
章節試閱
第三十一章
兩日後,汪觀琪醒了過來。
父子倆談話時,張小碗就站在那外屋,她清楚地聽得裡屋的汪觀琪口口聲聲說要親手把那惡毒的婦人碎屍萬段。
他那充滿著惡毒意味的口氣讓外面的張小碗聽得不寒而慄,饒是她強自鎮定,身上的寒毛也因他那滿是惡氣的聲音而倒豎,沒得多時,背後已一片冷汗。
張小碗未聽得汪永昭的聲音,一會兒後,在汪觀琪發狂的聲音中,張小碗聽得一道凌厲的巴掌聲響起,還有那劍被抽出鞘的聲響;又過了一會兒,汪永昭走了出來,他那額頭還纏著布條的臉上有著一個清晰五指的巴掌印,脖子間還有一道血痕...
兩日後,汪觀琪醒了過來。
父子倆談話時,張小碗就站在那外屋,她清楚地聽得裡屋的汪觀琪口口聲聲說要親手把那惡毒的婦人碎屍萬段。
他那充滿著惡毒意味的口氣讓外面的張小碗聽得不寒而慄,饒是她強自鎮定,身上的寒毛也因他那滿是惡氣的聲音而倒豎,沒得多時,背後已一片冷汗。
張小碗未聽得汪永昭的聲音,一會兒後,在汪觀琪發狂的聲音中,張小碗聽得一道凌厲的巴掌聲響起,還有那劍被抽出鞘的聲響;又過了一會兒,汪永昭走了出來,他那額頭還纏著布條的臉上有著一個清晰五指的巴掌印,脖子間還有一道血痕...
»看全部
目錄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商品資料
- 作者: 溫柔刀
- 出版社: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08-15 ISBN/ISSN:978986328338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6頁 開數:正25開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