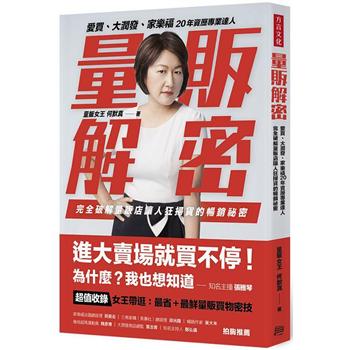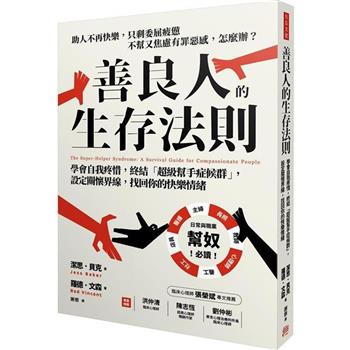為圓夙願,她本以為人生再無滋味,只餘無窮算計,
可夫君明明看透一切,卻甘於為她做盡大小事,
這般憐惜,竟教她早已死絕的情愛之心復燃了……
前世恍如一場夢魘,教重生後的顧晚晴不能忘也不想忘,
都恨她識人不清,引狼入室,害死了娘親,連自己也慘遭毒手,
豈料再世為人,不但沒聽見那包藏禍心的庶妹遭到報應,
還因「賢孝之名」被指婚給平親王世子,教她如何甘心?!
既然蒼天無眼,那就由她親手了結這段弒親奪嫡之恨──
素聞平親王姜恒雖是而立之年,卻因接連剋死五妻而無人敢嫁,
那教名媛們避之唯恐不及的王妃之位,便是她復仇之路的開端,
無論如何,她都要先一步嫁進王府,設下天羅地網,
任憑那庶妹本事再滔天,她也要與之纏鬥不休,
死過一回之人何懼之有?如今,她要把失去的一一討回來……
本書特色
帶著憾恨重生而來的王府續弦妃、
不甘落於人後的穿越世子媳,
大家各憑本事,置之死地而後愛!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重生婆婆鬥穿越兒媳 (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9 |
中文書 |
$ 189 |
文學作品 |
$ 204 |
小說/文學 |
$ 216 |
穿越文 |
$ 216 |
華文羅曼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重生婆婆鬥穿越兒媳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