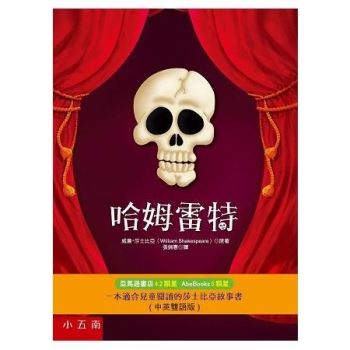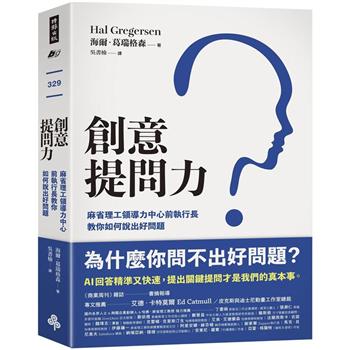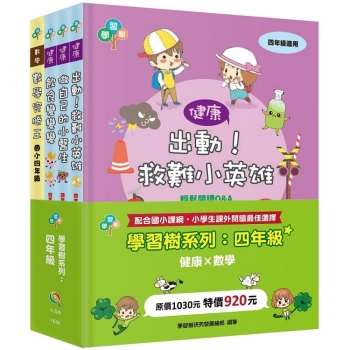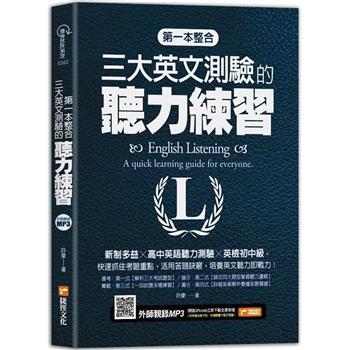第一章 穿越
初春的傍晚,夕陽餘暉打在穿著白大褂的喬梓瑞身上,將櫃檯上的藥單整理了一下,她環顧這個自己工作了三年的診所,心滿意足的笑著鎖門下班。
三年前,喬梓瑞在江城最負盛名的中醫學院畢業後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工作,一次偶然的閒逛,發現在這個復古的里弄裡,居然開著一家很雅致的中藥診所,出於好奇走進來,就這樣在這個小診所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喬梓瑞很喜歡這份工作,恬淡安靜,並且還是自己一直喜歡的專業,就這樣一直做了下來。
江城四月的傍晚,天氣微涼,關好店門,朝離這裡不遠的家走去。一百六十五公分的喬梓瑞不是那種讓人驚豔的類型,兩道一字眉,一雙清澈的杏眼,白皙的皮膚,整個人有一種淡淡的書卷氣,讓人感覺很舒服。
輕快的走進家裡那條弄堂,一道光線從身後射過來,回頭一看,是一輛小車,可能是因為在弄堂裡車速並不是很快,喬梓瑞下意識的往路邊靠了靠繼續往家走,對面不知道怎麼突然就竄出一條白色的小京巴狗,對著喬梓瑞使勁搖尾巴。
她看看後面的車,離自己還有幾公尺遠,車速好像也還不是很快,便蹲下去把小京巴狗抱起來,以免可愛的小東西萬一被車撞傷,可是就在剛站起來的一剎那,覺得身後傳來一種異樣的感覺,剛想抱著小京巴狗閃躲一下,只聽見「砰」的一聲,喬梓瑞感覺自己飛了起來,最後下意識的看了一下那隻小京巴,還好沒事。
喬梓瑞覺得自己好像掉進了一個黑暗的漩渦,不停的旋轉翻滾拉扯,終於落到了實處,使勁睜開眼睛──啊?!我這是到了哪裡呀?!
她躺在一張古色古香的床上,淡紫煙色的蚊帳攏在床的四周,身上蓋著一床鴨蛋青的被子,房間不大,床的對面是一個臨窗大炕,炕上放著一張炕桌,正面也是鴨蛋青的靠背,兩邊散落著幾個半舊引枕。地上是兩張靠背椅子,也搭著椅搭,炕的邊上是一個只有在江城古玩店見過的洗臉架,上面架著一個盆子,邊上掛著的,是塊白布吧,好吧,就算是洗臉毛巾吧。在洗臉架的邊上有個碎花漆的好像是梳妝檯的東西,靠床的那邊放著一張碎花漆的五屜桌子,桌子邊上有幾個同樣漆色的箱子。
喬梓瑞悲催的想──一定是死了,但這也太倒楣了點,就為了抱隻狗,被一輛發了瘋的車給撞飛了,這應該不是閻羅殿吧?難道現在的閻羅殿也開始流行復古裝修了,還是我已經到了某處仙山?
「咳咳!」喬梓瑞覺得頭很痛,嗓子也很難受。
剛咳嗽完,就見外面碎步跑進來一個穿著綠綾襖的丫頭,明快的五官,親和的笑容,大約十四、五歲的樣子,急忙過來,輕聲道:「姑娘您醒了,太好了,老爺和太太這兩天都急死了。」
喬梓瑞看著她沒有說話。
那丫頭又道:「姑娘,喝點水嗎?」
喬梓瑞點點頭。
那丫頭走到炕桌邊倒了一杯水,輕輕的吹了吹,用勺子小心翼翼的餵給喬梓瑞喝。
喝完水,她拿起枕邊的帕子幫喬梓瑞擦了擦嘴,然後道:「姑娘,您現在可有覺得哪裡不適?」
喬梓瑞覺得自己現在可以肯定不是到了哪座仙山,應該是狗血的穿越了,自己現在的這具身體比自己原來的小一號,看來還是最通常的魂穿,喬梓瑞這下不淡定了──死老天、臭老天,我很喜歡我原來的身體好不好,我也很喜歡我的工作好不好,這次也不知道祢給我發了具什麼身體,還這麼小。
看著那個丫頭,腦子裡閃過一個名字──「穀雨」,難道是那個丫頭的名字,喬梓瑞試探的開口:「穀雨。」
那丫頭果然笑著道:「奴婢在,姑娘有什麼吩咐?」
看來這具身體還是殘留了原宿主的記憶。
喬梓瑞想了想道:「我現在只是覺得有些頭疼,其他倒也沒有哪裡不適,老爺和太太呢?」
穀雨邊把茶杯放回炕桌上邊道:「自從姑娘摔倒昏迷了,老爺和太太可急壞了,特別是太太,一直守著姑娘不吃不喝。」穀雨說著眼眶都紅了。
喬錦書看得出這個丫頭很爽直,也是真的關心自己。
「這不,錢嬤嬤勸了半天,太太好不容易才肯去吃點東西,換身衣服,太太剛走開一炷香的工夫,姑娘就醒了,可真是老天保佑。」穀雨擦擦眼角的眼淚道:「姑娘要沒有哪裡不適,就先躺著歇會兒,奴婢去回了老爺、太太,他們不知道得多高興呢!」
喬梓瑞看著穀雨,心裡也沒來由的有些感動,前世自從外婆離世就是一個人生活,從來沒有人關心自己,看著穀雨為自己或悲或喜,也不由得對這個才來的世界和家生出一分親切感。就拉著穀雨的手道:「我沒事了,妳去告訴老爺和太太吧。」
穀雨幫喬梓瑞掖掖被角就出去了。
想著穀雨的話,腦中又閃過一些畫面,在一棵大柳樹下,有一塊半人高的石頭,石頭旁邊站著一個身穿半舊鵝黃褂子,下穿灰綠色棉裙的小姑娘,踮著腳,想去折柳枝,不遠處的小石子路上,猛的竄出來一個穿著紫色棉袍、和小姑娘差不多大的男孩,把穿鵝黃褂子的小姑娘一把推倒,那小姑娘冷不防被推,朝後仰倒,頭直接撞上了身後的大石頭。在那小男孩身後不遠處站著一個穿紅著綠的婦人,看著撞向石頭的小姑娘,冷冷的陰笑。
小姑娘躺在床上,旁邊有一個溫柔婉約、雙眉入鬢的婦人,和一個留著鬍鬚、長相精明的男人,那溫柔的婦人抓著小姑娘的手,哀哀悲泣,聲聲喚著:「錦兒、錦兒,妳醒醒啊!」
喬梓瑞霎時都明白了,自己這具身體的原主人叫喬錦書,那個留著鬍鬚的男人是自己的父親,自己的母親是正室,生了自己,那個推倒自己的男孩應該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弟弟,那個他身後穿紅著綠的婦人,應該就是生下那個男孩的宋姨娘,看來他們是故意推倒了自己。
聽著門外有腳步聲,喬錦書靠著枕頭半坐起來。門口懸著的桃紅碎花軟簾一動,穀雨掀起門簾,那個溫柔婉約的喬太太吳氏,帶著一個嬤嬤和一個丫鬟走進來。
吳氏頭綰墜馬髻,斜插著根碧綠翠玉簪,身穿藍色銀絲褂子,急匆匆的走過來道;「錦兒,妳可醒了,急死娘了。」
看著吳氏一臉憔悴,雙眼含淚,不知道是這具身體的緣故,還是感受到那種緣自心底的親情,喬錦書沒來由的一陣心酸,眼淚也不由得落下,伸出手拉著吳氏道:「娘。」卻是喊了一聲,便再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是靠進婦人的懷裡輕聲哽嚥著。
吳氏輕輕拍著喬錦書的背,哄著:「錦兒乖,不哭啊,都是十一歲的大姑娘了,哪裡不舒服告訴娘。」
喬錦書抽泣著抬起頭噘著嘴道:「娘,錦兒哪裡都沒有不適,就是醒不來的時候,好像作了個好長的噩夢,錦兒好怕見不到爹和娘了。」
一聽錦兒說沒有哪裡不適,吳氏立馬鬆了口氣。
母女兩個正依偎著說體己會,門外又進來了幾個人,穀雨等忙見禮。
喬錦書看著進來的男人,自己的爹──喬楠楓。一身冰藍色長棉袍,腰繫銀灰錦帶,五官俊朗而透著幾分商人的精明,姿態閒雅,手裡牽著那個推她的男孩,那個男孩子的另外一隻手牽在緊隨其後的宋姨娘手裡,十足是相親相愛的一家三口,而走在後面的宋姨娘,臉上雖帶著謙卑的表情,眼裡卻透著得意,示威的看著吳氏和喬錦書。
喬楠楓邊走邊道:「錦兒,妳可醒了,爹這兩天都急死了,妳看看妳這麼大的孩子了,真不小心呢,我總要多找幾個人跟著妳才是。」
喬錦書偎在吳氏懷裡看了一眼宋姨娘沒動,只是欠身彎腰道:「錦兒見過爹,讓爹娘擔心了,都是錦兒的不是。」說著又朝喬楠楓伸出手道:「爹,錦兒這兩天昏迷著一直作噩夢,夢裡都找不到爹娘了,錦兒好害怕。」
看著錦兒,一張小巧的瓜子臉上,兩道彎彎的眉毛,一雙水汪汪的的杏眼,清澈透明,眼裡泛著淚光,淡粉色的嘴唇就像天然的花瓣,微微噘著,因為受傷,齊眉勒著一條粉色的絲巾,喬楠楓看得心裡一片柔軟,這是自己的掌上明珠啊,有多久沒這樣和自己撒嬌了,嘴裡卻笑著看了吳氏道:「咱們的錦兒摔了一跤,倒摔小了,還和爹撒嬌了。」
說著大步向錦兒的床榻走來,坐在錦兒身邊,用自己的大手握住吳氏和錦兒握在一起的手,道:「錦兒可有什麼想吃想玩的,只管告訴爹,爹讓人給妳買去。」
喬錦書依偎在爹娘身邊,挑釁的看著宋姨娘,宋姨娘眼裡快速的閃過一陣陰冷,要不是喬錦書一直觀察著宋姨娘,根本就不可能發現那一閃而逝的陰狠表情,再仔細一看,宋姨娘還是一臉謙卑的看著他們。
喬錦書看著宋姨娘的掩飾工夫就斷定這女人絕不是省油的燈,心裡暗暗發狠──不論妳是誰,要想破壞我好不容易才有的家,姊就絕不放過妳。
喬錦書帶著幾分天真的看了喬楠楓道:「看姨娘是不是也高興傻了,都忘記向我娘行禮了呢。」
宋姨娘聽了這話極不甘的看了喬楠楓一眼,卻見喬楠楓只看著喬錦書,根本沒有看她,便無奈的帶著那個男孩一起移步上前向吳氏施禮。
「見過太太。」
「見過娘。」
吳氏伸手虛扶一把,道:「起來吧,一家人不必客氣。」
宋姨娘笑著推了喬仲青一把道:「仲青去見過你姊姊。」
喬仲青嫉妒的看了眼喬錦書,直接走過去想拉開喬楠楓握著喬錦書母女的手。
喬錦書看著喬仲青的小動作,眼睛一轉,看著喬仲青走近,她故作害怕的靠近喬楠楓懷裡道:「爹,那天是仲青弟弟推我的。」
宋姨娘臉色一下子白了,慌忙道:「錦兒,妳看錯了吧,那天是妳自己不小心摔倒,仲青是去扶妳的。」
錦兒?喬錦書心裡冷笑,姨娘不過是半個奴才的身分,對自己所生的兒子尚且要稱少爺,更何況對自己這個嫡出的姑娘,由此可見這個宋姨娘平日的張狂。
喬仲青畢竟也只是個十歲的孩子,比錦兒只小幾個月,也心虛的道:「姊姊,我不是推妳,是想拉住妳。」
喬楠楓看著兩個小孩皺了皺眉頭,剛想說話,吳氏眼底閃過一絲精光,伸手把喬仲青拉到自己身邊,摸了摸喬仲青的頭,道:「仲青,姊姊是摔到頭,受了很重的傷,不記得那天的事了,你別著急,姊姊醒來了,也沒大礙,你安心唸書就是。這幾天錦兒就好好休息,妳祖母和叔叔去廟裡還願還要幾天才回來,這幾天妳的請安就免了,仲青的也免了,都好好休息。」
喬楠楓笑著看了眼吳氏,眼裡都是讚許,對著喬仲青心疼的安慰道:「是啊,你姊姊傷了頭,才會誤會你的,你別害怕,大家都知道你是個孝順的好孩子,沒人說你推姊姊的。」
喬仲青乖巧的看著喬楠楓點點頭,然後又挑釁的看了喬錦書一眼。
喬錦書只作不見。
這幾天吳氏不許她出門,喬錦書就待在屋裡,喝了幾天的苦藥,倒也恢復得很快,悶在屋裡無事可做,就把前主人的書翻出來看了一下,大多是史書和詩詞歌賦類的,對於這個朝代的歷史倒是有了一些瞭解,
這是一個不存在於中國歷史的架空朝代,這個朝代已經歷了五朝皇帝,現在的皇帝是聖安帝,年號是啟源八年,至於禮儀風俗倒與中國歷史大致相同,等級嚴格,男尊女卑,嫡庶分明。
屋裡沒有一本醫書,可見這個前主人是從不看醫書的,心裡便盤算著總要找個藉口看些醫書,這樣以後自己的醫術才有用武之地。
再說喬錦書在屋子裡悶了幾天,和穀雨聊天也知道了家裡的大概狀況,這個家是在遠離京城西南面的慶陽縣,因為靠近口岸倒也算是富庶之地,喬楠楓早年中了個秀才,因為父親去世就沒有繼續科考了,繼承了祖業開始經商,家裡開著一間名叫松鶴樓的酒樓,一間慶餘堂藥鋪,外帶一間米鋪和幾百畝地,算不上大富之家,只是小康倒也衣食無憂,使奴喚婢,日子悠閒。
喬錦書還有祖母和小叔,祖母卻不是親生的,喬錦書的親祖母在生小叔時難產了,為了照顧年幼的小叔,祖父便續娶了現在的祖母,因小叔身體不好,祖母帶小叔拜佛還願去了。
清晨,窗外的小鳥驚醒了喬錦書,睜開眼睛看著周圍陌生的一切,懵懂中有著片刻的不適應,然後輕嘆一聲,披衣起床,走到炕前看著窗外,小鳥在剛抽出新芽的枝椏間蹦跳,遠處的青山、房屋都似籠在一片雲霧中模糊不清,清新的空氣中彷彿有著清甜的味道。
二十一世紀的江城,自己大概是永遠都回不去了吧,電腦、電視所有的電器,還有琳琅滿目的化妝品和衣服,香醇的咖啡和才認識的令自己心動的「他」,大概都是此景從此夢中尋了。從此以後再沒有了喬梓瑞,只有啟源八年的喬錦書了,呵呵,喬梓瑞,喬錦書,也許曾幾何時她們原本就是一人吧,又有誰知道呢?
「姑娘,您怎麼下床了,天氣還冷著呢,快去床上偎著,我伺候姑娘穿衣,昨兒個晚上太太身邊的春分來傳話,明天初五,雖說老太太和二爺不在家,但一家人還是要一起早膳的,叫我們不要去晚了,老爺會不高興的。」穀雨端著盆熱水邊走邊道,放好洗臉水,取了套嫩粉色的裙褂過來。
喬錦書看著窗外的新綠道:「穀雨取套淺綠色的衣服吧」。
「是,姑娘。」穀雨邊走還邊自言自語道,不是最不喜歡綠色衣服嗎?今兒個倒想起要穿了,還是取了套嫩綠得幾乎鵝黃的顏色,恰似樹上剛抽出的新芽,倒合了喬錦書的心意。
穀雨伺候著洗漱更衣後,扶著喬錦書坐到梳妝檯前,穀雨看著喬錦書額頭上淺粉色的疤痕,心裡一疼,並沒說話,只是不作聲的拿起梳子,分了一些稍長的頭髮下來做劉海,然後俐落的梳了個雙丫髻。
喬錦書看著鏡子,雖然沒有現代的清晰,但是已經能很清楚的看見人的五官了,鏡中的女孩,一張巴掌大的小臉,讓過長的劉海遮去了一半,顯得嬌弱而無神,讓人憐惜也讓人覺得可欺,這大概就是以前的喬錦書吧。
喬錦書心中唸著──
喬錦書,這是我最後一次這樣稱呼妳了,以後這個名字就屬於我了,我會在這個世界好好的、認真的、精彩的活著,妳安心的去吧!
想著隨手撥開頭上的劉海,她看著自己額前的疤痕。
穀雨見了連忙道:「姑娘,且別著急,大夫說了這疤痕很淺,勤著點上藥,過個十天半月就會好的。」
喬錦書歪著頭看著穀雨俏皮的道:「我怎麼會怕小小一個疤痕呢?就算有,我也會讓它消失的,我只是不喜歡這個劉海,妳幫我梳上去,然後給我找一條鵝黃色的絲帶來便好,其他交給我。」
穀雨只當小孩說話,也沒當真,只回道:「姑娘不會覺得疤痕不好看嗎?」
「妳梳上去,我有辦法。」喬錦書道。
穀雨便依著喬錦書梳好了頭,就去找絲帶了。
喬錦書拿起描唇筆,沾了點粉色的胭脂,細細的沿著那疤痕,畫出了一朵梅花。
穀雨回來看著鏡中的那張臉,整個人一呆,鏡中的人沒有了劉海,露出了整張精緻的瓜子臉,兩道新月似的眉毛,一雙顧盼生輝的杏眼,秋水粼粼,像花瓣一樣的淡粉色的唇,額間飄著一朵梅花。
「姑娘,您今天像畫裡的仙子一樣。」穀雨驚詫的道。
呵呵,錦書笑著教穀雨將絲帶穿過頭上雙丫髻,在後面繫個蝴蝶結,和頭髮一起披散在肩上。
看著那個靈動飄逸,超凡脫俗的小女孩,喬錦書得意的笑了笑道:「穀雨,咱們給我爹娘請安去」。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藥香襲人(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60 |
二手中文書 |
$ 195 |
社會人文 |
$ 197 |
中文書 |
$ 197 |
文學作品 |
$ 225 |
古代小說 |
$ 225 |
華文羅曼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藥香襲人(上)
本 書 特 色
作者維西樂樂筆調文風,
綿柔裡藏著犀利,明快中深情流露!
二十一世紀的中醫師穿越成了架空時代的小蘿莉,
小門小院小商戶,且看小蘿莉怎麼鬥繼祖母、救親叔叔、鬥姨娘,幫娘生了嫡親小弟弟,幫爹爹賺大錢……
還看她怎麼用一顆七巧玲瓏心,降服城府深的腹黑男……
內 容 簡 介
如果可以,人家不嫁!
不得不嫁,人家不做小妾!
來生再約,人家不做平妻!
文創風246《藥香襲人》上 維西樂樂◎著
她原本是二十一世紀的中醫師,
為了救一隻狗竟穿越重生成了架空時代的喬錦書小姑娘,
這喬家雖然不是名門高府,
可這門裡的妻妾之爭、嫡庶之鬥、繼室之私,可不容她掉以輕心吶!
還以為從此要跟她最愛的中醫說掰掰了,
沒想到在這兒超實用,甚至成了她的保命平安符,
不僅幫她鬥繼祖母,救親叔叔,鬥姨娘,還幫娘親生了小弟弟,
甚至還幫爹爹、一家人親親熱熱賺大錢。
不過她再聰穎,還是遭人算計,
嫁了個冷酷、武功高強的腹黑大男人顧瀚揚當平妻,
這嫁入顧府的日子,比起喬家來更不簡單,
先她入門的妻妾沒一個能讓她省心的,
就連她嫁的這位爺,也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好好伺候呢!
作者簡介:
維西樂樂,晉江原創網簽約作者,處女座,不是走在路上肆意歡笑,就一定是宅在家裡的落地窗前發呆,嚮往風一樣的自由自在,溫柔的外表下藏著一顆女漢子的心,最希望的就是把自己天馬行空的夢變成一個個溫暖的故事。已經發表的作品有《藥香襲人》。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穿越
初春的傍晚,夕陽餘暉打在穿著白大褂的喬梓瑞身上,將櫃檯上的藥單整理了一下,她環顧這個自己工作了三年的診所,心滿意足的笑著鎖門下班。
三年前,喬梓瑞在江城最負盛名的中醫學院畢業後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工作,一次偶然的閒逛,發現在這個復古的里弄裡,居然開著一家很雅致的中藥診所,出於好奇走進來,就這樣在這個小診所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喬梓瑞很喜歡這份工作,恬淡安靜,並且還是自己一直喜歡的專業,就這樣一直做了下來。
江城四月的傍晚,天氣微涼,關好店門,朝離這裡不遠的家走去。一百六十五公分的喬...
初春的傍晚,夕陽餘暉打在穿著白大褂的喬梓瑞身上,將櫃檯上的藥單整理了一下,她環顧這個自己工作了三年的診所,心滿意足的笑著鎖門下班。
三年前,喬梓瑞在江城最負盛名的中醫學院畢業後一直沒找到合適的工作,一次偶然的閒逛,發現在這個復古的里弄裡,居然開著一家很雅致的中藥診所,出於好奇走進來,就這樣在這個小診所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喬梓瑞很喜歡這份工作,恬淡安靜,並且還是自己一直喜歡的專業,就這樣一直做了下來。
江城四月的傍晚,天氣微涼,關好店門,朝離這裡不遠的家走去。一百六十五公分的喬...
»看全部
目錄
序
第一章 穿越
第二章 和好
第三章 生日
第四章 拜師
第五章 興家
第六章 有孕
第七章 比試(一)
第八章 比試(二)
第九章 曦園
第十章 搬家
第十一章 出診
第十二章 危機
第十三章 產子
第十四章 洗三
第十五章 中計
第十六章 羞花
第十七章 病因
第十八章 出閣(一)
第十九章 出閣(二)
第二十章 回門
第二十一章 訓僕
第二十二章 財迷
第二十三章 心語
第一章 穿越
第二章 和好
第三章 生日
第四章 拜師
第五章 興家
第六章 有孕
第七章 比試(一)
第八章 比試(二)
第九章 曦園
第十章 搬家
第十一章 出診
第十二章 危機
第十三章 產子
第十四章 洗三
第十五章 中計
第十六章 羞花
第十七章 病因
第十八章 出閣(一)
第十九章 出閣(二)
第二十章 回門
第二十一章 訓僕
第二十二章 財迷
第二十三章 心語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維西樂樂
- 出版社: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4-12-05 ISBN/ISSN:978986328387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36頁 開數:25開(14.8×21)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