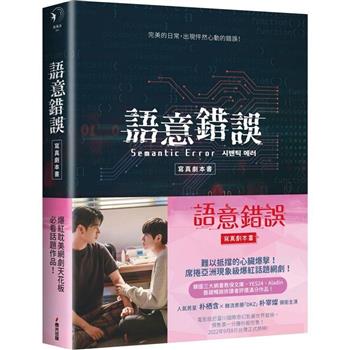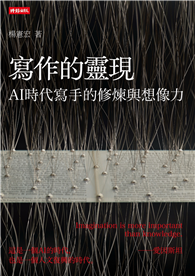未婚夫能吃嗎?
她餓得只看得見他手上的白饅頭,
吃飽可比嫁人還要緊吶!
她餓得只看得見他手上的白饅頭,
吃飽可比嫁人還要緊吶!
初到陌生環境的魏清莛和弟弟被關在一個廢棄小院裡謀生存,
有人「穿」過來立刻身分加級大富貴,
她卻「穿」得好心酸,瞧瞧她的身家背景──
曾為三朝元老的外祖父突然被定以謀反罪,
太子自盡,皇后被禁,她兩個舅舅被流放,生死未卜,
而母親也在這時候病倒身亡了……
爹不疼,爺姥不愛就算了,姨娘還落井下石,
餓得不行,給的飯菜還有毒,
幸好偷偷摸摸溜進來一個少年,硬說他是自己未來的老公,
跟她約好長大後要退親,還塞給她幾個饅頭,
她啃著饅頭,懶得理他,哪有工夫去想長大的事,
眼前這麼多人想害她,她肯定要帶著弟弟活得更好才行……
本書特色
全文風格輕巧討喜,笑裡藏情。
情節豐富,妙趣橫生,
文筆逗趣輕鬆,人物溫馨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