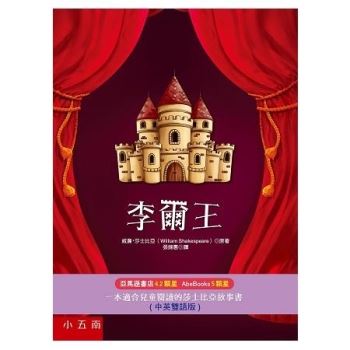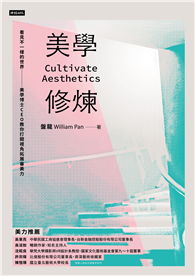她不願再被折斷雙翼,
囚禁在華美卻令人窒息的牢籠中。
她想看得更多,走得更遠!
晏雉自幼爹不疼、娘不愛,被長嫂虐待卻無人聞問,
為了家族,她被迫嫁給豪門浪蕩子為妻,飽受欺凌。
如今生命即將走到盡頭,她不恨不怨,
只是格外想念家中後院的秋千,想念幼時的燦爛春光……
當她發現自己竟回到記憶中的春日時,滿心失而復得的快樂。
機緣巧合下,她與兄長同時拜入名士門下,
每日學習的不是婦德、婦功,而是兵法騎射,治國策論。
不甘心受困閨閣之中,膽大心細的她隨兄長赴任,
搶救災民、懲治貪官,打響了晏家四娘的名頭。
她知道,在外人眼中她離經叛道,
收留逃奴須彌,更與他過從甚密,全然不在意女子名節。
那些耳語她一律拋在腦後,
這一生,她決心只為自己而活!
本書特色
晏雉抑鬱而終,睜眼竟回到六歲那年,她決心扭轉命運。巧遇良師的她讀兵書、習騎射,眼裡看的不再是小情小愛,今生她不想再當嬌嬌女,她要自立自強!在一場詭異的七月雪中,她撿到了擁有一雙琉璃色眼瞳的須彌,從此改變兩人的人生。作為幕僚隨兄長赴任各地,總是守在她身後的須彌也投身軍旅。他們的重生不只為了再度相遇,也為了大邯的盛世太平。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閨女好辛苦 (上)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閨女好辛苦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