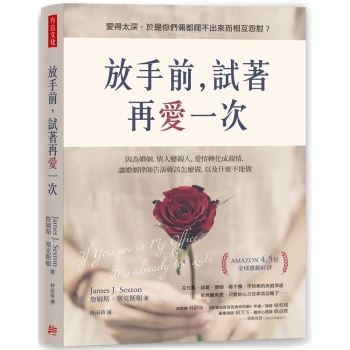第一章 擦肩而過
江南逢春,正是清明雨紛紛的時節。方才有些陰鬱的天空已經飄起了小雨,映著青山綠水,頗有些煙雨濛濛的感覺。
不遠處是一大片青瓦白牆的人家,在雨中瞧著尤讓人覺得冷清,門楣上的白幡還沒收起來,被雨水打得濕淋淋的,將「謝府」兩個字蓋去了一半。一個穿著素服的女子站在廊下的青石板臺階上,探著身子往外頭看了幾眼,腳下的繡花鞋沾到雨水,濕了半邊。
興許是雨中風大,她低頭咳了幾聲,身後的嬤嬤急忙上前,將一件外衣披在她的身上。
「夫人放心吧,這雨下不大,姑娘一會兒就回來了。」說話的是謝家女主人徐氏身邊的管事媳婦張嬤嬤。張嬤嬤是徐氏的陪房,如今已有四十出頭,在謝家也已經過了二十來年,是徐氏身邊的老人了。
徐氏點了點頭,心下卻還是忍不住有些擔憂。丈夫一個月前病故,如今在家裡停靈已有二十多日,她最近身子又不好,勉強才能起身,如今這選墳地的大事,就落在她跟丈夫唯一的閨女身上了。
都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可她這個女兒雖然從小養在蜜罐裡,卻因為父親病故,好似換了一個人一樣,原本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姑娘家,彷彿一夕間長大,硬是在眾多的叔伯族人面前,活出了當家人的樣子。
徐氏想到這裡,不禁深深嘆了口氣。
謝玉嬌坐在轎子裡頭,伸手挽起了轎簾,看了煙雨紛飛的景色一眼,一張嬌俏清麗的臉上頓時染上一抹愁容。
提起這件事,謝玉嬌還覺得胸口疼呢!她不過就是睡個覺而已,誰能料到這一覺醒來,就到了這前不著村、後不著店,連電腦、手機、iPad都沒有的地方。謝玉嬌從小喪父,跟母親相依為命,好不容易開始上班,可以賺錢孝順母親,誰知道就這樣穿越了……
也不知道這身體的原主去了哪裡,她連找個對象抱怨都沒辦法,若不是如今這位徐氏的容貌、姓名跟謝玉嬌在現代的母親一模一樣,她還真想撂挑子不幹了。
這算什麼啊!穿越來的時候,爹已經死了,娘還生病,最關鍵的是,他們居然沒生出一個兒子來,謝家偌大的家業,就這樣「暫時」壓在謝玉嬌的肩頭上。
古代的規矩跟現代不太一樣,現代就算是女兒,也有繼承權,父親過世,女兒繼承遺產合情合理;可在古代,女兒打從出生,就被看成是別人家的人,沒有繼承權不說,若是錢落到了別人家的手裡,將來有沒有嫁妝還是問題呢!
父親剛辭世,族長自然不會提出分家的事情,但就是提了,謝玉嬌也不會那麼容易讓他們得逞,憑什麼謝家幾輩子辛辛苦苦攢下的銀子,要分給沒出過什麼力的人?如今唯一的辦法,就是在族中找一個孩子過繼到謝家來,沒準兒還能保住這份家產。
族長已經同意了這個想法,但是關於這個孩子的人選,實在是一言難盡。
謝玉嬌的父親雖然是老太爺的獨子,可在老太爺那一輩當中,倒是有幾個叔伯兄弟,雖然年輕時候各自分家過日子了,這些年也沒少來家裡打秋風,因此對於謝家正房這一筆巨大的財富,他們都如猛虎惡狼一般覬覦著。
她前幾天剛穿越過來,人都還沒認全的時候,就已經被領著看了十幾個孩子,大到二十出頭,小到剛剛滿月,凡是謝家五服之內的子孫,人人都有機會。
徐氏直接稱病不肯出來見人,謝玉嬌只好耐著性子一一見過,所幸輩分沒弄錯,只是名字紛亂,一時記不住,她把謝家的族譜給請了出來逐一對照,才算是把這群人都認清楚了。
那些已經長大成人的就不說了,沒幾個看得順眼的,十歲以下的又不知道長大後是個什麼模樣,眼下謝玉嬌都十四了,翻了年十五,就算是為她爹守孝三年之後嫁出去,也不過一眨眼的工夫。
要是選個大的,等於奉送全部家當;要是選個小的,三年之後也調教不出個什麼樣子。謝玉嬌支著額頭發愁,眼下只能拖一天是一天了。
外頭的雨越下越大,丫鬟打著傘跟在轎子旁邊,小聲囑咐。「欸,你們慢著點,小心路滑晃著小姐了。」
幾個轎伕都是謝家土生土長的奴才,很靠得住,衣服都濕了,也沒人有半句怨言,只冒雨抬著謝玉嬌回去。
謝玉嬌見轎簾都潮了,心知這雨必定下得不小,便支起簾子,往外頭看了一眼,只見淅淅瀝瀝的雨幕不遠處,有一處外觀為土黃色的廟宇,正是這一帶的土地廟。鄉下種田人家尤其信奉土地、龍王一類的神仙,認為祂們可保佑風調雨順,莊稼穀富米充。謝家身為這一帶最大的地主,自然是這土地廟最闊氣的香客。
「喜鵲,妳去廟裡問一聲,看看能不能讓我們進去歇歇腳,這雨不小,身上淋濕了也不舒服。」謝玉嬌開口說道。
叫喜鵲的丫鬟脆生生地應了一句,打著傘走了幾步,又轉身對轎伕們道:「你們慢著些,走穩了,別急著跟過來。」
土地廟裡頭,這會兒正好先來了兩位客人,其中之一是今年新到任的江寧知縣康廣壽,是上一科的狀元,三年散館之後,便來江寧縣這裡做一方父母。
康廣壽年約二十五歲,書卷氣息濃厚,模樣成熟穩重。他身邊另一位男子,穿著一身石青色緄邊錦衣,盤腿而坐,看上去二十出頭的樣子,容貌不俗,一雙劍眉眉飛入鬢,烏黑的眸子點漆一般深邃睿智,眼神中還帶著幾分讓人不可捉摸的冷傲。
今天康廣壽帶著錦衣男子私下到各處走走,正巧遇上下雨,便到土地廟裡躲雨。
廟祝是個五、六十歲的老人家,江寧縣本地人,從小就在這土地廟出家,對地方上的大小軼事都熟悉得很。
「大人來江寧縣這地方,怎麼能不知道何家跟謝家呢?不說在江寧,就是在整個應天府,何家跟謝家也是數一數二的人家。何家是江寧縣最大的財主,聽說除了鄉下的土地,城裡的鋪子共有上百間,整個貢院西街都是他們家的祖產,每年光是那些店家收的租金,就能堆幾間倉庫。」
廟祝侃侃而談,顯然對這些事情如數家珍。「謝家就更不得了了,他們是江寧縣最大的地主,這附近幾個鎮的土地都是他們家的,就連隔壁的秣陵縣,也有不少他們家的田地。除了土地,又兼做絲綢、茶葉生意,光是宅子,城裡城外就有五、六處,聽說先帝南巡的時候,還住過他們家的宅子呢!如今謝家的當家主母,跟當今皇后還是堂姊妹,實在是名副其實的江寧縣首貴,無人能及啊!」
一旁的錦衣男子聽了,略略皺了皺眉頭,隨口問道:「這麼有錢,豈不是剝削了很多百姓,怎麼沒聽過百姓說他們不好,想來是有些手段了?」
廟祝聽男子說起這件事,忍不住哈哈笑了起來,說道:「這位公子,您這麼想可就錯了,雖說謝家有錢有地,卻從來不剝削佃戶,這一帶就數他們家的田租收得最少;要是遇上災荒,還會搭棚施粥,附近幾個村鎮的百姓沒少受過他們家的恩惠,可謂積善之家。」
廟祝說到這裡,忍不住嘆了口氣,繼續道:「只可惜好人不長命,上個月謝老爺得病去了,留下偌大的家業,剩下孤兒寡母兩個女人看著。」
錦衣男子聽到這裡,倒是有了些興致,問道:「謝家沒兒子嗎?」
「就是沒兒子,獨獨一個閨女,當掌上明珠一樣養著,聽說謝家小姐平常洗澡都不用水,而是用莊子裡奶牛擠下來的牛乳呢!謝老爺去世之前,就是謝家宅裡,也沒幾個人見過謝小姐的模樣,說是比天上的嫦娥還要漂亮。老衲前陣子去謝家為謝老爺做法事的時候,遠遠瞧了一眼,那姑娘的皮膚,白得跟外頭開著的玉蘭花瓣一樣,只可惜這麼年輕就沒了爹,可憐啊!」
這兩個男人顯然對謝小姐的長相沒什麼興趣,錦衣男子又問起了其他問題。「謝家跟何家可有什麼姻親關係?說起來地方上的富豪,多少有些勾結。」
廟祝皺著眉心想了片刻,開口道:「謝家的老夫人是何家的姑奶奶,後來何家想跟謝家再攀個親戚,讓何家大少爺求娶謝家小姐,但是謝老爺實在太寶貝這閨女了,沒捨得答應,如今他去得早,謝小姐的婚事也沒訂下來,不知道後面會是個什麼光景。只是謝家沒個頂梁柱,孤兒寡母的,又守著這麼大一筆錢財,只怕以後日子不好過嘍!」
他的話還沒說完,外頭的小沙彌跑進來說道:「師父,廟門口有個姑娘,說是謝家的丫鬟,他們今日去了隱龍山為謝老爺選墓地,這會兒外頭下雨,想進來躲個雨。」
廟祝一聽是謝家的人,白眉毛抖了抖,回道:「快去請他們進來,開春雨多,天氣又冷,凍著就不好了。」
小沙彌合掌唸了一句佛偈,又道:「那丫鬟說要一間乾淨的禪房,來的人是謝家的小姐。」他雖然六根清淨,但畢竟修練的年歲有限,還達不到心無萬物的境界,耳根微微發熱。
廟祝這下倒是為難了,他這土地廟小,也就這一間待客的禪房還像樣,謝家小姐要來,那眼前這兩位客人,又要去哪兒呢?
康廣壽見廟祝臉上露出一絲苦惱的神色,爽快起身開口道:「時候也不早了,不知道什麼時候雨才會停下來,我們就先告辭了。」
他話一說完,身邊的錦衣男子也站了起來,朝廟祝拱了拱手,示意要離去。
廟祝雖然認得新來的縣太爺,可他並不知道這位長相不凡的公子身分為何,不過他常年修練,平常替人看相多少有幾分準頭,心裡早認定這位公子非富即貴,見兩人起身要走,也沒挽留,點了點頭一路將兩人送到門口。
此時廟門口不遠處,一抬平頂皂幔轎子正從遠處緩緩行了過來。轎旁站著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打著油紙傘,紮著雙垂髻,一眼就能看出是小姐身邊的丫鬟。
康廣壽回身向廟祝拱手作了一揖,開口道:「老師父對這邊的風土人情這般熟悉,改日必定請您去縣衙一敘。」
廟祝雙手合十唸了一句「阿彌陀佛」,目送兩人上了馬車,見他們在雨霧中越走越遠,這才鬆了神色,默默回想著方才那位錦衣男子的容貌:頭上有物,如博山之形,有此靈物,方能噓氣成雲,扶搖直上,飛升於九天也,此為特貴之相。
他此生也算閱人無數,倒是頭一次看見有人面相如此,正揣測那位公子的身分時,卻聽耳邊傳來一個清脆悅耳的聲音,猶如三月的鶯歌,四月的黃鸝。
「老師父,打擾了。」
廟祝回過神來,只見那丫鬟扶著一個嬌滴滴的姑娘下了轎子,那姑娘朝著自己微微福了福身子,皓齒星眸、粉黛青娥,實乃人間絕色,只消一眼,他就認出這是謝老爺家那個嬌貴的小姐。
「謝施主裡面請。」廟祝回了一個佛禮,引眾人進去。
方才待客的禪房裡已經空無一人,廟祝帶她們進屋後暫時告退,小沙彌則重新沏了茶上來,謝玉嬌謝過之後,開口道:「煩請小師父取些熱茶,給我那幾個轎伕喝一口,讓他們也暖暖身子。」
小沙彌紅著臉答應,喜鵲見他出門了,才笑著道:「小姐,不是說和尚都六根清淨嗎,怎麼他見著您還臉紅,豈不是犯了色戒?」
謝玉嬌回了喜鵲一記眼刀,嚇得喜鵲急忙噤聲,捧著茶盞送到謝玉嬌面前,說道:「這是舊年的陳茶了,小姐湊合著喝一口吧!」
謝玉嬌點了點頭,捧起喜鵲送上來的茶盞,低頭看了碗裡碧青的茶水一眼。雖然她不知道喜鵲怎麼看得出這是陳茶,但這會兒才農曆三月,尋常人家若是想喝一口新茶,只怕沒那麼容易。不過謝家有茶園,前一陣子那邊送了好一些明前雨花過來,喝起來確實順口。
謝玉嬌喝了兩口茶,一時之間身上的潮氣褪了不少,這房間裡燃著寶塔檀香,清清淡淡的,很讓人舒心,只是這檀香之中,似乎還混雜了一些別的香氣,雖然不濃郁,但是對於鼻子特別靈的謝玉嬌來說,很容易就能分辨出來。如果她猜得沒錯,這屋子片刻之前才待過客,大概就是方才與他們錯身的那輛馬車裡的人。
謝玉嬌想起這些,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若不是自己要過來歇腳,只怕他們也不會這麼急著離去,雨天趕車本就不便,她這樣倒是難為了別人,不過現在想這些也沒什麼意思,反正人都走了。
小沙彌離開沒多久,廟祝再度走進禪房,他六根清淨,不必避嫌,見謝玉嬌端坐在房裡,慈祥地笑道:「小姐今日出門,可是為謝老爺選好安寢之地了?」
謝家祖墳在隱龍山,那邊依山傍水,是福蔭子孫的好地方。謝老爺雖然早逝,可備受族人愛戴,他的墓室所在,也是族裡的人請了三、四個有名望的風水師父連番推算出來的,定下了地方之後,才請謝玉嬌過去看。
謝玉嬌對這些事情可以說一點都不懂,好在家裡的管家一路上為她解說,如今她也算是明白了一些其中的門道。
「地方已經選好了,家父下葬之日,還要請老師父前去做法事,過幾日我再送帖子過來。」謝玉嬌說道。
廟祝連連說了幾句不敢當,又往謝玉嬌的臉上掃了一下,終究不敢細看人家姑娘的長相,只知道這皮膚確實白皙透亮,吹彈可破。
好在春雨來得快、去得也快,不過一盞茶的工夫,雨就變小了。謝玉嬌念著徐氏一個人在家恐怕又要擔心,便起身告辭。
喜鵲上前扶著謝玉嬌起身,替她整理好起縐的衣裙,卻見一枚玉珮落在方才謝玉嬌坐過的蒲團上。喜鵲正要喊謝玉嬌留步,見她已轉身出了禪房,便急忙拿了帕子,將那玉珮包裹起來,藏在身上跟了過去。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嗆辣美嬌娘(1)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65 |
古代羅曼史 |
$ 197 |
中文書 |
$ 197 |
文學作品 |
$ 213 |
小說/文學 |
$ 225 |
古代小說 |
$ 225 |
華文羅曼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嗆辣美嬌娘(1)
本書類型屬於穿越時空+靈魂重生+經營謀略+親情互動+婚姻經營。
說起穿越重生這件事,其實謝玉嬌沒什麼太大的反應,反正橫豎是回不去了,就這樣老老實實待著也不錯,就算家裡只有她一個女兒,非得招個嗣子進來或討個上門女婿繼承家業,依舊無法動搖她的心思。然而,天有不測風雲,看似平靜的江南魚米之鄉,逐漸受到北方戰亂的影響,就在謝玉嬌忙得焦頭爛額時,一個男人忽然闖進她的生活,甚至對她做出各種輕薄的舉動!原本謝玉嬌以為自己對他厭惡至極,卻沒想到在接到他戰死的消息時,一顆心會像瞬間被掏空一樣……
家裡沒個男人撐著又怎麼樣?
誰說孤兒寡母就好欺負!
看她使出看家本領,各個擊破……
對謝玉嬌來說,穿越到另一個時空其實並不可怕,
就算爹不幸離世,也有個跟她前世的媽長得一模一樣的娘,
加上謝家是江寧縣的頭號地主,即便她不是什麼枝頭上的鳳凰,
總歸是富霸一方的土豪千金,稱頭得很!
只可惜,現實生活總是有那麼一點小小的缺憾,
她這羸弱女兒身,終究注定不被人放在眼裡,
那些在一旁虎視眈眈的親戚不但三天兩頭找理由索討花用,
還要以「繼承謝家」為名義,企圖塞些不成材的傢伙來當嗣子,
更有唯我獨尊的老姨奶奶,想把她當娃兒放在手心上拿捏,
逼得謝玉嬌只能板著張俏臉挺身而出,
左打不識相的族親一拳,右賞不安分的姻親一掌,
若是這樣還不夠,那她乾脆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西,
招個上門女婿跟她生孩子,看誰還能再拿她這「母老虎」說事!
作者簡介:
芳菲,80後巨蟹座女子,生於江南水鄉蘇州,現居六朝古都南京,喜歡一切富有歷史韻味的人、事、物。也曾揮汗如雨開創一片事業,最終卻選擇在家相夫教子,閒暇時譜寫心中所愛,與君同樂。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擦肩而過
江南逢春,正是清明雨紛紛的時節。方才有些陰鬱的天空已經飄起了小雨,映著青山綠水,頗有些煙雨濛濛的感覺。
不遠處是一大片青瓦白牆的人家,在雨中瞧著尤讓人覺得冷清,門楣上的白幡還沒收起來,被雨水打得濕淋淋的,將「謝府」兩個字蓋去了一半。一個穿著素服的女子站在廊下的青石板臺階上,探著身子往外頭看了幾眼,腳下的繡花鞋沾到雨水,濕了半邊。
興許是雨中風大,她低頭咳了幾聲,身後的嬤嬤急忙上前,將一件外衣披在她的身上。
「夫人放心吧,這雨下不大,姑娘一會兒就回來了。」說話的是謝家女主人徐氏身...
江南逢春,正是清明雨紛紛的時節。方才有些陰鬱的天空已經飄起了小雨,映著青山綠水,頗有些煙雨濛濛的感覺。
不遠處是一大片青瓦白牆的人家,在雨中瞧著尤讓人覺得冷清,門楣上的白幡還沒收起來,被雨水打得濕淋淋的,將「謝府」兩個字蓋去了一半。一個穿著素服的女子站在廊下的青石板臺階上,探著身子往外頭看了幾眼,腳下的繡花鞋沾到雨水,濕了半邊。
興許是雨中風大,她低頭咳了幾聲,身後的嬤嬤急忙上前,將一件外衣披在她的身上。
「夫人放心吧,這雨下不大,姑娘一會兒就回來了。」說話的是謝家女主人徐氏身...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自序
第一章 擦肩而過
第二章 孤兒寡母
第三章 初次交手
第四章 精打細算
第五章 巧言求碑
第六章 洋人畫師
第七章 意外之喜
第八章 心懷不軌
第九章 拆穿詭計
第十章 苦命姑母
第十一章 遊刃有餘
第十二章 上門聲討
第十三章 出手教訓
第十四章 權衡輕重
第十五章 二度受創
第十六章 積攢房產
第十七章 如意算盤
第十八章 別有心思
第十九章 喜獲麟兒
第二十章 涇渭分明
第一章 擦肩而過
第二章 孤兒寡母
第三章 初次交手
第四章 精打細算
第五章 巧言求碑
第六章 洋人畫師
第七章 意外之喜
第八章 心懷不軌
第九章 拆穿詭計
第十章 苦命姑母
第十一章 遊刃有餘
第十二章 上門聲討
第十三章 出手教訓
第十四章 權衡輕重
第十五章 二度受創
第十六章 積攢房產
第十七章 如意算盤
第十八章 別有心思
第十九章 喜獲麟兒
第二十章 涇渭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