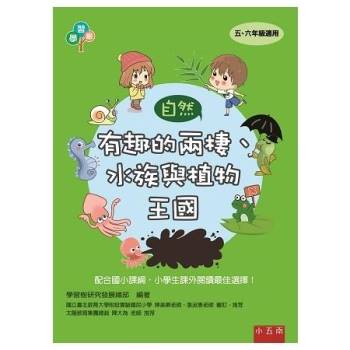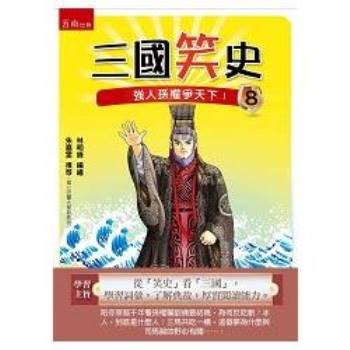第一章
李空竹一大早被人從炕上挖起來,還未待睜眼,就被人連拉帶拽的強行套了件大紅的粗棉交領窄袖衣裙。
待一方浸了清涼井水的濕帕抹上臉後,她終於意識到一點什麼,開始睜眼四顧起來。還不待張口,再一次被身旁那三十多歲,自稱她娘的婦人給推到一張破舊的梳妝檯前。
「柱子娘,妳來吧!」郝氏見自家女兒老實的坐下後,這懸著的心總算鬆了一點,轉頭對守在外面請來的全福夫人喊道。
「欸,好!」木板門被人從外推開來,一名跟郝氏差不多年歲的婦人走進來。兩人互相對視一眼,那婦人便移到李空竹身後,轉頭對郝氏笑道:「妳放心,這兒有我就成了。」
「噯,那我出去忙別的了。」郝氏抿了下一絲不苟的髮髻,臨走時還不放心的用眼角瞥了眼過於安靜的女兒。
兩人點過頭後,柱子娘便從袖口中拿出一截紅棉細繩出來。「開始了啊!」
「喔!」李空竹淡淡的點頭,閉了眼。
柱子娘看得愣了一下。只覺這丫頭今兒咋有些不一樣了?隨後一想,都到這步了,就是再鬧也改變不了啥的,還不如認命來得好。想著,她便癟了下嘴,咬住一頭紅繩,兩手撐著繩子,快速的在那張嬌豔的臉蛋上走了起來。
麻麻痛痛的感覺自臉上各處傳來,李空竹閉眼沈思。想著才來不到一天的工夫,都還來不及細細打量這房中擺設,居然就要嫁人了?雖說上輩子混到了二十七、八歲也沒人願娶她,可不代表她就該恨嫁不是?
幾不可聞的輕嘆了一聲。伴隨著臉上的痛感消失,她一睜眼,就見柱子娘將一盒白粉倒扣了大半在手上,對著她的小臉就是一通大抹。
農家婦人的手沒幾個是細皮嫩肉的,這婦人的手更是有好些皸裂開的口子,那大力的塗抹,讓李空竹疼得不由輕皺了下眉頭。
「咋地?還不甘心呢?」將半盒子的白粉扣到她的臉上,柱子娘看了眼那白得嚇人的小臉,滿意的點頭道:「要說妳如今的名聲,能有個娶妳的人,已是莫大的福氣了。這大戶人家裡的丫頭雖體面,可爬過主子床的,到底有些傷風敗俗不是?」
柱子娘一邊說著,一邊又拿了胭脂出來,同樣的倒了半盒在手,雙手交替的搓著,在她兩邊顴骨上大力揉搓了幾下後,這才拍了拍手,轉移陣地的又給她盤了頭,插了根細細的銀簪子固定住。「行了!」
「謝謝嬸兒。」李空竹看著銅境裡那跟鬼有得一拚的形象,沒來由的心頭一鬆。這模樣,只要不是個憨的,想來沒幾個人有心情下得去口。
「嗯?喔!」柱子娘愣了一下,隨即趕緊應了她的謝。見她衝自己笑得恬淡,就沒來由的為剛剛那番話感到心虛。認真的看她幾眼,見她正眉眼溫和的與自己對視,就尷尬的搓手道:「開臉完了,一會兒讓妳娘進來跟妳說些貼心話。」
「好。」
柱子娘得了她的回話,便轉身出去,不想正好碰到有人進來。見到來人,她心口一鬆,臉上堆笑道:「梅蘭來了,來跟妳大姊說說話,這一走,得回門那天才能看到呢。」
「呵!」李梅蘭輕呵了聲,柱子娘卻恍若未聞的趕緊行了出去,李空竹淡笑著點頭目送她走。一旁的李梅蘭見了,就不由得譏諷道:「怎麼?上吊一回,腦子也吊正常了?」
聽了她這話的李空竹轉眸看了她。見她不過十一、二歲,小模樣清清秀秀,雖比不得原身嬌豔白淨,可作為農家女子,已算得上花兒一朵了。
「正常了。」相較於她尖刻的嘲諷,她倒是淡然。
李梅蘭沒想到她會這般回答,愣了一下的同時,又忍不住輕哼一聲,說了句「但願不是狗改不了吃屎」後,就又轉身,行了出去。
李空竹淡漠的看著那淺綠衣袂消失在門角處,轉眸看向鏡子裡被厚粉遮蓋的嬌顏,不由苦笑連連。
原身的腦子,也不知咋想的,十年的賣身契約不好好遵守,偏要憑著幾分姿色去爬床,若不是活契的身分,怕是早被主家打死掩埋了。就這樣,仍不消停的要賣身做妾,搞得名聲盡臭不說,連帶還連累自己的弟弟妹妹。
如今好不容易有人家願娶了,卻作死的要去上吊。這一吊,倒真真是給作到頭了。
李空竹摸了下頸間的紅色勒痕,聽著院中已然熱鬧起來的人聲,不知是誰高喊了一聲:「趙家兒郎來接親了。」緊跟著嘈雜哄鬧和喜慶的鞭炮聲也隨之傳進來,聽得她雙手開始不自覺的緊握起來。
接著只見郝氏急匆匆地跑進來,喝道:「趕緊將蓋頭蓋了,來接人了呢!」說著,也不待她反應過來,一條厚實的棉紅蓋頭就罩在她的頭頂。「柱子,快來揹你堂姊出嫁。」
「欸!」一名正處變聲期的粗嗄男聲響起,隨著腳步走近,他半蹲在李空竹的身邊。「堂姊,俺揹妳出嫁。」
李空竹平復了一下發緊的嗓子,淡淡的輕「嗯」一聲後,上了他不寬的背脊。隨著身下之人移動的步子,她心頭沒來由的慌了一下。
耳邊的人聲越來越響。有人在那兒高聲叫笑道:「趙家三郎,抱得動你婆娘上車不?哈哈哈……」
「兒啊──」眾人嘲笑聲中,郝氏開始了號哭。
隨著李空竹被背上牛車坐穩,一道潑水聲響起,代表這個閨女從今兒開始正式成了別家之人了。
告別了喧鬧的李家村,車行到達趙家時,不說什麼嗩吶鞭炮之聲,就連喧鬧吃席的賓客也無。出來迎接的是男方同一屋簷下所住之人。
來人遞了一根紅色布條放入李空竹的手中,有婦人大著嗓門的道了聲:「老三,牽著你媳婦去堂屋拜拜爹娘。」
於是,李空竹便跟著那扯緊的布條慢慢的下了牛車,跟進了院子。來到他們口中所說的堂屋後,便有人在身邊扶了下她的手臂,下跪磕了三個響頭。
待起身時,一道沈著的男聲響起道:「先這麼著吧。這熱孝期間不能大辦,委屈你了老三!」
「大哥、二哥也是為小弟著想,算不得委屈。」清清冷冷的低沈之音不鹹不淡的逸出,瞬間令氣氛冷卻不少。
有婦人上前打著圓場,扶著頂著蓋頭的李空竹道:「這禮成了,還是送新娘子進屋歇著吧。」
李空竹淡漠的將手中的紅布捏緊,跟著那牽引紅繩之人,抬步行了出去。
一盞茶的工夫後,不知何時已停下腳步的男人,淡道一句「到了」後,就有似老舊的木門聲,「嘎嘎」的響了起來。
聲音過後,男人的腳步聲也跟著走動起來。李空竹傾耳聽了一下,沒有感受到手中紅布的緊扯感,就慢慢將紅布向手中收了收。發現布條另一端似耷拉在地,心中一鬆,繃緊的嘴角也跟著向上輕微的翹起來。
她摸索著門框,藉著腳下的方寸之地跨過門欄,進屋後,又摸索著想將門給關起來。不想,聽到響動的趙家三郎,轉眼看到她的動作後,眉頭便不經意的挑動了半分。左側臉上密布的傷痕隨著他眉毛的挑動,顯得愈加猙獰。
李空竹將門關上後,就自行將蓋頭揭下來。待適應了光亮,再睜眼時,卻被不遠處立著的紅衣挺拔男子吸引了目光。
只見他面目清冷,唇薄淡粉,鼻挺拔俊秀,眉飛揚入鬢,鳳眼深沈如墨。她想,若不是左臉那張如荊棘般錯綜的傷痕,毀了他那如玉的容顏,即便是個瘸子,光憑著那張白皙如雪的無雙俊顏,也能讓不少良家好女子點頭同意了這門親事。
趙君逸見她沒有半分怯意的盯著自己看了半晌,就有些不悅的蹙了蹙眉。隨即似又想到什麼般,嘲諷的勾起嘴角,眼中慍怒一閃而過。
李空竹本能的感受到他的不喜,卻不在意的走過去,將蓋頭直接扔過架子床頂,轉了頭,衝他淡淡一笑。「當家的可否幫著打盆水?」
既他無意,那麼她臉上這厚得能嚇死人的白粉,也沒有留的必要了。
趙君逸微不可察的再次蹙了眉峰,卻沒有多說什麼的轉了身;拖著那條斷了的右腿,一瘸一拐的開門走出去。
見他出去,李空竹隨即坐在那張陳舊的架子床上,剛一落坐,床就「嘎吱」的搖晃了一下,心下嘀咕了句「還真是破舊」,眼睛便在屋子裡掃了起來。
不足二十坪的地方,除了一角擺了個箱櫃,臨窗有張斷腿小黑桌外,就再無其他多餘的裝飾了。泥糊的牆上開了如手臂粗的裂縫,連著頭頂蓋棚的茅草,也有好些已是發黑陳腐。也不知這樣的房子,是如何經受住四季的雷雨冬雪的。
將打量完,人就回來了。趙君逸冷著臉將水放在斷了腿的小黑桌上。李空竹淡然的笑著,起身衝他有禮的要著毛巾。
趙君逸冷淡的掃了她一眼後,轉身就去箱櫃處,拿出一條嶄新的扔過來。
李空竹微不可察的聳聳肩,快速的將臉上的脂粉洗去。
待擦淨臉龐,趙君逸見她樣貌清麗白皙,臉如鵝蛋,眼如秋波,鼻子秀挺,唇紅如朱的,倒真真是有七分好顏色,也難怪會生了那等不該有的心思。
心下鄙夷間,外面如今的趙家當家人,趙金生喚了聲。「老三,一會兒過來,哥仨一起喝一頓。」
「知道了,大哥!」趙君逸淡道,轉眼見人已打理好,又端了水盆出了屋。
正找地兒掛巾子的李空竹見狀,不在意的挑了下眉頭,將毛巾撣在架子床的側床架上後,又找出陪嫁拿來的包袱。打開,見裡面只有兩件灰布的補丁麻布衣衫,就不由得蹙了眉。
那套原身從府裡穿出來的細棉衣裙,為何沒在包袱裡?記憶裡昨兒原身還套在身上才是,今兒出嫁換衣……
心下有些明白的李空竹,淡然的拿了一件補丁較少的出來。將身上那件土紅的衣服換下後,又將頭髮拆了,另梳了個用麻布包著的婦人頭,至於那根細細的銀簪,則小心的放在身上的粗布荷包裡。
趙君逸被喚去跟趙家兩兄弟吃飯喝酒,直到近申時才回。
彼時的李空竹,已經有些撐不住的坐在床頭,倚著床架子,閉眼打起了瞌睡。「嘎吱」一聲,隨著推門聲的響動,讓她眉頭輕皺的頭向下一歪,立時給驚醒過來。
抬眼看去,見進來的趙君逸手中正提著兩個裝有半麻袋東西的袋子。見到她時,只淡淡的將她掃了一眼,道:「在分碗,妳且去拿兩副回來。」
分碗?
並不理會她的不解,男人徑直將提著的兩個半袋麻袋,用力往桌上一擱,轉身又走了出去。李空竹見狀,趕緊起身整理了下衣衫,隨著他步了出去。
一出來,趙家的格局立時映入眼簾。整個房屋格局呈凹字形,三間上房並東西兩間廂房,雖是土磚所壘,但房頂卻是實打實的青瓦。
李空竹他們所住的地方,則是院子裡東西兩面用泥土另起的草棚。兩邊各三間,隨著她邁步到院中,還看到靠三間房後,離院門不遠的牆邊地方,另還有兩個棚子。
從這樣的布局看來,趙家倒算是戶不錯的農家了。
「喲,三弟妹也跟著出來了,正好,這碗筷俺都給你們分好,放盆子裡裝著了,妳趕緊端過去吧。」
李空竹回神,見廚房裡出來的女人肥胖黝黑,一雙小眼瞇成縫,正對自己咧著大嘴笑。目光順著她手中的盆子看去,兩雙筷子,兩個粗瓷中碗,並一個大碗放在裡面。
見她看著不動,女人扯著嗓子又道:「趕緊幫著收拾,一會兒妳男人還得壘灶呢。不然光憑老三一個人動彈,得忙活到啥時候去?愣著做啥,趕緊接手啊。」
壘灶?李空竹恍然,趕緊伸手在對方不善的目光中接了過來。
另一邊,正提著鎬頭和筐子從倉房走出來的玉盤臉,看著挺討喜的婦人見狀,不由得笑著解圍道:「大嫂,老三家的才頭天兒進門,還不知道咱們分家呢。」
「哼!」被叫大嫂的鄭氏從鼻孔中不屑的輕哼了聲,轉身就又回到廚房去分劃東西了。
「她就是那麼個強脾氣!妳別太在意。」已走過來的圓臉婦人張氏,笑得溫和的給她勸解。
「哪裡的話,是我糊塗,不明白這家中的規矩哩。」
張氏挑眉,見她已經福身端著盆子徑直回了屋,只好作罷的將提著的筐子和鋤頭,拿到東面的一間房裡放好。
一下午的時間,李空竹除了拿回那兩副碗筷,便再無多餘的東西。坐在屋子裡,聽著外面一陣陣的嘈雜聲。她頭倚床架,努力回想著腦中原身所知道的一些資訊。
這趙君逸聽說是趙家老爺子八年前進深山打獵時撿回來的,當時看他傷得嚴重又可憐,老倆口就心善的將他當作第三子養在了趙家。
本來在頭年秋,老倆口已經著人商議這趙君逸的婚事了。奈何,這趙家三郎除了跛腳毀容外,還不是趙家老倆口的親生兒子。大多數的農家人,都不太願意將自己好好的閨女,嫁給一個不能分家產的外來人。
是以,這親事,也從頭年秋一直耽擱到了今年秋。
本來媒婆拿了趙家老倆口的媒人錢,還盡心的找著。可不想就在一個月前,秋糧下來之際,趙家老倆口上山找木料做衣櫃時,卻被自己砍下的大樹,給壓死了,這老倆口一死,趙家三郎的親事就更不好找了。
為著讓老倆口瞑目,趙家的趙金生、趙銀生兄弟倆,便放出話說,只要有閨女肯嫁過來,哪怕聘禮高一點也成。原身的娘就是在聽說這樣的條件後,就立馬答應了這門親事。
如今看來,這趙家兩兄弟怕不是為著讓爹娘瞑目,而是急於把趙君逸給劃出去才是。不然的話,就算再急切,也不可能找她這麼個無人敢娶,名聲盡毀的爬床丫鬟了。
正想著,門就被「砰」地撞開來。
進來的趙君逸雙手沾泥的抬在空中,紅衫的前襬別在腰間,露出裡面的黑麻褲。
看到還在發呆的李空竹時,他面無表情的道:「灶還未壘好,妳等等借了大房、二房的廚房多做點飯,兩家哥嫂晚上吃飯算在我們這一房。」
大房、二房他們廚房沒有分開?
雖然疑惑,李空竹仍點了頭,起身到小黑桌前,將兩個半袋子打開來。見裡面是高粱米和玉米麵粉,就抬眼看向男人問:「可有分菜園?」
趙君逸微不可察的搖了下頭。「妳看著煮吧,咱家是啥情況,想來他們也知道,儘量煮多點。一會兒端出來,別讓人說了小氣。」
李空竹心中腹誹,面上卻很恭敬的點頭道:「知道了。」
男人眼角掃向她平靜如常的臉,見看不出任何異樣,隨即也懶得再理的步了出去。
李空竹用小碗挖出兩碗高粱米,又用小木盆裝了半盆玉米麵。端著出屋時,正好看見自家屋角那忙活的三個大男人的身影。
聽見響動的三人,有兩人轉頭,回看了過來。
李空竹有禮的衝兩人喚道:「大哥,二哥!」
兩人見狀,皆頷首的回了個嗯字。轉回頭時,趙銀生愣是用眼角多瞄了幾眼那窈窕的身影。「還真別說,大戶人家裡頭待著的,就是不一樣。你說是不老三?」
趙君逸沒有吭聲,只平淡的將和好的黏泥給遞過去。
趙金生黑厚憨實的臉上有些不悅,看了自家二弟一眼。「都過去的事了,以後都是一家人,可別再說了這話。」
趙銀生不屑的癟癟嘴,油滑的臉上滿是堆笑。「我這不是想誇兩句嘛,大哥你做甚這麼警醒,再說老三都沒說啥呢。是不是啊老三?」
趙君逸並不答腔,見他抽了手想混空兒,就自己上手的擠了他的位置,道:「二哥若覺著累,就在一邊歇息吧,這點兒,我來弄就成了。」
「那敢情好,我正腰疼呢,反正也只剩這些了。你跟大哥弄吧,我回屋去炕上直直腰。」說罷,就當真轉身向院子走去,衝著廚房喚了聲。「媳婦兒,給我打盆水來。」
剛進到廚房的李空竹,正跟鄭氏和張氏寒暄著。
聽到喚的張氏,笑著嗔了句。「怕是腰病犯了,想著趁空偷懶呢。」說著,便順手拿了門口架上的木盆,去到放水缸的地方打了瓢清水,招呼了聲鄭氏和李空竹,就走了出去。
再回來時,便問李空竹:「三弟妹準備做啥樣的晚飯?」
李空竹倒是沒做啥像樣的晚飯,只做了個高粱米水飯,並著烙了一盆的玉米麵餅,由於沒油沒鹽,又沒菜的。就捨了臉皮跟張氏求了點,弄了個炒白蘿蔔絲,就當作是三家人的晚飯了。
吃飯的時候,兩家的兒女也跟著出來聚在一起。三家人,十二張嘴,不到兩刻鐘的時間,就將那盆高粱米水飯和一小盆的玉米餅給吃了個乾乾淨淨。
末了,鄭氏看桌上菜盤子裡剩下的一點沾盤的菜汁,還很可惜的咕噥了句。「真是敗家,都不知道少炒點,這油水一洗,都得扔畜牲肚裡去。」
李空竹有些無語,只當聽不見的起身,快手快腳的拾掇起來。張氏抱著有些犯睏的三歲小女兒,只笑了笑的起身,向著西廂走去了。
趙金生瞪了眼不識趣的自家婆娘,隨即又跟趙君逸低聲的商議幾句什麼。待兩人談完,就各自回了各房,閉門歇起了覺。
李空竹將碗筷洗好,收拾完,出廚房時,天已經徹底黑了下來。農家人嫌點燈費油,大多數會趁著天將黑就開始閉門睡覺。
這會兒站在院子裡,四周一片漆黑,寂靜的夜空連一個星點也無,深秋的涼風一吹,凍得人直打哆嗦。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巧婦當家(1)的圖書 |
 |
巧婦當家 1 出版社:狗屋 出版日期:2017-05-19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20頁 / 25k正 / 14.8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65 |
華文羅曼史 |
$ 188 |
古代小說 |
$ 197 |
中文書 |
$ 197 |
文學作品 |
$ 213 |
小說/文學 |
$ 225 |
古代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巧婦當家(1)
半掩真心,巧言挑情/半巧
結了婚,卻是郎無心,妾無意。
可聲名有損的她,能上哪兒去?
李空竹才睜開眼,一條紅棉布就蓋上了頭,
做了二十多年的黃花閨女,這會兒竟這般隨意就嫁做人婦了?!
她可沒如此恨嫁呀!
但弄明白這身子的壞名聲,她也只能認栽,
好歹她仍活著,就是往後會碰上麻煩,也定能化解。
瞅著空蕩蕩的家以及冷冰冰的新婚夫君,
要想過上好日子,恐怕得費上一番努力,
幸而她有著好手藝,白手起家不成問題,
問題是她的夫婿趙君逸,不僅身懷武功,似乎還有著隱情。
不過婚都結了,甭管他有什麼秘密,要過好生活也得出些力。
瞧他臭著臉乖乖做力氣活,她很是滿意,
未料這般與他搭伙過日,她居然感到有滋有味起來,
可這男人對她總是忽冷忽熱,到底是怎麼回事兒?
作者簡介:
半巧,生於西南,長於西南,現定居東北,自由寫稿人。
以前最大的願望是成為世界名人,照過鏡子後,改為少做多掙;再照一次後,覺得能把想寫的故事寫好才是實事。如今,只希望文筆越來越好,能帶動更多書迷,一同品嘗書中的喜怒哀樂!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李空竹一大早被人從炕上挖起來,還未待睜眼,就被人連拉帶拽的強行套了件大紅的粗棉交領窄袖衣裙。
待一方浸了清涼井水的濕帕抹上臉後,她終於意識到一點什麼,開始睜眼四顧起來。還不待張口,再一次被身旁那三十多歲,自稱她娘的婦人給推到一張破舊的梳妝檯前。
「柱子娘,妳來吧!」郝氏見自家女兒老實的坐下後,這懸著的心總算鬆了一點,轉頭對守在外面請來的全福夫人喊道。
「欸,好!」木板門被人從外推開來,一名跟郝氏差不多年歲的婦人走進來。兩人互相對視一眼,那婦人便移到李空竹身後,轉頭對郝氏笑道:「妳放心,這...
李空竹一大早被人從炕上挖起來,還未待睜眼,就被人連拉帶拽的強行套了件大紅的粗棉交領窄袖衣裙。
待一方浸了清涼井水的濕帕抹上臉後,她終於意識到一點什麼,開始睜眼四顧起來。還不待張口,再一次被身旁那三十多歲,自稱她娘的婦人給推到一張破舊的梳妝檯前。
「柱子娘,妳來吧!」郝氏見自家女兒老實的坐下後,這懸著的心總算鬆了一點,轉頭對守在外面請來的全福夫人喊道。
「欸,好!」木板門被人從外推開來,一名跟郝氏差不多年歲的婦人走進來。兩人互相對視一眼,那婦人便移到李空竹身後,轉頭對郝氏笑道:「妳放心,這...
»看全部
TOP
目錄
序文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半巧
- 出版社: 狗屋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5-19 ISBN/ISSN:9789863287278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320頁 開數:正25開【14.8*21公分】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